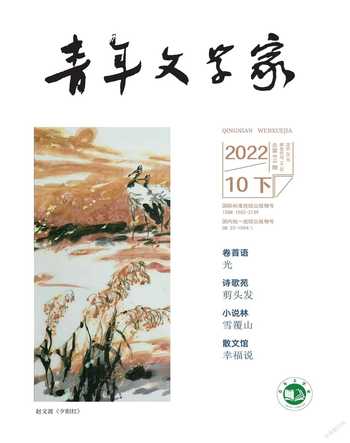重估劉熙載文藝美學思想之當代價值
肖蓉欣

一、劉熙載文藝美學思想形成原因
(一)時代背景
劉熙載生于晚清末期,一生經歷五朝帝王。晚清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可能是劉熙載一生大部分時光都投入到教育事業的原因。劉熙載經世致用的思想,不僅是受儒家影響,同樣也離不開晚清時期特殊的社會背景。他的這一思想也正好迎合了當時以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等人為代表的救亡圖存的社會潮流。在劉熙載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他一直在上海龍門書院擔任主講,培養了一大批為中國現代化效力的經世致用之才。劉熙載的眾多學生,如祁兆熙、張煥綸、胡傳、袁昶、范當世、葛士濬、姚文棟、李平書等近代知識分子,他們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包含晚清的邊防、教育、外交等多類事務。故要論劉熙載的個人成就,他遠不止作為文藝美學思想家而已。
(二)思想淵源
對劉熙載思想形成造成影響的可以分為內外兩個方面:
首先,是內部的傳統文化思想。在傳統文化思想方面,儒、釋、道思想在劉熙載身上均有體現,但就筆者看來,劉熙載的根本立場還是代表了正統美學,是對唐以來“文以載道”的觀念的強化。不過,劉熙載在晚年說過:“余之少也,學不知道,雖從事于六經,然頗好周秦間諸子,又泛濫仙釋書。”又說:“憶余自始學以來,知圣賢之道不易明,欲從他道參驗之,至如陰陽道釋之言,茍有明之者,竭誠以問,不憚再三焉。”從他的自述來看,他說自己雖然事于六經,但是也愛好眾多,周秦諸子,陰陽道釋均為他所重。可以看出,劉熙載的思想是以儒家為主,但也兼通釋、道。《藝概》站在內外學術思潮激烈碰撞的時期,可以代表古典正統美學對文學進行的一次回望和總結。劉熙載對六經最為推崇,重視作者人品,重視作品的教化功能。但同時劉熙載又吸收了道、釋兩家的思想精華與思維方式,多種思想的碰撞使他有豐厚的思想基礎,他的《藝概》能流傳后世飽受稱贊,脫離了儒、釋、道哪一家恐怕都會減色不少。
其次,是外部的時代文化思潮。在時代文化思潮方面,“民國”《續修興化縣志·人物志》中曾記載:“熙載治經,無漢、宋門戶之見,其論格物,兼取鄭義。”漢學盛行于東漢期間的古文經學,治學方式講究“實事求是”,崇尚原始儒學、漢儒,同時又重訓詁、考據;而宋學,指的是宋明理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清人的宋學主要是指程朱理學,治學方式講究使經學理學化、以理貫經。清代時,漢學盛行,清代儒士們推崇漢儒,對宋儒那種空洞注經的毛病不屑一顧,于是呼之為“宋學”,以此與“漢學”相區別。但到了晚清時期,因為此時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這一時期哪怕是再封建的知識分子,不管原來他們是宗漢儒還是宗宋儒,在這種急需救亡圖存的時代形勢下,都開始盡力汲取對方之長,以達到經世致用的效果。融會貫通思想和經世致用思想是這個時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所以綜合言之,晚清時期的儒學主流是一個漢宋調和的過程,是故云,“道咸以來,儒者多知義理、考據二者不可偏廢,于是兼綜漢宋學者不乏其人”(徐世昌《清儒學案》)。這種兼取眾家、融會貫通、經世致用的思想同樣對劉熙載的影響巨大。
二、是粹然儒者,也是實踐者
劉熙載說:“為學不專在讀書倫常之地,日用行習之間,事事準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實學問。”又說:“禮樂、兵刑、天文、地理、農田、水利,皆有專書,皆為有用之學。能專習一種,自有一長,泛泛涉獵,無當于學也。”
從這可以看出,在思想上劉熙載是重視各種專門的實用性的學問的,并不像傳統意義上保守的儒生那般看不起實用技藝。劉熙載注重實用主義,不唯書,敢于突破程朱理學的藩籬,用辯證的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在實踐中發揮最大的作用,這是劉熙載在思想上傳授給弟子們的寶貴財富。重視對學生專門技藝的培養,因材施教,真正開發出學生的興趣,使他們在某一領域刻苦鉆研,學有所成,這是劉熙載思想上經世致用,力圖從人才教育上挽救國家之危機的重要體現。
此外,在行動上劉熙載也是以身作則。他熟悉六經典籍沒錯,但他對算術、地理知識、音樂、文字學、天文學等非傳統儒家的學科也有研究。劉熙載能根據不同學生的不同興趣予以指導,離不開他本人廣泛的知識經驗。胡傳的兒子胡適曾經提到,說他父親在上海龍門書院當學生時,養成了對中國地理的興趣,尤其是對邊疆地理的興趣。正因為劉熙載本人也對地理有所了解,所以他在知道弟子胡傳對地理有興趣時才能及時給他具體的指導。胡傳后來在地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劉熙載的細心栽培。
有的學者說:“劉熙載生在一個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文化學術急劇變革的時代,卻采取了一種不介入、不趨時、不偏倚的態度。”筆者并不認同這一說法。根據楊抱樸先生著的年譜記載,劉熙載在上海龍門書院擔任主講十四年,實乃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龍門書院在劉熙載的嚴格要求下,培養出了一大批講究實干的杰出人才。在劉熙載的弟子中,袁希濤、沈恩孚、張煥綸等學生在中國近代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李平書、姚文棟、胡傳對邊疆輿地之學的研究作出了不少貢獻,使得中國近代的邊防外交、城市建設工作取得很大進步;另外還有文學家范當世、數學家劉彝程等人,均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其實,劉熙載順應救亡圖存、經世致用的時代潮流辦學,為龍門書院培養出了一大批為中國近代實業發展效力的知識分子,為中國早期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就是劉熙載選擇的一種介入社會、改變社會的方式。劉熙載注重實學、強調躬行實踐、經世致用的思想在上海這個特殊的背景下,在龍門書院這所特殊的學院內,存在著嚴密的契合。
通過對劉熙載任教龍門書院期間,于教書育人方面所作出的貢獻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他絕不僅僅是一位曾經被皇帝夸獎過的“粹然儒者”,也不僅僅是一位知識豐富、對各門類知識不存門戶之見的教育家,他更是一位通變務實、思想先進、關心國家發展的偉大實踐家,只不過他介入社會、改變社會都是通過教書育人這一途徑達成的。
三、劉熙載文藝理論之創新:“鏡喻”“燈喻”與“日喻”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序言中說:“本書的書名把兩個常見而相對的用來形容心靈的隱喻放到了一起:一個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則把心靈比作發光體,認為心靈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18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征,后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關于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
自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的“模仿說”就對西方文藝理論界產生著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古羅馬的普羅提諾在前人基礎上進行了補充,認為藝術不僅可以模仿感性世界,還可以模仿理念世界。至此,西方的“模仿說”沿著兩條路發展:一條是將文藝創作視作對外界環境真實反映的現實主義表達,一條是“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序言》)的浪漫主義表達。艾布拉姆斯分別用“鏡”與“燈”對此作出了形象的概括。
劉熙載文論思想的創新之處在于,他沒有拘泥于傳統的“鏡”與“燈”的比喻中,而是進一步提出了“日喻說”:“鏡能照外而不能照內,能照有形而不能照無形,能照目前、現在,而不能照萬里之外、億載之后。乃知以鏡喻圣人之用心,殊未之盡。”又說:“人之本心喻以鏡,不如喻以日,日能長養萬物,鏡但能照而已。”
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文,心學也。”他十分重視作者情感對作品起到的根本性作用,認為作者的情感和意志會對文學藝術作品起到根本性影響。不過,劉熙載認為,以“鏡”喻人心不如以“日”喻人心,因為“鏡”只是外在地、平面地、客觀地反映事物,而“日”則是內在地、立體地、能動地表現事物。“鏡喻說”主要突出了是文藝的社會功用,而“燈喻說”“日喻說”則是強調文藝的審美價值。劉熙載覺得,以“燈”喻文藝作品之效用不如以“日”喻之,因為燈照一時,日照古今;燈照一隅,日照千里。燈只是照亮,日卻能滋養萬物;燈需要依靠外在能源,而且會有熄滅的時候,日卻與宇宙同生,恒久發光。“日”的特殊之處在于它與被照之物一同為宇宙的組成部分。劉熙載的高明之處可見一斑。
四、是繼承者,也是發揚者
有人評價劉熙載:“他這種人生與治學態度,決定了他在理論上恪守儒家傳統教條,不可能有站在時代前列的、激動人心的創新獨白。”筆者不認同這樣的說法,相反覺得劉熙載在文藝美學理論上的建樹被學術界大大低估了。劉熙載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了對中國古典文藝美學的一次總結沒錯,但絕不意味著他沒有自己的創新之處。全盤西化的未必就是好的,古典美學里也未必就找不出創新意識。之所以現在很多人有這樣的偏見,是由于當代文學界缺乏對古典文藝理論的重視,未能深挖我國古典文論中精彩之處而導致的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因而我們立足于當下,對劉熙載文藝美學思想進行當代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從劉熙載的《藝概》中,可以見他的文藝美學思想有以下特點:
一是劉熙載對古典文藝美學的總結,實則暗含了他的現代意識。首先,劉熙載說道:“文,心學也。”他認為文藝創作歸根結底是靠創作者的心聲,外在的其他條件只是次要因素。劉熙載對文藝是“心學”的強調,體現了在那個時代他對作者個性的肯定、對文藝作品表達自我的肯定。劉熙載充分鼓勵作家表現在言論著作中的個人意識,正所謂“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個自家在內。后世為文者,于彼于此,左顧右盼,以求當眾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其次,這種現代意識也表現為他對古典文藝美學的總結。劉熙載剖析各類文藝現象,以藝術辯證法論之。例如,劉熙載在自己的著述中就運用了陰與陽、丑與美、正與變、工與不工、是與異等兩兩相對的范疇。這些范疇,包含了文藝的形式、內容、風格等各個方面,不管是在內涵還是在外延上,它們既各自可以獨立論證,又相互交叉關聯,形成了一個既有邏輯規律,又有充滿變化的紛繁復雜的網絡。雖然這些相對的范疇有不少在前人的文論中已有論述,但劉熙載作為集大成者,其自覺性、全面性、系統性和深刻性方面,實在超過前人不少。
二是劉熙載的文藝美學思想是帶著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劉熙載論述中國古典文藝美學,從思維方式到話語系統,都具有中國古代文論之獨有特色:不是抽象論證,而是結合具體實例進行具體分析;表達形式上也是中國古代文論所特有的那種語錄體,多比喻,形象生動。比如,劉熙載對杜甫詩歌的評價是“高、大、深”,對蘇軾詩歌的評價則是“打通后壁說話”。我國學者朱良志指出:“《藝概》是一部具有典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美學著作,這個‘概可以說是中國美學精神之‘概,不僅在形式上反映了中國美學的特點,在精神氣質上也體現了中國美學的內脈。”
就實際情況來看,劉熙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國的文學理論、美學理論一直處在“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的狀態,更像是“西方文藝美學在中國”而非真正的“中國文藝美學”。這一個多世紀以來,由于我們對自身文化缺乏自信,西方的各種文化觀點、文化思潮都在中國留下足跡,這使得中國學界充斥了廣泛但混雜的聲音。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研究卻被很大程度地忽視了。我們站在今天重新審視劉熙載的文藝美學思想之精彩處、創新處,重溫他關于“藝者道之形”的文學作品論,“文之道,時為大”的作品與時代關系的文藝發展論,“論詞莫先于品”的作者與讀者關系的接受論等文藝美學觀點,對我們接續中國文藝美學傳統,弘揚中國文藝美學精神,建構既兼具中國傳統特點,又具有現代意義的文藝理論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