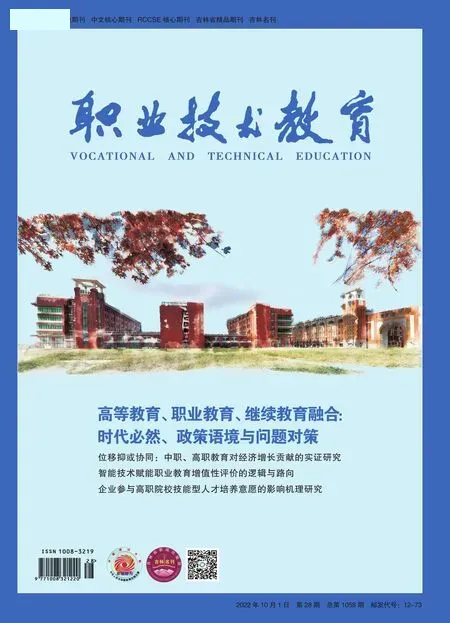英國學徒稅制度:背景、挑戰與發展趨勢
王玉苗 謝勇旗 祝聳立
制度是歷史景觀中相對持久的特征,是推動歷史沿著一系列路徑發展的核心因素之一[1]。英國有著悠久的學徒制歷史,以羅斯托的階段理論為依據,其發展大致經歷了手工業行會學徒制、早期國家立法學徒制和集體商議工業學徒制三個發展階段。1993年,英國政府推出以政府為主導的現代學徒制,倡導“使現代學徒制成為16歲以上青年群體的主要學習選擇”,2012年,《理查德學徒制評論》(The Richard Review of Apprenticeships)的發布代表著英國現代學徒制新一輪改革的開始,學徒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雇主、政府和培訓提供者之間的關系,雇主主導成為現代學徒制改革的價值選擇。經費保障體系是決定學徒制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針對政府主導產生的學徒制經費不足,學徒培養偏離雇主需求出現的“質量求低”等問題,英國于2017年4月啟動了學徒稅(apprenticeship levy)制度。學徒稅制度作為學徒制經費改革中的關鍵性制度,同時也是英國政府構建“雇主主導型”學徒制培養模式的一項重要舉措。2014年8月,我國教育部頒布了《關于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的意見》,隨后教育部先后分三批遴選了562家現代學徒制試點單位,2022年通過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規定“國家推行中國特色學徒制”(第三十條),可見,現代學徒制已經成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現代學徒制正處于不斷發展完善階段,尚未建立起符合國情的學徒制經費政策體系,這使得“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撐”成為“現代學徒制基礎條件尚需完善”的任務之一。本文旨在通過分析英國學徒稅制度的背景、內容、挑戰和發展趨勢等,為我國學徒制經費政策體系的構建提供借鑒與啟示。
一、英國學徒稅制度的背景
(一)雇主對學徒制培訓的參與和投資不足
提高生產力是英國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英國的生產力水平較低,比七國集團(G7)其他成員國低20%左右[2],英國工人的每小時工作產量分別比美國、德國和法國低23%、21%和22%[3]。英國學徒制作為提高國家技能水平的一種機制,為學徒和雇主提供了強勁的回報。就職業生涯的整體收入來看,二級學徒的平均增收為4.8~7.4萬英鎊,三級學徒在7.7~11.7萬英鎊之間,而四級及以上學徒平均可以多掙15萬英鎊……政府在二級和三級學徒制培訓上每投入1英鎊,就會獲得26~28英鎊的回報,這一比例遠高于繼續教育資格證書1∶20的投入回報率[4]。但是,英國僅有15%的雇主參與學徒制培訓,遠低于澳大利亞(30%)和德國(25%)。英國雇主對培訓的投資不足,1998年,36%的培訓時長不到1周,至2018年這一比例達到了54%[5];參加脫產培訓的雇員數量從1995年的15萬個跌至2014年的2萬個,跌幅高達87%[6]。雖然雇主對于培訓的投資總額從2011年的438億英鎊增至2017年的442億英鎊,增幅為0.9%,但是,勞動力規模的迅速增長意味著每個雇員的平均培訓成本減少了6.3%。2005~2015年間,英國雇員平均培訓成本的降幅為23%,這與歐盟22%的增長率形成鮮明對比[7]。學徒制經費缺乏的問題尤為明顯,相對于本科生每年9000英鎊的平均經費,新增學徒的平均經費為每年2500英鎊,所有學徒的平均經費則只有每年1000多英鎊[8]。
(二)學徒制經費政策的持續推進
路徑依賴是歷史制度主義中一種重要的分析范式,一旦制度在政治沖突之中被設計出來,隨即就會進入一個正常的路徑依賴時期[9]。20世紀80年代至2010年間,英國學徒制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提供的公共資金,政府將經費直接撥至培訓機構和考評機構,經費來源單一、經費總量過少,并且間接導致雇主參與學徒制的積極性不足。政府主導的學徒制經費投入方式與學徒制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諸多矛盾,英國政府努力尋求一種新的方式,學徒稅制度的出臺有著明顯的路徑依賴特點,是英國政府在學徒制培養模式從“政府主導型”到“雇主主導型”轉變過程中的一項重要舉措。
2011年11月,英國就業和技能委員會(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UKCES)發布了《雇主擁有技能:確保長期的可持續合作伙伴關系》,提出“建立雇主主導的技能體系”,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利途徑是改變經費在學徒制體系中的流動方式,將投資的責任和獎勵直接交給雇主”[10]。2012年11月,道格·理查德(Doug Richard)在《學徒制評論》中認為“培訓的購買力必須牢牢掌握在雇主手中”[11],但學徒制經費體系“過去由培訓機構驅動,因而不能充分反映雇主的需求”[12],他相信“經費是政府推動學徒制改革的主要杠桿,建立一個促進高質量、積極鼓勵擴大學徒制機會、促進有效利用政府和私人投資的經費體系,是本報告所有其他建議的重要基礎”[13]。英國政府分別于2013年7月和2014年3月發布了兩個咨詢報告,設計了四種不同的資助模式,引發了數百個利益攸關方的回應,但這四種模式要么被拒絕,要么被撤銷。這些錯誤嘗試的結果導致在《理查德學徒制評論》發布兩年之后,學徒制經費改革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2015年,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關系專家艾莉森·沃爾夫(Alison Wolf)指出,所有人都贊同“學徒制是個好主意”,但學徒制改革需要更多的資金,資金從哪里來?在目前的英國環境下,實現這些目標的最直接和可靠的方法是“通過對工資實施小額稅收的方式建立國家學徒制基金(national apprenticeship fund)”[14],沃爾夫認為“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機制,那些歌頌學徒制的政客將發現自己是在白費口舌”[15]。同年7月8日,新當選的保守黨政府在《夏季預算》中宣布要實施學徒稅,以資助旗艦政策“新增300萬學徒”目標的實現,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認為,學徒稅是一個激進但必要的步驟。
2015年8月,英國政府發布了《學徒稅:雇主主導的學徒制培訓》咨詢報告,以此為基礎,2015年的《秋季聲明》描述了學徒稅從2017年4月起將如何運作,同年12月,英國政府公布的《英國學徒制:2020年愿景》對學徒制經費改革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指出“學徒資助將通過向雇主征收學徒稅的方式建立可持續的資金支撐”[16]。2016年2月,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M Revenue and Customs,HMRC)發布《學徒稅制度》報告,指明了其背景、起始時間和做法等。2016年8月12日,英國政府發布了學徒制經費草案,共收到892份反饋[17],同年10月25日,《英格蘭學徒制資助:始于2017年5月》發布,確定了最終的學徒制經費政策,提出“資助政策以學徒稅制度為基礎,以支持英格蘭學徒制經費支付方式的改變”[18]。截至2022年6月,《英格蘭學徒制資助》共有8版,其最新版于2021年11月1日發布。
二、英國學徒稅制度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
學徒稅作為一項制度,英國政府對其征、用、補等有著嚴格的規定,自2017年4月實施以來,學徒稅對學徒制培訓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學徒稅制度的主要內容
1.學徒稅的征收
學徒稅的納稅對象為英國所有符合要求的雇主,稅額為其年度工資總額的0.5%。政府為雇主提供每年1.5萬英鎊的稅收津貼以抵消征稅,這意味著只有年度工資總額超過300萬英鎊的雇主才用繳稅,而這樣的雇主占比僅為2%[19]。無論是否開展學徒制,雇主均需通過所得稅預付系統(Pay As You Earn,PAYE)向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MRC)按月支付稅款。雇主需要在“學徒制數字服務中心”(Digit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DAS)注冊電子賬戶,經費每月按照規定時間打入雇主賬戶,同時政府為雇主提供10%的配套津貼,即每劃入其電子賬戶1英鎊,雇主實際獲得的經費為1.1英鎊。雇主也通過該系統向培訓和評估機構支付培訓和評估費用。2018/19學年的學徒稅總額達到了近24億英鎊,用于學徒制培訓的總支出為7.16億英鎊;納稅雇主的學徒稅平均貢獻約為13.7萬英鎊,學徒制培訓的平均支出約為4.2萬英鎊[20]。
2.學徒稅的使用
學徒稅有著嚴格的使用期限,其有效期為2年,系統按照先入先出的原則優先使用最早進入賬戶的資金,以使資金到期的可能性最小化。納稅雇主可以將其未使用的學徒稅經費,每年以最多25%的比例轉移給其他雇主,接受轉移資金的雇主可以使用該筆資金支付培訓和評估費用。學徒稅的使用有兩種方式,分別為學徒制框架(apprenticeship framework)和學徒制標準(apprenticeship standard),學徒制框架正在逐漸被新的學徒制標準所取代。每個學徒制標準或框架對應某一經費等級(funding band),共有30個經費等級,每個等級不設下限,但是各設定一個上限,從1級的1500英鎊一直到30級的27000英鎊。
英國政府規定,學徒稅只能用于學徒制的培訓和評估,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如學徒的工資等。所有超出經費等級上限的培訓和評估費用,均由納稅雇主和非納稅雇主自行承擔。若培訓和評估費用在經費等級區間范圍之內,納稅雇主賬戶內有足夠資金的情況下,則使用此款項支付相關費用,如納稅雇主帳戶內的資金不足以支付相關費用,則雇主支付剩余費用的5%,而政府支付95%;對于非納稅雇主,政府和雇主通過聯合投資(co-invest)的方式共同承擔學徒制的培訓和評估費用,非納稅雇主支付該費用的5%,其余95%由政府支付。
3.學徒稅的配套補貼
針對學徒的類型,英國政府有相應的配套補貼。一是刺激性獎勵補貼,每雇傭一個新學徒,雇主將獲得3000英鎊的補貼,該款項直接支付給雇主,在第90天和第365天時分兩次等額支付。二是扶弱性補貼,每雇傭或培訓一個16~18歲的年輕學徒、或曾受“健康和社會關愛信托基金”(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資助過的19~24歲學徒、或屬于當地政府“教育、健康和關愛計劃”(Education,Health and Care plan)中的19~24歲學徒,雇主和培訓機構將獲得1000英鎊的補貼,該款項通過培訓機構支付給雇主,在第90天和第365天分兩次等額支付。三是助學金,曾受“健康和社會關愛信托基金”(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資助過的16~24歲學徒,可能面臨額外的經濟障礙,政府將為其提供1000英鎊的助學金,該款項通過培訓機構一次性支付給滿足條件的學徒。
4.學徒制培訓機構的注冊
學徒制和技術教育研究所(IfATE)向教育部提供每個學徒制標準或框架的適當資助范圍的建議,并定期審查現有標準或框架的資助范圍。學徒制培訓機構需要在學徒制培訓機構登記局(Register of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Providers,RoATP)登記注冊,然后雇主根據學徒的層次和類型,從登記冊中選擇符合其培訓目標的培訓機構,每個學徒制項目的具體資助標準由雇主與培訓機構對照經費等級協商確定。培訓機構有三種類型:主要機構(Main provider),納稅雇主可從中選擇適合的培訓機構;雇主機構(Employer provider),納稅雇主經批準可為其雇員或相關雇主的學徒提供培訓;支持性機構(Supporting provider),以分包商的形式每年承擔培訓金額為10~50萬英鎊的學徒制培訓[21]。2019/20學年,學徒制數字服務中心(DAS)賬戶中的納稅雇主總數為16642個,多于2016/17學年的14878個;2017/18至2019/20學年,工資單等級(1000萬~5000萬英鎊)雇主的占比從27%增至30%,而最低工資單等級(300萬~500萬英鎊)的雇主占比從32%降至28%,其他工資單等級雇主所占比例則相對穩定,雇主(500萬~1000萬英鎊)約占31%,雇主(超過5000萬英鎊)占比略高于10%[22]。
(二)對學徒制培訓的影響
學徒稅制度實施以來,學徒制培訓在新學徒數量、學習層級和年齡等方面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新學徒數量顯著下降。學徒稅實施的第一季度(即2017年5月到7月),新學徒僅有48000個,比去年同期減少59%(75000)[23]。新學徒數量從2015/16學年的峰值(509400)降至2017/18學年的375800,降幅為26%,2018/19學年的數量雖然略有回升(399000),但仍比學徒稅實施前低了1/5[24]。
第二,由低層級向高層級轉移的趨勢。2015/16、2016/17和2017/18三個學年的數據顯示,新學徒中中級學徒(二級)數量的降幅最大,從2015/16學年的291300個降至2017/18學年的161390個,降幅為45%;高級學徒(三級)的數量從190870個降至166220個,減少24650個,降幅為13%。與之相反,高等學徒(四級及以上)的數量從27160個增至48150個,增加20990個,增幅為77%[25]。
第三,成人學徒占比增加。2018/19學年,只有25%的新學徒在19歲以下,25歲及以上的有30%,其中納稅雇主的學徒中,56%的年齡在25歲以上,而非納稅雇主的這一比例為37%[26]。這可能是由于納稅雇主希望通過對現有雇員的投資來收回其所繳納的學徒稅,而不是主要將這些經費用于新員工和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
第四,當把學徒制層級與年齡相結合時,情況更加令人擔憂。在學徒稅實施后的兩年中,66%的高層級學徒在25歲及以上,共有80500個,只有7100個在19歲以下,46%的學徒在開始學徒制培訓之前,至少為原雇主工作了6個月[27]。這說明有經驗的成年雇員正成為學徒稅的關注重點,而對較年輕和缺乏經驗的學習者的關注度逐漸下降。
三、英國學徒稅制度面臨的挑戰
學徒稅制度實施以來,商界對其高度關注,其中以批評居多。英國工程雇主聯合會(Engineering Employers Federation,EEF)制造業集團主席朱迪思·哈克特夫人(Dame Judith Hackitt)認為,學徒稅對雇主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CBI)表示學徒稅是“破碎”的。學徒稅制度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有研究者認為“學徒稅制度給我們上了一堂課,告訴我們如何不引入新制度”[28]。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學徒制在這一時期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故很難把學徒稅與同時發生的其他改革措施對學徒制產生的影響相分離[29]。盡管不能根據各界的反應以及某些變化來判斷學徒稅制度的成敗,但它的確面臨著較大挑戰。
(一)經費使用對象欠規范
2012年,理查德在《學徒制評論》中指出,學徒制試圖保持“多樣性”使得其定義被過度延伸,“存在一種趨勢,把很多培訓都稱為學徒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30]。2017年,學徒制與技術教育研究所(IfATE)在其網站發布《什么是高質量學徒制》,承認“并非所有的培訓都是學徒制”[31]。值得注意的是,學徒制改革以雇主為核心,讓雇主決定什么可以被稱為學徒制,于是有些雇主為了獲取學徒稅經費,利用了“學徒制”定義模糊性的弱點,將某些培訓課程重新包裝為學徒制,這就是所謂的“虛假學徒制”(fake apprenticeships)[32]。
一是低技能課程。學徒制標準要求經過12個月的培訓,學徒就能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工作,即不同的就業環境可以被同一個學徒制標準所覆蓋,這意味著專業知識和嚴格訓練的缺乏,通常代表著低技能課程的強烈跡象。更令人失望的是“垂直分化”(vertical differentiation)現象的存在,即通常有幾乎相同的二級和三級學徒制標準,由于其經費完全獨立,于是雇主和培訓機構就可以分兩次提取學徒稅經費。
二是管理培訓及專業發展課程。理查德在《學徒制評論》中指出,“在現有工作中提高技能的培訓不應被視為學徒制”,但雇主考慮到任何被指定為學徒制的課程(甚至是管理級別的課程)都能獲得95%的經費補貼,于是積極地把以前由自己支付的培訓課程重新包裝為學徒制。已獲批準的學徒制標準中包含許多為在職人士提供發展機會的專業課程,如早期教育中心領導、高爾夫球場經理、酒店經理和零售經理等。克蘭菲爾德大學(Cranfield University)管理學院就把現有的行政工商管理碩士(Executive MBA)項目納入新的高級領導者學徒制。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報道,“英國商學院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好運,可以使用學徒稅經費來實施MBA課程”,并引用了克蘭菲爾德大學MBA課程總監保羅.貝恩斯(Paul Baines)的話稱,“學徒稅制度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的機會”[33]。
(二)學徒稅經費預算超支
學徒稅制度實施以來,新學徒數量減少,這意味著學徒制體系的規模相對變小,但學徒稅經費的預算壓力卻越來越大,這似乎是矛盾的。2018年的《財經周刊》首次報道了這一情況,2019年國家審計署(National Audit Office,NAO)發布了關于學徒制的報告,其中也強調這項稅收很快就有超支的風險。據英國教育部估計,2019/20學年可能超支7200萬英鎊,到2021年可能超支15億英鎊[34]。
有三個關鍵原因導致學徒制培訓的成本增加。一是由學徒制框架向學徒制標準的轉變。教育部要求自2020/21學年起,所有學徒制培訓均按學徒制標準進行,而標準比框架所需的培訓時間更長,并且有終結評價(end-point assessment)的要求,故其平均成本相對更多。2017/18學年,按照學徒制標準培訓一名學徒的平均成本約為9000英鎊,大約是預算允許成本的兩倍[35]。二是向高層級學徒制的轉移,它們比低層級學徒制更為昂貴,最昂貴的為會計/稅務專業人士(Accountancy/Taxation Professional)7級學位級別學徒制(相當于碩士學位),共占用了1.74億學徒稅[36]。三是“虛假學徒制”的存在。自2017年4月以來,學徒制經費共有29億英鎊,而“虛假學徒制”就消耗了43%的稅收經費,如高級領導學徒制,在短短兩年內占用了4500多萬英鎊[37]。在這種情況下,學徒制對經濟的附加價值可能與學徒稅經費的數額不成比例,這就形成了一定風險。
(三)對培訓機構缺少有效監督
學徒制培訓機構注冊局(RoATP)的成立“旨在開放市場和增加競爭,從而提高經費的利用價值”[38],相關機構通過其鑒定成為培訓機構是獲取學徒稅經費的主要途徑。2017年3月,英國教育標準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Ofsted)總督察阿曼達·斯皮爾曼(Amanda Spielman)警告稱,“很明顯,將有很多新成員加入進來,其中很多機構的培訓經驗有限,培訓質量可能會形成相當大的分裂”[39]。其預測被證明完全正確,2018年12月,登記在冊的培訓機構約有2600個,較稅前的800多個大幅增加,而且許多都是新進入市場的培訓機構,其中約900個尚未與任何雇主簽訂合同[40]。教育標準局(Ofsted)在其2018年的年度報告中對“一些質量被稀釋的早期預警信號”表示擔憂,只有58%的機構在學徒制培訓方面被評為“良好”或“優秀”,約有1/3的學徒是由“不合格”或“需要改進”的機構提供的培訓[41]。
列入培訓機構登記冊只是第一步,培訓機構的第二個任務是與雇主協商確定學徒制培訓的價格。2012年,理查德在《學徒制評論》中建議,學徒制培訓的價格由雇主和培訓機構協商確定,并預測,“以市場為導向的學徒制培訓價格,將會帶來更高質量的培訓、更低的培訓價格,并最終為學習者、雇主和社會帶來更好的結果”[42]。但是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的報告指出,在征收學徒稅的情況下,更有可能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認為“將看到一個強烈的趨勢,即機構會把培訓課程的價格定在或接近于給定區間的最大值,因為培訓機構擔心定價低于最大值將表明其課程質量較低,且這種趨勢可能會加劇,故現實中雇主很難把價格信號作為衡量質量的指標”[43]。所以,一旦培訓機構(無論多么缺乏經驗或不合適)被列入登記冊,其理性反應是把培訓價格推得盡可能高,以便從學徒稅經費池中獲取最大收益。
(四)對高層級學徒制的監管薄弱
學徒制是一個復雜的領域,正如《學徒制責任聲明》所概述的那樣,有過多的機構管理學徒制,至少有教育部(DFE)、教育標準局(Ofsted)、資格及考試管理辦公室(Ofqual)、學生辦公室(OfS)、質量保障署(QAA)、學徒制和技術教育研究所(IfATE)、就業和技能資助署(ESFA)七個機構。自學徒稅制度實施以來,學徒制培訓出現了戲劇性的、加速的向高層級學徒制的轉移,這使得對學徒制質量的監管更為困難,尤其是由誰負責高層級學徒制監管存在相當大的混亂。
《學徒制責任聲明》規定,由教育標準局“負責監管各層級學徒制培訓的質量,并公布檢查結果”,但是當涉及到四級及以上高層級學徒制時,規定由教育標準局和學生辦公室共同承擔監管的責任,在學生辦公室注冊的學徒制培訓機構如果提供四級及以上學徒制培訓,則學生辦公室需要向教育標準局提供相關信息,并告知其審查結果[44]。但是由學生辦公室監管高層級學徒制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其在規范學徒制和職場培訓方面缺乏專業知識,不適合這項職責;二是不像教育標準局,學生辦公室沒有權力進入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場地進行現場檢查。至于為什么選擇學生辦公室而不是教育標準局作為高層級學徒制的主要管理機構,教育部沒有給出任何解釋,這表明該制度的合理性令人擔憂。
四、英國學徒稅制度的發展趨勢
根據變遷程度的差異,歷史制度主義將制度變遷劃分為制度微調、制度轉換、制度置換和制度斷裂四種類型,其中制度微調是對已有框架內的部分內容進行微小的調整[45]。學徒稅作為一項新制度,其實施效果不應由單一的指標“新學徒的數量”衡量,英國政府認為,“那些接受新的、高質量的學徒制培訓的人數迅速增加,超出了預期”[46],故學徒制質量已有所改善,但雇主存在“磨合期”帶來的“不適應”。隨著學徒稅制度的不斷微調,其優越性與實施效果將逐漸明朗。
(一)引入新的學徒制定義
教育和技能(EDSK)智庫負責人湯姆·里士滿(Tom Richmond)指出,為規范學徒稅經費的使用對象,應當重新定義“學徒制”[47]。學徒制作為全球知名品牌,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ILO)將其定義為“把職業教育與以工作為基礎的中等職業技能學習(即超出常規的職業培訓)相結合的培訓項目”,另外還強調學徒制的其他關鍵特點,如培訓對象側重于年輕人,培訓是一個長期和系統的(即預定義的)學習方案等。英國政府于2013年對學徒制的定義為,“學徒制是一種需要大量和持續培訓的工作,通過培訓使學徒達到學徒制標準的要求,并獲得可遷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此定義與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存在明顯差異,一是對于什么是“技能型職業”(skilled occupation)缺乏精確描述,因此雇主就不必專注于此,而只需要描述任何他們希望被貼上學徒制標簽的工作或角色,從而直接導致“虛假學徒制”的出現。二是“持續培訓”(sustained training)的概念被移除,而以“12個月的最少培訓時長”代替,這遠低于三年的國際基準,即學徒制標準并不一定需要促進長期或系統的培訓,盡管這在其他國家被視為學徒制的核心特征。英國應該引入新的符合國際標準的學徒制定義,任何不符合新定義的學徒制標準均不應獲得學徒稅經費的支持。
(二)支持不同群體的經費需求
某種程度上,學徒制被視為“社會的靈丹妙藥”(social panacea)[48]。2015年保守黨在競選宣言中承諾“在未來五年內新增300萬學徒”(強調數量),并“確保提供雇主需要的技能”(強調質量),但是這兩個承諾很難調和。前技術部長羅伯特·阿爾豐(Robert Halfon)也認為:“學徒制可以提高社會公正、經濟生產力和技術基礎”[49]。但是學徒制其實很難同時實現這些目標,事實上,不同的目標可以把系統拉向不同方向。例如,提高生產力的項目(通常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更高層次項目)不太可能面向最近沒有就業、沒有教育(或培訓)的年輕人,部分原因是他們之前的資格水平較低;如果學徒制的重點在于幫助雇主填補技能缺口和員工進步,可能會鼓勵公司投資于現有的勞動力,而不是將更多的年輕人引入勞動力市場。
成功的學徒制培訓應該以高質量、高強度的培訓為基礎,為年輕人和重返職場者提供一條清晰的技能之路,而不是提供一次性的沒有明確路線的培訓。有研究者建議采取一種更有針對性的方法:納稅雇主將相當大比例(至少一半)的學徒稅經費用于公司的新雇員,同時給予年輕人(30歲以下的學徒)一定比例的經費[50]。當然,這兩類人通常是同一個人,因此,相當大一部分學徒稅經費將繼續提供給年長的雇員或已經在公司任職的雇員。作為首要任務,決策者應考慮低技能群體、低收入群體、年輕一代等不同群體之間的適當平衡,以及雇主在確定技能需求時的適當靈活性水平。
(三)減輕雇主的行政負擔
正如巴蒂斯頓(Alice Battiston)等人所指出的,學徒稅制度的實際實施效果可能存在滯后性,雇主需要時間來適應這項新的稅收制度。2017年9月,一項針對1400多家公司的調研發現,近1/4的受訪者不了解這項稅收,或者不知道將如何應對,超過半數表示這只是一項額外開支,56%的受訪者認為不會收回任何或部分經費[51]。學徒稅制度的實施使得雇主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他們必須通過其數字賬戶承擔以下任務:不斷監察可動用的征款總額及用途、每月監控每個學徒與培訓機構的交易、留意現時可用的學徒稅經費的到期日期等。雇主從未表達過承擔這些負擔的強烈愿望,而在學徒稅制度實施前,培訓機構承擔了大部分責任,雇主的精力主要用于培訓學徒,但是學徒稅制度的整體設計使得雇主很難將這些責任中的一部分轉嫁給培訓機構,故雇主代表對學徒稅的批評一直是有力和直接的。為解決這些問題,有研究者提出應該引入一種新的“學徒券”(apprenticeship vouche)模式[52],將把購買力牢牢掌握在雇主手中,允許他們選擇學徒制標準和培訓機構,但個人學習者記錄的管理、評估和其他行政負擔將由培訓機構承擔。
(四)關注中小雇主的經費缺口
學徒稅把雇主區分為納稅雇主和非納稅雇主,其占比分別為1.3%和98.7%,非納稅雇主大部分是中小企業,他們貢獻了經濟的大部分份額(超過99%),但是學徒稅制度實施以來,中小企業卻面臨著經費缺乏的問題。學徒制與技術教育研究所(IfATE)首席執行官珍妮弗·庫普蘭(Jennifer Coupland)表示,小企業沒有足夠的經費,故政府需要為大約8.5萬個學徒制項目提供7.5億英鎊的經費支持。就業和學習供應商協會(Association of Employment and Learning Providers)調研發現,3/4的培訓機構不能滿足中小企業的需求,1/4的培訓機構不得不放棄為中小企業培訓學徒[53]。為解決日益擴大的經費缺口,有研究者提出四種可能的選擇:一是限制某些類型學徒制對經費的使用,二是要求納稅者支付某些類型學徒制或學徒的培訓費用,三是擴大學徒稅的征稅范圍,四是提供額外的公共經費以補充學徒稅經費[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