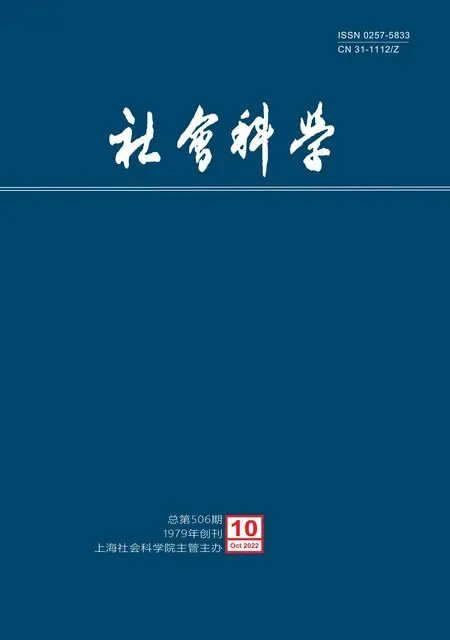歷史政治理論序論
楊光斌
幾乎所有政治理論都是歷史性的,“政治理論”更嚴謹的稱法是“歷史政治理論”,這是由政治理論的知識論原理決定的。從社會科學體系,諸如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和政黨中心主義;到我們耳熟能詳的眾多名詞、概念,諸如自然法、契約論、理性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等;再到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或政治學的方法論,如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主義等,都是歷史分析的產物。歷史政治學的提出,不僅使中國政治學終于有了政治學專屬的研究方法,即中國政治學不再和其他學科一樣使用社會科學的一般性方法,更為政治理論的發現和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歷史路徑,使得政治學的學科專業性屬性更加鮮明,中國政治學因此可能在建設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上走在前面。我們認為,只有當一個學科有了自己專有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才有可能在建設自主性知識體系上邁開步伐。
一、政治學的知識論原理
政治學以及所有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包括概念、理論、理論體系和方法論)是從哪里來的呢?或者我們熟知的政治學知識體系是如何產生的?這就是知識論要回答的問題。在哈貝馬斯看來,社會科學的知識來源于歷史、現實實踐與理論本身,這大概是在知識論上對社會科學最好的概括。①哈貝馬斯:《理論與實踐》,郭官義、李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作為理論來源的“元理論”,其實也是特定實踐和歷史文化的產物,因此嚴格說來理論主要來自實踐和歷史。只不過,在理論貧困而又渴望理論的時代,理論本身成為一種“思想供貨商”,成為需求方的理論來源。至于理論與現實—歷史的關系,或者說理論為什么誕生于實踐和歷史,已經有很多的討論。簡單地說,古今中外的政治統治都需要對現實進行理論、觀念的闡述,以使政治統治合理化、合法化,減少政治統治的成本;現實實踐是歷史制度變遷的延續,論述現實的理論必然要追尋“正朔”,歷史必然成為理論的最重要源泉。另外,在中國自先秦“諸子百家”以來就形成了“士文化”,士人階層在書寫并傳承歷史中有著特殊作用;而在歐洲,從中世紀的修道院到大學的誕生,知識階層得以形成,他們的使命就是從現實—歷史中“發現”甚至“發明”理論。這樣,士人階層或知識階層建構的理論或者觀念就成為世界本身,或者說世界就是他們構筑的觀念的矛盾體。政治統治的需要與知識階層的存在,使得理論基于實踐—歷史而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而它們反過來又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并改變著現實世界,理論本身構成了“存在”,成為后來人實踐的淵源。
首先,理論本身。“發現”或“發明”以新概念為核心的理論或者理論體系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理論一旦被發展出來,會演變為流行性觀念而固化為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形成嚴重的路徑依賴。哪怕是以訛傳訛的觀念,在生活中也有可能演變成信念,比如“黨爭民主”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或話語體系(包括實踐中的制度體系)。內在原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0頁。統治階級會利用優勢的制度性資源去推廣有利于自己統治利益的思想,基于理論的思想觀念自然會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得以延續,并據此塑造一代又一代人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所以,理論產生得越早,延續性影響越大;理論一旦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會代代相傳。這就是每個時代的部分社會科學理論來自既有理論的原因。
國內政治的政治理論可以通過政治社會化而得以延續和傳遞,世界政治中的政治理論生態分布更不均衡,不但存在誘致性吸納,更有強制性變遷。社會科學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國家發展的先后決定了世界社會科學的不平衡性、不平等性。按照沃勒斯坦的統計,歷史學和三門探討普遍規律的學科——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直到20世紀上半葉,95%的學術研究都是僅僅在5個國家——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和意大利中進行的,而且它們也主要是研究這5個國家。剩下5%研究的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低地國家、俄羅斯、伊利比亞半島,并在很小范圍內研究點拉丁美洲。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4卷,吳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10頁。
95%的知識存量為二戰后的冷戰提供了充足的彈藥。冷戰是意識形態戰爭,因此冷戰時期的社會科學堪稱“冷戰社會科學”尤其是“冷戰政治學”。在這個過程中,對立的兩極都給對方貼上標簽,西方以民主—專制二分法建構起“冷戰政治學”。在薩托利看來,戰后西方社會科學的最大成就是把“自由”和“民主”兩股道上跑的車擰在一起,建構出自由主義民主理論,③喬萬尼·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并被鼓吹為“普世價值”。
冷戰是一場極不對稱的意識形態戰爭。當西方扛起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這面大旗時,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致力于從經典著作中找答案,甚至一度取消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比如政治學和社會學。以至于到改革開放時,中國還沒有社會科學,理論匱乏是必然的。因此,當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之時,西方社會科學以排山倒海之勢涌入中國,中國留學生也如過江之鯽前往歐美“取經”。這是知識社會學上一種典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過程說明,存量理論本身就是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存量理論在傳播過程中,以科學主義化的乃至普遍主義的形式涌向理論貧困地區,顯現出非歷史性。然而,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科學所接受的概念和理論,幾乎都是特定國家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政治實踐經驗的理論化產物。因此,對于中國人而言的非歷史性的社會科學理論,基本上都是即時即地的政治實踐的產物。
其次,現實政治實踐。毛澤東曾通俗地講:“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頁。毛澤東最有資格說這話,統一戰線、政治協商、人民民主專政國體、民主集中制政體等政治學的關鍵詞,都是革命實踐的產物。
什么樣的現實政治實踐能產生理論?無疑是制度變遷的關鍵時期,作為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無不如此。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動蕩期催生的是霍布斯的個人解放的個體主義思想——這是自由主義的本體論;進而,當政制穩定下來后,主張財產權的洛克式自由主義應運而生;財產權催生了工業革命這個人類歷史的第一次巨變,工業革命使得遠程貿易成為可能,財富的急劇增長催生了以休謨、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蘇格蘭啟蒙學派,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初步成熟。英國的成功讓法國人艷羨不已,以追求英國政制為目標的法國啟蒙運動主張比如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進一步完善了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并直接成為美國建國者的憲制藍圖。至此,從英國首倡到在美國和法國落地,自由主義都是政治實踐的產物。
伴隨著作為近代西方世界“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誕生和發展,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先后出現,也都是誕生于政治實踐之中。當法國大革命以極端手段進行時,英國的政論家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一系列批評,就構成了后來被稱為保守主義的思想來源,伯克因此被稱為保守主義的鼻祖。
同樣,共產主義思想也是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產物,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經典的《共產黨宣言》是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政綱,有了政綱的工人運動才有后來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以及由歐洲到東方的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這些國際性運動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但作為政治思潮發展起來,列寧還找到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手段——無產階級及其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亨廷頓不無贊嘆地指出,如果說杰佛遜發現的是代議制,列寧發現的則是政黨,他們才是政治學大師級人物。②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4—281頁。革命到了中國,曲折的實踐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③《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9—408頁。并以田野調查和歷史政治的路徑去踐行這一信念。
實踐出真知,而作為“真知”的理論往往誕生于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社會大革命、國家大轉型都是發現理論的關鍵時刻和寶貴資源。
再次,理論的歷史性。正如理論具有實踐性的特質,現實實踐性也具有歷史性。一方面,即時即地的實踐性必然承襲了各自的歷史文明基因,另一方面,過去的政治實踐就成為了今天的歷史,而且歷史本身直接成為理論和思想的淵源,因此幾乎所有的政治理論都具有歷史性。
作為西方政治理論的文化基礎或本體論的個體主義,并不是霍布斯的“發明”。因為在之前的文藝復興運動,尤其是宗教改革,已經使得個體從神權政治的蒙昧狀態逐漸蘇醒過來,并經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發現”而上升為“自然權利”。實現個人權利的制度安排是比文藝復興運動更早的代議制,代議制使得“王在法下”,因此保護了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個人權利即當時的封建領主們的權利,由此催生了三權分立的代議制政府(后來又被稱為代議制民主)。西方政治理論的社會史屬性非常特殊,代議制是社會史的產物,而且以個體主義文化為基礎。由此可以理解,在那些既非個體主義文化又無社會史的國家,實行代議制究竟意味著什么。何況,很多國家時至今日已經不再是均質化文化,而是異質化的多民族國家,基于個體主義的具有對立性的代議制對國家建設又意味著什么,很多國家無休止的政治動蕩根源于此。
歷史是發現理論的不竭之源。社會科學體系中的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都是基于不同歷史而演繹出來的。基于歷史的制度變遷,本身存在著很多道理,這些道理有待被發現而成為理論。西方人已經充分地發掘了自己的歷史并使之理論化,比如歷史社會學的重大貢獻,西方歷史的影響因此更具世界性。比較而言,更有連續性的中國歷史所貢獻的社會科學理論甚少,沒有理論化的歷史便處于休眠狀態而陳放在博物館里“休眠”,意義大打折扣。中國史學界似乎習慣了歷史的博物館化,當錢穆這樣的學者試圖在中國史研究的基礎上提煉一些概念時,比如“士人政府”,依舊會招致歷史學界的異議乃至非議。更有甚者,新文化運動所塑造的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的史觀影響深遠,比如給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國歷史扣一頂類似專制主義的總帽子。這種現象完全是中國社會科學思維滯后的表現,認為歷史的研究應該純粹而不應該有“雜質”,殊不知,社會科學的進步就體現在交叉性上;同時也是史觀滯后的表現,未曾想過如此“壞”的歷史怎么會孕育出如此輝煌燦爛的文明,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復興?
就規模而言,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大文明體之一;就連續性而言,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大型文明,因而不存在“古中國文明”之說;在包容性上,中華文明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吸納了最多外來文明,因而最具有普遍性。這樣的文明即使不是湯因比所說的唯一能夠管理21世紀的文明,①阿諾德·湯因比、池田大作:《選擇生命》,馮峰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至少也是最能引導21世紀走向新文明形態的文明。對于這樣一個文明體,政治理論的發現工作赤字太多。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是中華文明的產兒,是中華文明的承載者和繼承者,這其中的內在邏輯和機理有待發掘。比如,民主集中制與大一統的關系、民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協商民主與協商政治傳統的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天下觀的關系、仁愛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系,等等,都是重大的歷史政治理論命題。
已知的中外政治理論都是歷史的產物,關于中國的政治理論比如大一統、民本思想本身就是歷史的決定性組成部分,關于西方的政治理論比如自由主義和代議制政府理論也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并被加工成理論體系。不僅如此,產生如此多重大理論的政治實踐也不過是制度變遷中的關鍵時刻,即時即地的政治實踐本身就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才說幾乎所有的政治理論都具有歷史性和地方性,政治理論也被稱為歷史政治理論。
當我們強調政治理論的歷史性和地方性的時候,是就其起源而言的。理論一旦變成觀念,就呈現出超越地域的彌散性而成為影響異域的思想,比如宗教和被西方稱為“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這一方面可能導致人類共同價值的形成,比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但同時也招致大量的文明沖突或文化沖突,這種沖突的根源就是異域理論與在地歷史之間的張力。因此,理論產生于歷史,理論的生命力也在于歷史。
接下來我們具體闡述,無論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支撐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還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都具有歷史性,都是歷史政治理論。
二、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以社會中心主義為例
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對主要國家的現代國家建設或現代化道路進行系統化總結的結果。現代化進程的組織主體不同,所產生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也有巨大差異。英國—美國的組織者主要是個體化的商業集團,由此塑造的理論體系便是個體中心主義或者社會中心主義;德國—日本等國的組織者主要是國家或者國家化的官僚制,由此產生的理論體系便是國家中心主義;后來者比如俄國、中國的現代化組織者主要是政黨組織,因此應該有一套政黨中心主義的理論體系。顯然,這三大理論體系都是特定國家特定歷史經驗的理論化“發現”,而非沒有歷史場景的理論“發明”。對于社會科學體系上的“三大主義”及其產生的歷史性實踐性,筆者在15年前已經有較為系統研究,命名為“制度變遷的路徑及其社會科學價值”,②楊光斌:《制度變遷的路徑及其社會科學價值》,《中國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夏季卷。在此不予贅述。
產生于特定歷史—實踐的政治理論必然具有適用性上的歷史性和局限性。然而,在國際社會科學中,社會中心主義理論體系處于絕對主導性地位。主張國家作用的理論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雖然有從亨廷頓、米格代爾到“回歸國家學派”的大力呼喚,但因國家總是紙面上、觀念上的而非實踐中的存在,總是“找不回”國家,國家中心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反映德國、日本等早發達國家的歷史政治理論。而與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相比,政黨研究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是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首先都是本國中心主義的,而在社會科學最發達的西方國家,政黨是國家憲制下的產物,比如英國、美國的政黨都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后為選舉政治而設計出來的或演繹出來的政黨政治,政黨只不過是一種類似利益集團的社會組織,因此政黨研究也必然被納入社會中心主義體系。但是,不同于早發達國家的是,以俄國、中國為代表的很多后發達國家,不是國家憲制塑造了政黨,而是政黨塑造了國家憲制或者國家的根本議程,形成了絕對不同于西方的政黨—國家體制,因此社會中心主義乃至國家中心主義的理論體系都不能解釋“政黨—國家”,只能有一個政黨中心主義的“第三個主義”。
“政黨—國家體制”與西方國家憲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國家的憲制結構是三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但“政黨—國家體制”中的政黨的權力是“領導權”,領導權造就了“三權”。①姚中秋:《領導權:基于中國實踐的權力類型學研究》,《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1期。如果說“三權”是程序主義的、行政層面的,領導權則是決斷性的、政治層面的。在政治實踐上,如果只有程序主義的行政,那么權力關系就可能如美國政治之間的三權制衡以及聯邦—地方之間的分權制衡,結果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政治性問題總是得不到解決,比如控槍問題。一個可能會產生的疑問是,既然有如此大的弊端,西方為什么能夠實現早發達?西方的早發達不是簡單的制度主義所能回答的,需要從世界政治史的角度看問題。現代西方國家的誕生和發展起源于互相關聯的“兩架馬車”,一個是戰爭制造的國家,一個是殖民貿易的掠奪,通過戰爭與掠奪而來的源源不斷的資源極大地化解了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階級對立和政治矛盾,財富掩蓋了制度性矛盾。即便如此,意大利雖然在1900—1920年間移民1/5的人口,最終還是因階級矛盾惡化而選舉出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希特勒當選也是國內階級矛盾、政治矛盾白熱化的結果。
今天,世界貿易中的財富結構的變化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矛盾很難被豐裕的財富分配所消解。更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激烈的階級矛盾可以通過海外殖民去化解,比如歐洲人移民到新大陸、大洋洲、非洲和南亞,十三州的美國白人可以向西移民、向南掠奪;今天則出現了“反向移民”導致的歐洲亂民危機和美國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危機。一句話,曾經因社會中心主義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面對新的世界秩序,以社會為中心而設計的充滿緊張、乃至對抗性關系的彼此制約的權力結構,已經很難化解國內矛盾;在發展效率上,以社會中心主義歷史而組織起來的國家,也難以與以政黨中心主義傳統而組織起來的國家相競爭。
道理很簡單,以社會為中心的國家組織化程度有限,乃至是分散的個體,這樣的分散性組織在面對更弱組織化的社會可能是有效率的,比如英國幾門大炮就能征服清政府,一家商業公司就能壟斷世界市場。但是,當這樣的分散化組織的國家遭遇到以政黨組織為基礎而組織起來的國家時,國家能力、制度競爭力都捉襟見肘。這是“中國威脅論”的大歷史背景。
但是,在發展上處于比較弱勢的西方卻擁有話語權上的比較優勢,也就是沃勒斯坦所說的居絕對優勢的知識存量,這種社會科學的數量優勢在二戰后又適時地轉化為社會科學化意識形態優勢。到目前為止的國際社會科學中,都試圖將“政黨—國家體制”納入社會中心主義或國家中心主義之中,試圖消解“政黨—國家”。比如,在政治學上,冷戰時期建構成體系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核心是競爭性選舉或者黨爭民主,以此區分民主—非民主而將“政黨—國家”妖魔化,好像只要有競爭性選舉,國家建設就大功告成。冷戰結束后,這種冷戰時期形成的意識形態戰爭非但沒有褪色,反而強化,西方政治學研究完全基于“轉型學”范式的民主轉型,在全世界推廣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社會中心主義思想和政治觀念。與此相適應,在政治社會學上,主張以社會組織為治理主體的治理理論、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理論也開始流行,意圖進一步消解國家、政府或者政黨的作用。在經濟學上,流行的基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或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華盛頓共識”主張以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休克療法”。這種由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化、社會個體化構成的理論“金三角”,不過是“百慕大三角區”,駛入“金三角”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包括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自身,最終都將被吞沒掉。
美國等發達國家深陷泥沼,是因為作為社會中心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國家,很難與以政黨中心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國家去競爭。大歷史告訴我們,國家之間的競爭導致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組織化程度的競爭。在歐洲內部,軍事革命直接導致民族國家的興起并加強了這等民族國家的競爭力;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之所以一直領先西方兩千年,是因為秦朝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性特征的以農業為基礎的組織化國家,而這種國家在歐洲直到16—17世紀才開始出現。之后中國開始落后于西方國家并在中西碰撞中敗下陣來,是因為西方民族國家是靠戰爭和貿易組織起來的,組織化程度比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更高,這就是19世紀中期中國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之高但依然敗北的原因。但是,政黨把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重新組織為“新中國”,其組織化程度遠比西方國家更高;而且這樣的國家一旦被賦予市場活力,基于活力的政黨—國家的競爭力就被西方認定為“中國威脅論”。確實,中國以自身的發展而改變了世界秩序,這在世界近代史上實屬罕見,因為西方之所以發達,沒有哪個國家不是依賴戰爭和掠奪,只有中國以自身的和平與發展而改變了世界。這樣的國家被認作“威脅”,可見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荒唐到何等程度。說到底,是和平起家的中國威脅到靠掠奪起家的支配性國家。
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陷入泥沼,是因為社會中心主義的“金三角”理論使它們“返祖”。現代性國家的一個根本特征是其組織性,將分散于部落或封建領主的權力集中起來,形成“主權者”。這一任務中國秦朝就完成了,歐洲16—17世紀方才完成,美國的聯邦制事實上包含著很多封建制的成分(比如所謂的地方自治、行業自治等)從而導致強制泛濫,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依然是世襲制、封建制或者部落制。對于尚未形成“主權者”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首要任務是將國家組織起來。米格代爾的“強社會中的弱國家”深刻刻畫了國家權力被種種傳統勢力所綁架的現象,①喬治·S.米格代爾:《強社會與弱國家》,張長東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35頁。使得“找回國家”不過是理論家們的一廂情愿。在這種亨廷頓筆下的“普力奪社會”中,競爭性選舉只不過是強化了古老的社會結構,②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60—219頁。從而導致的不是政治發展,而是普遍性的政治衰敗。
“前車”并沒有成為鏡鑒。冷戰勝利的意外之喜更讓社會中心主義理論體系登峰造極,弗朗西斯·福山一改無數智者論述政制的歷史性和條件性時的審慎美德,“歷史終結論”一鳴驚人,認為代議制民主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也是最終的政府形式,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就這樣,起源于南撒哈拉沙漠國家研究的“治理”開始流行,讓國家靠邊站,只有社會組織主導的治理才能實現透明化、效率化、合理化乃至合法化。在此基礎上,公民社會也應該聯合起來,實現“全球治理”——意味著只有以公民組織為主體的全球治理,才是透明的、有效率的、合理的乃至合法的。和自由民主理論一樣,這種社會中心主義的治理理論也一度在中國相當流行,無奈中國的“政黨—國家體制”具有強大的自主性,社會中心主義的治理理論被適時地改造為政黨中心主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命題。
社會中心主義理論體系在西方的困境和在很多非西方國家的失敗,根源于其產生的歷史性和使用上的透支性。英國是最早因資產階級革命而催生工業革命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對這一深刻改變人類進程的大歷史的書寫也必然深刻地影響著其他社會的觀念和思維方式,以實現“趕超”。有成功的趕超者,比如德國在1890年成為歐洲第一大工業強國,這是因為德國走了自己的不同于社會中心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的道路。再后來,就是中國趕英超美的故事,中國的成功也是因為走了不同于社會中心主義的政黨中心主義的道路。而眾多的后來者為什么不能趕超英國、甚至陷于泥沼而難以自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模仿了社會中心主義的道路。殊不知,社會中心主義道路是為英美量身定做的,或者說社會中心主義知識體系是歐美社會史演繹的制度變遷方式以及由此而塑造的政治理論。筆者曾系統地研究過地方自治、英國的商業集團、美國的實業家集團等“社會力量”在英國—美國的現代化歷程中的主導性作用。①楊光斌:《政治變遷中的國家與制度》,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203頁。
實踐—歷史的路徑和屬性決定了政治思想。產生于英美經驗或解釋英美經驗的理論的一個主導性線索就是對西方文化、西方人影響深遠的“自然權利”,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為英美經驗而“量身定做”(tailor-made)的理論。“自然權利”講的是誰的權利(權力) ?望文生義,當然是社會(商業集團)而不是國家的權利(權力),其中心思想是“社會”而不是“國家”,因此圍繞“自然權利”而展開的“社會契約論”可以理解為“社會中心論”,由“社會契約論”而演繹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中心論”的思想和理論。
作為工業化現代化先行者的英國自然要以“教師爺”的架勢向其殖民地和后來的非西方國家輸出經驗,以社會為中心的經驗演變為“分而治之”,使得殖民地社會難以形成統一的政治力量而反抗殖民者。對于美國人而言,正如亨廷頓指出,美國人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方案首先想到的都是地方自治、分權、制衡、競爭性選舉等,結果使得很多非西方國家的“國家建設”陷于古老社會結構而更加無望。②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4—6頁。
這就是政治理論所揭示的歷史語境以及非歷史性理論所招致的后果。誕生于英美歷史的社會中心主義是其現代化成功的經驗,但是對于那些尚未組織起來的后發國家而言,社會中心主義則是“無組織性社會”的致命傷,使得它們難以形成作為現代國家前提的“主權能力”。其實,即使對于英美這等早發達國家而言,社會中心主義所以管用,還在于當時的世界處于“無主地”狀態,它們可以以自己的先發優勢而幾乎節制地掠奪,一個商業集團就相當于一支強勁的軍隊而所向披靡,幾百個人就是在“無主地”建立一個“新國家”。這事實上是組織化集團與無組織狀態的非對稱性競爭,其優勢自然無與倫比,財富自然急劇增長。這是我們理解以“自然權利”為基礎的社會中心主義的時空背景。時空轉換至當下,組織化國家成為世界政治的主角,競爭是國家之間的事,在國際發展意義上,社會中心主義還有多少功用呢?
簡言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具有歷史性。首先,它誕生于特定國家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經驗。其次,即使在同一個國家或社會,當其所處的世界政治空間完全不一樣的時候,曾經的歷史性顯現出非歷史性,比如英國美國在二戰后國家主義政策的大量出現。再次,產生于特定歷史文明中的旨在解決重視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理論,很難不顧歷史文明的差異性而“拿來主義”,否則必然“畫虎不成反類犬”。
在本質上,社會科學具有即時即地性,但是“文化帝國主義”即漢斯·摩根索所說的改造異族心理結構的帝國主義行為,又使得民族主義的地方性知識具有普遍主義,從而形成“文明的沖突”。作為構成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大廈的基石的基礎性概念既是“文明的沖突”的重要推手,又是文化帝國主義的重要工具。
三、社會中心主義的關鍵詞:以民主為例
歷史制度主義代表學者詹姆斯·馬洪尼(James Mahoney)總結道:“在概念發明的意義上,比較歷史研究者貢獻出了社會科學重要概念中的很多指導性定義,包括但不限于威權主義、資本主義、統合主義、民主、發展、封建主義、意識形態、非正式經濟、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在概念的類型學意義上,比較歷史研究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概念性辨別,諸如政體的類型(如民主的、威權的、極權的),革命類型(如政治的、社會的、反殖民主義的),國家類型(如強國家、弱國家、掠奪型國家、發展型國家)以及福利國家制度(基督教式的、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的)。上述列舉只不過是管中窺豹。”①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0, 2004, p.93.但是出于意識形態戰爭的需要,這些歷史性概念被改造為普遍主義的知識,意圖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社會科學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助推了社會科學普遍主義的雄心,以為只要理解了個人行為心理—選擇的一般性原理,就能建構起普遍主義的社會科學原理。 1951年成立的哈佛大學行為科學委員會志在于此。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社會科學比較政治研究委員會更是雄心勃勃,當時的少壯派阿爾蒙德如此豪言壯語:在過去50年里,基于老歐洲形成的“政治科學的概念體系已經逐步喪失了它的能力,甚至無法應付西歐政治的現象”,因此必須尋求替代性術語,比如以“政治體系”代替“國家”,以“功能”代替“權力”,以“角色”代替“職責”,以“結構”代替“制度”,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社會化”代替“民意”和“公民訓練”,而“當我們把新的術語和舊的術語加以比較時,就會有這種建立一個新的概念統一體(即范式——引者注)的沖動”。②阿爾蒙德等:《發展中地區的政治》,任曉晉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頁。
美國人不但要建立新概念,更重要的是要改造老概念以使其時代化,這集中體現對“民主”一詞的詮釋上。自從有人類,必然就需要解決公共生活或社群的各種問題,這種解決方式在有的社會一開始就被稱為民主。比如古希臘的廣場政治辯論是解決公共生活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這種與生俱來的競爭性方式后經神權政治的教皇選舉制、以及受此影響而形成的俗世政治制度即選舉構成的代議制等演變,最終使得競爭性選舉成為歐洲文明的處理公共生活問題的主要形式。而在其他文明中,比如儒家文明,解決公共生活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協商,比如早朝中的“廷議”,家族中的祠堂是協商的主要場所。在伊斯蘭文明中,《可蘭經》規定“公議”是重要原則,清真寺是公議的主要場所。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如果以一種公共生活方式代替基于其他文明的公共生活方式,公共生活的失序、乃至戰爭就會層出不窮。
不僅如此,就民主的內涵而言,即使競爭性選舉被視為民主,但民主絕對不限于或者停留在選舉上,如前,神權政治和中世紀代議制都有了選舉,為什么那時的選舉政治被稱為貴族制或者封建制而不被稱為民主?民主必然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含義。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曾認為馬克思的民主觀就是選舉權問題,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人民的統治,就是人民通過由人民選舉出來的為數不多的代表來實行統治”,對此,馬克思毫不留情地嘲諷道,“蠢驢!這是民主的胡說,政治的瞎扯!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國公社和勞動組合中都有。選舉的性質并不取決于這個名稱,而是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頁。顯然,馬克思主張的民主首先是經濟上的統治權,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奪取政權并獲得經濟統治權,才有真正的人民權利。顯然,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民主首先是經濟權力問題。我們會發現,一個世紀后,西方高舉的民主大旗恰恰就是巴枯寧所理解的、被馬克思所唾棄的“選舉式民主”。
對于社會大眾而言,在既定的政治統治秩序下,即使擁有了一人一票的選舉權,以財產權為主的經濟權利的獲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隨著社會進步,以社會保障為基礎的社會權利成為“公民資格”④T.H.馬歇爾、安東尼·吉登斯等著,郭忠華、劉訓練編:《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必需品,也是一種“可行能力的自由”⑤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這樣,民主事實上就成為實現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公民權利的制度安排。如果以這三種權利構成的公民權利去認識民主或者民主模式,以公民權利的實現程度去認識民主,人們關于民主的結論可能完全不一樣。⑥楊光斌、熊宇平:《民主模式與公民權利的實現》,《國家建設現代化研究》2022年第3期。
社會主義革命所實現的民主恰恰是一種綜合性的制度安排,即使在經濟水平低下的階段,也致力于各種權利保障的實現。比如新中國1954年憲法所保障的公民選舉權、土地制度改革和公有制所體現的經濟統治權以及社會建設(婦女解放、義務教育、公共醫療工程)所實現的遠高于經濟水平的社會權利程度,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政治實踐和制度建設。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才有民主,民主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觀念才得到普遍化認同。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足以作為民主的樣板而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西方知識界產生巨大吸引力。從《共產黨宣言》發表到二戰的百年間,社會主義已經成為西方知識界的一種普遍價值,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瑟斯在192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中指出,時代到了今天,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價值,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在更早的馬克思的時代,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密爾在19世紀60年代就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同情的理解,認為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沒有財產的階級主張政治權利的現象,但不能不承認其合理性。①約翰·密爾:《密爾論社會主義與民主》,胡勇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
可以說,從《共產黨宣言》發表到1970年代的一個世紀多的時間里,社會主義等于民主、民主等于社會主義的思想已經成為一種普遍觀念,甚至連美國政治學界也在20世紀20、30年代開始懷疑,一般民眾不適合進行民主投票。但是,面對大眾政治的洶洶來勢,美國必須將自己論述為“民主國家”,與社會主義陣營爭奪民主話語權。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美國人最終實現了民主話語權上的“逆襲”,將一種基于自己政治制度的競爭性選舉,論述為非歷史性的民主模式。
改造民主意涵。民主自古以來就是人民的統治的意思,對此并無爭議。如此,人民的統治不僅是在政治上或政治程序上的制度安排,人民還必然是經濟的主人并享有各種實質性權利即前述的社會權利。照此標準,美國不但不是民主國家,還必須是以民主理論去解放的國家,美國憲法規定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必須被廢除,即在美國必須進行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這顯然是美國支配階級不可接受的。但是,民主的觀念又是如此普遍主義化,習慣上以“自由”而非“民主”自居的美國則必須把自己包裝成民主國家。出于這種合法性政治的需要,“選舉式民主”或“熊彼特式民主”適時而生,即把實質性民主的人民的統治權,置換為人民選舉產生政治家的過程,即前述巴枯寧所誤解的馬克思的民主觀。熊彼特1942年提出“選舉式民主”之后,美國幾代民主理論家,從羅伯特·達爾、李普塞特到薩托利等人,都是在論證“選舉式民主”就是民主,即民主等于選舉,選舉等于民主。以此來定義民主,那么中世紀的代議制、俄國的原始公社、蒙古人的大汗選舉制,都是民主制度了。這顯然是荒誕不經的。但是,“三人成虎”,說得多了,宣傳得多了,普通人也就不加思考地接受了。
改造民主性質。在改造民主概念的同時,美國人還改造了民主的性質。二戰之前,說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基本上都用“資本主義民主”或者“資產階級民主”。這是準確的表述,因為作為一種政治程序的政治民主不是生存在空氣中,而是植根于社會結構、經濟關系中的,存在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民主自然是資本主義民主,正如存在于世襲制社會結構中的民主是“封建制民主”一樣。但是,對于很多知識分子而言,資本主義代表著不平等,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這不符合他們追求的自由、平等理念,即民主必然要以平等為基礎。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民主不是讓人喜愛的制度。鑒于此,羅伯特·達爾說以民主的標準去衡量,沒有真正的民主國家,但存在多元主義民主基礎上的多頭政體。②羅伯特·達爾、布魯斯·斯泰恩布里克納:《現代政治分析》,吳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5頁。從此,多元主義民主、多頭政體概念就代替了資本主義民主,掩蓋了民主的經濟關系和階級實質。羅伯特·達爾曾經的合作者林德布洛姆指出,談論民主避開經濟關系是沒有實質意義的。遺憾的是,被視為政治學大師的民主理論家達爾,一輩子尤其到了晚年都避談民主背后的經濟關系,他的多元政體即民主政體的七大標準,沒有一個是涉及經濟關系的。③羅伯特·達爾、布魯斯·斯泰恩布里克納:《現代政治分析》,第105—107頁。
改造合法性概念。第三步是在改造民主概念的基礎上改造合法性概念。馬克斯·韋伯的合法性概念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無人問津,但冷戰讓合法性概念派上用場。韋伯的概念是指由合法程序組成的并有效率的官僚制政府就值得人們信仰和服從。在熊彼特改造民主概念的基礎上,李普塞特將“合法律性”置換成競爭性選舉,由競爭性選舉產生并有效率的政府才是合法性的。④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頁。從此,“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在意識形態戰爭中被推廣開來。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自由主義民主”被建構起來,薩托利認為這是戰后美國社會科學最大的成就。原因在于,自由主義一直是以財產權為核心的,保護的是少數人的特權;民主是以平等為核心的,主體是大眾權利。因此,在理論上,自由和民主具有與生俱來的內在張力,這種緊張關系在歷史上也帶來巨大的沖突。但是,“冷戰政治學”硬是把兩股道上跑的車擰在一起成為一個“普世價值”。如此結構性缺陷的理論得以流行,說明他們很“講政治”。
不管如何,競爭性選舉確實是西方中世紀以來宗教和俗世的一種公共生活方式。然而,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選舉式民主的社會條件是民主的均質化,即同一個民族信奉同一種文化價值。在中世紀,競爭性選舉一直是“我族”內的事,即使到了冷戰時期,主張競爭性選舉的達爾、李普塞特等學者都強調均質文化的重要性,①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第56—57頁。達爾甚至指出,在那些既沒有歷史條件又無現實基礎的社會搞選舉式民主,要么是脆弱不堪,要么是徹底的失敗。②羅伯特·達爾:《論民主》,李風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3—150頁。菲律普·施密特甚至政治不正確地抱怨,民主所以普遍很糟糕是因為有些社會的“基因”問題。③Philippe C.Schmitter, “Twenty-Five Years, Fifteen Finding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1, No.1, 2010, p.19.
我研究發現的是選舉式民主導致政治沖突的內在邏輯關系。我認為,競爭性選舉其實是一種黨爭民主,選舉政治是由政黨組織的,政黨的社會基礎來自階級、種族、宗教,競爭性選舉事實上變成了階級斗爭、民族主義分裂和宗教斗爭。④楊光斌:《觀念的民主與實踐的民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黨爭民主是一種條件苛刻的民主形式。全球化推動了選舉式民主的普遍化,同時也刺激了競爭性選舉導致的認同政治乃至政治的部落化。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的“民主回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文化的異質化,存在種族矛盾如烏克蘭、宗教矛盾如中東和階級矛盾如泰國。不僅如此,那些曾經是均質化文化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也越來越因為移民、亂民潮而演變為文化多元主義乃至異質化文化,競爭性選舉導致的是認同政治、極化政治乃至“否決型政體”,結果這些國家的民主成為“無效的民主”。無效的不能治理的民主顯然不是人們所欲求的。
總之,民主的社會條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在既沒有歷史條件又無現實基礎的社會實行選舉式民主,這種政治制度反過來只能讓與民主不匹配的社會結構更加固化,認同政治更加極化,結果不但不是全球化推動的一體化的現代性政治,反而是碎片化部落化的“返祖政治”。
四、社會中心主義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選擇主義為例
知識體系和概念的歷史性不難為人識別,但以科學主義面目出現的方法論的歷史性、地方性則不易辨別。我認為,政治學科誕生以來的研究方法,作為知識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特定國家特定歷史經驗的產物。流行于歐陸的制度主義方法論當然是歐陸政治傳統、尤其是為證明代議制的優越性而產生的,歐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證明“真正正當的統治權理論是代議制政府原理,亦即所有的專制權力不論以什么名稱和在什么地方出現,都是完全不合法的”。⑤弗朗索瓦·基佐:《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張清津、袁淑娟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9頁。至于代議制政府是實行議會制好還是總統制好,都是對英國和美國的政治制度的制度主義描述,對代議制研究并無多少實質性價值,雖然到了1980年代后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又展開一輪總統制—議會制爭論。⑥Juan J.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1, 1990, pp.51-69; Alfred Stepan, Cindy Skach,“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Vol.46, No.1, 1993, pp.1-22; José Antonio Cheibub,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所以說這種爭論沒有多少價值,總統制多或議會制多能說明什么問題呢?實行什么樣的政府形式說到底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歷史文明的性質。任何國家都需要解決或完善政治制度問題,因此制度分析看上去很有價值。但是,起源于歐陸的制度主義塑造的歷史觀是代議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代議制政府是社會史的產物,與這種歷史觀相應的無疑是一種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的政治制度。
二戰后,歐陸的制度主義式微,以國家、政府等為代表的“高政治”研究轉向社會成員的個體行為、團體行為研究,行為主義社會科學一統天下。在制度主義政治學讓位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展中,統計學、心理學、經濟學涌進政治學,基于個體行為的研究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政治問題。這其實是自由主義鼻祖們的夢想。在霍布斯看來,要認識國家,就要理解構成國家的“部件”即個人,就像認識鐘表要首先認識其零件一樣。“人”是什么?在霍布斯看來就是能進行利益計算的、趨利避害的“理性人”。①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沿著霍布斯的開宗立派之論,盧梭斷言,理解了作為理性人的人性,人類政治的種種煩惱就能得到永久性消解,一個至善的共和國得以建立。②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此后,“理性人”假設是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合理性的最重要的立論。
在政治思想史上,這種宏論并不鮮見,作為研究經濟生活的方法也可以理解,因為經濟交易具有個體性。但是,在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上,把這種解釋經濟生活的方法論用于關注公共生活的政治學,確實是一場政治思想的革命。雖然政治學和經濟學關系密切,但根本旨趣卻是南轅北轍,經濟學關心的是資源最大化的效率問題,政治學關心的是秩序穩定下的公正問題,而效率和公正具有與生俱來的張力甚至沖突性。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個體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公正歷來不是核心價值,政治學自然要依附于經濟學以捍衛資本主義社會,以追求效率而犧牲政治學的學科品格。
“理性人”假設雖然誕生于歐洲,但歐洲畢竟有著深厚的人文傳統,理性選擇主義這樣的為個體主義張目的方法論還不至于登堂入室。不同于歐陸,“新大陸”的原主人被種族滅絕后,就是一塊“無主地”,奉行先占先得原則。廣袤無垠的新大陸為釋放人性之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從東部拓展到西部,從北部擴張到南部,信奉約翰·洛克的勞動成果才是財富的殖民主義理論的白人肆意擴張,因此美國就是一個個體主義原則塑造的“例外國家”。這樣的歷史意味著美國就是“理性人”的天選之地,個人利益至上的行為原則進而上升到政治學學科高度,成為一種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進而讓個體主義原則進教材、進課堂、進大腦。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曾批評個體化的團體政治研究代替階級政治研究,是掩蓋了政治的本質。③貝納加:《施特勞斯、韋伯與科學的政治研究》,陸月宏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殊不知,“去政治”的政治學(社會科學)正是為了掩蓋政治的本質。
理性選擇主義是一個以“理性人”為核心的家族概念。首先是社會選擇理論。“阿羅不可能定理”是其代表,是指不同的個人或者人群在不同的議程上存在不同的意見和訴求,即使今天在A議程上形成多數意見,明天這群“多數意見”在B議程上就可能是分裂的,因而永遠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多數。既然不存在穩定的多數,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公共利益,不存在為實現公共利益的公共產品。④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丁建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這種以科學方式論證的“博弈論”,其實質就是否定公共福利這等公共產品,而且論證上的“科學性”完全有違現實政治的真實性。比如,難道美國中下階層不需要在歐洲早就實行了的社會保障諸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難道生命安全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最迫切、最穩定的訴求?這種方法論的深入人心最終把以個體主義為本體論的資本主義社會推向極端化,政治因此也呈極化狀態。
其次,公共選擇理論。以布坎南為代表的理性選擇主義者認為,正如存在一個經濟市場一樣,也存在第二個市場即政治市場,政治家與選民之間的關系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政治家生產政策這樣的產品,選民以選票購買政策。這是一般性的理想狀態。⑤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財政論》,穆懷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其實,正如商家可以惡性誘導消費者一樣,以個體主義為本位的政治家同樣可以用惡政誘導選民,比如歐美基于認同政治的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在歐美,很多政黨為了選舉的需要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比如立陶宛甘當美國的馬前卒而不惜得罪俄羅斯和中國,美國國會議員們為誘導選民實現軍工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竄訪臺灣以惡化中美關系并最終可能傷及美國根本利益。這樣,在公共選擇學派那里,歷來講究秩序、公正、美德的政治在二級市場上被賤賣了。
再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講的是“理性人”的價值偏好受到制度約束,這似乎是對理性選擇主義的一種矯正。但是,“制度”是什么?美國憲法規定的個人有權持槍條款,就是一項根本性制度,但是這種前現代的、人口稀少的處于叢林規則的社會所規定的制度,到今天意味著什么?那就是每年3萬人死傷于槍擊案。另外,“制度”的空間有多大?幾條簡單的規定,比如修憲需要2/3議員和2/3州的同意,讓保護生命的訴求比如控槍屢次落空,原因在于200年前的兩個2/3是可及的,無論是議員人數還是州的數量,2/3多數都可能通過協商而達成。但是,時至今日,議員人數和州的數量,都使得2/3多數很難成為現實。于是乎,很多當務之急的問題無解,前現代社會制定的憲法完全不適用于今日之美國,“否定型政治”根源于美國憲法。
總之,理性選擇主義所以在美國大行其道,是因為美國起源于個體主義肆意擴張的“理性人”社會;在此基礎上,“理性人”方法論的流行鞏固了個體主義社會,即將資本主義社會極端化,形成了不同于歐洲福利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自由資本主義。“新大陸”讓自由資本主義野蠻生長,但從百萬人、千萬人、一億人再到幾億人的美國,僅在空間意義上,都使得自由資本主義必然受到國內空間的約束。另外,自由資本主義的前途也取決于對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當世界市場的支配權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后,自由資本主義的世界空間也必然受到擠壓。這也意味著,為極端化個體主義論述的理性選擇主義的解釋力和生命力必然受到質疑。在政治思潮上,社群主義的興起就是對以個體主義本位的自由主義的一種反思和批判。
主張社群主義的西方學者突然發現,儒家中國就是一個天然的“社群主義社會”。如果說“人”在西方自由主義那里是個體(individuallity),而儒家的“人”首先是“仁”,是基于仁愛的集體。因此,不同于理性人假設的個體主義,中國人必然處于“仁”的“關系主義”之中,人是由歷史、思想和社會關系所塑造的“社會人”。英國著名政治學家芬納這樣說:“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希臘以來的西方傳統完全不同。事實上,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它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與主流的社會價值相輔相成,這是自從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政府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特別是西方更不曾出現過。因此,中國穩定、持久的社會政治體系與躁動不安的西方相比,后者更依賴于自由行動與個人責任;而前者更依賴于集體,每一個人都要為其他人的錯誤承擔責任。”西方傳統體現了人類在法律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華夏國家與之相反,一開始就是等級式的人際關系,但是“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所有這些不平等都被導入一個總體上和諧的有機社會”。①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古代的王權和帝國》第一卷,馬百亮、王震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289頁確實,在這樣一個等級構成的和諧社會里,“國家”只是“家庭的國家”即家庭的放大,從來不存在西方式的對立性的國家—社會關系,因為“國”和“家”從來是一體化的。用李澤厚先生的話說,中國文化是相對于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關系主義”,而這種“關系主義”是建立在家庭本位之上,國家是家庭的放大版。因此,正如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美國教授所言:“在西方傳統中,獨立自主的個人占據著重要位置。要在中國傳統范圍內尋找這種西方知識分子所推崇的主導思想,將是徒勞的。更重要的是,表述這些思想成分的價值觀、行為以及制度在中國傳統中不存在。”②郝大偉、安樂哲:《先賢的民主: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何剛強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25頁。他們還深刻地指出:“政治與經濟同是文化的表述,它們的效能必須與其他的文化價值觀一起來評估。而且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們認為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和以權利為基礎的民主以及自由企業資本主義,都是西方現代性歷史發展的具體產物。因此,任何試圖將這些東西在各文化中普遍化的做法都可能是愚不可及的。”③郝大偉、安樂哲,《先賢的民主: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第16—17頁。
中國“人”和西方“人”存在本體論屬性的差異,但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基于“理性人”假設的政治學方法論卻是中國人學習的教材。以理性選擇主義方法論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必然把中國變成一個人面獅身的怪物。中國政治學必須尋求自己的出路,建構自己的研究方法。
五、探索中國史的理論性:歷史政治學
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并不是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這是由政治學知識論原理決定的。相較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更多“客觀規律”的研究,比如經濟學研究的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最大化、社會學研究的現代性分工,政治學研究的是更加具有主觀性、民族性、國家性的政治文明、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一個并非絕對知識的觀察是,近代以來,二流國家可能提供一流的經濟學、社會學知識產品,比如經濟學上從凱恩斯主義到奧地利學派,社會學上從涂爾干的分工論到法國學者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而從中國政治學學科史的角度上,每個時代流行的政治學知識產品都是那個時代最強國家提供的,晚清—民國時期的政治學來自歐陸(那時美國雖然是世界第一強國了,但孤立主義傳統使得歐陸國家在世界政治中仍扮演主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取消了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政治學,這無疑是來自最強國家蘇聯的學問;改革開放之后恢復政治學和世界政治研究,世界政治研究最終演變為美式國際關系學,可見美國對中國影響有多大。中國政治學學科史告訴我們,相對于經濟學和社會學,政治學的“國家性”屬性更加強烈。這也是為什么政治學在建設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走在前列,我們提出的歷史政治學必然使中國社會科學具有“歷史+N”的影響,比如有學者已經用“歷史行政學”或“歷史公共管理學”。①楊立華:《歷史行政學或歷史公共管理學及其他:國家治理研究的歷史之鏡》,《中國行政管理》2022年第6期。
我們相信,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出路在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和中國歷史文明相結合。從革命、建設到今天的“中國之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結合的產物,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明相結合的研究只是在政治學領域開啟,尚未在社會科學所有學科有著方法論意義上的展開,或者說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是“歷史+N”的結果。我們的自信源自本文前述的社會科學知識論原理,從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這樣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到“民主”這等作為知識體系基石的概念、再到研究知識體系和概念的方法論,都是歷史演變的產物,都具有歷史性,只不過以普遍主義代替民族主義的面目而進行“非歷史性”傳播。
我們認為,只有當一個國家擁有自己的政治學方法論,以國別命名的政治學,比如“中國政治學”而非“中國的政治學”才能成立。“中國政治學”是立足于自己方法論的政治學,而沒有自己方法論的“中國的政治學”則主要是把中國當做是外來理論的試驗場,研究議程和研究方法大多數是外來的,常見的就是以某個概念來分析中國政治,比如“合法性”“治理”“普世價值”等等。沒有自己方法論的政治學必然是不受歡迎的,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政治學”與中國本身一直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緊張關系,根源就在于沒有“中國政治學”。
在中國政治學學科史上,田野政治學和歷史政治學的誕生意味著“中國政治學”嶄露頭角。田野調查雖然是一種世界性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在中國學術史政治史上也并不新鮮,比如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流行的社會調查。但在中國政治學學科語境中,田野調查的意義在于第一次將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從“高政治”研究降沉到“低政治”研究,村民自治、基層民主成為政治學研究議題。再者,我認為,田野調查的意義并不局限于理解當下中國,還在于通過觀察當下基層中國而發現了“歷史中國”,比如徐勇教授提出的“家戶制”“祖賦人權”“關系疊加”等概念,能夠深入理解現實中國和歷史中國。②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徐勇:《祖賦人權:源于血緣理性的本體建構原則》,《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徐勇:《中國的國家成長“早熟論”辨析——以關系疊加為視角》,《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因此,田野政治學與歷史政治學可謂異曲同工,田野政治學通過觀察當下中國而發現歷史中國,歷史政治學通過研究歷史中國而發現當下中國。
中國政治生活中的諸多重大現實政治和政治理論問題,如果用非歷史性的知識體系、概念或方法論去解釋,根本解釋不通,甚至必然會得出否定性結論。比如作為中國根本政治制度即政體的民主集中制,必然會被以個體為中心的代議制政體理論所否定;再比如,中國有民主嗎?這樣的根本制度和重大理論問題也必然會被以社會為中心的“選舉式民主”所否定;還比如,如何看待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問題,以“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標準去看,又必然得出否定性結論;在國際問題上,習慣于國家之間戰爭狀態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必然不相信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凡此種種,都需要新方法、新范式去研究和回答。
歷史政治學適時誕生了。歷史政治學探尋重大現實政治和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和時間性因果關系,旨在發現理論和概念。比如,亟需探討的民主集中制政體、協商民主、政治合法性、人類文明新形態,等等。顯然,歷史政治學研究歷史但并不同于歷史學,歷史學更多關注的是歷史事件的史料發掘,比拼的是史料;歷史政治學是通過研究政治史的事件或者演變方向而提煉概念、發現理論。并非沒有根據地說,雖然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在世界上成就輝煌,但中國歷史的世界性影響的擴大,非得通過歷史政治學發現的歷史政治理論不可,因為概念、理論是知識的路線圖,可以大大簡單化人們對包括歷史在內的知識的理解,對非歷史學術界而更多的是居于社會科學學界的學人而言,他們關心的并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基于歷史的歷史政治理論。試想,西方如果沒有從馬克思、韋伯到二戰后那些群星璀璨的歷史社會學學者而發現的歷史政治理論或歷史社會理論,西方歷史或者西方政治的影響怎么可能影響如此巨大?至少,一部分歷史學者應該有宏大的政治關懷,而不是把宏大的才華安放于博物館。對于有政治關懷的歷史學家而言,歷史政治學是一種重要路徑和方法。
那么,到底如何認識歷史政治學的知識論原理?有幾個概念對于歷史政治學很重要。首先,歷史本體論即歷史屬性。我們都知道歷史很重要,但前提是我們得清楚我們心目中的歷史是什么屬性的。布羅代爾說歷史有兩個面向,一個社會面向,一個政治面向。①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不同屬性的歷史所演繹的制度變遷方式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理論,很可能具有天壤之別。在布羅代爾看來,歐洲歷史主要是社會史,而中國眾多史家都認為中國歷史以政治史、國家史為主。呂思勉有論,“以變態論,自秦以后,分裂之時,亦不為少。然以常理論,則自秦以后,確當謂之統一之國,以分裂之時,國民無不望其統一;而凡分裂之時,必直變亂之際,至統一則安定也”。②呂思勉:《中國社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7頁。嚴耕望指出,“中國史學傳統,特重政治。一部《廿五史》大半為政治史。政治史包括政事與政制,政制即為政事演變之結晶”。③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頁。歷史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政治”這個最根本的概念、也是政治學知識的出發點的認識和理解的天壤之別乃至南轅北轍。
其次,歷史連續性。“軸心文明”是怎么來的,那是人類學的大課題。我們能看到的是,事件發生越早的歷史,成為約束人們思維和行為的可能性越大,“軸心文明”的影響力更是如此。尤其是在以國家史為主流的中國,相對夷族而言,中原的文化體系制度體系實在過于發達、過于優越,因此即使雄踞中原,也要自我儒家化;即使在中原紛爭時代,人們思考的還是何時一統。社會史和政治史都產生路徑依賴,但以國家為核心的政治史的路徑依賴程度更強更大。
理解歷史連續性,少不了時間序列、時間性等概念,也就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先后以及制度變遷中的歷史關鍵點。“政治中的時間”是歷史制度主義方法論的貢獻。
再次,時間空間化。在路徑依賴中,連續性制度變遷最終導致歷史空間化即時間空間化,也就是常說的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提出的“中國基體論”就是一種歷史空間化的概念,即當下中國是幾百年來乃至千年來歷史中國的展開。④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11頁。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的“中華文明基體論”所包括的種族、文字、疆域的穩定性、大一統國家、民本政治社會體制、仁愛的社會關系以及對外的“公家秩序”(天下為公、天下一家),是幾千年中國歷史的當代化典型。
在理解歷史政治學的幾個關鍵詞的基礎上,基于知識論的比較歷史分析,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歷史政治學的知識論原理或者說知識路線圖:認識歷史本體論—研究制度變遷方式—發現歷史政治理論。
關于歷史本體論的重要性,前面已經有簡單敘述。重點是,作為事情起點的歷史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制度變遷方式的不同。政治史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是大一統以及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大一統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社會史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是“多統”或者地方自治為主的“城邦”政治,到近代演變為分權制衡的代議制。
制度變遷方式的差異性,強化著歷史屬性并由此演繹出不同屬性的政治理論。基于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的制度變遷的歷史敘事必然是天下秩序和致治政治,因此政治原理產生于“儒官”之手,將其實踐經驗轉化為“原理”,正如錢穆先生概括:“治亂興亡,多載實際政務,政治思想政治理論皆本實際政治來。此與經學無大異。故中國經史之學,可謂即中國之政治學。”①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87頁。講究秩序和致治的經史之學必然以“公益”為主旨。基于多統—代議制的制度變遷的歷史敘事必然是地方權力和個人權利,這樣的政治學必然是以“私利”為要害。
“政治”產生的歷史基礎的差異性有天壤之別,人們對“政治”的認識必然不同,關于政治生活的政治學原理也必然各具形態各具特色。歷史政治學賦予我們關于“政治”的新思維,也激發著我們重構政治學原理的沖動。不但如此,歷史政治學所揭示的歷史屬性所演繹的關于“政治”的文明差異性及其在全球化時代的呈現特征,更讓我們對中華文明多了一份自信,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斷言:“希臘模式廣泛適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階段,中國模式則廣泛適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階段。”②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頁。因為以歐洲為代表的“各文明史的晚后階段”開始有進入有了國家的政治史,而中國幾乎一開始就是政治史屬性的大型文明體。與此前的產生于歷史并不久遠的國家的歷史政治理論,幾千年連續性政治史的中國更是產生政治理論的富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