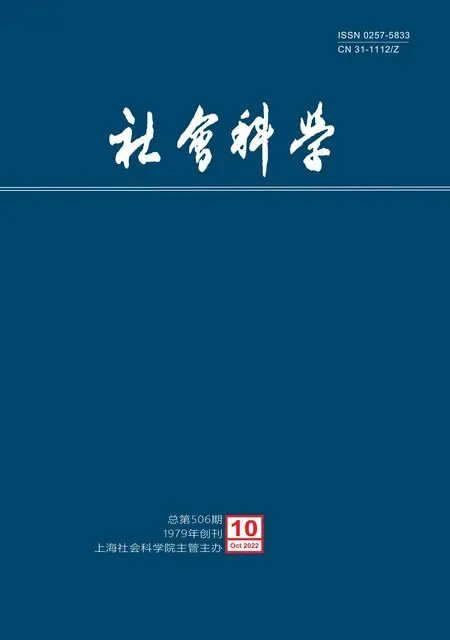從下第舉人到乙榜進士:元代科舉副榜制度的形成、實踐及影響
耿 勇
傳統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之所以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無疑是因其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打破了門資、血緣、私人關系對于仕途的壟斷,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國的官僚結構、政治生態、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形態。因此,從柯睿格(Edard A.Kracke)、何炳棣開始,科舉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關系日漸成為研究的熱點。雖然相關研究從多種角度探討科舉制度的創立、調整和具體運作在兩宋以降中國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其對于社會流動性的討論均立足于對科舉成功者的家庭背景、應試經歷、仕途發展的分析之上。①從科舉制度的運行討論傳統中國后期社會流動性的代表性觀點,參見Edward Kracke, “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7, 10(2), pp.103-123;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Elman Benjamin, “Political,Social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1, 50(1), pp.7-28; Qin Jiang, James Kai-sing Kung, “Social Mobil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Hypothesis”,Modern China, 2020, 47(5), pp.628-661; 徐泓:《明代向上社會流動再探》,《歷史人類學學刊》2017年第1期。換言之,在這些研究看來,各級科舉考試成功者的身份轉換與仕宦經歷等同于社會流動的全部。而實際上,通過科舉考試獲取任官資格、將知識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的情況,并非僅局限于在整個考生群體中占比極低的中式者,一部分落榜士子同樣可以通過科舉體制當中某些特殊的安排,獲得邁入仕途的機會。
這種制度安排最早出現在北宋,此后歷代王朝也都設法在科舉體系內部為一部分正榜定額無法容納的考生創設特殊的功名及相應的授官制度,盡可能將其吸納進官僚體系,充實基層行政力量。具體而言,兩宋時期是以“舉數”和“年甲”為衡量標準的特奏名制度,此后則主要是在鄉試、會試層面增錄副榜。而從特奏名到副榜的轉變,則是在元代完成的。
元代副榜制度的推行,意味著一部分原本應該被歸入落第之列的士子,雖然沒有參加更高一個層級考試的機會,但中選者亦可獲得任官資格。科舉體系中一個介于中式者和下第者之間的群體就此出現,副榜亦成為整個科舉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補充部分。
目前,有關宋代特奏名、明清副榜的研究已有不少,①有關宋代特奏名、明清副榜、清代中正榜、明通榜的研究,參見張希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544頁;郭培貴:《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0—291頁;丁星淵:《明代鄉試副榜及其成效研究》,《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李世榆、胡平:《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84—709頁;王學深:《乾隆朝“中正榜”探研》,《歷史檔案》2019年第4期。但是對于副榜制度在元代的創設及實踐的討論并不充分。②目前學界對于元代科舉的研究,多集中在進士層面,有關科舉副榜的討論,多是在分析元代整體科舉考試的制度性規定時附帶論及,所述較為簡略。相關討論,參見陳高華、宋德金、張希清主編:《中國考試通史(宋遼金元卷)》,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3—374頁;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第26—27頁;韓岑:《元代落第士子初探》,浙江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30—32頁;吳志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元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34、539—541頁;申萬里:《元代科舉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9—160頁。這不僅影響到我們深入認識傳統中國科舉副榜制度的演進和社會流動性等議題,也阻礙了我們對于元代在中國科舉史上歷史地位的理解。基于此,本文將從會試下第舉人“恩例”的演變、鄉試副榜、會試副榜三個方面,討論副榜在元代科舉體制中的形成過程、具體實踐及其社會價值與歷史意義。
一、特奏名因素的消退與會試下第舉人“恩例”的制度化
科舉考試制度雖肇始于隋唐,但當時所取之士較少,進士科每年所取少則幾人,多則不過二三十人,并非是官員出仕的主要途徑。至宋,錄取額數大幅度提升,科舉考試成為國家選拔官員最為重要的渠道,“上自中書門下為宰相,下至縣邑為簿尉,其間臺省郡府公卿大夫……皆上之所取貢舉人也”。③柳開著,李可風點校:《柳開集》卷8《與許景宗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17頁。然而,宋代的國家規模與官僚體系的容納能力,限制了進士貢額的增加幅度,絕大多數投身舉業的考生都難逃下第而歸的命運。面對數量日益膨脹的考生群體,宋初創設了專門針對省試、殿試落第舉子的特奏名制度,用以安置一部分累試不第的考生,籠絡士人階層。開寶三年(970),宋廷開始于貢舉正奏名之外,另立特奏名,規定“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后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赴試”。④脫脫:《宋史》卷155《選舉志一·科目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609頁。此后,特奏名制度雖屢有調整,但始終以應試舉子的“舉數”和“年甲”為標準,而非基于單一科次的答卷優劣和排名;理論上,任何一位累試不第的士子,只要其參加省試或殿試的次數、年齡符合官方所定標準,經當地州縣官員勘會奏聞之后,即可獲得禮部特奏名。⑤例如,南宋紹興間規定,“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并年四十以上;進士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并年五十以上者,許特奏名”(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選舉》4之20,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4300頁)。盡管特奏名的待遇及仕途發展難以企及正奏名,但畢竟為相當數量累試不第的士子提供了一個步入官場的渠道,使之得以獲任試將作監主簿、國子四門助教、州長史、文學、助教等低階散官。⑥有關兩宋特奏名進士的賜第及出官情況,參見張希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第530—538頁。
宋元更替,科舉一度停擺。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經過近四十年的激烈爭論,元代統治者決定恢復科舉考試。⑦元在滅宋之后,就是否在漢地采行科舉取士制度有長時間的爭論。爭論的過程、停廢科舉的具體原因和社會背景,參見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19—269頁;吳志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元代卷)》,第443—455頁。元代科舉雖然在很多方面襲自兩宋科舉,但也有創新和發展。至正三年(1343)之前,元代專門針對會試落第舉人的“恩例”大體上繼承了兩宋特奏名制度,年齡和參加會試的次數依舊是取舍的標準。但至正三年之后,針對會試落第士子的“恩例”便逐步擺脫了兩宋特奏名制度的影響,由面向歷科下第士子且以“舉數”和“年甲”為準,轉變為僅限于參加當科會試的下第士子,且以“終場”為據。
延祐元年(1314)八月,十一行省、兩宣慰司和四直隸省部路分按照中書省頒布的《科舉條制》,首開鄉試,次年二、三月間,經會試、殿試后,“賜護都沓兒、張起嚴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①宋濂:《元史》卷25《仁宗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568頁。進士發榜后,丞相怗木迭兒、阿散、平章李孟等人奏準:
(會試)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于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②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科目》,第2026—2027頁。
因為這是元朝首次開科取士,且距離南宋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已達四十年之久,參加會試的舉子并無累積“舉數”的可能,故延祐二年(1315)針對會試下第舉人的“恩例”,僅以年齡和是否有出身為等差。③根據皇慶二年中書省頒布的《科舉條制》,允許兩類已有出身者參加科舉考試,一是流官子孫以恩蔭出身者,“愿試中選者,優升一等”;二是在官未入流品之人,“若中選,已有九品以上資級,比附一高,加一等注授。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優詮注”(《元典章》卷31《禮部四·學校一·儒學·科舉條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097頁)。泰定元年(1324),因“推龍飛恩”,中書省再次頒布針對會試下第舉人的“恩例”:
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以上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先有資品者,更優加之。不愿仕者,令備國子員。④袁桷撰,王珽點校:《清容居士集》卷23《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28頁;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科目》,第2027頁。
在泰定元年之前,延祐二年、延祐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已舉行過三科會試,故而該年所頒布的“恩例”對于“舉數”有了要求,得選教授者除年齡要達到相應的規定外,還必須具備至少參加兩次會試的經歷。這與兩宋特奏名制度非常相似,但最大的差異是“恩例”的對象僅限于泰定元年會試的下第舉人,此前三科會試中符合“舉數”和“年甲”條件的下第舉人則被排除在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延祐開科之后針對會試下第舉人的“恩例”,并不是適用于每一科會試的制度化措施,而是一項時有時無、并不連續的臨時性舉措。延祐二年會試舉行之前,元廷事先并無選取會試終場下第舉人出任教官的打算,然而作為復行科舉之后的首次會試,“試者銳于一得,既而被黜者嘩言不公,至作歌詩譏詆主司”,為安撫下第舉人的不滿情緒,才于殿試結束后匆忙頒布針對下第舉人的“恩例”,“凡與計偕者授以校官有差”,但同時強調這一政策只是針對該科會試舉人的特例,“后舉不為例”。⑤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14《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28頁;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科目》,第2027頁。延祐五年會試結束后,元廷未曾頒布恩賞會試終場下第舉人出任教官一事,可從現存元代文獻中得到進一步證明。據吳澄(1249—1333)文集所載,江西上饒士子邵憲祖,“中延祐四年鄉貢,次年會試于京師,未能成進士,退歸”,無法比照延祐二年會試終場下第舉人“恩例”,獲得出任教授、山長、學正等教職的機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6《送邵文度仕廣東憲府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308頁)。因此該科之后,“自余下第之士,恩例不可常得”,間或頒布,即被視為“特恩”。⑥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科目》,第2026頁;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4《送鄉貢進士董方達赴吏部選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第265頁。例如,延祐五年會試前,集賢修撰虞集(1272—1348)鑒于“天下學官猥以資敘,強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亦弗信之,于學校無益”的狀況,奏請改革教官選任舊法,“取鄉貢之退者,其議論文藝猶賢于泛泛莫知根柢者”,但終因“朝臣韙其論而憚改作”,該科會試下第舉人沒有獲得出任學官的機會,黯然而歸。⑦歐陽玄著,湯銳校點:《圭齋文集》卷9《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歐陽玄全集》上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21—222頁。此后泰定元年、(后)至元六年(1340)兩科會試,一再強調授予終場下第舉人教職的“恩例”,“后勿為格”,“今后下第舉人止聽再試,不許教官、書吏內取用”。⑧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都省奏準科舉條畫》,日本靜嘉堂文庫藏至正元年建安務本堂刊本,第14b頁。
會試下第舉人“恩例”對于參加會試次數和年齡的相關要求,后來被下第士子在考試中的表現所取代。至正三年(1343),經監察御史成遵(1308—1359)奏請,元廷在殿試舉行的前一日,調整了有關會試下第舉人“恩例”的規定:
腹里、行省山長、學正,擬至正二年為始,于終場下第舉人內注充,須歷兩考,五十以上,止歷一考,依例升轉。國子生員不愿者,許聽再試。①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終場舉人充教官》,第17b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1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3頁。
較之延祐二年和泰定元年,此次頒行的“恩例”政策有兩方面變化:一是降低了符合條件的下第舉人所授學官的級別。此前達到相應規定的下第舉人可被授予正九品的教授一職,而自此以后,會試下第舉人僅被授予不入流品的山長、學正兩職,而且還要經歷一考或兩考之后,才可依例升轉;二是取消了此前對于“舉數”和“年甲”的要求,會試下第舉人只要達到“終場”這一條件,即可獲授山長、學正的職務。而所謂“終場”,是指參加會試的考生盡管未能中式,但能夠按照科場要求順利完成全部場次的考試。結合延祐元年《科舉程式》、(后)至元六年《都省奏準科舉條劃》相關內容,元代科舉“終場”應該符合四個要件:②(后)至元六年再次恢復科舉之后,雖然發布了《都省奏準科舉條劃》,但“鄉、會試應行事理,并依元降詔書、奏準條格,即節次省部頒行各事例施行”,科舉考試的具體運作過程未有變化(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都省奏準科舉條畫》,第16a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1輯,第161頁)。其一,右榜的蒙古、色目人全程參加第一、二場考試,并呈交《四書》、本經、時務策問答卷;左榜漢人、南人全程參加第一、二、三場考試,并呈交《四書》、本經、古賦、詔誥章表、經史時務策問答卷;其二,赴考舉人應該嚴格遵循考試時間,“就試之日,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③《元典章》卷31《禮部四·學校一·儒學·科舉程序條目》,第1102頁。交卷時間不能超過黃昏,逾時不獲彌封、謄錄;其三,是對策字數應達下限,左榜漢人、南人第三場經史時務策答卷“限一千字以上成”,右榜蒙古、色目人第二場時務策答卷“限五百字以上成”;④《元典章》卷31《禮部四·學校一·儒學·科舉程序條目》,第1099頁。其四,答卷不能出現“不考格”的錯誤,即試卷文字不能存在“犯御名、廟諱——偏犯者非,及文理紕繆,涂注乙五十字以上”⑤《元典章》卷31《禮部四·學校一·儒學·科舉程序條目》,第1101頁。延祐元年決定舉行科舉之時,中書省就下發了有關御名、廟諱的注意事項,此后坊間刊刻的日用類書中也不斷增補這一方面的內容,供考生應試之用。關于元代考生在應試過程中需要避諱的御名、廟號,參見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1輯,第166—168頁。的情況。至此,元代針對會試下第舉人“恩例”之中存留的兩宋特奏名因素已經完全去除,標準從“舉數”“年甲”轉為“終場”;全程參加會試各場考試,按時上呈答卷,且文字沒有出現觸犯御名、廟諱、涂改過多以及“文理紕繆”等過錯的當科下第舉人,可以獲得出任各路府、州書院山長、儒學學正等職的資格。
二、基層教官選任體制的變革與鄉試副榜的推行
對于元代后期科舉下第者而言,至正三年成遵奏請的意義,不僅體現在會試終場下第舉人出任山長、學正成為一項制度化的規定,更重要的是其同時力推鄉試增錄副榜擔任路學學錄、縣學教諭,將與學校教育無關的直學排除出儒學教官的晉升渠道,拓寬了儒士入仕的途徑。元代地方儒學,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與上、中州各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較之教授、學正、山長,縣學教諭雖職級稍遜,但在整個儒學教官體系中占比最大,有千余人之多。然而在至正三年之前,路、府、州、縣儒學以及書院中的直學基本上壟斷了縣學教諭、路學學錄的職缺。直學雖屬地方儒學中的員缺,但主要職責是“掌管學庫、田產、屋宇、書籍、祭器、一切文簿”,⑥不著撰人,王珽點校:《廟學典禮》卷2《學官職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頁。與教育關系不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方官學中“司錢谷而躬其會計出納之勞”的直學,以“三十月為滿”,經本地文資正官、教官出題考校,并行移集賢院考校之后,即可正式升轉路學學錄、縣學教諭兩職。⑦宋禧:《庸庵集》卷11《送蘇生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2頁;《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教官·正錄教諭直學》,第309頁。元代基層教官隊伍選任制度中“以直學為之基”⑧李存:《俟庵集》卷19《贈李叔陽之延平儒學學錄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3冊,第715頁。的做法,使得當時原本以培育人才為主責的教官,反而“以將迎為勤,以會計為能,而怠于教事”,①程鉅夫著,張文澎校點:《程鉅夫集》卷15《代白云山人送李耀州歸白兆山建長庚書院序》,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76頁。出現“知通會計,烏能知教”②吳海:《聞過齋集》卷1《贈閩縣學教諭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b頁。的局面。
“科舉、學校之制,相為表里者”,③吳師道著,邱居里、邢新歡點校:《吳師道集》卷15《贈姚學正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8頁。在元代科舉停廢期間,儒學教職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借徑以階仕進”④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7《贈紹興路和靖書院吳季淵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第314頁。的工具,其中存在的問題尚未引起特別的注意。但是,隨著科舉本身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改革“以直學為之基”的基層教官選任制度,日漸進入支持科舉的政治人物的視野之中。至正三年,成遵在奏請制度化會試終場下第舉人“恩例”的同時,建議鄉試增取副榜,“今后學錄、教諭,亦合于每舉鄉試下第舉人遴選文辭通暢、義理詳貫者,取用少者,從實申達省部,以憑類選”。⑤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終場舉人充教官》,第17b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2輯,第163頁。在奏疏中,成遵從直學多出身于胥吏及富豪子弟而無法勝任育才之職的角度,解釋遴選一部分符合資質的鄉試下第舉人出任路學學錄、縣學教諭的合理性:
學校乃育才之地,教官當遴選其人。蓋師儒所以講經籍,范后進,茍所任不職,則學校何由可興,人材何自而出,風俗教化實源于此。今諸處教官多由直學升轉,直學本為典司金谷而設,皆吏胥、富豪子弟夤緣為之。試補之際,無非假手請托,通經學古,百無一二。致學校廢弛,人才不振。⑥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終場舉人充教官》,第17a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2輯,第163頁。
自延祐復行科舉,反對科舉的政治勢力持續指責開科之后“儒者之效不彰”,⑦虞集:《道園類稿》卷47《黃縣尹墓志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406頁。甚至科舉的支持者們也不得不承認科舉所取之士“內而才學名者可數也,外而政治聞者可數也”,⑧許有壬:《至正集》卷32《送馮照磨序》,《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5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65頁。之前對于科舉的期待大打折扣。為了回應反對勢力對于科舉效用的質疑,支持科舉的一方試圖通過改革與科舉互為表里的基層教官選任制度來提升人才培育的水平,使科舉所取之士盡量符合政治的需要與社會的期待。成遵建議鄉試增取副榜,選用具備一定儒學素養并受過舉業訓練的鄉試下第舉人擔任基層縣學教諭、路學學錄,代替此前為“吏胥、富豪子弟”所壟斷的直學,正是在這一歷史脈絡下展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據黃溍、歐陽玄記載,成遵提出“鄉舉放次榜以充教諭、學錄”的建議之后,朝廷曾經咨詢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的意見,后者“力贊成之”。⑨歐陽玄著,湯銳校點:《圭齋文集》卷10《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銘》,《歐陽玄全集》上冊,第301頁;黃溍著,王珽點校:《黃溍集》卷31《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40頁。盡管囿于文獻記載的缺失,現在尚不明確揭傒斯支持在鄉試中增取副榜取代直學升轉教諭、學錄的具體理由,但其對直學的批評態度則有跡可循。揭傒斯曾不止一次批評當時科舉所取非人,主要是由于“學無賢師”,⑩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送劉旌德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9頁。直學出身的“職教之徒”大多“臃腫腆?,孳孳焉規錙銖,計升斗是急”,?? 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第332頁。? 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終場舉人充教官》,第17b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2輯,第163頁。? 虞集:《道園類稿》卷26《江西貢院題名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第9頁。背離了培育人才的本職。
至正三年三月,在揭傒斯的推動下,元廷正式批準成遵的建議,規定自下科鄉試開始增取副榜,中選者可以出任縣學教諭、路學學錄,而“直學人員在路學者,許充路吏;在州學、書院者,許充州吏。俱歷三十月,挨次收補”。?? 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第332頁。? 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終場舉人充教官》,第17b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2輯,第163頁。? 虞集:《道園類稿》卷26《江西貢院題名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第9頁。次年八月為鄉試之期,各地鄉試考官于原設貢額之外“以新制取次榜”“留省以備學官之任”。?? 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第332頁。? 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終場舉人充教官》,第17b頁;陳高華:《元代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2輯,第163頁。? 虞集:《道園類稿》卷26《江西貢院題名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第9頁。至于當時官方對于各地鄉試錄取副榜的具體規定,因為《終場舉人充教官》這份重要文書殘缺不全,現今已不可考知。但從現存元代相關文獻的記載來看,至正三年以后各地鄉試取錄副榜大體具備以下三方面特征:①此前對于元代鄉試錄取過程的研究,多集中在正榜的錄取過程與標準。有關這一方面問題的討論,詳參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清華元史》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19—176頁;申萬里:《元代科舉新探》,第140—154頁。
一是較之會試下第舉人“恩例”僅以“終場”為準,鄉試副榜的錄取更加注重士子在考試中的表現,以答卷質量為取舍依據。如前文所述,成遵于至正三年建議擇取鄉試下第者任教官時,條件之一即是取中者的文字能夠做到“文辭通暢、義理詳貫”,答卷的文學水平與義理闡發都要達到相當的水準。至正二十二年(1362)山東濟南路宣慰司鄉試取中五名副榜,入選標準即為“文理通貫”。②胡德琳:《(乾隆)歷城縣志》卷24《山東鄉試題名碑記(至正二十二年)》,《續修四庫全書》第6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5頁。鄉試副榜制度創立伊始雖將“文辭通暢、義理詳貫”定為中選標準,但只是劃定了一個大致原則,較為籠統,并沒有詳細給出各地鄉試在運作過程中如何甄選符合副榜錄取標準之士的具體辦法。③較之鄉試,元代會試評閱試卷等第的規定較為清楚。會試各場次考試結束后,“知貢舉居中,試官相對向坐,公同考校,分作三等,逐等又分上中下,用墨筆批點。考校既定,收掌試卷官于號薄內標寫分數”,即將各類別試卷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并綜合各場次成績,決定最終中式人選、排名(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科目》,第2025頁)。姚大力先生根據《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收錄之各地鄉試中式舉人名次、考官評語,梳理出元代鄉試評閱試卷與決定中式人選的過程:考試結束后,負責評閱第一場五經義和第二、三場古賦、擬詔、擬誥、章表、對策的初考官,各按每個義項舉薦兩三份試卷,覆考官對其加以確認,或進行為數不多的調整,形成備選的“薦卷”,最終主考官遵循“通場考校”的原則,衡量三個場次的成績,確定最終的中式名單和具體排名。④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札記》,《清華元史》第2輯,第167頁。進入備選名單的“薦卷”數量大多超過鄉試解額,因而在最后一道程序被主考官所黜的“薦卷”所在多有,以“文辭通暢、義理詳貫”為準的鄉試副榜,極有可能選自這一部分落選的“薦卷”。
二是鄉試副榜與正榜一樣也分左、右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或南人為左榜。至正十一年(1351),義烏縣學教諭沈文衡在回顧延祐以來教官選任制度演變時,明確指出各地鄉試在正額之外“置左右副榜”:
延祐甲寅,(縣學教諭)例以學院直學為之。天歷以來,又用御史議,舉茂才之經明行修可為師表之任,察憲體試官亦用之。既而言司又謂直學乃會計之職,茂才非教諭之科,其以直學為吏,而止茂才之例,由是朝議于各省鄉貢進士名額之別,置左右副榜以羅致天下。浙省三歲一舉,正榜之士四十,俾與計吏,偕試春官;副榜之士二十有五,則以浙右、江左教諭、學錄處之。⑤熊人霖:《(崇禎)義烏縣志》卷9《碑銘·學官題名記》,《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17冊,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494頁。
這一點,可以從至正四年江西鄉試中得到進一步證明。據該科鄉試糊名官、休寧縣主簿楊翮記載,此次江西鄉試共錄取副榜二十五名,其中左榜十六名,右榜九名:
江西行省遵用詔書故事,合所部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人大試而賓興之,舉三歲之典也。……八月甲戌,二府復大會作樂,以宴考官暨于列職。……九月辛丑拆名,黎明榜出,龍興路官屬導以鼓吹儀仗,揭之省門之外。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人,合三十又一人。貢額之外,又二十五人焉,右九而左十六也。蓋三十又一者,貢額之舊,而二十又五,則昉自今始。⑥楊翮:《佩玉齋類稿》卷8《江西鄉試小錄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0冊,第114頁。關于至正四年江西鄉試取中副榜的人數,虞集的記載與此不同。據《道園類稿》卷26《江西貢院題名記》載,至正四年江西鄉試,“得右榜九人,左榜廿二人。又以新制取次榜,右生六人,左生十有二人,留省以備學官之任”(虞集:《道園類稿》卷26《江西貢院題名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第9頁)。對此,蕭啟慶認為“兩者必有一誤”。楊翮、虞集同為元代后期著名學者,二人對此記載存在差異之原因,雖尚待進一步考證,但考慮到《江西鄉試小錄》為該年鄉試舉行之后由官方編集刊行,且楊翮為該科江西鄉試負責糊名的外簾官,可信度較高,本文姑以之為準。
因為江西鄉試左榜本無漢人名額,故而該科左榜中的十六名鄉試副榜全屬南人;右榜中的蒙古、色目鄉試副榜共九人,至于二者名額如何分配,尚不清楚。
三是鄉試副榜雖有一定的額數,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主其事者未必足額錄取,這一點如同正榜。關于鄉試副榜的正式定額,盡管現存元代官方文獻中并無記載,然而至正三年頒布增取鄉試副榜之時,既已經對應取額數有明確之規定。《佩玉齋類稿》載:
至正元年,復鄉舉里選之制。明年大比天下多士,春官上其名,天子親策焉,第其等而官之。又明年,用監察御史言,取貢士下第于春官者,用之為校官。復以貢額未廣而天下之材或遺也,始自今更定名數于貢額之外,取以補校官之未等,秩視下第者益讓焉,著為令。于是南士之額在江浙省與貢者廿有八人,而以遺才取者又十有六人。①楊翮:《佩玉齋類稿》卷5《送屠彥德教諭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0冊,第96—97頁。
結合前引沈文衡《學官題名記》中的相關記載,可以看出至正三年元廷決定于原有鄉試貢額以外另錄副榜之初,就正式確定了各地鄉試副榜的人數,不僅“定名數”,而且“著為令”;而江浙行省鄉試副榜總額為二十五人,左榜南人額數為十六人,右榜蒙古、色目額數為九人。至正十年,翰林國史院典籍毛元慶被聘為山東濟南路宣慰司鄉試考試官,談及是科所取之士,亦指出:
(山東鄉試)粵自九月二日揭榜,得士蒙古四人、色目五人、漢人七人以充賦,而備選者十有五人,從定額也。②胡德琳:《(乾隆)歷城縣志》卷24《山東鄉試題名碑記(至正十年十月)》,《續修四庫全書》第694冊,第449頁。
該年濟南路宣慰司正榜共取十六名,其中右榜蒙古、色目九人,左榜漢人七人,完全符合延祐元年《科舉程式》中對于濟南路宣慰司鄉試區域及族群配額的規定,毫無疑問是遵從定額。而副榜錄取十五人,亦言“從定額”,足見至正間副榜有明確之定額,濟南路宣慰司鄉試副榜額取十五名。
元代鄉試正榜有明確的定額,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所取往往不及額數。鄉試副榜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前引楊翮所記,至正四年江浙鄉試副榜南人額數為十六名,而在至正十八年(1358)的浙江鄉試中,“選中左右兩榜凡三十有六人,備榜十有五人”。③楊維楨著,鄒志方點校:《東維子文集》卷5《鄉闈紀錄序》,《楊維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75頁。該年所錄蒙古、色目、南人副榜僅十五名,尚不及額定副榜南人中選之數。又如至正十年(1350)山東濟南路宣慰司鄉試,正榜取中蒙古、色目、漢人十六名,副榜依照此前的規定,足額錄取“備選者十有五人”。④胡德琳:《(乾隆)歷城縣志》卷24《山東鄉試題名碑記(至正十年十月)》,《續修四庫全書》第694冊,第449頁。而至正二十二年(1362),該地鄉試僅錄“文理通貫充副榜者”五人而已。⑤胡德琳:《(乾隆)歷城縣志》卷24《山東鄉試題名碑記(至正二十二年九月)》,《續修四庫全書》第694冊,第455頁。
較之前代以府、州為單位發解舉人的方式,元代改行大考區制,將全國劃分為十七個鄉試區域,總共錄取三百名合格舉人。這種“昔之舉士選于州,今之舉士選于省”的轉變,使得元代鄉試競爭極其激烈,錄取率很低,出現“省領州數十而登名者不當一州之數,是一州不一人,而于是有連數州不舉者”的情況。⑥程端學:《積齋集》卷3《送李晉仲下第南歸序》,《叢書集成續編》第109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457頁。與此同時,隨著科舉復行,“士亦唯務業科舉”,⑦李祁:《云陽集》卷4《王子嘉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9冊,第668頁。投身舉業的人數越來越多,例如江浙行省,每科鄉試入場者“不下三四千人”。⑧程端禮:《畏齋集》卷3《江浙進士鄉會小錄序》,《叢書集成續編》第109冊,第40頁。鄉試副榜的出現,不僅打破了直學等出身于“吏胥、富豪子弟”者對于儒學教官職缺的壟斷,優化了基層教官結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有限的鄉試解額與日益膨脹的考生群體之間的矛盾,為一部分鄉試下第者進入仕途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
三、元代族群政策與會試副榜
各地于至正四年、至正七年(1347)兩次鄉試取中副榜之后,會試在保留“恩例”的同時,也開始在正額之外增取副榜。至正八年(1348)四月,中書省奏準于會試正榜之外,另在參加會試的國子學積分生中,增取副榜二十人。《元史·百官志八·選舉附錄》載:
(至正八年)四月,中書省奏準,監學生員每歲取及分生員四十人,三年應貢會試者,凡一百二十人。除例取十八人外,今后再取副榜二十人,于內蒙古、色目各四名,前二名充司鑰,下二名充侍儀舍人。漢人取一十二人,前三名充學正、司樂,次四名充學錄、典籍管勾,以下五名充舍人。不愿者,聽其還齋。①宋濂:《元史》卷92《百官志八·選舉附錄·科目》,第2344—2345頁。同書卷41《順帝紀四》載:“(至正八年四月)乙亥,帝幸國子學,賜衍圣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喪、省親等法”,而中書省奏準于參加會試的國子生中增取副榜同樣也在該年四月間,因元順帝臨幸國子學而制定的國子學“弟子員出身”與國子生參加會試及增取副榜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關聯,尚需進一步考證。
至正八年會試和殿試已經分別于二月、三月間相繼舉行完畢,此處所規定“今后再取副榜二十人”,應該從下一科,即至正十一年(1351)會試開始實施。從這一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最后一次舉行會試,其間一共開科六次,如果全部足額錄取,會試增取副榜也不過一百二十名,在取士規模本已很小的元代科舉中所占比例不大。盡管如此,元代會試的副榜制度仍然有一些特別顯著的特點。
從中選會試副榜的資格來看,雖然同為副榜,但較之各地鄉試副榜,元朝官方明顯縮小了副榜制度在會試層面的適用范圍,只有參加會試的一百二十名國子學積分生才具有取中副榜的資格,其余經由鄉試取解參加會試的舉人不在考慮范圍之內。也就是說,副榜制度在會試層面的施行,影響最大的是參加會試的國子學積分生。自至正十一年開始,會試中選的國子生獲得參加殿試的機會,最終成為進士;“文在所取而限于額數者”,②佚名:《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459頁。則被錄為副榜,依照規定獲任相應的職缺;剩余未被正榜和副榜錄取的國子生,則依照至正三年會試終場舉人例,授予山長、學正之職。如劉燾孫,“至元丙子(至元二年,1336),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為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至正八年,1348),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③王袆著,顏慶余點校:《王忠文公集》卷21《劉燾孫傳》,《王袆集》下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28頁。
從會試副榜的族群配額來看,盡管鄉試和會試副榜在錄取過程中都實行優待蒙古、色目的族群配額制,但是,會試副榜對于南人的壓制更為嚴重,因為名義上南人在會試副榜中沒有獨立配額。眾所周知,元代各級科舉考試均基于“四等人制”,將額定錄取數分配給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族群,鄉試副榜亦是如此。但是,前引至正八年中書省有關從國子學積分生中增取副榜的規定,二十名副榜名額只分配給蒙古、色目、漢人,獨缺南人。這一點,極為清楚地體現在兩通存有會試副榜中選者信息的國子學貢試題名碑中。④目前有關至正時期會試副榜,除前揭《元史·百官志八·選舉附錄》所錄中書省奏準條文外,以《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所存之會試副榜中選者信息最為詳細,兩者均為當時負責其事的官員撰寫,并由國子監鐫刻。前者為國子祭酒張翥撰寫,后者之撰者姓名不詳,但蕭啟慶先生認為雖然撰者姓名已佚,“但由記文看來,他應為出身國子學的一位本科考試官”(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458頁)。至正二十年(1360)會試,依制足額錄取了國子生正榜十八名、副榜二十名。時任國子祭酒張翥所撰《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完整保存了該科中選國子生正榜、副榜的名單。副榜名單載于正榜之后,分為蒙古、色目、漢人三類,逐名登錄:
副榜
蒙古
孛羅帖木兒,字□□,□□。
關奴,字親遠,□里吉歹。
定住,字□□,□□兒多。
布巒吉歹,字□□,□烈歹。
色目
□□理,字□□,□□。
同同,字□□,唐兀。
□□,□□□,□□。
法達忽剌,字彥德,賽易。
漢人
余植,字士立,寧州。
蒙大舉,字士高,□安。
□□□,字□□,□□。
李以約,字景升,鄢陵。
王琬,字之文,洛陽。
仇機,字□□,□□。
趙溥,字□□,□□。
張海,字大□,趙州。
□□,□□□,□□。
王宗仁,□□□,□□。
劉興,字□孫,□□。
王升,字□□,□□。①張翥:《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456—457頁。
又如,至正二十六年(1366)會試,正榜取中的國子學積分生,“通二十人”,②宋濂:《元史》卷92《百官志八·選舉附錄》,第2347頁。比定額多出二名。該科副榜錄取人數雖不可考,但《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中“副榜三色”的榜單同樣附于正榜之后,目前尚存六位被會試副榜取中的蒙古、色目國子學積分生的相關信息:
副榜
蒙古
□□□,字符貞,哈兒吉歹。
桂同,字一校,察罕塔兒。
迺蠻臺,字文德,乃蠻氏。
神家奴,字天祐,乃蠻氏。
色目③《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目前共有三個版本存世,分別為“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哈佛燕京學社藏拓本、《宋元科舉題名錄》所收本。三者文字詳略各有不同。蕭啟慶先生以傅圖藏拓本為底本,以后面兩種為參校本,進行點校。對于題名記中的副榜部分,蕭啟慶先生據《宋元科舉題名錄》本,在“冀珍溥化,字天章,□□思氏”后增入“色目、漢人缺”五字。上述五字增入之后,無意間會使讀者以為副榜中從“□□□,字符貞,哈兒吉歹”至“冀珍溥化,字天章,□□思氏”間的六名副榜中選者全部是蒙古人,色目和漢人的名單缺失。實際上,這是《宋元科舉題名錄》的編者在抄錄原碑時,因為不了解元代蒙古、色目族屬名目,將二者混為一談而誤增。根據前文所述,至正八年規定參加會試的國子學積分生中,蒙古得以取中副榜者的名額只有四位,若依照蕭啟慶先生的點校理解,此處所列題名顯然不符合規定。實際上,根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1《氏族》所載蒙古、色目族屬,欽察氏為色目三十一種之一,“□□思氏”應為“蜜赤思氏”,亦屬色目種類,故□帖木兒、冀珍溥化二人均應是出身于色目的會試副榜中選者,殆無疑問。因此,題名中的六名副榜,前四名為蒙古人,后兩名為色目人,“□帖木兒,字仲章,欽察氏”前應缺“色目”二字,應補入。
□帖木兒,字仲章,欽察氏
冀珍溥化,字天章,□□思氏④佚名:《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461頁。
由以上所引兩種題名記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會試在錄取副榜的實際過程中,表面上的確遵行了至正八年中書省的規定,僅以蒙古、色目、漢人三色區分副榜所錄之國子學積分生。然而,會試副榜“漢人取一十二人”中的“漢人”,是否完全將南人排除在外?對于這一問題,蕭啟慶認為其中“應含南人”,但沒有給出具體的理由。⑤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27頁。盡管目前尚未找到中選會試副榜的國子學積分生中存在南人的直接證據,但結合元代國子生的族群背景、官方有關國子學積分生參加會試的規定,以及中選會試正榜的漢人國子學積分生的本貫來看,蕭啟慶的推測應是成立的。
一如此前的漢唐宋等王朝,元代國子生同樣以官僚子弟為主。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初,就下令“于隨朝百官、怯薛歹、蒙古、漢兒官員,選擇子孫弟侄俊秀者入國子學”。⑥《元典章》卷31《禮部四·學校一·蒙古學·蒙古學校》,第1081頁。隨后,官員子弟進入國子學的資格得到進一步明確,規定“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為國子生,隨朝三品以上官得舉凡民之俊秀者入學,為陪堂生伴讀”。①宋濂:《元史》卷87《百官志三》,第2193頁。此時南宋尚未覆亡,元代朝廷中的官員以蒙古、色目和原來金朝舊境內的北方漢人為主,從這些官員子弟中選拔出來的國子生,自然也多出身于以上三類。元朝統一全境之后,南宋境內的南人進入官僚系統,此后的國子生中雖然開始出現“自江南來者”,②虞集:《道園類稿》卷20《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5冊,第532頁。但囿于元代的統治策略,南人在仕途上始終難以企及深受元代統治者青睞的蒙古、色目和漢人官員,國子生中南人出身者自然也為數不多。據虞集記載,在元朝立國已六十年的至順(1330—1333)年間,“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③虞集:《道園類稿》卷46《倪行簡墓志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第402頁。
南人在國子學中人數極少,加之本來就存在的壓制南人的族群政策,使得元廷在制定國子生歲貢、積分和會試貢額等政策時,自然會忽略南人。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制定的國子生歲貢和會試貢額分配政策中涉及族群身份之處,多數只有蒙古、色目、漢人三類。在恢復科舉以前,國子生出仕主要通過保舉、歲貢兩種途徑。④元代官方對于國子學采行保舉法和積分歲貢法的優劣進行過長期的爭辯,具體施行過程中也有反復。相關討論,參見王建軍:《教養化育與科舉主導:元代國子監辦學模式的演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年第2期。國子學在保舉過程中是否存在族群配額的情況,現不可知,但是歲貢法從一開始就清楚地劃分出蒙古、色目、漢人三者的額數。大德八年(1304),元廷正式頒布國子生出貢之法,“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⑤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學校》,第2029頁。兩年之后,因營建國子學,國子生貢額也得以增加,“蒙古、色目、漢人生員二百人,三年各貢二人”。⑥宋濂:《元史》卷21《成宗紀四》,第467頁;卷81《選舉志一·學校》,第2029頁。
國子生能否獲得出貢的資格,取決于建立在“升齋等第”之上的考試積分,而最終高等生員的配額,同樣分配給蒙古、色目、漢人三個族群。元代國子學六齋共分三等,下兩齋為游藝、依仁,中兩齋為據德、志道,上兩齋為時習、日新。國子生入學之初,先入游藝、依仁兩齋,根據每一季度考試“所習經書課業”的表現,“以次遞升”。漢人國子生升至上等時習、日新二齋,蒙古、色目國子生升至中等志道、據德二齋,始獲得參加國子學私試積分的資格。私試的內容和積分錄取的高等生員額數,亦以蒙古、色目、漢人為別:
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為上等,準一分;理優辭平者為中等,準半分。每歲終,通計其年積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為額,內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歲終試貢,員不必備,惟取實才。⑦宋濂:《元史》卷81《選舉志一·學校》,第2030頁。
從以上對于國子學歲貢、積分制度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國子學公試與科舉會試尚未合并之前,因為南人生員數量較少,國子學所制定的與族群配額相關的政策中,只分蒙古、色目、漢人三類。
延祐開科之后,隨著國子學公試與科舉層級中的會試逐漸合一,原來國子學管理體制中缺少南人專門配額的族群政策,也很自然地影響到國子生參加會試的資格及錄取配額。初復行科舉之時,元廷對于國子學生員參加會試,只籠統規定“國子監學歲貢生員及伴讀出身,并依舊制,愿試者聽。中選者,于監學合得資品上從優詮注”。⑧《元典章》卷31《禮部四·學校一·儒學·科舉程序條目》,第1102頁。此時,國子學生員參加會試尚屬自愿,官方并沒有為他們劃定單獨的錄取額數,被錄取的國子生中自然也就不存在單獨的族群配額。⑨其間,會試中選的國子生員,官方根據他們各自的族群歸屬,于相應的族群配額內錄取。例如張崇智,河南江北行省襄陽路均州鄖縣(今湖北省十堰市)人,元統元年(1333),以國子學伴讀入試,中會試第四十三名,名列左榜(漢人、南人)三甲第八名(佚名:《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北京圖書館珍本古籍叢刊》21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85頁);又如延祐五年(1318),八兒思不花(又作巴爾斯布哈、八思溥化),蒙古人,以“胄監生”入試,會試中選,殿試被取為右榜(蒙古、色目)第二名(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卷10《題名·秘書郎》,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9頁;黃溍著,王珽點校:《黃溍集》卷12《送八元凱序》,第433頁;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150頁)。(后)至元六年,此前傾向壓制漢人和主張停廢科舉的權臣伯顏被廢逐。⑩有關伯顏廢止科舉的政治背景及其與當時派系斗爭之間關系的討論,參見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第254—259頁。此次頒降的科舉詔書對于國子學積分生參加會試,不僅由自愿變為定制,而且為其劃定了單獨的錄取額數,并清楚地規定蒙古、色目、漢人三個族群各自所占的比例:
國子生員積分,并依舊制。已及分數應公試者,禮部給據,隨例會試,通并百人之數,出身依監學舊例。每年取蒙古、色目、漢人各二名,三年一次,共取一十八人。其余生員、伴讀,許于大都鄉試。①劉貞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都省奏準科舉條畫》,第13a—14b頁。
這標志著國子學公試與科舉體系中的會試正式并軌,積分達到八分以上的國子生即獲得參加會試的資格。原來額定為一百名的進士貢額之中,單獨劃出十八名,專門分配給國子學積分生;而這十八個貢額內部,又以族群為區分,蒙古、色目、漢人各占六名。②順帝(后)至元間,元廷在會試貢額之內,分配給國子學考生單獨的錄取額數,實為明代科舉國子監皿字號制度之濫觴。關于明代皿字號制度的創始和發展,參見李小波:《明代兩京鄉試中的皿字號問題》,《文史》2016年第1期。這一配額,成為以后歷科會試取中國子學積分生的定制。③只有至正二十六年會試除外,據《元史·百官志》和“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載,該科會試正榜共取中國子學積分生20名,超出原來規定18名的限額;其中,除色目額數保持未變,仍為6名,蒙古、漢人則各多取1名。盡管(后)至元六年放逐伯顏和恢復科舉的舉動是元代政治中樞對之前排抑漢人、南人政策的一種糾正,然而限于國子學的生員構成,南人并沒有在國子學積分生會試中選貢額內獲得單獨的配額。
那么,國子學制定的歲貢、積分以及中書省頒布的國子生會試貢額諸項政策中,都沒有單獨劃出南人的配額,是否意味著實際的錄取結果中沒有南人呢?從現存的一些資料來看,情況并非如此,而是由于南人在國子學中人數較少,漢人較多,故將南人附于漢人之中。例如,至正二年,恰逢國子學公試與會試并軌之后的首次會試,按照前年頒降的詔書,足額錄取了十八名國子學積分生,據時人記載,中間包括“漢人、南人共六名”。④宋濂:《元史》卷92《百官志八·選舉附錄·科目》,第2344頁。這一年舉行的會試,也確實可以找到南人出身的國子學積分生員得以中選的例子。如王銓,江浙行省饒州路浮梁縣人,至正二年“由國學積分就試禮部,登第,擢為太常禮儀院郊祀署丞”。⑤李存:《俟庵集》卷20《王伯衡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3冊,第722頁;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306—307頁。該科之后,盡管涉及會試正榜錄取國子學積分生員的記載名義上只有蒙古、色目、漢人三色,但是南人以國子學積分生身份參加會試并得以中式的實例,亦可考見。據明初解縉所述,其祖父解子元,江西行省吉安路吉水州人,為“至正(五年)乙酉進士”,歐陽玄則明確指出其為“國學進士”。⑥解縉:《解學士文集》卷8《鑒湖阡》,《明別集叢刊》第1輯第27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668頁;歐陽玄:《圭齋文集》卷14《跋劉士行墓志銘》,《歐陽玄全集》上冊,第395頁。結合二者所言,解子元這位南人,應該是以國子學積分生的身份被至正五年會試錄取,最終成為進士。
元代會試正榜錄取南人出身的國子學積分生員,并將之附于漢人額數之內的這一特點,在現存兩種國子學貢試題名記中體現地更為清楚。《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內登載正榜漢人六名,籍貫尚可辨識者僅有一人——“郭永錫,字九疇,永嘉”。⑦張翥:《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456頁。元時,永嘉縣隸屬江浙行省溫州路,故郭永錫為南人。由此更可以確定,元代會試正榜取錄的國子學積分生員中確有南人出身者,但并未將之另行劃出,而是附于漢人之內。
至于南人附于漢人之中的原因,前文指出這是由于國子生中南人出身者數量稀少。國子學及會試取中的積分生員中漢人多而南人少這一特點,可以從《至正丙午國子監公試題名記》所保存的中選者信息中看得更為清楚。該科是元代最后一次科舉,在參加會試的國子學積分生員中,分“蒙古、色目、漢人凡三色”,正榜共錄取二十人;其中,漢人一色下取中七人:
漢人,賜正七品出身,授承事郎
蔡玄,字德升,泉州(今屬福建省泉州市)人
周寅,字尚賓,東平(今屬山東省泰安市)人
丁鏜,字彥升,蠡州(今屬河北省保定市)人
劉驥,字德載,濟南(今屬山東省濟南市)人
劉登,字夢升,青州(今屬山東省濰坊市)人
李植,字子久,南皮(今屬河北省滄州市)人
張國祺,字符禛,白馬(今屬河南省安陽市)人①佚名:《至正丙午國子監公試題名記》,“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第460—461頁。
以上所列七名中選者,除第一名蔡玄的籍貫是江浙行省泉州路,屬于南人外,其余六名中選者都來自中書省轄下腹里各路,屬于漢人。從周寅至張國祺,其本貫分別為東平路、真定路、濟南路、益都路、河間路、大名路。這份姓名、字號、籍貫俱全的名單,一方面再次證明了元代會試所取南人出身的國子學積分生員被附于漢人名目之下;另一方面,會試正榜取中的七名非蒙古、色目出身的國子學積分生員之中,來自北方的漢人多達六人,而出身南人者僅有一人,也從側面反映出漢人在元代國子學中人數眾多,南人國子生之數量難以企及。當時由官方制定的國子生員考試積分、出貢以及會試錄取國子積分生中各族群配額諸項政策,未將南人配額另行劃出,而是附于漢人一色之內,正是在這一現實背景下展開。
會試正榜在取錄參加考試的國子學積分生員時既然如上文所述,而至正八年頒降的會試副榜政策,同樣將中選者的資格限定為參加會試的一百二十名國子學積分生,而且二十名副榜名額中的族群配額也一如正榜,僅分為蒙古、色目、漢人三色。換言之,具體到參加會試的國子學積分生員部分,正榜與副榜在制度層面上是對應的,副榜只是正榜的延伸而已。因此也可以推定,確如蕭啟慶先生所言,會試副榜分配給漢人的十二個名額中間,應當也包括南人。
目前關于會試副榜取中之國子學積分生員的具體信息,除前引《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外,尚未尋見其他更多的資料。該通題名記共登載了至正二十年會試所錄取的正、副兩榜國子學積分生三十八人。其中,副榜漢人一色之下有十二人,現在姓名、籍貫俱可辨識者共有四個人,分別是:
余植,字士立,寧州(第一名)
李以約,字景升,鄢陵(第四名)
王琬,字之文,洛陽(第五名)
張海,字大□,趙州(第八名)
以上四人中間,名列副榜漢人第一名的“余植”,最有可能是南人出身的國子學積分生員。據《元史·地理志》,當時共有三處以“寧州”為名者:一在甘肅,元時隸屬陜西行省鞏昌等處總帥府,現為甘肅省慶陽市下轄之寧縣;一在云南,元時隸屬于云南行省臨安路,現為云南省玉溪市下轄之華寧縣;一在江西,元時隸屬江浙行省龍興路,現為江西省南昌市下轄之修水縣。②宋濂:《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30頁;卷61《地理志四》,第1477頁;卷62《地理志五》,第1508頁。
如前文所述,元代國子學生員資格是與官僚體系緊密相連的,在朝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成為正式的國子生,而“凡民之俊秀”只有在得到朝中三品以上高官的舉薦后,方可有機會成為沒有積分資格的陪堂生、伴讀。換言之,如果不是出身任職于大都的仕宦家庭,或是與朝中高級別官員有很深的關系,進入國子學的機會微乎其微。翻檢甘肅寧縣、云南華寧縣兩地編于明清時期的方志,不僅沒有發現余氏在元代曾有出仕的記錄,而且當地其他姓氏的人物在元代后期官場上的表現也不突出。因此,該件題名記中所載之“寧州”,位于甘肅或云南的可能性比較小。
至于江浙行省龍興路所轄之寧州,盡管沒有能夠在該地的方志中尋見與“余植”相關的直接記錄,然而余植來自元時江浙行省龍興路所轄寧州的可能性比較大。不同于甘肅、云南境內的寧州,北宋天圣(1023—1032)以降,龍興路轄下寧州境內的長茅余氏與莫氏、黃氏、冷氏、陳氏同為當地科舉望族,仕宦人物眾多。宋、元兩代,余氏舉進士者有十八人。③王維新:《(同治)義寧州志》卷19《選舉志·進士》,《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第15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0—265頁。最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歷時悠久的科舉教育傳統以外,元代(后)至元(1335—1340)、至正間,該地余氏一族中也確實產生了任官于大都,且品級達到子弟入學國子學相應規定的仕宦人物。元代龍興路轄下寧州境內,僅有余貞一人中進士。泰定三年(1326),余貞為鄉試所取,次年中進士。《(嘉靖)寧州志》對于余貞登科以后仕履的記載較為詳細:
余貞,字復卿,(余)良肱之裔。登進士,歷官上海丞、棗陽尹,所至有善政。事父至孝,每事必咨稟而后行。及居鄉,四方來學者不遠千里。后至元庚辰(六年,1340)秋,召為翰林修撰。修遼、金、宋三史,史成,即懇乞歸養。中途聞父喪,慟哭徙跣數百里。居喪盡制,有司上其行于省府,未幾,以疾卒。①龔暹:《(嘉靖)寧州志》卷17《人物·余貞傳》,《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4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683—684頁。
正如前文所述,官員子弟能否成為國子生,是與官員的品階直接相關聯的。根據以上所引內容,(后)至元六年,余貞入大都,出任翰林修撰一職。元廷于至正三年下令開局撰修遼、金、宋三史以后,余貞也曾參與其事。現于《宋史》所附《進宋史表》《修史官員》之中,均可尋見余貞之名。不同的是,在至正五年(1345)右丞相阿魯圖十月所上《進宋史表》《修史官員》當中,余貞的結銜分別是“翰林應奉”②脫脫:《宋史》卷末《進宋史表》,第14254頁;歐陽玄撰,湯銳校點整理:《圭齋文集》卷13《進宋史表(代丞相阿魯圖撰,至正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歐陽玄全集》上冊,第364頁。和“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③脫脫:《宋史》卷末《修史官員》,第14258頁。。元制,翰林兼國史院眾多屬官之中,翰林修撰之下為應奉翰林文字,前者品階是從六品,后者品階為從七品。④宋濂:《元史》卷87《百官志三》,第2190頁。余貞在至正五年的時候,尚是從七品的應奉翰林文字,因此不可能早在五年之前就獲任從六品的翰林修撰。至于其升任翰林修撰的具體時間,應在至正五年以后。該年,元順帝以遼、金、宋三史纂修完工,下詔嘉獎修史官員,“四品以下,各進一官”。⑤黃溍著,王珽點校:《黃溍集》32《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公神道碑》,第1162頁。余貞曾參與纂修《宋史》,居官也在四品以下,此時擢為翰林修撰也順理成章。元代的國子學,“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為國子生”,⑥宋濂:《元史》卷87《百官志三》,第2192—2193頁。至正五年之后,余貞已為翰林修撰,作為從六品的在朝官員,其子弟也可獲得成為國子生的資格。
在基本排除該通題名記所載之“寧州”位于陜西行省或云南行省之后,并結合上文對于龍興路所轄寧州境內余氏自兩宋以來科舉之表現,以及余貞在順帝(后)至元、至正間的仕履,可以有足夠的理由推測,題名記中所載寧州籍之余植,極有可能就是翰林修撰余貞的子弟,寧州指的便是江西行省龍興路下轄之寧州。這說明在至正二十年的會試錄取中,盡管仍然以蒙古、色目、漢人三色劃分中選副榜的國子學積分生員,但是與正榜一樣,副榜漢人一色之內,也附有南人出身者。
換言之,受元代族群政策的影響,元代國子生當中,蒙古、色目、漢人居多,南人極少,得以通過積分一途參加會試及為正榜所取的國子生中雖有南人出身者,但數量很少,始終沒有獲得單獨的配額,而是被附在漢人之內。正如《至正丙午國子監公試題名記》所顯示的那樣,該科正榜取中七人之中,只有蔡玄一人具有南人的背景,其余六人全部是漢人。會試副榜既然是正榜的延伸,中選副榜的國子生里面,大概率也會出現漢人多而南人少的特點。《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漢人一色之內四名姓名、籍貫俱全的副榜之中,除第一名余植是南人外,其余三人皆是漢人出身。其中,兩人出自河南江北行省,如第四名李以約為汴梁路鄢陵縣(今河南省鄢陵縣)人,第五名王琬是河南府路洛陽縣(今河南省洛陽市)人;一人來自中書省,為第八名張海,籍貫為真定路趙州(今河北省趙縣)。
除此之外,第二名蒙大舉、第十名王宗仁二人之籍貫雖不可辨識,但可以在其他文獻記載中得到補充。如前文所示,蒙大舉之題名,目前尚存“蒙大舉,字士高,□安”諸字,籍貫處不可辨識。而在《秘書監志》所載秘書監典簿題名之中,存有蒙大舉的相關信息:
蒙大舉,字子高,大都人。由庚子科(至正二十年)國子公試生、中政院職官掾史、以從事郎遷,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上。①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卷9《題名·典簿》,第183頁。
從中可以知道,蒙大舉是大都路人。題名記涉及籍貫處尚存“□安”二字,元時大都路所轄州縣,有固安(今河北省固安縣)、東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區)二州,則蒙大舉之籍貫應為二州之一。
至于第十名王宗仁,盡管尚未在史籍之中找到直接的記載,但在其妻宋氏的傳記里面,保存了王宗仁籍貫的信息: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褧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宋氏從夫避于鏵子山。夫婦為軍所擄,行至玉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攜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②宋濂:《元史》卷201《列女傳二》,第4514頁。
宋氏守節一事,亦見于《(弘治)永平府志》,云宋氏為“盧龍王宗仁妻”。③張廷綱:《(弘治)永平府志》卷4《貞節》,《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51頁。結合兩處所記,王宗仁之籍貫應為中書省永平路盧龍縣。
綜上,《至正庚子國子學貢試題名記》副榜漢人一色之下,除余植一人出身南人外,目前籍貫可以確定的五位中選副榜者,全部出自中書省、河南江北行省轄下的州縣。這一現象,也恰好反映出,與正榜取錄國子生一樣,會試副榜同樣也受到元代特殊族群政策及國子學中生員比例的影響,南人出身者雖偶有中選者,然而在數量上難以企及北方漢人出身的國子生。
元代自至正十一年正式施行會試副榜制度,每科錄取額數僅有二十人,六科會試共錄取一百二十人而已,且范圍嚴格限定在南人占比極少的國子學積分生之內,在當時的影響十分有限。然而,元代科舉中的這一創新,卻為明代會試所繼承,極大地改變了此后近三百年會試下第舉人的命運。明初,隨著各省鄉試解額的增加,鄉試不再取中副榜,會試副榜仍依舊實行,中選者授予教諭、訓導之職。更為重要的是,明代會試副榜的錄取名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數量甚至是正榜名額的數倍之多。如永樂四年會試取中副榜三百三十一人,宣德五年、宣德八年、正統元年、正統四年、正統十三年會試,副榜人數分別為六百八十九人、四百七十三人、四百五十三人、二百九十一人、六百零二人。④解縉:《解學士集》卷9《翰林藍君日省墓志銘》,《明別集叢刊》第1輯第27冊,第706頁;楊士奇:《明宣宗實錄》卷64“宣德五年三月丙寅”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1518頁;楊士奇:《明宣宗實錄》卷100“宣德八年三月壬申”條,第2247頁;李賢:《明英宗實錄》卷15“正統元年三月乙亥”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281頁;李賢:《明英宗實錄》卷52“正統四年閏二月乙酉”條,第994頁;李賢:《明英宗實錄》卷163“正統十三年二月戊辰”條,第3162頁。會試大量錄取副榜,一方面能夠為教官隊伍持續輸入眾多受過系統舉業訓練的舉人,優化教官結構;另一方面則在進士之外為士子拓寬了入仕途徑,使更多的士子獲得了進入官僚系統的機會。
結 語
科舉自創設以后,在逐漸成為傳統中國選拔官僚主要途徑的過程中,將絕大多數希望通過應試來維持或改變自身所處政治、經濟地位的知識階層裹挾進科舉體系之內。然而,限于傳統中國的國家規模和官僚隊伍的容納能力,較之數以萬計的考生,舉人、進士等高級功名的額數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官位數量,顯得少之又少。因此,從北宋開始,歷代都試圖在科舉體制內部進行一些調整,使一部分很可能布衣終身的下第士子得以邁入仕途,有機會實現階層的躍升。總的來看,科舉體制內長期存在的安撫下第士子的措施,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兩宋時期以“年甲”“舉數”為依據的特奏名制度,面對的主要是參加省試的各地發解舉子;另一種是此后以當科考試成績為準的副榜制度,面向會試、鄉試兩個層級的下第舉子。而從特奏名到副榜制度的轉變,正是完成于在中國科舉史上地位并不突出的元朝,尤其是再次恢復科舉之后的至正年間。
因為科舉制度的機會均等原則與元代政治社會組織偏重出身的中心原則有抵觸,科舉在元代官僚選拔體系當中居于邊緣。①根據姚大力、蕭啟慶的統計,元代歷科所取進士總數僅占文官總數的百分之四左右。具體數字及相關討論,參見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年第6期;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1分。較之兩宋及此后的明清兩代,元代全境十七個鄉試區域,解額僅為三百人,會試中式名額更低至一百人,且按照四大族群區分的配額,又明顯偏向蒙古、色目。在這種情況下,科舉考試的競爭更加激烈,原本生活在科舉傳統熏染下的中原和南宋故境內的漢人、南人,入仕途徑更為狹窄。會試“恩例”、鄉試與會試副榜制度的推行,盡管名額不多,所授官職亦以下層儒學教官為主,但對于一部分家庭出身不高、缺少人脈關系的下第士子而言,無疑是“亦以循資歷,聊為入仕門”②蒲道源:《閑居叢稿》卷3《洋州儒學正劉敏道得代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0冊,第589頁。的選擇之一。元明鼎革以后,會試依舊延續了副榜制度,并隨著科舉取士在十五世紀以后重新成為政府選拔官僚最為主要的途徑,副榜錄取的額數也日益增加,成為明代優化教官隊伍、充實基層州縣官隊伍的重要選項。在這個意義上,元代副榜制度可以說是科舉取士之法從宋過渡到明的重要一環,也是元代留給后世的一項重要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