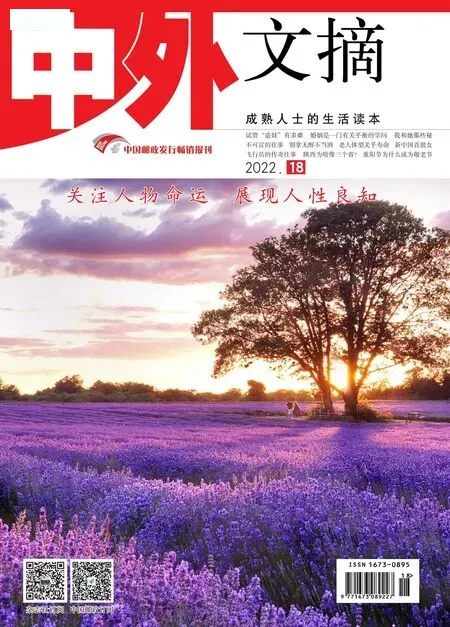小鎮青年:沒錢,敢花
□ 徐 晴

月薪2600 的“有錢人”
林菲是個95 后,大學畢業后考上了襄陽老家的公務員。回到縣城生活后,林菲一直想不明白,身邊的有錢人怎么這么多?
她有一個00 后朋友,大專畢業,正在準備考編,這兩年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備考。就是吃喝玩樂。與大城市相比,縣城的薪資水平差了一大截,林菲每個月到手只有3000 元,但她覺得消費水平并不比城市低多少:每次和朋友們出去吃飯,稍微好點的餐館,人均將近一百元;周圍人喜歡在路邊的服飾店買衣服,也不是什么品牌,隨便一件就要500 元、1000 元;玩游戲也都會充錢,幾百元、上千元的,都沒當回事兒。
生活在西部某縣城的啾啾也是95 后,她做幼師工作,每個月的工資是2600 元,但幾百元的科顏氏淡斑精華、蘭蔻粉底液,啾啾都舍得給自己買。
相比一線城市,一些縣城里的年輕人有時候更敢花錢,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一般工作穩定,沒有租房或買房的壓力,父母也還處于壯年,能在經濟上給予幫扶,讓他們有了“掙多少花多少”,甚至是“入不敷出”的底氣。
他們的畫像一般是這樣的:年齡20~30 歲,在父母的幫助下買了房,全款或者很少的貸款,或者與父母一起生活,有一輛十幾萬的小汽車;工作結束后有大把的閑暇時間,能和朋友聚會、喝酒、打牌。或者在網上消費娛樂,最常見的方式是網購、游戲、短視頻、在線閱讀。最重要的,是有很強的消費意愿。
互聯網讓縣城消費迅速與一線城市接軌,只要有消費能力,都能買到一樣的東西。而另一面,小鎮年輕群體有著更強的消費意愿和充足的閑暇時間,也讓城市的消費潮流更快涌向縣城。
趕不上消費升級的人
同樣在縣城,一些年輕人卻無力追趕時髦的消費潮流。
溫文在河北縣城老家的工廠上班,工資每個月到手4000 元。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開支,他很少亂花錢,即便在自己的愛好上,也想方設法,能省就省。
溫文的父母都沒有工作,家里沒有什么積蓄。對他來說,到縣城買房這件事有些困難。因為家里出不起學費,溫文十幾歲就輟學打工。不管在哪里,他的工作都并不穩定。
還有人在消費降級。在縣城開手機維修店的陳樂趕上過縣城手機市場的紅利期,那是2016 年,手機維修、賣手機配件的利潤非常高,一個月能賺兩萬多。那會兒她花錢大手大腳。現在,維修店的經營越發慘淡,一個月只能賺幾千,經常入不敷出,需要父母支援。
小鎮青年逐步在分化——對一部分人而言,買房是輕松的,房價是相比一線城市低廉太多的,但對溫文和像他一樣缺乏家庭支撐的人,房價是越來越高、越來越難夠得著的。一些縣城里,新開的樓盤連兩室一廳都沒有,都是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縣城里,像溫文一樣的男性面臨著困境。對買不起房的溫文來說,結婚簡直是一種奢望,他甚至做好了準備,“走一種小眾路線”,不結婚。
但除了房子之外,消費逐漸成為另一種“標準”和“面子”。溫文的同事大多是年輕人,同樣一個月賺4000 元錢,“他們月月光。經常就是去唱歌、喝酒、吃飯、買衣服”。
消費習慣改變的同時,互聯網將所有年輕人塑造成了差不多的樣子,都有類似的價值標準和想法。
中部縣城公務員余芊因為過度消費,欠下了十來萬元的網貸。在她的邏輯里。有些便宜不占白不占,提前消費是“為了省錢”。工資沒剩多少不要緊,信用卡還有額度,但現在不買就沒有折扣了,她每個月都要收幾十件快遞。她也熱衷醫美,雙眼皮、紋眉毛和美瞳線、打瘦臉針,做一次就是一個月的工資。消費的欲望難以控制,至今,她還沒能還完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