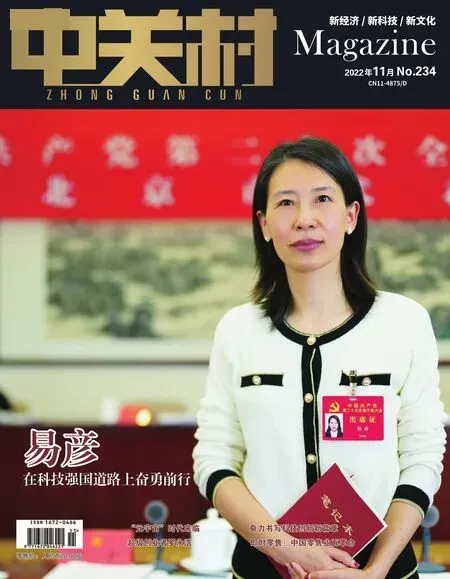即時零售:中國零售業再革命
文畢夫(廣東)
除了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前不久推出的《即時零售開放平臺模式研究白皮書》做出了即時零售風口已至的明確判斷外,商務部日前發布的《2022年上半年中國網絡零售市場發展報告》也首次提及“即時零售”,并肯定了即時零售作為新零售業態代表在線上線下深度融合中發揮的作用。民間與官方報告一致性唱多即時零售,意味著即時零售接下來還會展現出更旺盛的商業前景拓展力。
所謂即時零售,是指消費者在線上交易平臺下單,線下實體零售商接單并通過第三方或自有的物流配送運力提供商品與服務的上門送達服務,送達時效一般控制在1小時之內。與傳統電商零售相比,即時零售將快遞時間從4-5天壓縮到了最多只需60分鐘,之所以能夠做到如此地快捷,核心就是倚重本地實體門店,其中既有商超百貨、品牌連鎖和便利店,也有閃電倉、前置倉等本地倉儲,與此同時,作為鏈接實體門店和消費者中間環節的開放平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即正是平臺的超級算力、完備運力以及智能化解決方案的輸出讓及時履約配送成為可能,形象地說就是打通了城市物流的“最后一百米”。
鏈接“人、貨、場”的零售商業史在不同技術與經濟力量的作用下發生過不同形態的裂變與進化。古老的西爾斯百貨伴隨著美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而推出了郵購目錄,從而成為現代零售業的鼻祖,也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充當著零售業的代名詞;沃爾瑪抓住美國城郊化的趨勢開設大賣場,提供質優價廉產品深受用戶喜愛,大型超市開始在全球以強勁的圈城掠地之力伸展開來且至今風采依然;亞馬遜、阿里巴巴等在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的武裝下以電子商務的閃亮面孔脫穎而出,并生成了特有的O2O新零售商業模式,使得線上購物的魅力顛覆與改變了公眾的消費方式,也在海量用戶中建立起了十分明朗的心智和足夠強大的黏性。
電子商務在擠壓線下零售的同時,后來也遭遇到流量的“天花板”,并不得不開始創造性尋找與挖掘線下市場的空間,如同技術創新經濟學家熊彼特在談及零售領域的競爭時說過的那段精辟語言:“競爭壓力強迫激發了企業家用新的想法、新的產品、新的流程、新的組織來替代舊的東西”。于是,傳統電商陣營中除了遠程快遞之外,國內后來便出現了由美團、順豐以及達達等操盤的同城(即時)配送,雖然配送產品主要圈限于餐飲或跑腿業務,而且只有小眾用戶,但卻是即時零售的強勁胎動。
商業狂潮因為疫情的暴發和蔓延而觸發。在新冠肺炎的肆虐與撕扯之下,不僅線下實體門店遭遇歇業關張的煎熬,線上零售也承受著傳遞路徑受阻以及無奈延遲交貨的痛苦,同時許多城市的市民也被隔離與封閉于家中,如此危情的覆壓之下,活下來便成為人類最大的希望。于是,擺脫人煙稀疏的迷茫,實體門店向著線上進一步尋覓自我救贖的機會,掙脫物流受阻的困擾,電商平臺朝著線下再聚力拓展自主求存的空間,消解行動受限的煩憂,普通民眾開始主動尋找無接觸性消費的產品,而且基于生活與生命的急需還必須選擇最近的賣方市場,三方力量聯袂共振,供給與需求的相向而行,即時零售便以更寬的厚度與更大的力度風采盎然地走到了前臺。
按照麥肯錫的報告,疫情高峰期,約有74%的消費者在線上就近購買了更多食品雜貨,而21%的消費者在線上購物的費用支出在不斷增加。當然,疫情之下即時零售的主要消費產品線雖主要集中在生鮮食雜身上,但十分重要的是疫情解封之后用戶消費習慣也順勢延續與保留了下來,即時零售所承載的產品也非常自然地拓展到了服裝鞋帽、3C電子、鮮花蛋糕、醫藥美妝等所有品類以及相關的服務上來,昔日即時配送的“送餐飲”也華麗晉級成了即時零售的“送萬物”。
無論是傳統電商牽引下線上消費習慣的養成,還是疫情倒逼之下線上與線下近場消費行為的誕生,客觀上與時下國內人口結構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聯,也就是那些互聯網的原住民以及“Z世代”的年輕人才是即時零售的最龐大與最主要的陣容。據艾瑞咨詢的數據顯示,即時零售的用戶群體中,85后及90后人群占比超64.6%,同時埃森哲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超過50%的95后消費者希望在購物當天甚至半天就能收貨,7%的消費者希望能在下單后2小時收到商品,看得出,正是有了巨量年輕群體的存在,即時零售才獲得了與消費用戶對接的清晰對象。當然,年輕人的消費方式在家庭成員以及親族之間是很容易逆代向上傳染的,因此,根據Mob研究院數據,目前中國即時零售用戶規模已達到了7億人之多。


從電商平臺的搭建,到物流快遞的暢通,再到線下門店的快速響應,及至消費需求的迅疾滿足,即時零售的全程如期履約須臾不可離開國內物流基礎設施的健全與改善。除了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北斗導航衛星定位系統的輔助之外,更有各種可以承載冷藏保鮮、低溫分揀以及移動倉儲等終端設備場所的強力支撐,同時還有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全新技術的策應與護航,而在末端配送寬帶上,還活躍著占全國人口基數近1%且數量為1300萬名的外賣騎手,也正是他們的風雨兼程,才打通了城市社區配送的“最后1米”,也才讓即時零售的“微循環”暢通無阻。
回過頭去看,對于處在需求側的消費者而言,即時零售除了產生“快”(及時送達)和“近”(本地門店)的消費體驗外,還可以享受到“多”(商品豐富)與“好”(可信度高)以及“省”(節約成本)的超級紅利。這是因為相比于傳統線下近場購物范圍受到局限,線下與線上的融合不僅可以讓用戶的選擇區域伸展,而且可選產品的數量也大大擴充,這樣,消費者所面對的將是一個品類廣、品牌廣、地域廣的供給場景,并能通過“貨比三家”挑選到價格更實惠的產品;另外,正是基于本地門店優勢,在滿足產品即得性的同時,即時零售也解決了消費者所重視的產品確定性疑慮,畢竟相比于傳統電商的遠程供給而言,本地實體提供的商品與服務安全度相對較高,而且即便是需要產品退換,用戶所花費的等待時間成本也要小得多。
從供給側的角度分析,即時零售創造了最大紅利無疑是破解了作為傳統頑疾的市場邊界約束。一方面,借助即時零售,本地商家的產品輻射半徑可從方圓1-2公里拓展到方圓5-6公里,其面對的是一個客群廣、場景廣、訴求廣的需求場景,并最終獲得了更大的增量市場;另一方面,不同于傳統零售下實體門店基于大人流與高銷量訴求而必須開在商業繁華區,即時零售背景下商家門店的位置選擇不再十分重要,門店裝潢也不必亮眼項目,從而可以大幅降低租金成本與經營成本。不僅如此,即時零售牽引下的商家注意力不在價格優勢上,而是沉淀在效率優先與質量至上的層面,只要提供即得性更快與可信度更高的產品,便可贏得更強的復購。更為重要的是,即時零售還可以推動線下渠道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也就是在平臺技術能力支持下,對每家門店的消費者群體構成、消費習慣與偏好等進行分析與畫像,在此基礎提高產品采購精確率與需求匹配度,在穩定高頻需求的同時發現稀缺的長尾需求,進而導入更豐沛的用戶流量。
從對行業溢出的紅利角度看,不同于傳統電商對實體零售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與博弈且多多少少地對后者產生了“擠出效應”,即時零售通過為實體零售創造市場增量以及充分賦能,構造出了線下與線上相互包容、互為協同與彼此促進的正向循環,并最終培養出市場主體之間1+1>2的效能;另一方面,即時零售與傳統電商也不是競爭關系,前者滿足的是計劃性消費需求,后者關注的是突發性與應急性消費需求,同時相比于傳統電商立足于國內統一市場的大循環,即時零售則是立足于本地市場的微循環,二者同時并存且實現差異化發展。也正是如此,我們可以將即時零售看成是中國電商行業的又一次升級,或者是中國零售業態又一次富有價值意義的創新。
放在更寬大的宏觀視域觀察,因為即時零售依賴本地實體門店,同時為實體門店輸出了降低成本與提高利潤的紅利,這無疑可以激發更多全新市場主體的創建,并且實體零售背景下大小企業公平與公正地展開競爭,眾多的微小商戶獲得了成長的機會,同時也勢必激勵更多的實體門店擁抱實體零售,進而豐富與增加當地商品流通量與提高市場活躍度,并為本地財政創造新的稅收來源;另外,即時零售撬動的是突發與應急需求這一先前未曾開發的消費市場,相應地就可以疊加出更多的本地消費勢能,進而增厚地方經濟的內生增長動能。
也許正是基于以上多種能量的聚合與溢出,在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看來,至2025年國內即時零售開放平臺模式市場規模將達到1.2萬億元,年復合增長率保持在50%以上,同時艾瑞預計,至2026年中國即時零售訂單規模將接近千億量級,達到957.8億單,未來五年年合增速可達到28%。因此,動態地判斷,已經站上“風口”的即時零售接下來還會迎來高速增長,并有可能成為未來10年中國零售行業的最強大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