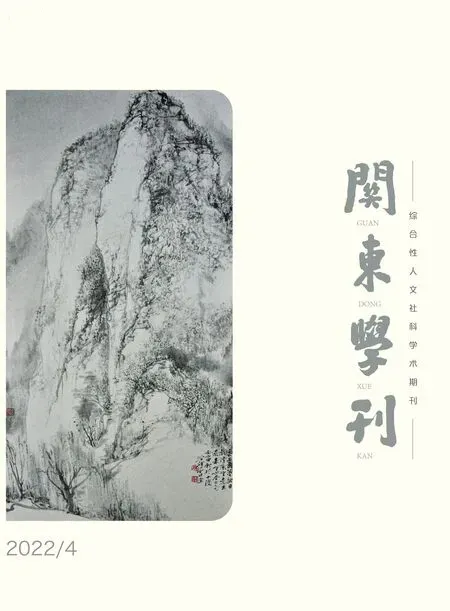數字勞動異化的批判與反思
林 晶 唐春燕 于 洋
伴隨著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蓬勃發展,數字技術全方位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一種新的勞動范式——數字勞動便應運而生。然而在數字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之下,數字技術逐漸控制并奴役人類,成為一種異己的、統治人的力量,如何對數字勞動異化現象進行反思與揚棄,已成為目前數字勞動相關問題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近年來,國外學者克利斯蒂安·福克斯與國內學者藍江在馬克思理論視域之下研究數字勞動異化問題,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本文在學術界眾說紛紜之下,首先在馬克思勞動范疇基礎上對數字勞動重新進行概念界定,在此基礎上將數字勞動劃分為標準雇傭數字勞動、靈活雇傭數字勞動和非雇傭數字勞動三種類型,進而將數字勞動置于數字資本主義的現實背景下,對數字勞動異化的生成機理進行深入剖析。其次,數字勞動表現出與傳統勞動形式的巨大差別,但其異化風險依然普遍存在,本文通過引入馬克思“異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以對三種類型數字勞動異化的系統反思為核心議題,著重運用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對數字勞動異化的四重表現形式進行專門的探討,透視數字勞動異化的運行邏輯與社會后果。最后,以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作為支撐和引導,結合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探求對數字勞動異化揚棄的試解方案與治理路徑,試圖有效利用數字技術造福人類,實現人在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與全面發展。
一、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語境
隨著數字技術全方位滲透到社會生活中,一切都被納入數字化生產的軌道,與舊工業社會中主流勞動形式相比,數字勞動創造了更加巨大的生產力,互聯網、云計算、5G等新興產業如雨后春筍,新型勞動方式也層出不窮,傳統勞動模式面臨著被解構的威脅。資本主義邁入了數字資本主義階段,“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頁。,然而數字技術的革新并未改變馬克思曾指出的資本主義剝削實質,受資本邏輯支配的數字勞動給人們帶來了更深層的異化困境,面對數字異化,我們必須從數字勞動的出場審視其生成機理,以期針對此探尋消解路徑。
(一)數字勞動的概念界定
國外學術界高度關注數字勞動的研究,進一步展開了對數字勞動及其異化的批判性分析。數字勞動概念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學者達拉斯·斯邁茲,他基于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提出“受眾商品論”。“數字勞動”一詞由意大利學者蒂齊亞納·泰拉諾瓦率先提出,他認為數字勞動是一種非物質勞動,是“互聯網用戶在網上創立網站、調試軟件、閱讀和發送郵件以及構建網絡虛擬空間等互聯網無酬勞動”(2)Tiziana Terranova,“Free Labou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no.2,2000.。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數字勞動屬于物質勞動,“在數字媒體技術和內容的生產過程中,資本積累所需要的所有勞動都屬于數字勞動”(3)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4.。同時福克斯還在《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中通過論述國際數字勞動分工下(IDDL)的各種數字勞動,指出數字勞動是以對勞動主體、勞動產品、勞動工具與勞動產品的異化為基礎的,而數字勞動的異化將在一定程度上長期存在,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真正破除其存在根基(4)[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國內學者對數字勞動的研究成果頗豐。謝芳芳、燕連福將數字勞動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上的數字勞動由兩部分組成,一方面是在使用上的一切腦力和體力活動,另一方面是數字媒介技術和內容的生產以及流通。狹義上的勞動僅限于用戶活動,即依靠數字技術為終端的社交媒體而進行的活動”(5)燕連福、謝芳芳:《福克斯數字勞動概念探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2期。。吳歡、盧黎歌認為,“數字勞動即無形資產,關鍵生產資料也是數字化信息,并以數字化技術為根基,包含各個方面,在一定網絡空間內消磨人們的時間進行的數據化勞動形式”(6)吳歡、盧黎歌:《數字勞動與大數據社會條件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與創新》,《學術論壇》2016年第12期。。藍江分析了數字拜物教與數字人生存的異化狀態(7)藍江:《數字異化與一般數據:數字資本主義批判序曲》,《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強調要立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將數字異化作為普遍現象進行考察(8)藍江:《數字資本、一般數據與數字異化——數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引》,《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總之,目前學術界對數字勞動及其嬗變過程的研究方興未艾。國內外學術界對于數字勞動概念并未達成共識,筆者認為,數字勞動是伴隨信息技術發展出現的新型勞動范式,與傳統勞動方式相比呈現諸多新特點。在勞動主體方面,傳統勞動以雇傭工人為主,而數字勞動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只要掌握基礎的網絡使用,不論個體差別或雇傭形式,都是數字資本積累鏈條中的一環;在勞動過程方面,傳統勞動的勞作集中于工廠,數字勞動突破了時空限制,只要存在網絡,數字勞動便可以進行;在勞動資料方面,傳統勞動依靠機器、廠房等設備,而數字勞動資料依靠網絡技術,呈現出非物質性特征;在勞動產品方面,傳統勞動產品作為實體存在,數字勞動產品卻可以被廣泛復制和分享,無限循環使用。但是數字勞動在勞動主體、勞動過程、勞動資料與勞動產品中的內在規定性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其實質并未脫離馬克思的“勞動”范疇,基于此,本文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內重新界定數字勞動,即數字勞動是人們利用數字技術在互聯網平臺展開的生產數字產品或提供數字服務的勞動。在這里需要將“數據勞動”從“數字勞動”中區分出來,數字勞動者不一定是數據勞動者,數據勞動者一定是數字勞動者;數字勞動是絕對的材料消耗型勞動,數據勞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材料消耗的增殖勞動(9)蔣志紅、江堯:《何為數據勞動——對數字資本主義批判中生長性數據的一種思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在明確界定了數字勞動概念之后,還需要深入考察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背景下的不同數字勞動者及其勞動過程,據此劃分數字勞動的不同類型,以便對數字勞動異化問題具體闡述。對于數字勞動的劃分方面,筆者克服了目前學界數字勞動劃分方式所存在的范圍交叉的問題,以是否存在雇傭關系為標準,將數字勞動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標準雇傭勞動”,是指勞動者與雇傭方正式簽署勞動合同的、存在明確雇傭關系的勞動,以軟件工程師和程序員為代表,勞動場所與時間較為固定,勞動過程以軟件開發設計或收集整理數據信息為主,勞動成果包括提供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二是“靈活雇傭勞動”,是指勞動者并未與雇傭方正式簽署勞動合同,雇傭方式較為靈活、市場化契約較為隱蔽的勞動,以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和主播等為代表,其勞動場所與時間不固定,勞動過程必須借助互聯網平臺才能實現,勞動成果不限于數字產品與服務;三是“非雇傭勞動”,是指不存在任何雇傭關系的勞動,互聯網用戶通過網絡平臺無償為資本家提供大量數據信息資源的勞動,其勞動場所與實踐高度靈活,僅僅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娛樂或消費,便可無償為數字資本家提供服務,勞動成果為個人數據信息,這類數字勞動是“產消合一”的勞動,生產和消費同時進行。這三種形式的數字勞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異化狀態,筆者在之后論述中需要基于這三種類型的數字勞動展開。
(二)數字勞動異化的生成機理
與馬克思生活的圖景不同,數字技術不僅帶來了革新和進步,也讓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有種無所適從的眩暈感。(10)藍江:《從物化到數字化: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異化理論》,《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青年馬克思將其所處的情形描述為“異化”,“異化”是馬克思用于描述不平等或受支配的社會關系的術語,人們因無法控制社會關系的過程和結果,最終導致喪失自我的結果,主要運用于一般經濟關系之中,但我們如今所面臨的數字異化向個人、國家乃至世界拋出難題,人們正在遭遇數字技術帶來的生產領域之外的全新意義上的普遍異化。為何在生產力如此發達的數字資本主義階段,社會普遍物化現象并未得到遏制反而進一步進化為數字異化形態。數字勞動異化問題無法回避,我們需要從其現實邏輯出發分析數字勞動異化樣態,進而探尋其生成機理。
首先,在標準雇傭勞動過程中,表面上數字勞動者擁有較高的自主性,但其在勞動過程中受到的精神壓力相比傳統勞動倍增,數字勞動者所有勞動過程都處在資本家的技術監控之中,隱秘的算法權力蠶食和占據著數字勞動者的生命活動。不同于傳統勞動“看管機器的人”,數字勞動者被無數符號代碼所淹沒成為“緊盯屏幕的人”,他們看似作為數字世界的建構者,實則被各種機制所量化,淪為資本家謀取剩余價值的數字符號,面臨著勞動時間長、精神壓力大等一系列更深層的剝削,因此在標準雇傭勞動過程中出現了異化狀態。其次,在靈活雇傭勞動過程中,勞動者以獨立生產者的身份加入數字平臺,借用數字平臺的力量獲得收益。在這一勞動模式中,平臺資本家依靠其掌握的平臺資本與平臺壟斷信息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他們在實際生產中,既沒有參與產品或服務的直接勞動,也沒有支付其他不變資本,卻可以獲得絕大多數的價值分配成果,同時,由于目前國內外勞動力市場處于動態飽和狀態,平臺資本家擁有大量的勞動力后備軍,對數字勞動者的剝削與控制會進一步加強,因此在靈活雇傭勞動過程中出現了異化狀態。最后,在非雇傭勞動中,數字用戶在互聯網上進行點擊、評論等操作中,數字資本將這些生成的數據記錄、收集、儲存與整合,成為數字資本生產的“原材料”。數字平臺還通過使用一些數字軟件和平臺之前設置的服務協議、隱私條款等方式免費獲取數據使用權,福克斯用“家庭主婦化”,即像家庭主婦一樣免費貢獻勞動力來形容此類無酬并且受剝削的勞動形式,因此在靈活雇傭勞動過程中出現了異化狀態。在這三種類型的數字勞動中,非雇傭勞動的異化程度大于靈活雇傭勞動,標準雇傭勞動次之。
綜上所述,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邏輯通過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實現對人的操控,是數字勞動異化產生的根源。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依然是數字資本占據支配地位的時代,“數字資本主義只是改變了資本增殖的方式方法,但并沒有改變資本增殖的目的和宗旨”(11)白剛:《數字資本主義:“證偽”了〈資本論〉?》,《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數字勞動無非是與數字資本相適應的新型勞動形態,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數字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并成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基礎。數字技術革命推動“數字”成為資本中心位,當數字技術與數字資本邏輯相結合之時,數字勞動便不可避免地被資本所掌控。數字技術作為中性詞原本不歸屬于某種社會制度,但如今卻與數字勞動生產過程相結合創造巨額利潤,數字勞動者被裹挾進入數字技術所架構的現代社會,數字技術本可以給人們帶來美好的生活,但在資本邏輯控制下奴役、管制和支配著勞動者,技術理性重塑并最終導致日常生活殖民化。無論數字勞動者是否與資本存在雇傭關系,都深陷數字異化的泥潭。
二、數字勞動異化批判的四重維度
數字技術開啟了重大的時代轉型,數字勞動異化呈現出新的本質與特征。數字勞動異化作為一種新型的普遍異化現象,區別于以往的勞動異化、交往異化和消費異化等其他異化形式。數字勞動異化的顯著特征在于人的需求和欲望被數字技術無限放大,更易受到異己力量的支配與剝削。“這種剝奪不是發生在個體工人身上(因為協作已經昭示著集體性),而是發生在社會勞動身上,以信息流動、交往網絡、社會符碼、語言創新以及情感和激情的形式表現出來。”(12)[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4頁。它囊括的主體范圍更加龐大,不僅包括網絡從業者,還有海量主動或被動卷入網絡世界的民眾,同時數字勞動異化過程中包含著便利與享樂的因素,麻痹和禁錮著個人本性。數字勞動依然處于資本邏輯控制之中,數字異化的本質仍然是人的異化,個人與社會都無法逃脫異化的結局與宿命,數字勞動異化遵循馬克思異化理論的人與物、人與人的兩條主線,因此并未超越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框架。為了正確理解數字勞動異化的全新表征,沿著馬克思的批判思路,我們可以在數字勞動者與數字勞動產品、數字勞動過程、類本質以及主體間的異化的四重視角進行重新解讀。
(一)數字勞動者與數字勞動產品的異化
馬克思于工業時代指出:“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13)[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頁。數字勞動者雖然創造了更多的數字勞動產品,但其自身卻越來越難以享受數字發展成果。數字產品是數字勞動的產物,但其無一例外地轉化為獨立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外的數字商品,成為異己的存在物反過來壓迫數字勞動者本身。由于靈活雇傭關系和非雇傭關系的廣泛存在,數字勞動者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與勞動產品的對立。
首先,在標準雇傭勞動下,以網絡專職人員為主的數字勞動者生產的勞動產品不再只是桌子、衣服或者汽車等實體性的存在,而是更多地展現為數據、代碼、符號等非物質形態在數字空間進行流通。在資本宰制的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數字勞動產品雖然形態較以往發生改變,但平臺資本家依然強制占有數字勞動產品。勞動者雖然獲得了勞動報酬,但這與其創造的數字剩余價值相比微乎其微,“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14)[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1頁。數字勞動者貢獻的越多,數字平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越高,勞動產品越成為一種“外化”和“異己”的存在物,越成為資本家剝削和奴役數字勞動者的工具。其次,在靈活雇傭勞動中,以零工勞動為代表的數字勞動形式尤為突出,原本資本家需要付出極大的人力成本與高昂的支出費用,如今只需要支付極少的勞動報酬就可以完全占有勞動產品。比如人工智能的發展需要大量重復且枯燥的數據標注工作,這種數字勞動通常以眾包的形式出現,當人工智能技術獲得成熟發展后,便會取代更大部分的人力工作,數字勞動者與數字產品呈現出非常明顯的異己關系。最后,在非雇傭關系的數字勞動中,數字勞動者作為免費勞動力生產的數據完全被資本家占有。隨著抖音、小紅書、淘寶等智能平臺的出現,大量數字勞動者通過點擊或者搜索生成一系列瀏覽記錄,運營商或平臺企業通過爬蟲程序收集匯總數據信息,“通過數據化,在很多情況下我們能全面采集和計算有形物質和無形物質的存在,并對其進行處理。”(15)[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肖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和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5頁。這些零散的數據信息最終被資本家賣給廣告商牟取利益,廣告商再基于數據構建消費者的需求,實現廣告的精準投放,這實質上是互聯網用戶與自己生產的“數據-流量”的分離。馬克思在其早期的“異化勞動”理論中,勞動者由于在生產過程中付出了時間與心血,最后勞動產品不能歸自己所有,所以這一異化過程是痛苦且壓抑的;但數字技術帶來的異化卻給人們帶來了歡愉,使人們沉溺在便利的互聯網與虛擬的社交網絡之中,人們在虛擬數字空間中依然消耗了時間與精力,但被剝奪的注意力卻未能復歸到人自身,人們并沒有得到足夠的物質或精神上的反饋,數字勞動產品的屬性最終與勞動對立。
(二)數字勞動者與數字勞動過程的異化
由于勞動產品作為對象化的東西被剝奪,因此勞動過程對于工人來說是摧殘而非生命的完善,馬克思由此指出:“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16)[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3頁。在勞動過程中,“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7)[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3頁。在馬克思所處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勞動者可以逃離勞動,生產和休閑還存在分明的界限,但是在數字社會中,消費本身也是生產,勞動過程擴展到生產領域之外,“諸眾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是有生產性的,不僅在工作中生產,在家里也生產,諸眾的生產力正是資本主義的原動力,而資本則愈加成為諸眾生產力的寄生蟲。”(18)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佟登青:《西方社會批判理論的新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年第6期。同時數字技術支配著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主體沒有能力從這個被高度監控的勞動過程中抽離。
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勞動者與數字勞動產品發生異化,其勞動過程必然也陷入異化狀態,而數字勞動異化最大的表現就是數字生產過勞化。“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愿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19)[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3-54頁。首先,標準雇傭數字勞動者便是類似的處境甚至更糟糕,他們的數字勞動過程一定程度上僅作為謀生手段具有非自覺性,一旦可以逃離工作崗位,他們會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勞動。尤其在信息技術類的企業中,數字勞動者為維持或提高自身工資待遇,加之各種算法與排名機制的“強迫”,他們不得不承受腦力與體力雙重高壓狀態的工作,在如此扭曲的數字空間適應資本法則的勞動過程中,“猝死”或“過勞死”現象頻繁發生在數字腦力勞動者身上。其次,靈活雇傭數字勞動過程在時間地點方面看似更具彈性,但實際上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與盤剝。他們看似實現了對自己工作的自由掌控,實質與馬克思描述的實體工廠并無區別,“工人的精神也被他的工作本質和他工作于其中的條件摧毀了。”(20)[美]伯特爾·奧爾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王貴賢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85頁。以外賣員為例,他們的勞動報酬與平臺接單量與送單時間息息相關,如果未在大數據算法所要求的送單時間內送達,勞動報酬便會相應被扣除,因此他們會為了獲取更多勞動報酬付出更多時間與勞動,最終陷入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進行的“強制”勞動之中,這種超強度且隨時待命的勞動過程對勞動者的精神狀態是摧殘性的。最后,在非雇傭關系的數字勞動中,當人們打開任意一個APP時,第一步是要求用戶提供自己完整的身份信息,第二步是同意該APP的所有協議條款,開啟其獲取手機存儲空間和位置信息的權限后,才可以正常使用這款APP。我們在開始使用它開啟互聯網活動之前,就已經失去了自主權,平臺可以根據我們提供的信息進行精準的廣告投放,數字勞動者在各大媒體平臺的引導下無意識接受各種信息并為資本家生產原始的數據信息,這雖然不同于大機器時代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價值的強制占有,但剝削形式卻更為隱蔽。同時,互聯網用戶的線上活動看似是自由自主自愿的休閑活動,實則是個體被迫維持正常社會交往的工具或手段。馬爾庫塞曾指出,真正的自由選擇不僅表現在能否自愿選擇,還體現在可供選擇的范圍。數字技術重構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數字勞動者只能在數字平臺算法構建之下進行“自由活動”,數字平臺如同數字勞動者的監獄,現代人對數字平臺極度依賴,在數字技術對個人的捆綁過程中,生活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個人為了維持自己“社會人”的身份,也不得不沉浸在互聯網的虛擬空間。
(三)數字勞動者與其類本質的異化
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作為類存在物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人才是類存在物”(21)[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人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并與自然界相互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當勞動過程本身發生異化時,其生產的勞動產品發生異化,人與自然的內在統一性也被破壞,人自身的生命活動也與自身相異化,最終會導致“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22)[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4頁。,即只有當人實行動物本能的時候會覺得自由,人實行作為人的本能之時又與動物有著相似之處。馬克思將人與動物的行為進行比較,原因在于人能夠根據自主意識生產并支配著自己的勞動,但卻由于某種原因不得已進行相反的行為,這便使人與其“類本質”相異化。數字勞動看似實現了人“自由和自覺”的回歸,但實質上是資本對人從體力控制轉為腦力控制,從實體控制轉為技術控制,本質上仍然是對人“類本質”的剝離。但是數字技術的發展已經到達馬克思不曾設想過的高度,個人在算法面前變成了提線木偶,主體的類本質似乎由智能算法而非勞動決定。
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資本將數字技術與不同類型的勞動者相結合,使人與自身的類本質發生更為激烈的對抗。首先,在標準雇傭數字勞動過程中,完整的數字勞動過程被分解為零散的部分,勞動場所從生產場域遷至網絡平臺,數字技術發展為一種隱形的力量全方位滲透社會生活,智能化設備取代了相應的人力工作,人們明知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但只能服從數字技術發揮自身純機械部分功能,人最終淪為數字化體系的提線木偶。程序員重復編寫代碼的過程與傳統生產線中可隨時被替換的零件差別無二,外賣員重復高強度的訂單配送服務等,這些行為都是人在自我意識下的勞動,本應作為人感知自身的過程,如今卻成為養家糊口的工作。在這種數字生活境遇中,勞動主體的自主性和延展性日復一日喪失在數字勞動場域中。其次,在更廣泛的非雇傭數字勞動過程中,勞動主體由于被裹挾進資本主義生產,同樣在不斷喪失其主體性。傳統雇傭勞動者存在著明顯的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他們能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勞動的工作屬性,人們有意識地進行著生產活動,但如今由于數字勞動娛樂化的外衣,勞動者無法意識到自己被納入了數字生產體系,無法察覺自己受到剝削。并且,自從數字符號出現在人們生活中,人們幾乎所有的生產生活都離不開數據信息,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人們只有依靠“健康碼”“行程碼”才可以完成正常生活交往與社會工作,如果一個人出門忘記攜帶手機等通訊工具,便會陷入無盡的焦慮與孤獨甚至感覺與世界相疏離。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失去自己作為自由自覺的形式與人的類本質相異化,人們在數字生活中逐漸無法決定自己的勞動過程而成為一種“數字人”。“數字人”還表現在人們的思想逐步被數字媒體所引導和控制,人們逐漸失去自己的自主性與反抗意識進而迷失自我。隨處可見的“低頭族”以及沉迷虛擬世界的“賽博人”,看似是其遵從自主意識在各大社交軟件進行自由的表達,但表達的前提是“數字人”已完全臣服社交平臺的數字運行邏輯。加之數字媒體鋪天蓋地的文化觀點灌輸,人們的所思所想并不一定是自己的真實感受,人的潛意識已經受到數字媒體的影響并逐漸屈服于這種數字異化形式,所謂的個性的釋放與張揚也不過是數字同化的結果。人們的生活習慣或偏好也被抽象為一系列數字符號,但深受數字異化的人們對此依然深信不疑,堅定這是真實的自我的呈現過程,由此,人的“類本質”即人的創造性與自主性逐漸被數字異化所消解。
(四)數字勞動者與主體間的異化
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23)[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8頁。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生產出勞動產品,但勞動過程不屬于勞動者自己,勞動產品也作為與勞動者本身相對立的存在,那么勞動過程與勞動產品屬于誰?勞動者在進行有意識的活動時為什么不創造屬于自己的勞動產品。馬克思通過進一步分析指出與人相異化的勞動產品與勞動過程不屬于神或者自然,只能是存在著有別于勞動者自身的存在物,勞動者在生產出對象化勞動產品的時候,也生產出了統治人自身的異己力量。馬克思又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24)[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3頁。,這便是馬克思所表述的主體間異化最直接的表現。在傳統雇傭勞動關系中,勞資關系之間存在嚴重的異化狀態,勞動者被資本家所操縱與控制,形式上的平等無法掩蓋現實的不平等,如今的數字勞資關系依然無法擺脫異化的宿命,并且營造了一種“數字交流”的場景,這是更深層次的人與人之間的異化。
首先,在標準雇傭數字勞動過程中,數字勞動資料與數字勞動產品被資本家無償剝奪,數字勞動者經受精神與體力的雙重折磨與數字資本家的享受與放縱形成鮮明對比,加之數字資本家對數據的壟斷加劇了社會的信息鴻溝,許多低層次的技術工作被數字機器所取代,廣大數字勞動者更難改變現存生存狀態進一步實現階級跨越。其次,在靈活雇傭數字勞動過程中,主體間的異化表現在三方,即數字勞動者、數字平臺與數字服務對象。一方面,在數字勞動者與數字平臺之間的異化關系尤為突出,作為一種新型數字勞動關系,數字資本平臺以“代理”的方式通過“轉包”獲取大量廉價勞動力,一旦數字勞動者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數字資本便可以通過宣稱自己并未與其簽訂勞動合同或通過各種“簽署條文”等方式轉移自身責任,數字勞動者投訴無門,處于絕對劣勢的地位。另一方面,數字勞動者與其服務對象之間的異化關系,數字資本家通過數字平臺可以實時監管數字勞動者的行動軌跡,并形成一系列監督評價機制,比如美團、滴滴等,伴隨著評價指標的苛刻,數字勞動者為增加績效被迫延長時間和提高效率,并且這種機制引導數字勞動者認為自己的勞動報酬與其所服務的對象息息相關,一旦被服務對象給出差評,數字資本家便成功將自己與數字勞動者的矛盾轉移到市場中,長此以往必將加速勞資關系的失衡與異化。最后,以互聯網用戶為主的非雇傭數字勞動中,各主體間的社會交往關系也出現分離異化的狀態。由于此類數字勞動的自愿性與剝削形式的隱蔽性,非雇傭數字勞動過程所生成的數據資源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更為嚴重的是,社交媒體將個人束縛在“數字圍城”中,關閉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通道,進一步阻礙了人的現實社會交往。以Facebook為代表的數字社交媒體為了提升用戶黏度以鞏固自己平臺地位,吸引用戶在網絡虛擬空間營造自己的“完美人設”并為用戶設置過量的社交需求,由于用戶收到正反饋,足不出戶便可在互聯網世界中獲得極大的精神滿足,長此以往便會自我封閉進而厭倦復雜的現實社會交往行為。由于用戶長期處于虛擬社交場景之中,表情包、流行語等無形中破壞了個人的語言邏輯,而一旦其處于面對面的現實交流中便會手足無措,在網絡中熱情、活潑,在現實中卻冷漠、疏離,這是更深層次的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同時,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將代際差異拉大,ETC(電子收費系統)取代了保持微笑的收費人員,線上購物取代了實體商店,線上學習與工作也的確給人們帶來了便利,但我們仍能看到不會使用移動支付設備而選擇柜臺排隊支付的中老年人,這使得沒有跟上數字化時代的人面臨尷尬處境,他們與年輕人的交流也將形成深層次壁壘。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所說,“社會的、種族的或者經濟的力量在如今都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力,代際差異才真正舉足輕重。現在年輕人是富有者,而老年人是匱乏者。”(25)[美]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38頁。
三、數字勞動異化的消解路徑
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數字勞動的異化現象愈發深入和嚴峻,并將在一段時期內與人類共存,數字技術原本可以為人類帶來更多福祉,卻因資本邏輯的控制成為數字勞動異化的工具。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資本運行邏輯存在,數字勞動的異化便不可能真正消失,為此我們有必要遵循馬克思資本批判的總體性方法,重審數字勞動的異化,為消解數字異化探尋新的方案和路徑,以期有效利用數字技術造福人類,重塑人在數字時代新的生存方式。
(一)喚醒“數字人”主體意識,以人本邏輯超越資本邏輯
喚醒“數字人”的主體意識,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時代課題。如今海量的數據并未讓人成為真正自由自覺的個體,反而將人納入數字生產體系之中,受到桎梏的不僅包括“碼農”等標準雇傭數字勞動者,也包括互聯網用戶在內的大量非雇傭數字勞動者,數字勞動者們都無意識的、欣然地接受數字資本家的剝削。找尋數字勞動者迷失的主體性,在實踐中消解數字化生存的交往困境,對破解數字異化的困境至關重要。
喚醒“數字人”的主體意識,首要的便是理清人與數據的主客體關系。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認識對象是客觀實在,然而如今“數據”成為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數字化認知與表達,除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之外,人工智能、虛擬實踐等進入大眾視野成為新的認識客體,可以說數字技術變革了哲學的研究客體和認識對象;而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認識主體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不再局限于感覺器官,而是通過數字技術依托計算機等物質載體滿足包括社交、消費等一切精神需求,認識主體的范圍似乎也被拓寬,但實際上數字技術只是作為高效便捷的實踐中介,數字網絡空間只能作為人認識世界的工具無法代替人的主觀能動性,只有“現實的人”、具有主體性的人才是真正的認識主體。但人作為主體的地位和發揮主體性的作用不是從來就有和永恒不變的,伴隨著客體的力量即“數據”對人的控制和侵蝕不斷加深以致超出主體的掌控,人類主體更應警惕自己的生存狀況,強化并鞏固自身作為認識主體的根本性地位,盡管數字技術為人們提供了超現實的體驗,但人的認識和實踐是無限發展的,人類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不斷開拓新的需要,真正擺脫數字技術的控制,將自己塑造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新主體。
喚醒“數字人”的主體意識,遏制數字交往異化對人主體性的控制,需要在社會交往實踐中消解數字化生存的交往困境,重塑個人精神交往與價值追求。馬克思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起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自身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26)[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51頁。馬克思在此明確,從事精神交往的主體并非是孤立的個體,而是基于現實需要從事生產實踐活動中的現實的個人。但是如今社交軟件等虛擬平臺交往方式成為數字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交往活動已逐漸脫離現實歸于虛擬,我們有必要回到馬克思的交往觀方面探究數字交往異化的困境。這要求我們正確看待自身的交往需求,虛擬平臺社交可以成為自身發展的工具,但不能讓其成為自身的全部追求,我們可以在現實中關照人的需求與問題并滿足生理與心理的需要,而非將現實需求訴諸網絡。同時,要加強數字勞動者自身教育,普及相關勞動保障制度與法律知識,及時更新數字儲備知識,提高公民的數字素養,引導數字勞動者樹立正向的情感交流意識,實現公民在復雜多元的數字化交流中保持初心與理智;推進建設便民利民的數字服務圈,在積極維系現實社會關系過程中,將自身的需要從網絡拉回現實,在實踐中正確認識和完善數字身份,以此消解數字技術對人在交往中的異化與宰制。
(二)重構數字生產關系,解放數字生產力
數字勞動異化根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并未改變數字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化數字生產的基本矛盾,只要數字技術處于資本邏輯控制之下,就永遠成為數字資本統治的工具。無論數字勞動是否與資本家存在雇傭關系,最終數字勞動者所創造的數字勞動產品都會被數字資本家無償占有并以高價出售,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27)[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1頁。。因此只有在根本上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重構畸形的數字生產關系,才能將數字技術從資本的束縛中解放,才能讓數字勞動者平等占有生產資料與勞動產品,才能實現數字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
歷史證明:哪里存在剝削,哪里就存在反抗。數字勞動者作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新型無產階級同樣承擔著反抗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新的數字生產關系的使命,覺醒了的數字勞動者具有了對數字勞動產品的主人翁意識,開始反思數字勞動產品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合理性問題。重構數字生產關系首先要明確數字勞動產品所有權的歸屬,數字平臺以其提供的服務為由拒絕對用戶提供報酬,但這并不能成為其剝奪甚至壟斷數字生產資料數字產品的理由,數字勞動者因其勞動實質理應得到勞動成果或者基于勞動產品的利潤分配,但僅僅是明確數字勞動產品的歸屬一定意義上是肯定私有財產存在的合理性,無法消除數字勞動異化形態。馬克思根據異化勞動的工具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財產問題,深度剖析勞動產品的歸屬問題,闡釋了揚棄異化的兩個步驟:“第一步是以私有財產的初步揚棄作為中介,第二步是揚棄這個中介,在自身基礎上積極發展,達到人的解放和復歸。”(28)熊子云:《〈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概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72頁。因此若要徹底消解數字異化,我們需要對私有財產進行否定之否定,打破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堅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結合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建立與完善與數字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加強規范有序的數字平臺建設,拓展開放共享的數字公共服務,增加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的優質供給,在對一般數字生產資料共有的基礎之上,才能保證數字勞動者對勞動產品的所有權,通過完善數字勞動保障與法律體系,依法保護數字勞動者的勞動產品,進一步確保勞動分配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釋放數字勞動者與其數字產品生產中的活力。
(三)打造“數字命運共同體”,共建共享數字自由
馬克思基于異化勞動的視角指出資本主義共同體的“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所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的共同性。”(29)[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頁。“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系。”(30)[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3頁。馬克思在此基礎上指出要廢除私有制,消解資本主義異化問題,馬克思對揚棄異化指出的途徑是“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31)[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9頁。馬克思這一論斷在如今的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仍行之有效,數字資本異化的根源仍然在于人類共同活動的力量及抽象發展,而消解數字異化便需要現實的人重新駕馭這種力量,駕馭這種力量的組織形式就是“數字共同體”,同時,數字生產資料與傳統生產資料的區別在于它使得共享成為可能,從而使以大數據共享為基礎的“真正的共同體”的建構成為可能。
面對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數字浪潮,只有站在歷史與時代的高度思考全人類共同發展和前途命運,在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理論基礎上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才能彌合數據鴻溝,共建共享數字自由。“‘真正的共同體’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中具有目標指向意義的重要思想,內在蘊含著共享發展理念。”(32)劉卓紅:《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創新》,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96頁。擺脫數字勞動異化狀態的束縛,建設“數字命運共同體”,政府需要加強數字監管,建立數字網絡綜合系統,明確數字各平臺主體責任,加強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數字產業新模式,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數字平臺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要兼顧社會效益,不只提供短暫享樂的信息,還要根據算法為用戶提供深層次的理論思考,滿足互聯網用戶的動態需求,創造出被人民大眾真正需要的數字產品。根據國家規劃,本世紀中葉我國將基本建成三維信息基礎設施,以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助力數字經濟深度發展。此外,中國將初步建構起數字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出臺《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中國不僅多方位推進數字中國建設,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全面貫徹“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在網絡方向的延伸“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方向,致力于推動構建數字共同體,始終秉持“共商共治共享”的理念,讓數字文明造福世界人民。此外中國還持續推進數字空間國際交流與協作,以聯合國為主渠道參與制定數字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構建保護數字要素、處理數字安全事件的國際協調機制,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新絲綢之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等援助,以共同體意識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新模式,全世界攜手共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共建共享數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