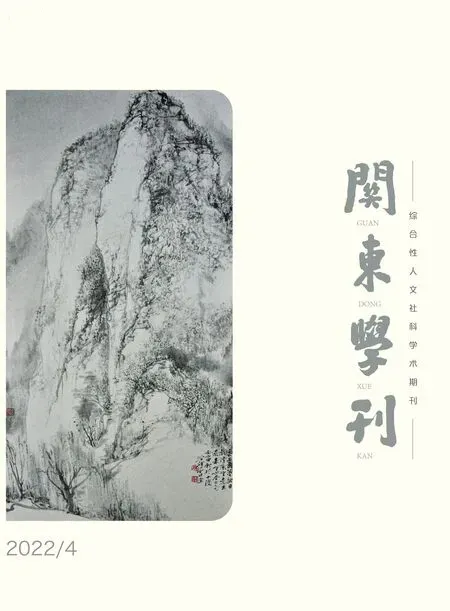芻議馬克思哲學對西方哲學現代性轉向的引領和超越
孟 婷 劉 婷
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以絕對精神運動發展的邏輯圓圈將一切舊哲學囊括在內,在推動形而上學走向巔峰的同時,也將西方哲學置于了“該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馬克思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基于“人的現實”,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變革實現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的徹底超越,展開了對人之存在狀態和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理解。在馬克思引領下西方哲學在批判舊哲學中逐漸將視野回歸人自身,開啟了現代性的轉向并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傳統的批判、反思和揚棄。雖然西方哲學嘗試從解釋世界的形而上學中超拔出來轉而關注人的現實存在境遇,但它對人之語言、人之存在、人之生活世界的詮釋與馬克思仍存有本質差異,這也是馬克思哲學引領和超越西方哲學現代性轉向之所在。
一、馬克思立足“現實的人”引領西方哲學向人的轉向和回歸
形而上學是西方哲學的思想傳統,是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和絕對理念為終極關懷的特定哲學形態。傳統形而上學通過探究“本體”來把握世界,嘗試賦予“本體”以絕對的、終極的、自足的理論性質,由此創造出某種“實體本體化”的理論形態。此種以解釋世界為理論原則來探問外在于人自身的某種實體化本體的哲學必然造成認識論的割裂,即將認識對象異化為認識主體之外的存在,造成世界的“無我化”和“非人化”。抑或說,傳統形而上學在試圖把握現實世界時求助于實體本體,反而人為地將本體世界和現實世界“兩離”,由此一面塑造了抽象的、懸置的、靜態的世界,一面失落了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生活,使其自身異化為脫離人和敵視人的哲學。無論傳統的唯物主義哲學還是唯心主義哲學,無論囿于物質本體而漠視精神的能動作用,還是桎梏于精神實體而遺忘客觀物質世界,都僵持于單一化的實體本體而引致物質與精神的絕對不相容,實質是一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一個時代的終結往往孕育著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伴隨西方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推進,人之存在和發展的異化、物化危機紛涌促使人們對只能解釋世界而無法改變現實的形而上學喪失興趣。當極大成者黑格爾憑借絕對精神的“自給自足”所創造的世界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時,人們便像死狗一樣將其拋棄。關注人的現實存在狀態、關懷人的現實生活世界成為哲學轉向的應有之義。馬克思以“現實的人”為立足點對傳統形而上學展開了“意識形態批判”,從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出發來詮釋人與世界的關系本質,開創和引領了哲學的現代性轉向。馬克思在洞悉世界的自在性存在的同時詮釋人之能動的價值創造,揭示了社會意識與世俗世界之間的真實關系。馬克思不像傳統形而上學一般將世界本源訴諸于某種“超人”的實體本體,而是轉而關懷“現實的個人”“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以人之實踐活動的現實性發掘人與世界二者間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成就,以人之實踐活動的意義開拓性實現對自然的、感性的、肉體的自在存在和具體的、有限的現實世界的不斷超越。由此馬克思從人之實踐活動出發看到了人之生命的自在性和自為性的同一,將有限的、具體的自在生存境遇同超越的自為的能動生命活動耦合起來,把人“當下之所是”的現實狀況同超遠的價值理想統一起來,使人能夠真正立足大地,從現實出發創造出屬人的文化世界。如此,便真正克服了實體本體論思維方式的抽象性、二元對立性和與現實的人相敵對的弊端,引領哲學從“彼岸”到“此岸”,從知識論范式轉向生存論范式,從關注實體本體轉向關懷現實的個人,從絕對理念世界跨入現實生活世界。
正是由于馬克思立足“現實的人”,以人之現實的實踐活動終結了傳統形而上學對世界的實體本體化詮釋,才將人們的視線關注點重新回歸于現實生活世界中的具體的有規定性的人。在馬克思的領路下,西方哲學家們紛紛開始求索如何摒棄傳統形而上學實體本體化的理論思維,實現向現實的人的轉向和回歸,并在對人之存在及其生活世界的解讀方面取得了不容忽視的理論進展。“從總體上看,西方現代哲學強調重新評估一切價值,著力用科學理性的觀點來解釋人,要求揭示人的非理性或超理性存在的意義,關注人類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狀態,并把科學當作哲學的依據,把科學方法當作哲學方法的重要事實依據等,都是沿著馬克思所開辟的新研究域而展開的。”(1)陳永盛:《芻論馬克思哲學引領西方現代哲學研究域轉換》,《理論導刊》2019年第2期。西方哲學在現代性轉向中將人作為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對傳統哲學隔絕人、漠視人的抽象做法給予批判、摒棄和匡正,這與馬克思對現實的人及其存在的關切一致和統一。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在沿著馬克思開辟的現實研究視域和理論視野前進的過程中,西方哲學“矯枉過正”“誤入歧途”,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西方哲學力圖證明自身所具有的變革意義,通過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拒斥”和“重估”來確立起自身的“現代性”,其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態度是十分激進的,結果以一種新的知性邏輯代替了傳統哲學的理論形態,不自覺地構建了另一種形態的形而上學。例如,分析哲學高舉“拒斥形而上學”的大旗,否定一切理論思辨的意義,但最終走向對客觀邏輯的過度推崇;尼采高呼“打碎偶象”“重估一切價值”的宣言,得出價值崩潰的結論,陷入價值相對主義的思想囹圄;弗洛伊德主義否定乃至消解理性主義哲學,將現實世界的自在發展皈依于精神決定論;現象學對傳統知識論哲學“地基”的拋棄以及后現代主義哲學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在場形而上學”的顛覆等。此種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拋棄”看似“徹底”,實質仍同傳統形而上學一樣沒有超越那種脫離實際、脫離人的現實生活的抽象思辨的理論思辨,仍沒有把哲學對人和世界的探究建立在客觀現實的根基之上,扎根在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之上。
二、馬克思實踐語言觀對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的超越
西方哲學對“現實的人”的關懷是通過“語言學的轉向”而展開的。馬克思從生產生活的需要和產物的視角將語言置于現實的人的交往活動、實踐活動之中,克服了傳統形而上學對語言、思維、意識的單一化、抽象化理解,為西方哲學以語言為中介挖掘并理論地表征凝聚在語言中的人的存在狀態提供了思路。
馬克思洞察到語言的實踐本質,將語言定位于實踐活動及其創造的社會關系性產物來詮釋。在馬克思看來,實踐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生成性本質的真理形式,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物質生活過程,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即語言,“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人的意識”(2)[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頁。。換言之,語言在人之實踐活動中逐漸生發和形塑,語言的形成與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物質交換等勞動實踐的需要緊密相連。“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3)[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1頁。;“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4)[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2頁。。人之生產關系的結成和社會關系的拓展要求語言作為橋梁和中介,而語言作為人與人交往和聯系的工具,也成為社會人特有的一種意識并伴隨人之思想的進步而不斷多樣化、豐富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為自己也為別人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5)[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1頁。實際上,語言本身即具有實踐性,通過語言符號進行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人的現實的社會生活在語言的溝通和交流等實踐活動中得以延展。實踐不僅是語言的本質和展開形式,而且也是一種內在的把握方式、思維方式。將語言理解為構成這一生活世界的個人的活生生的感性基礎,實際上就是把語言看作人的本質對象性生成的基礎。這種立足實踐來理解的語言才稱得上“現實生活的語言”,也只有立足于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來詮釋人的語言,才是從語言最本質的基礎——人的實際生活過程出發來開展的哲學思考。因而與其說馬克思在討論語言,不如說是在討論“語言活動”。
西方哲學在語言學轉向中涌現出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思潮。科學主義思潮認為哲學的使命在于“語言治療”和“邏輯凈化”。一方面科學主義思潮對邏輯實證主義、經驗批判主義和自然科學方法的推崇看似將哲學立足于現實的實證研究之上,實質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將哲學異化為科學的“副產品”;另一方面科學主義思潮從活生生的語言活動中抽象出一個穩定的、封閉的語言邏輯系統和科學方法論,將語言觀建立在“無我”的基礎之上,形塑了語言的“無我性”。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科學主義思潮雖然拒斥實體本體論卻仍葆有強烈的還原論色彩。而人本主義思潮雖然力求向人自身的真切回歸,但它對語言的詮釋是從客體的直觀的形式展開的,而不是將其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的創造,因而在語言中所把握到的人之存在只能是某種純粹的能動性和絕對自由,亦不能獲得對人之存在的現實性、本真性理解。此種語言學轉向看似與馬克思哲學一樣既實現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的超越也回歸了現實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但究其實質只是對舊哲學進行語言概念的形式轉換,并沒有真正觸及和解決人的生存異化和生存悖論等現實難題。
在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視野中,語言是人類開展社會交往的中介和橋梁,是人類文明的創造和表征,但卻并非人類的終極關懷和永久棲居之地。因而任何語言作為某種意識形態只能于最大程度上實現對人之現實存在的全面把握和透徹解釋,而無法真正實現對人之現實存在的直接實踐和根本變革。在此意義上,西方哲學通過語言學轉向而實現的對人的關懷只能為人提供暫時棲居之地,卻無法如馬克思哲學一般將人深深立基于現實的實踐的根基之上。
三、馬克思實踐生存論對西方哲學存在論轉向的超越
繼馬克思轉向“現實的人”、關懷人之生存發展之后,西方哲學也開始摒棄傳統形而上學囿于實體本體而遮蔽和漠視人的做法,嘗試構建關于人之存在的哲學體系。特別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派別存在主義直接把“存在”作為哲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關注人的感性存在狀態,追求自由的理想存在境遇。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第一次提出“存在主義”這一概念范疇。他將存在和存在者二分,認為人作為存在者存在的同時便蘊含著“非存在”的狀態,并在分析“人向死而在”這一最極端最絕對的可能性存在狀態中追問人生在世的意義。一方面海德格爾提出人之生命的有限性決定了人之存在本身的無意義,一方面他又嘗試在自我選擇、自我創造和自我成就中創造和探尋人之存在的意義可能,在此基礎上他將對自由和個性的尊重作為人之存在的根基。同樣標榜人之自由和個性至上,并推進存在主義進一步繁榮的是薩特。他將人之存在劃分為自在存在和自為存在,并立足人之自為存在的立場在有限生命存在基礎上力求拓展人之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寬度,從人之自為存在的不斷超越中得出人乃“存在先于本質”的“存在者”。正是“存在先于本質”的特性決定了人不可能受先天存在狀態的束縛而可以在自由選擇中創造和豐富自我的個性本質。存在主義的思想實際上在神秘主義和唯意志主義那里便已萌芽。克爾凱戈爾的存在主義思想帶有強烈的基督教教義色彩,他拒斥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批判一切否定人之存在、地位和尊嚴的思想體系,提出人乃世間唯一確實可靠的實在。他進而高度推崇人的個性、人的心理體驗和主觀意識并將其作為人之最基本的存在方式。雅斯貝爾斯繼承克爾凱戈爾的存在主義思想,關注人作為“此在”的當下生活危機并洞悉到人之生存自由的有限性,在如何超越有限存在的路徑上強調借助內心體驗完成自我超拔達于完滿。尼采同樣要求肯定人之存在的意義,他一面振臂高呼“上帝死了”,一面將人的存在價值訴諸“超人”的“強力意志”,陷入了非理性主義和唯意志主義的思想牢籠。存在主義一面表達對個體選擇、個體自由、個體意志的絕對追求,一面譴責科技理性的擴張給人之存在和社會生活帶來的意義危機,但在一定程度上漠視了科技理性對社會發展的進步作用,同時還因對人之存在的絕對能動性和絕對自由性的過分推崇而遺忘了作為現實的、具體的人之存在發展的社會歷史制約性,走向了彰顯自我中心主義、非理性主義的另一種極端。
馬克思從人之實踐活動出發去理解一切存在及其價值。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存在”與“存在者”的內在統一性、不可分離性,同時又現實地、歷史地揭示出存在者的存在活動、存在狀態、存在過程和存在發展趨勢。“人的對象性活動”是馬克思對人之存在理解的立足點。立足人的對象性實踐活動,自然不再是純粹的自在存在,而是現實的、具體的人生存于其中并通過對象性活動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展開為“自然界的生活”;人不再是抽象的自我意識、絕對精神或抽象自由的化身,而是從事物質生產等現實活動、推動社會歷史前進并以自身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發展旨趣的“有規定性”的人;社會不再是“無人”的抽象的實體存在物,而是在人的對象活動中歷史性生成延展的人類文化共同體。如是,存在者作為對象性活動的現實的個體,是自然存在物、類存在物、社會存在物的統一,他既在活動中存在,在自然和群體中存在,更在人創造的關系和歷史文化中存在,并跟隨社會歷史的進步而始終處于不斷生成的未完成狀態。自然、人、社會在對象性活動作用下實現了生存論意義層面的統一。
質言之,馬克思的生存論實質是一種實踐生存論,它表明了人通過實踐活動在社會歷史中創生和發展的狀態,最恰當地反映了人之生存的本真性和未竟性。當西方哲學僅僅從理論上單向度、抽象化、絕對化地理解人之存在而使其生存論轉向陷入理論困境之時,馬克思的實踐生存論卻彰顯了一條擺脫理論困境的實踐向路。
四、馬克思“現實的生活世界”超越西方哲學“意識到的生活世界”
傳統形而上學對生活世界的理解實質是一種“無人”的純粹本體世界。它囿于兩個極端,一個是漠視生活世界的理想性、能動性和超越性而給予其不可撼動的自在性、自然性和客觀性,推崇自然的絕對優先地位;一個是立足人之超越性的維度跨越生活世界的自在性而從絕對精神、絕對理念的能動性出發實現對世界的統一化詮釋,將現實的生活世界化身為某種精神實體、理性實體的世界。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人在其中的現實世界。馬克思在批判傳統形而上學“本體世界”的基礎上力圖將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于現實的生活世界中追求生存意義和價值支撐。西方哲學在馬克思理論視野的引領下從形而上的理念世界轉向現實的生活世界,從諸多維度展開了對生活世界異化的憂慮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但在對生活世界的理解范式進而如何轉向生活世界的進路問題上,馬克思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存有本質差異。
生活世界是現象學流派的核心研究范式。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一書中首次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范疇并呼吁哲學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但他卻常常將生活世界桎梏于意識活動的限域將其化身為“意識行為相關項”。維特根斯坦與晚期胡塞爾幾乎同時提出有關生活世界的理論,他將“語言述說”“語言活動”定義為一種“生活形式”,并主張“通過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來解決“哲學的問題”和“時代發展的疾病”。表面上看,向生活世界回歸的問題已然解決,實際上他只為人們提供了某種“精神的避難所”,通過拒斥科技理性而把生活世界歸結為某種人的情感體驗,一定程度上用理性或情感遮蔽了現實生活,故而一旦將這種理論探入現實便瞬間失去了說服力。
馬克思不再通過各種解釋世界的原則在真實的生活世界之外構建某種虛幻的世界,而是直面現實生活世界本身,發掘生活世界的異化現狀并秉持問題意識,敏銳地捕捉到人之異化的根本緣由,主張“改變不合理的現狀”,對生活世界中的諸種異化及其背后的不合理社會體制展開“無情的批判”,在批判舊世界中構建新的美好生活世界。當西方哲學在現代性轉向中將人的實踐活動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而使生活世界脫離了現實根基的同時,馬克思以人的勞動實踐為基礎展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突出強調實踐活動對于生活世界的基礎性。立足于實踐,人創造并推動著生活世界的發展,人向生活世界敞開,生活世界亦向人敞開。在人與生活世界的雙向開放包容中,人開拓著生活意義的豐富性。如是,人不再是某種抽象的意志或情感的集合,而是創造和推動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世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而然的自在存在,而是載負著人的目的性要求的充溢意義和價值的屬人的現實生活世界。抑或說,生活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成和發展的世界,是由人說出、為人把握、被人所感觸到的世界。馬克思立足于實踐對生活世界的詮釋,既昭示出生活世界對人的現實性,也表達了生活世界所內涵的理想意蘊,這種經驗與超驗的統一彰顯出生活世界的完整意義和詩意價值。
西方哲學雖然通過關注現實的人轉向對生活世界的關懷,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生活世界對人而言的內在性和意義性,但沒有把握住生活世界的現實基礎,此種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只能是思想意識層面的回歸,而非現實層面的回歸,表現出回歸的不徹底性。正是由于對生活世界的理解缺失了實踐的向度和現實的根基,因此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生活世界的社會歷史之維和其中蘊含的有關人類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訴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馬克思哲學所詮釋的生活世界稱之為“現實的生活世界”,而將西方哲學轉向的世界稱之為“意識到的生活世界”。
結語
自馬克思開啟的西方哲學的現代性轉向通過關注現實的人和人的現實生存境遇嘗試向人自身的回歸。馬克思哲學立足現實的人,通過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變革實現了在語言觀、生存觀和生活觀層面的徹底革命,既克服了傳統形而上學絕對不相容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也超越了西方哲學在現代化轉向中對人之存在和人之生活世界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馬克思哲學實現的是“思想的革命”,而西方哲學的現代性轉向僅是一場“思想的變革”。對于馬克思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的關系問題關涉馬克思哲學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定位和價值問題,亟待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