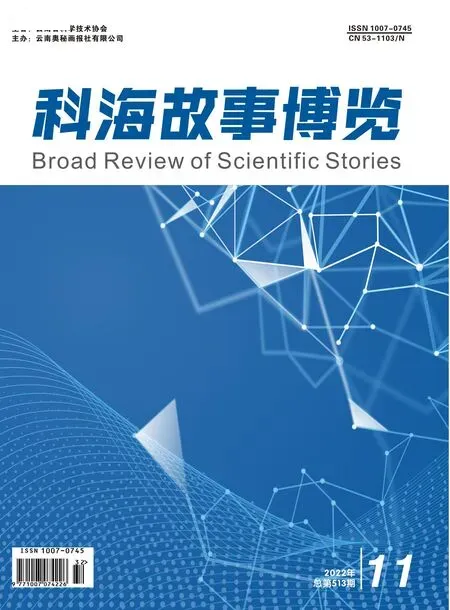5G 技術(shù)下對數(shù)字代溝的影響及對策
祝錦俊
(廣東技術(shù)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曾提出:媒介即訊息。認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信息,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nèi)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質(zhì)、它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所帶來的社會變革。
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shù)(5th-Generation,以下簡稱5G),具有高速率、高可靠性、低時延、低功耗等特點。隨著5G 技術(shù)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應用得以實現(xiàn),如“5G+4K/8k 直播”“5G+AR/VR”“5G+物聯(lián)網(wǎng)”等新應用形式的出現(xiàn)、普及,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革命性變化,也打開了公眾對未來的無限想象。但“數(shù)字代溝”問題正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加劇和5G 技術(shù)的發(fā)展而逐漸嚴峻起來。本文擬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分析5G 技術(shù)是如何擴大數(shù)字代溝,以及社會該如何來彌合已經(jīng)被擴大的數(shù)字代溝。
1 5G 技術(shù)下的數(shù)字代溝呈現(xiàn)
代溝是指“由于時代和環(huán)境條件的急劇變化、基本社會化的進程發(fā)生中斷或模式發(fā)生轉(zhuǎn)型,而導致不同代之間在社會的擁有方面以及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的選擇方面所出現(xiàn)的差異、隔閡及沖突的社會現(xiàn)象。”數(shù)字代溝,是數(shù)字鴻溝在代際層面的一個表現(xiàn),主要指存在年齡差距較大群體之間的代際數(shù)字鴻溝,表現(xiàn)為父母(親代)與子女(子代)在新技術(shù)采納、使用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知識方面的差距,是傳統(tǒng)代溝在數(shù)字時代的延伸。[1]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分為“接入差距”和“使用差距”兩個方面,作為數(shù)字鴻溝下的一個子領(lǐng)域,對數(shù)字代溝的研究也將沿用“接入差距”和“使用差距”兩個方面。成長于傳統(tǒng)時代的親代和成長于新時代的子代,在諸多方面存在著鮮明差異,因此兩代人在融入5G 時代的進程中,存在著明顯的數(shù)字代溝。
1.1 5G 技術(shù)擴大“接入”差距
數(shù)字代溝的第一道溝是“接入溝”,結(jié)合荷蘭特文特大學傳播學系榮譽退休教授簡·凡·迪克(Jan A.G.M.Van Dijk)的“接入”的概念,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進行分析。
一是精神接入,由于個體行為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xiàn)象,因子代與親代成長年代不同,當他們成年后依舊會保留其青年時期所養(yǎng)成的行為特性,這導致親代與子代在新技術(shù)的接入上出現(xiàn)了精神接入差異。《第50 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 年8 月,我國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規(guī)模為10.47 億,其中10~19 歲占比13.5%;據(jù)《中國移動經(jīng)濟發(fā)展報告》顯示,我國人均擁有1.3 張SIM 卡。[2]根據(jù)以上推算,我國10~19 歲用戶約有1.41 億,九成青少年從小就開始接觸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證明親代在青年時期,他們習慣了通信技術(shù)的升級換代,也對通信技術(shù)的迭代具有濃厚興趣;而親代,特別是年齡越長的老年人,其青年時期較少地接觸互聯(lián)網(wǎng)絡,他們習慣了不依靠互聯(lián)網(wǎng)絡的生活,因此他們對技術(shù)升級換代的關(guān)注度相對較低。
二是物質(zhì)接入,由于4G 手機無法使用5G 網(wǎng)絡,因此想要接入5G 網(wǎng)絡,需要更換最新的5G 手機或其他5G 上網(wǎng)設備。據(jù)學者王飛等人在2020 年對河北省唐山市某老年大學的問卷調(diào)查顯示,60.6%的老年人更新手機的時間在2 年及以上,僅7.4%的老人更換手機周期低于1 年,由于該調(diào)查的樣本來自唐山市的某老年大學,唐山市是河北省GOP 的前三,老年大學抽查的樣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可以推測老年人手機更新周期在欠發(fā)達地區(qū)可能更糟。據(jù)學者王恩豪對河南省輝縣市B 村的調(diào)查顯示,農(nóng)村老年群體使用智能機比例較低,有80%調(diào)查對象未能接入智能手機。[3]此外,當前5G 上網(wǎng)的網(wǎng)絡資費較高,對于習慣節(jié)儉生活且尚未養(yǎng)成流量消費習慣的老年群體來說,這也是阻礙他們接入5G 網(wǎng)絡的原因。
三是技能接入,由于智能手機大多是為年輕人設計,字體顯示較小、系統(tǒng)操作較為復雜,對于老年群體來說,他們熟練掌握智能手機的功能會比較困難;日常生活中,老年群體缺乏對智能手機使用的交流與培訓,導致親代和子代在手機使用的技能上拉開差距;有很大一部分年長的老人,由于識字能力不佳,而無法看懂操作界面,導致他們無法使用智能手機;又由于文化中的“面子”問題,親代容易礙于情面,而不愿意過多地向子代請教,這也就加劇了親代與子代在技能接入上的差距;此外,由于老年人的健康原因,導致老年人在學習使用智能手機方面的進度比較緩慢。從上述原因看,種種可能的問題導致了親代在技能接入方面嚴重落后于子代。
四是使用接入,老年群體對5G,甚至是4G 技術(shù),僅僅停留在對搭載該技術(shù)的手機的使用上。而他們對手機的使用,主要用作電話與收發(fā)短信、微信。對于該群體,日常生活中,他們能夠使用該技術(shù)的機會非常少。在生活中使用依托5G 技術(shù)來實現(xiàn)的功能的機會較少,因此他們對技術(shù)的升級換代不太敏感。
1.2 5G 技術(shù)下的“使用”差距
當前討論有關(guān)5G技術(shù)的應用,主要指5G智能手機,數(shù)字代溝的“使用”差距,指親代與子代在5G 智能手機的使用上存在著使用鴻溝。
從手機功能的使用來看,據(jù)學者王飛對河北省唐山市某老年大學的調(diào)查顯示,電話功能是老年人使用最多的手機功能,占比69.14%;其次是拍攝、瀏覽新聞資訊,均占比61.14%;再次是即時通訊工具,占比54.29%。而與5G 技術(shù)應用關(guān)聯(lián)最精密手機游戲、在線教育、地圖定位、直播等功能,在老年群體中的使用比例微乎其微。[4]
對于手機游戲、在線教育、直播等功能的主要用戶年輕人來說,他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更愿意去更新上網(wǎng)設備。據(jù)個推大數(shù)據(jù)發(fā)表的《5G 手機首批用戶畫像報告》顯示,25~44 歲用戶占總5G 用戶的86.1%,這個年齡段是5G 技術(shù)使用的主力軍[5]。因此,從“使用溝”上,子代和親代拉開了差距。
2 彌合5G 技術(shù)擴大數(shù)字代溝的應對策略
2.1 鼓勵文化反哺,加強代際互動
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出“三喻文化”,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年輕人要向年長者學習;“并喻文化”指同輩間的學習;“后喻文化”指年長者向年輕人學習。由于技術(shù)的發(fā)展,社會逐漸過渡到數(shù)字化時代。學者普倫斯基(2001)用“數(shù)字化移民”(親代)和“數(shù)字化土著”(子代),來表現(xiàn)兩代人在新媒體技術(shù)運用上和數(shù)字化生活方式適應上的代際沖突。這種代際間的沖突也必然導致“文化反哺”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文化反哺”這一概念最早由我國學者周曉紅提出,它是在疾速的文化變遷時代所發(fā)生的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進行廣泛的文化吸收的過程,是一個和“嗷嗷林鳥,反哺于子”的生物現(xiàn)象十分相似的文化現(xiàn)象。
5G 技術(shù)普及的時代,也是一個“后喻文化”時代。親代應虛心向子代學習,子代應耐心為親代解惑。家庭,是老年人學習信息技術(shù)的最好學校,和諧的代際關(guān)系,能夠很好地促進老年人對5G 技術(shù)的接入。子代做好“文化反哺”,積極和親代進行教學互動,鼓勵他們?nèi)ナ褂?G 手機,讓他們對5G 技術(shù)充滿信心,消除他們的觸網(wǎng)恐懼。同時,子代也要為親代提供一定的物質(zhì)支持,幫助他們的智能手機升級換代,實現(xiàn)在硬件上推動他們?nèi)谌?G 時代。
美國的老年人網(wǎng)絡中心主張利用“代際互動方法”來彌合數(shù)字代溝。該方法通過招募高中生和大學生志愿者,組成教學團體去指導老年人掌握計算機基本使用技能。面對我國存在的數(shù)字代溝問題,該方法值得借鑒和實踐。[6]
2.2 整合社區(qū)力量,開展數(shù)字素養(yǎng)教育活動
伴隨著我國城鎮(zhèn)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人口的日益老齡化,我國“空巢老人”現(xiàn)象也日漸嚴峻。據(jù)智研咨詢發(fā)布的《2019-2025 年中國老年健康服務行業(yè)市場全景調(diào)查及投資方向研究報告》數(shù)據(jù)顯示,2020 年我國預計有1.2 億空巢老人。在彌合數(shù)字代溝問題上,空巢老人很難從子代那里獲得數(shù)字素養(yǎng)和數(shù)字技能的訓練。[7]
面對該現(xiàn)狀,社區(qū)應當采取一些行動,可以在社區(qū)內(nèi)開辟一個學習角,組織老年群體學習信息技術(shù),提高媒介素養(yǎng);征集社區(qū)志愿者,為老年群體開展多種形式的數(shù)字培訓;在社區(qū)內(nèi)開辟一個聊天角,為老年人交流如何使用手機提供方便,通過老年群體的內(nèi)部交流,有助于發(fā)揮同齡人里的榜樣作用,更有助于消除老年人的觸網(wǎng)恐懼。
2.3 政府政策引導,幫助老年群體融入5G 時代
當前的政策引導主要集中在技術(shù)層面和應用的普及方面。2018 年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基建”;2020 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diào)加快5G 網(wǎng)絡、數(shù)據(jù)中心等“新基建”進度;3 月工信部發(fā)布《關(guān)于推動5G 加快發(fā)展的通知》,圍繞5G 推進“新基建”;4 月國家發(fā)改委首次明確新基建范圍:在信息基礎(chǔ)設施、融合基礎(chǔ)設施、創(chuàng)新基礎(chǔ)設施3 個方面內(nèi)容,并作為“兩新一重”寫入當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提出:加強新型基礎(chǔ)設施建設,發(fā)展新一代信息網(wǎng)絡,拓展5G應用。[8]2021年,工信部起草編制了《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 年)》,以大力推動5G 應用。這些政策,在5G 與5G 應用普及方面,能夠較好地縮小5G 網(wǎng)絡覆蓋差距和數(shù)字鴻溝,促進更多的用戶融入5G 時代,同時發(fā)揮公共基礎(chǔ)設施在提升老年人數(shù)字技術(shù)水平方面的作用。但是當前,專門針對老年人融入5G 時代的政策尚未成熟,4G 時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明顯的代際鴻溝,5G 時代這種“舊溝未平,新溝又起”的現(xiàn)狀將繼續(xù)存在。為此,政府應當注意到這一問題,制定專門政策,引導市場關(guān)注老年人的數(shù)字需求。
2.4 加強媒體關(guān)注,設置數(shù)字代溝議題
在彌合數(shù)字代溝上,主流媒體應對數(shù)字代溝議題給予一定的傾斜性關(guān)注。在老年人數(shù)字代溝議題上,媒體可以借鑒“建設性新聞”的報道方式。“建設性新聞”,是丹麥記者烏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在2008 年首次提出的理念,他主張建設性新聞不僅報道新近發(fā)生的事情,揭露社會問題,也要啟發(fā)觀眾以更加樂觀積極的態(tài)度面對未來,因此新聞報道應引入社會反饋機制,提出對策、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9]
面對日益凸顯的數(shù)字代溝問題,主流媒體應當對老年群體給予一定的關(guān)注和報道,以此來提高相關(guān)議題的全民關(guān)注度和討論熱度。增加有關(guān)老年人數(shù)字生活現(xiàn)狀的報道,幫助他們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以此呼喚全社會對老年群體數(shù)字生活的關(guān)注,有利于全民對該問題的認識,進而促進相關(guān)政策的出臺、優(yōu)化。
此外,在建設性新聞的實踐過程中,公眾不僅具有討論的話語權(quán),還具有參與權(quán)。主流媒體在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的同時,也要積極引導相關(guān)議題的發(fā)酵,讓公眾參與進來建言獻策,以此來為解決問題提供多元視角,并推動問題的合理解決。[10]
3 結(jié)語
由于5G 技術(shù)剛剛開始民用化普及,當前對5G 技術(shù)造成的數(shù)字代溝,主要體現(xiàn)在親代與子代在5G 智能手機的“接入”與“使用”上。從“接入”方面看,老年人對新技術(shù)的使用意愿不太強烈;他們的上網(wǎng)設備較子代而言明顯落后;老年人在智能手機使用上也存在著技能不足的問題;老年人的生活習慣造成他們在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機的機會較少。從“使用”方面看,當前針對老年人的應用較少,舊技術(shù)下的智能手機便能滿足老年人的數(shù)字需求,進而導致難以融入5G 時代。彌合數(shù)字代溝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首先是家庭內(nèi)部的文化反哺;其次是動員社區(qū)力量;再次是政府的政策引導;最后是主流媒體對數(shù)字代溝議題的傾斜性關(guān)注。在多方主體共同努力下,才可有機會縮小數(shù)字代溝,讓老年人更好地融入5G 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