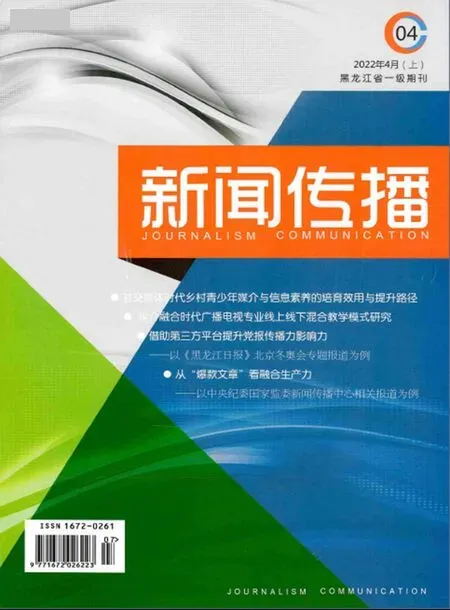“在農廣播”:應急廣播的媒介化鄉村治理
劉王平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江蘇 210023)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原本“消音”的農村廣播重回大眾視線,只不過其身份由扮演組織與教育的高音喇叭變為服務與宣傳的應急廣播。我國廣播從1940年發軔,80多年來,農村有線廣播將黨和國家聲音傳遍鄉村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鄉村治理中最重要的媒介。
媒介依靠其特有的技術特征,溝通各個主體達成集體協商,實現治理效果,這種媒介實踐被理解為媒介治理。肖恩認為媒介治理是公民社會的自我治理與完善、政府的監管與共治、跨國家機構和組織的跨文化治理。[1]但不同于西方世界,中國的媒介無疑是一種“治理技術”。“媒介在權力結構中運作,從而構成了權力的組成部分”。[2]媒介發展會受到政治邏輯的支配,媒介發展的過程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媒體不斷被納入治理體制的過程[3]。因此鄉村媒介治理便是國家依靠政治邏輯策略性選用媒體、并使之成為服務于鄉村治理改革的過程。媒介治理超脫于前述肖恩的三個層次,而是伴隨權力運作散布在鄉村生活的各個層面。
當前在鄉村振興的全面推動與基層治理改革之際,應急廣播建設和疫情高音喇叭的“硬核式喊話”使得鄉村廣播呈現回歸的趨勢。復歸廣播的角色與功能出現很多新的轉變,并給鄉村治理帶來很多創新亮點。但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有線廣播建國后的政治功用,以及考察其衰落動因。少數研究分析農村有線廣播回歸對鄉村治理的作用及復歸動因。因此,本文試圖吸納“國家與社會”的框架,從媒介化治理視角出發,考察農村應急廣播的回歸,探討當前農村應急廣播發揮的治理效用,對優化鄉村治理乃至推動鄉村振興具有建設性價值。
一、農村有線廣播的復歸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進行鄉村治理改革,新的鄉村治理框架更強調社會自治、公共服務、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4]因此,為實施基層社會治理、實現鄉村振興,建設平等開放、多元共治的鄉村媒介工程被提上了日程。當前,我國除了繼續推進“村村通”基礎工程、電影放映工程、縣級融媒體中心打造以外,應急廣播建設同樣是黨和國家的重點工作。
2013年《推進國家應急廣播體系建設工作方案》出臺,應急廣播建設的目標任務、工作分工和進度安排被明確。農村有線廣播“改頭換新面”,經再組織、再整合成為應急廣播,陸續在田間地頭重新奏響。同年12月3日,中國中央廣播電臺國家應急廣播中心揭牌,應急廣播中心網站上線,標志著我國應急廣播體系進入全面建設階段。[5]2014年陸續在四川、廣西進行試點實驗工作。隨后廣東、浙江、江蘇等著手建設應急廣播。到了2020年底,全國已有23個省及自治區開展了應急廣播體系建設工程。農村有線廣播不僅全面復歸,而且其功能與角色發生了重要轉變。
二、“在農廣播”與鄉村服務治理
2013年后新一輪鄉村治理改革向“服務治理”轉變,提出了兩大要求,一是更好地供給多元公共服務,二是更好地協調鄉村主體參與共治。應急廣播的技術特征為滿足“公共服務”與“公共商議”、實現多元共治的鄉村治理提供了可供性。
首先,應急廣播可作為鄉村公共服務媒介,發揮災害預警與抗災指導作用。在四川雅安、云南魯甸地區地震災害發生時,應急廣播發揮發布災情信息、穩定災區輿情、為抗震救災提供支持等重要作用。其次,應急廣播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2017年湖南建設的“村村響”應急廣播成為農村地區宣傳政策、傳播知識、服務日常的重要平臺。此外,滿足各級政府和基層組織的行政管理、主流輿論宣傳,為建設平安鄉村、推進新時代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
最后,應急廣播實現了“公共話語的可溝通”。地方政府及時公開民生信息,有利于鄉村公共話語的形成與表達,達成公共協商。不少村莊通過應急廣播硬核喊話,讓村民知曉“抗疫”政策,及時匯聚民意,打好疫情防控阻擊戰;又或在脫貧攻堅中,基層干部借助廣播同鄉村組織、村民的共同協商,實現產業發展。
具體在媒介化治理實踐中,應急廣播又體現了“雙重在場”的特征:
其一是應急廣播成為鄉村治理的在場參與主體。應急廣播提供了24小時預警、精準信息的傳達,以及鄉土味的信息娛樂服務,成為了協同鄉村組織、個體之間的中介。具體來說,應急廣播“用本地方言播出區、鎮新聞、解讀政策”,在鄉村服務中廣播媒介成了聯系干群關系的“連心橋”。此外,鄉村自制的文化節目,不僅喚起了老人的“集體回憶”,而且成為村民自覺的文化實踐。有線廣播通過富于地域性的文化節目,可以形成較強的文化場域力量,聚合鄉村社會共同體[6]。
其二是應急廣播突出了鄉村主體地位。農村中電視和手機等媒介的盛行,將農民束縛在封閉的自我空間中,使得個體對村莊事務等缺乏必要的敏感。應急廣播作為“掛在天空的耳朵”的公共媒介,在突發事件中制造附近的聲音景觀,將村民集中在同時空的公共事務的知曉與表達上。由應急廣播搭建的公共場域較微信、微博更具地域的開放與包容,可以容納村莊的各層次群體,能夠讓鄉村社會主體同心協力,實現多元共治。總的來看,應急廣播的建設是基層治理模式轉變與鄉村自組織能力提升的彰顯。
三、應急廣播媒介化治理的未來之路
當前,農村有線廣播的確在政治邏輯與媒介邏輯交織中得到復興,但廣播作為聲音媒介,單純依靠其自身的技術革新,無法實現聽眾的互動與表達的需求,無法獨立助力鄉村振興。“應急廣播”的多措并舉,最終仍有可能滑入精神宣傳與信息傳達無效的窠臼,例如疫情期間農村有線廣播的壓力型動員存在“硬核式無力”的問題[7]。而且已有不少研究發現當前鄉村文化凋敝,原因在于其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農民主體性依然難以發揮。此外,農村有線廣播因為聲音瞬時、范圍固定的限制,需要特定的場域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鄉村治理與文化振興的效用。
因此,為更好地推動鄉村振興,鄉村媒介治理需要開拓創新,更好地促進媒介融合,賦予農民表達權,喚起農民主體性,激發農民參與公眾生活的積極性。具體而言,應該努力做到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促進媒介融合,善用鄉村媒介生態。為更大可能地釋放農村有線廣播的媒介治理優勢,需要將農村有線廣播與鄉村在地媒介以及社會化媒介加以深度融合。例如將農村有線廣播與鄉村在地媒介包括電視、布告、宣傳單、口頭傳播等,以及社會化媒介QQ、微信和直播等資源整合,更好地推動農村媒介治理格局建設,實現媒介善治。
其二,賦予農民表達權,釋放農民主體性。除了思考治理媒介的行動之外,也應該從鄉村治理的內部、從國家與社會對話的視角出發,思考農村治理中“參與式傳播”的可能性。這就需要開拓創新鄉村傳播媒介形式與內容,在發揮主流輿論引導的同時激發農民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性。傳播形式與內容不僅要讓村民聽得懂,還要讓村民喜聞樂見,更是要培育鄉村治理主體參與鄉村共同體事務的能力與信心,推動鄉村“三治格局”的建立。
總之,在多元共治的鄉村治理邏輯中,農村有線廣播被賦予了應急服務、日常服務以及主流輿論引導的多重功能。但未來如何更好地助推鄉村振興,農村有線廣播仍亟須探索一條適宜的媒介深度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