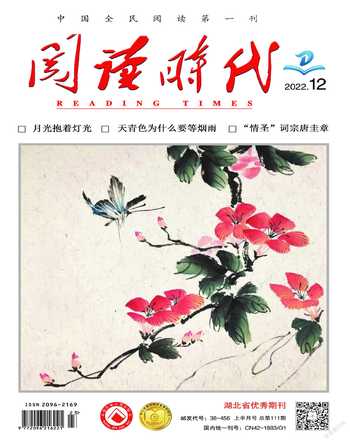讀書是一輩子的事
孫功俊
“讀書是一輩子的事”這句話,在我剛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對我說過多次。父親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沒上過學,用他自己的話說,“扁擔長的一字都不認識”。他出生在一九四九年前,小時候連溫飽都成問題,更談不上上學讀書了,這也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因此,父親后來就特別在意子女們上學讀書的事,常掛在他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兄弟倆要好好上學,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書讀好了才會有出息,不要和我一樣是個睜眼瞎子。”
在父親的心中,讀書就意味著有出息。可我小時候不懂事,更不明白父親說這些話的真正含義,反而覺得上學讀書是件很累人的事。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走兩里多的路到學校,課堂上要規規矩矩坐著,不能來回地走動;放學回家后還要做作業,考試不及格時還被老師罰“站黑板”。所以,那時感到讀書一點都不好玩。但盡管如此,我和弟弟卻從沒逃過一次學。
家在農村,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有時候,家里連我們上學的學費都拿不出。父親就去找左鄰右舍借,想盡一切辦法都要交上學費,不讓我們兄弟倆輟學。為了讓我們有書讀,我的農民父親和母親,每天除了在生產隊里做工分,家里每年還養了一大群鵝去賣。其中酸楚,至今想來,我的胸口還隱隱作痛。
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喜歡上了讀書,除了課堂上的書,我還漸漸迷上了課外書。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化最為繁榮的時期,各種文學作品、報紙雜志如雨后春筍般遍地林立。印象最深影響較大的刊物有《當代》《十月》《人民文學》《收獲》等,上面刊載了很多小說。盡管那時學習繁重枯燥,壓力很大,但經不住這些小說的誘惑,經常背著父母和老師偷偷看。一方面調節了我的學習生活,另一方面也豐富了我的文學知識。
十七歲那年中考落榜,離開校園后,我也和許多農家子弟一樣,過起背井離鄉的日子。在異鄉無錫的建筑工地,我曾對自己的人生徹底失望過,但后來又看到了很明朗的世界在眼前。打工的工地旁邊有一個租書店,兩毛錢一天,每天收工后我都去租書,利用晚上或雨天停工的時間看,看完再去租。雖然是舊書,但也讓我開了眼界,讀到了不少好書。每讀完一本書,我就會欣慰一次,感覺自己又回到了學生時代,有恰到好處的點滴幸福,有苦盡甘來的些許溫暖……
“腹有詩書氣自華。”通過讀書,文字的方磚,在我荒蕪的心田建起華美的宮殿;文字的長河,開始在我生命的河床里奔騰不息。我看到自己的夢想之光,也加入到文字方陣的浩蕩隊伍之中。在對文字進行不斷“排列組合”的過程里,我找到了一種和生活對話的新方式,找到了精神世界的新出口,更體會到了另外一種人生。從此,我沿著這條希望與艱辛之路,燃起執著點亮的心燈,以筆作楫,以書為舟,在顛簸中一路行進。如今,父親已離世近二十年了,但他當年說的話卻讓我受益一生。在我的影響下,我的兩個兒女從小就喜歡讀書,現在已先后考入大學。
“書不僅是生活,而且是現在、過去和未來文化生活的源泉。”讀書也是一個人的心靈遠行,是一份堅守、一份心境、一份樂趣,更是一種習慣。如今已過不惑之年的我,深深懂得讀書的意義,也深深體會到讀書的樂趣。在讀書的路上,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只要愿意,讀書的時間總還有的,因為讀書是一輩子的事。
責編:黃寒(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