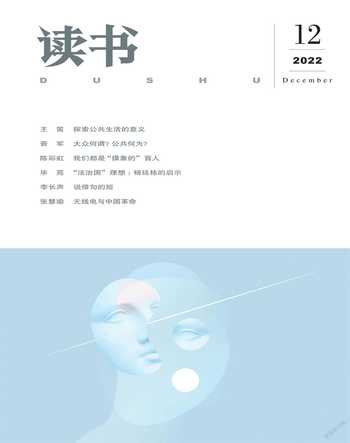探索公共生活的意義
王笛
當年我到了美國以后,離開了中國的文化環境,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成都的點點滴滴開始在腦海中不斷浮現。因此,在博士論文開始選題的時候,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研究成都這個城市。當時我有三個選擇,街頭文化、茶館和袍哥,后來根據資料收集的難易程度,決定還是選擇街頭文化,因為相對后面兩個題目,資料收集稍微容易一些。
在追尋街頭文化資料的過程中,陸續發現成都茶館的新資料,以至于《街頭文化》那本著作完成之前,我便決定把茶館作為我的下一個研究課題。關于二十世紀成都茶館的研究,最終發展成了兩部學術專著、一本文學和歷史學結合的大眾讀物以及一本茶館考察筆記。第一部專著寫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成都茶館,主要利用了檔案資料、報刊以及其他文獻。但是第二部由于涉及離我們比較近的時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寫作上遇到很多不利因素。要么沒有檔案,要么檔案還沒有到開放的期限,或者就是對時間比較近的檔案管理比較嚴格。不過有利的因素是,我自己作為研究者可以直接對茶館進行考察。在那幾年里,我考察了不同類型的茶館—從氣派非凡、多層的、可容納上千人的茶樓,到簡陋的只有幾張桌的街角茶棚,與茶館中各種各樣的人進行了交流。
我對成都茶館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一九九七年、二000年和二00三年的三次考察,以及以后的關于茶館的一些記錄,留下了這本茶館筆記。我對茶館進行的實地調查,得到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然而沒有預料到的是,利用這些資料的最后成果,竟然到了二0一八年才由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翻譯版二0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如果從一九九七年算起,也就是說前后二十一年,可見這項研究工作的投入有多么巨大。
考察方法
我的茶館考察最早是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的,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悅來茶園與熊倬云、周少稷、姜夢弼、余遜四位老先生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訪談。他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都是茶友,定期到悅來茶園碰面喝茶,然后就在附近的一個飯館吃飯,我也參加了二十一日的午餐。他們都非常和善,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經歷了時代的滄桑。和后來我的茶館考察主要是靠我與茶客聊天和觀察不一樣,那次我主要是聽他們講。我們在悅來茶園談了兩天,他們所講的往事,為我研究成都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細節。
我當時在四川省和成都檔案館看資料,十一點半就要交還檔案,下午兩點半才又開放。中午三個小時,除了休息和吃午飯,就是考察茶館的極好機會,省市檔案館周圍的茶館我幾乎都去過,那是我對茶館進行田野考察最活躍的一個時期。
除了一九九七年的那次訪談,當我考察茶館時,并沒有分發調查問卷,做筆記或錄音。我更傾向于隨意的交談,沒有一個預先設定的主題。這樣,我力圖得到被調查對象的最真實的表達,去傾聽他們的聲音。每天的考察結束后,我把自己當天的所見所聞,寫入田野調查的筆記中。所以這本書所記錄的,便是我在茶館中所見所聞和所談的實錄。可以說是原始的,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材料。
在傳統的街角茶館,顧客們并沒有什么隱私意識,可以放開講他們的故事,這對我的考察很有幫助。但是這樣做的缺點是,漫無目的,我所獲得的信息經常是隨機的,無法得到系統的資料。特別是在茶館與茶客漫談的形式,使我不可能長時期地、深入地了解我所觀察的對象,進入到他們的內心世界,或是進入他們的生活。因此與人類學家長期住在一個社區內的系統田野調查相比,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好在我是從歷史學的視角去對待我所收集的資料,并不試圖去建立一種人們行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變化過程中,公共生活是怎樣改變的等相關的歷史問題。
而且在使用這類調查記錄的時候,我盡力去保持資料的最初風格,最自然的東西。希望我講述的故事,不要太受我主觀意識的干擾。這些考察資料為我的成都茶館研究提供了故事和細節,增加了感性的認識。在考察的時候,如果我對某些談話或者發生的場景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我在筆記中也記錄下來,但會明確說明是我的思考。
考察筆記記錄的信息
從這些考察記錄中,可以看到很多雖然年代并不久遠,但是今天已經被遺忘的信息。如我世紀之交記錄的物價,在城內的小茶館里,最便宜的茶可以賣到八毛錢一碗,一般茶館的茶是二至五元不等。在成都郊區,當時甚至還有一角一碗的茶鋪存在。在二000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筆記中所提到的國際會展中心的順興老茶館,那里的茶最便宜的是十五元,但是到晚上最便宜的是二十八元,因為晚上茶館有演出。而當時成都最高檔的圣淘沙茶樓,白天最便宜的茶也是二十八元。茶價的檔次差別是非常大的,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到,如果要開一家茶館的話,當時只需要一萬多塊錢,甚至五六千元也能搞定。在茶館里掏耳朵,二000年收費是每次四元。掏耳師在茶館中謀生,雖然不需要許可證,但是每個月要給茶館交兩百元,作為使用茶館空間的費用。這些掏耳師多來自農村,月收入五六百元。算命先生也多沒有什么真本事,但是作為農民進城謀生,他們也能夠找到一口飯吃。當時算命是八元起步,好的時候一天可以掙到四十元左右,也就是說服務五個客人。而擦鞋匠一個月可掙兩三百元。
我還記載了茶館的經營。比如在花牌坊街四川省檔案館附近的一個“水吧”,在和女老板聊天的過程中,我知道這個水吧每個月的營業額要四千五百元才能保本,但是當月因為剛開張,估計最多能賣到三千元。當時房租是一千元,還要支付一千多元的工資,外加伙食、水電以及其他成本幾百塊,所以營業額三千元便要虧本。有意思的是女老板還提到她的女兒在四川大學讀二年級,每年學費和住宿費是六千元,加上伙食費共要一萬多。她說供一個大學生的負擔很重,而當時她的工資一個月才兩三百元,因此不得不提前退休,用單位給的補償來開店。
從關于茶館的這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候外來務工的人員,還是有可能開一個小茶鋪謀生。在今天看來,已經很難辦到了。隨著城市的更新,高大上的街道和建筑取代平民化的小街小巷和街邊的鋪面房,給他們提供的機會越來越少。
我所記錄的當時的人們在茶館中的談話,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說人們談論當時走紅的“散打評書”李伯清的表演。記得他諷刺的那些喜歡顯擺的人,拿著大哥大在農貿市場打電話,問家里人買不買蔥、買什么菜等等雞毛蒜皮的事,當時人們覺得很可笑。真是時過境遷,現在我們用手機從菜市場聯絡家人,詢問要買什么小菜,簡直是太尋常了。這提醒我們,文化和日常生活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在一個時期好像是非常新的東西,但是在另一個時期就過時了;在一個地方是很滑稽的,但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就完全不可笑了。
我在筆記中還記下了當時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些細節,如茶館提供了公用電話,這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服務,因為當時有手機的人鳳毛麟角。不過,相當多的成都人中(其實乃至全國),很多人都配有BB 機。如果要找某人,就發信息到BB 機服務臺,服務臺把信息轉到那個人的BB 機上,那么這個人就會用街頭、茶館或者小雜貨店所提供的電話打回去。筆記中還提到當時的收費情況,如果電話打給本市,前三分鐘三角;超過三分鐘,六角;超過六分鐘,九角,以此類推。當時正是“全民經商”的高潮,很多皮包公司的老板沒有辦公地點,整日在外面奔波,他們需要隨時聯系業務,這種電話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從這個茶館筆記中,還可以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記載的有些細節,當時無非是我所看到的東西,似乎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也不知道那些細節的觀察對我的茶館研究是否有用。但是在很多年以后,看起來卻充滿著新鮮感。比如說二000年七月三日所記錄的開茶館的小姑娘和隔壁光盤商店的王姐之間的相處,便是非常親密的、相互幫助的、自然而溫馨的關系。王姐開店門以后,茶館的女老板還幫她把冰箱搬到街沿上,王姐順便可以賣冰棍。然后王姐進來,用自己的茶杯倒開水,也不用在茶館里買茶,就用自己的茶,但是用的是茶館的開水。好像沒有任何問題,一切都習以為常。
又如在一個街邊小茶館,我看到一個老太太拎了一袋菜,路過茶館。顯然是老人家早上買了菜,半途走到這里有點累了,把菜放在靠門口的桌上。并不和女老板打招呼,也不買茶,坐在那里休息,還把菜拿出來在桌上整理,菜整理好了,又慢慢離去,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女老板也不打擾這個老太太,大家都很淡定,似乎都很默契。我很感慨當時周圍居民和小茶鋪的這種和諧關系,因為很多小店鋪,如果不消費的話,是不愿意你坐在那里的。
從上面的描述,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開茶館的老板女性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了當時在小商業的發展過程中,婦女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們在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增長中,所做出的貢獻一點都不比男人遜色。
二00三年七月九日,我在去成都郊區的一個小鎮考察的途中,司機由于走錯了路,拐進了一條鄉村土路,則意外地發現了一番不同尋常的鄉村景色:沿著那條鄉村土路,可以見到兩邊不少的簡陋茶館,有的就是用竹子搭起的簡易茶棚。雖然條件簡陋,但是農民們都顯得放松和悠閑,一邊喝著一毛和兩毛錢一碗的茶,一邊在茶館里打牌下棋聊天,有的手里編著草帽辮子,讓人恍惚回到了過去的鄉村生活。也就是說,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哪怕在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大城市的郊區,也會出現那種不變的似乎靜止的鄉村生活,我們可以在傳統和現代的時空不斷轉換的場景中對社會生活進行觀察。
對于住在城內的成都市民,特別是退休人員,茶館對他們的意義就更為明顯。他們定期到茶館去聚會、聊天、打麻將、聚餐,玩一天,茶錢、租麻將外加午餐,所花費的也就是在十元到十五元之間,茶館—其實也只有茶館—為他們晚年的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設施。
我在茶館里觀察到各種人物,各個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受教育程度的顧客,以及在那里謀生的人們,包括摻茶的、行醫的、賣藥的、賣繪畫書法的、掏耳朵的、擦鞋的、算命的、唱歌跳舞的……茶館的小空間,就變成了一個紛繁的大社會。
這些記錄的意義何在?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來,我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外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巨大變化。在我對成都進行考察后,不到十年時間,舊的城市幾乎從我們的眼前消失。雖然城市還是坐落在原來的地方,城市名稱也沒有改變,但是從這個城市的外貌和文化來看,又像是另外一座城市:另外一個城市格局,另外一種城市景觀,以及另外一種城市生活。
當時我考察的茶館,今天絕大多數都不復存在。過去它們一般開設在小街小巷,但是拆遷重建后的成都,出現了更多的為汽車服務的交通大道,逐漸失去了過去小茶館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空間。我在筆記中描繪過多次的大慈寺的茶園,雖然仍然存在,但是現在也不一樣了。當時是利用了大慈寺內的大殿以及庭院,現在的規模小多了,氛圍也不一樣了。當然,這種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慈寺現在是成都市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過,有時候我想,那個原來占用了幾個大殿和庭院的文博大茶園,其實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值得保護。雖然這個茶館的歷史也不算長,但是它所提供的那種文化氛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真正繼承了成都茶館的精髓。而大慈寺本身,在文物保護的旗號下,原來的木結構大廳和大柱,被換成了水泥結構,已經失去了本身的文物價值,現在無非是一個軀殼而已,這是非常可惜的。大慈寺是唐代的古寺,雖然經歷過幾次大火,但原來的那幾個大殿,也是清初留下來的建筑。把木建筑改為水泥建筑,原有的本質已經被抽掉了。
我一九九七年、二000年和二00三年夏天在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筆帖市、東糠市街等小街小巷考察的時候,那是當時成都所存不多的老城老街的格局。現在整個片區已經完全消失了,變成了最時髦的商業中心太古里。
有時候在同一家茶館,我感覺到了時間的停滯。我在二000年和二00三年夏天都去了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園,在二000年的筆記里記錄了人們在茶館里唱歌跳舞,在二00三年的筆記中,也描述了類似的活動。可見,一些茶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社區娛樂中都充當了一個重要角色。
不過最有意思的發現,是當我整理二0一九年夏天在彭鎮觀音閣老茶館照的照片時,發現一個打牌老人的樣子很面熟。結果我翻出了二0一五年秋天在同一家茶館拍攝的照片,發現有好幾張他都正在打撲克。由于這個老人的面部特征比較明顯,二0一五年的照片我反復看過許多次,他的形象竟然不知不覺地留在了我的腦海之中。沒有想到相隔將近四年的在茶館隨手拍的照片,竟然拍下了同樣一個人。這種機緣巧合可以說是神奇,我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便萌生了要去找到這個老人的想法并付諸行動,找到了機會在茶館直接和他聊天,挖掘他常年來茶館后面的故事。
從前許多在街上從茶館門口經過的各種挑擔子的小販,賣米的、賣水果的、賣涼面的、賣花的等等,現在也幾乎見不到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去這個城市與周圍鄉村的緊密聯系,由于受城市的擴展、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已經被割裂開來,或者以另外一種形式連接起來,即現代化的物流系統已經扮演著聯系城鄉的一個主要角色。
以蔬菜擺到城市居民的飯桌上為例,過去農民把蔬菜直接挑進城里(或者推車,過去成都郊區的農民普遍用獨輪車,叫“雞公車”,后來更多的是用自行車)和居民發生交易活動。但是在今天,蔬菜從菜地運進巨大的蔬菜中轉站,然后分發到各城市的蔬菜批發市場,再往下由各個菜場的蔬菜販或者超市把這些蔬菜銷售給居民。也就是說城市居民在得到這些蔬菜時完全和原始的生產者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系了。這種通過物流系統建立起來的連接,已經和過去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有了巨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其實也改變了城市居民和農民的生活乃至交流模式。
因此當時考察留下來的記錄便顯得特別珍貴,因為猶如當時按下了照相機的快門,記錄了那一個個歷史的瞬間。重構中國城市的過去是研究社會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的歷史學家們所面臨的重要任務和應盡的職責。
而且我也一直主張,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甚至為此專門發表過文章—《記錄我們的歷史》(《南方都市報》二0一0年四月二十日)。寫歷史,并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也不能把這個重要的使命完全交給他們去完成,因為他們記錄和書寫的歷史,只是他們眼中的歷史,或者是他們頭腦中的歷史。更何況這種歷史,還經常是用精英的視野和話語來撰寫的。個人的經歷記錄下來,現在可能看起來平淡無奇,但是許多年后,就是非常珍貴的記錄。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屠貓記》那本書,其中第二章,便是依據十八世紀巴黎一個小印刷作坊的學徒自娛自樂寫下的殺貓的惡作劇,結果后來卻為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寫他的這個名篇提供了基本依據。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二00三年考察的筆記要粗獷一些,沒有三年前的筆記那么多個人的故事和細致的觀察。因為那個時候,我認為茶館的資料已經大致收集齊備,而且我的茶館研究的截止年是二000年,離二000年越遠,對我的用處就相應地減少。茶館的觀察也差不多了,很多現象都是雷同的。所以,二00三年及以后的大多數記錄都帶有順便的性質,是因為在茶館里見朋友、見同學、聊事情,要不就是聚會、辦事,或者是經過順便看看,隨手記下來的一些信息,并沒有專門進行考察。現在把筆記整理成書,雖然比較簡略,但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然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一年春天暴發的“非典”,造成茶館生意蕭條,沒有了那種熙熙攘攘的氛圍,人們盡量躲開公共場所的活動。不過,這個茶館筆記,也可能呈現出了當時沒有想到的一種意義,即記載了那次疫情期間成都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人們對那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的反應。
歷史就是這么無情,當我在整理茶館筆記的時候,我們正在遭受又一次疫情的打擊。如果有許多人都記錄下在災難中的日常經歷和故事,就會給后人留下更全面的和真實的記錄。我們不能只依靠媒體的報道和個別知識分子的寫作,因為那只是有限的觀察和視角。民眾自己來記錄當下的故事,哪怕現在可能沒有機會傳播,但是多年以后,就是珍貴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