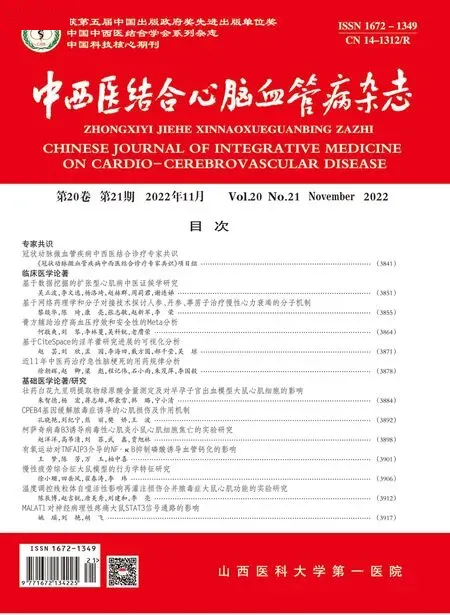microRNAs在急性肺栓塞中的研究進展
金 釗,施熠煒
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以各種栓子阻塞肺動脈或其分支為其發病原因的一組疾病或臨床綜合征的總稱,其中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為肺栓塞最常見類型。引起PTE的血栓主要來源于下肢的深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二者合稱為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二者具有相同易患因素,是VTE在不同部位、不同階段的兩種臨床表現形式[1]。
作為全球第三大急性心血管綜合征,VTE位于心肌梗死與腦卒中之后[2]。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肺栓塞年發病率為39/10萬~115/10萬,深靜脈血栓年發病率為53/10萬~162/10萬[3-4]。隨著年齡增加,VTE發病率增加,年齡>40歲較年輕病人風險增高,其風險大約每10年增加1倍[5];而在老年人中更為明顯,年齡≥80歲人群VTE發病率幾乎是50歲人群的8倍[3]。PTE致殘率和致死率都很高,其7 d全因病死率為1.9%~2.9%,30 d全因病死率為4.9%~6.6%[6]。此外,初始治療前6個月內為VTE全因病死率高峰期,隨后明顯下降[7]。以上的流行病學研究表明,VTE的早期有效診治仍面臨巨大挑戰。
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是一種常見的突發的具有高發病率及死亡率的VTE[8],其臨床表現多樣化,缺乏可靠的篩查方式,漏診率較高。早期及時準確的診斷非常關鍵,主要包括實驗室標志物及影像學檢查。D-二聚體是纖維蛋白降解產物,升高反映繼發性纖溶亢進,診斷肺栓塞具有高度敏感性,但其特異性較低,即陰性具有排除價值,而陽性仍需進一步檢查[9]。肺動脈造影曾是診斷的金標準,因其有創性已逐漸被CT肺血管造影(CTPA)取代,但腎功能不全以及對造影劑過敏等病人無法行CTPA檢查。總之,早期及時并準確診斷APE的新型無創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非常必要。
microRNA(miRNA)是內源性小分子非編碼單鏈RNA,通過結合靶基因mRNAs 3′非翻譯區抑制其翻譯[10]。循環miRNAs在內源性RNA酶的保護下較為穩定,易于收集且重復度高,是一種簡便可靠的生物標志物,疾病狀態下,可從細胞中被動或選擇性地釋放進入血液,作為信號交流的信使[11],于血漿或血清中迅速靈敏地定量檢測到,在心血管系統疾病方面已有廣泛的研究。此外,miRNAs與CTPA相比無創且沒有輻射,與D-二聚體相比則往往有更高的診斷準確性。miRNAs對早期準確診斷APE具備很高的價值,同時參與了APE的發病機制通路。本研究對microRNA在APE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miRNA-134與miRNA-1233
miRNAs用于診斷APE最早在Xiao等[12]的一項前瞻性研究中提出。該實驗收集了APE組32例、健康對照組32名、非APE組22例,通過Taqman微陣列分析篩選出30種差異化表達的miRNAs,并通過Taqman miRNA 實時定量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qRT-PCR)檢測3組miRNA-134,結果顯示,APE組血漿miRNA-134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及非APE組,首次提出miRNA-134可作為診斷APE的潛在生物標志物。但該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樣本數量相對較小,沒有結合臨床指標(如D-二聚體)探究更高的診斷準確性,同時未涉及miRNA-134的生物學功能、相關病理生理學機制及其對APE診斷模式的價值等。
Liu等[13]的Meta分析系統地評價了循環miRNA-134對于早期診斷APE的臨床價值。該Meta分析發現,APE組血清或血漿中miRNA-134明顯高于對照組,其整體靈敏度與特異度都很高,反映了miRNA-134對APE的診斷準確性較高。由于D-二聚體的靈敏度高及特異度低,其陰性常用于APE的排除診斷,該Meta分析提出miR-134聯合D-二聚體對準確診斷APE可能優于單一指標。該Meta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收錄文獻較少,且不同文獻具有異質性。盡管存在局限性,該Meta分析闡釋了miRNA-134可作為APE早期診斷的新型生物標志物。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具有與APE難于鑒別的臨床癥狀(如呼吸困難與胸痛),早期識別這兩種致命性胸痛并給予針對性治療對改善預后非常關鍵,而常用的肌鈣蛋白及D-二聚體并不足以將二者有效鑒別。Kessler等[14]首次提出miRNA-1233可作為鑒別二者的生物標志物,且具有高度的靈敏度(90%)及特異度(100%)。該研究測序了肺栓塞急性期(第1天)與慢性期(9個月后)的754種miRNAs,發現了37種差異化表達的miRNAs,其中miRNA-1233在急性與慢性肺栓塞中差異最明顯,并通過RT-qPCR驗證了其在NSTEMI組及健康組中明顯的差異化表達。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床旁測量技術及正常值范圍,miRNAs用于臨床早期鑒別APE與NSTEMI尚需更多研究。該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樣本量較小以及實驗組為高選擇性高栓塞風險的中心型栓塞重癥病人。該研究首次提出miR-1233作為鑒別診斷APE與NSTEMI具有高度準確性,可作為診斷APE更有前景的生物標志物。
隨著以上兩種miRNA在APE中的研究愈發廣泛,Peng等[15]為早期鑒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否合并APE,通過qRT-PCR檢測miRNA-134與miRNA-1233表達,結果顯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合并APE組miRNA-134與miRNA-1233表達較COPD穩定期及急性加重期組明顯上調。在APE組中,miRNA-134的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AUC)為0.931,miRNA-1233的AUC為0.884,二者AUC均高于D-二聚體(AUC 為0.628),經年齡調整后的D-二聚體(AUC 為0.705)及Wells評分(AUC 為0.705),提示miRNA-134和miRNA-1233可作為鑒別診斷AECOPD是否合并APE的潛在生物標志物。該研究還表明miRNA-134聯合miRNA-1233(AUC為0.957)診斷準確性高于單一miRNA,以及二者分別聯合經年齡調整后的D-二聚體對診斷準確性無明顯提高。該研究為單中心小樣本研究,而且因科室特殊性收集的AECOPD均為中重度,長期缺氧且活動不足,具備血栓形成高危因素。
2 miRNA-27a/b 與miRNA-221
不同miRNAs在診斷APE的研究也有所不同。Wang等[16]收集了78例APE病人與70名年齡、性別匹配的健康人,通過qRT-PCR檢測血漿miR-27a與miR-27b表達,結果顯示,APE組血漿miR-27a與miR-27b明顯增高,且miR-27a(AUC為0.784)優于miR-27b(AUC為0.707),并且miR-27a或miR-27b聯合D-二聚體明顯增加了APE診斷的準確性。該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這項單中心研究的樣本量仍相對較小;其次,該研究只測量了APE病人出現癥狀6 h以內的miRNA含量,并未測量其后續水平,且相關機制尚未明確;最后,miRNA的標準化正常范圍仍未確定。此外,Liu等[17]納入了60例APE病人及50名正常人,通過miRNA微陣列分析鑒別出血漿中差異化表達的32種miRNAs,并應用qRT-PCR驗證了miR-221(AUC為0.823)在APE組明顯上調,其程度與肺栓塞風險性增加相關,miR-221表達量與腦鈉肽(BNP)、肌鈣蛋白I及D-二聚體呈正相關,且其對于APE診斷的準確性更高。該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同其他實驗一致為單中心、小樣本研究;而且測序miRNA數量較少,無法確定有無其他miRNA參與APE進展;此外,因miRNA嚴格的時空特異性也無法確定miR-221是否為APE早期特異性標志物。
3 miRNA let-7i-5p與miRNA-320a
Fabro等[18]研究了經時間變化的PTE及不同表型肺動脈高壓miRNA的差異,并預測了相應miRNA的靶基因。該研究比較了急性肺血栓栓塞癥(APTE)與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TEPH)中miRNA的改變,以及CTEPH與特發性肺動脈高壓(IPAH)中miRNA的差異,發現了5個差異最明顯的miRNA。APTE組miR-let-7i-5p、miR-320a、miR-320b-1、miR-320b-2及miR-1291上調;CTEPH組miR-320b-1上調,miR-let-7i-5p、miR-320a、miR-320b-2及miR-1291下調;而在IPAH組miR-let-7i-5p與miR-320b-1上調,miR-320a和miR-1291下調。與對照組相比,APTE組miR-let-7i-5p和miR-320a明顯上調,CTEPH組明顯下調;而IPAH組miR-let-7i-5p明顯上調,miR-320a明顯下調。該研究表明miR-let-7i-5p作用的11個靶基因及miR-320a作用的20個靶基因,可能參與調節肺動脈外膜成纖維細胞、內皮細胞及平滑肌細胞增殖、血管收縮、炎癥及DNA損傷,且兩種miRNA的靶基因雄激素受體(AR)及蛋白激酶Cα(PRKCA)在癌癥中均有所研究。APTE組miR-let-7i-5p上調,而CTEPH組下調,與已知的D-二聚體、C反應蛋白及心臟指數等一致,反映了隨時間變化的異常血管重塑。在可能由于肺動脈外膜成纖維細胞、內皮細胞及平滑肌細胞的過度增殖與抗凋亡表型不平衡導致了二者差異的IPAH組與CTEPH組中,即let-7i-5p在前者上調,而在后者下調。miRNA-320a與miR-let-7b-5p聯合臨床特征有助于經時間變化的APTE與CTEPH以及不同表型的IPAH與CTEPH的鑒別診斷。
綜上所述,miRNA早期診斷APE具備很高的價值。
4 miRNA-21、miRNA let-7b-5p與miRNA-106b-5p
Liang等[19]通過建立姜黃素處理的APE大鼠模型,經蛋白免疫印跡法(Western Blot)分析及RT-qPCR證實了APE組Sp1、miRNA-21、NF-κB下調以及磷酸酯酶與張力蛋白同源物(PTEN)上調。病人研究表明,姜黃素可降低APE大鼠平均肺動脈壓(mPAP)、右心室收縮壓(RVSP)、血栓體積及肺部炎性因子。雙熒光素酶報告分析及染色質免疫共沉淀技術(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ChIP)分析顯示,Sp1可通過結合miR-21啟動子增加miR-21表達,且PTEN為miR-21的靶點。此外,通過評估腺病毒注射APE大鼠發現了miR-21或Sp1下調以及PTEN上調可降低肺動脈平均壓(mPAP)、右心室收縮壓(RVSP)、肺濕重與干重比值(W/D)、血栓體積及肺部炎性因子,表明姜黃素通過下調Sp1降低miR-21的表達,從而上調PTEN并削弱NF-κB信號通路,抑制APE大鼠肺損傷和炎癥。
Liu等[20]在體內及體外實驗通過缺氧/復氧(H/R)模型,發現APE中miRNA let-7b-5p可在轉錄后水平上調應激相關內質網蛋白1(SERP1)參與內質網應激反應,促進細胞凋亡,而SERP1激活后可調節其伴侶蛋白SEC61B參與應答,SEC61B可介導未折疊蛋白GRP78、蛋白激酶R樣內質網激酶(PERK)以及PERK-C/EBP同源蛋白(CHOP)通路的CHOP引發炎癥反應與肺內皮細胞凋亡。該研究表明miRNA let-7b-5p可通過上調SERP1并調節其伴侶蛋白SEC61B介導的GRP78及PERK-CHOP通路的PERK與CHOP參與內質網應激,最終導致肺部細胞凋亡及炎癥反應,參與了APE的發病過程。
Chen等[21]研究發現在APE小鼠體內及體外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PDGF)誘導的肺動脈平滑肌細胞(PASMCs)中,miR-106b-5p下調,腫瘤細胞核NR4A3(NOR-1)及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上調。在PASMCs中,PDGF可降低miR-106b-5p水平,并增強NOR-1/PCNA通路的表達;同時,也驗證了NOR-1過表達可以逆轉該miRNA對PDGF誘導的PASMCs增殖及遷移的抑制。該研究表明,miR-106b-5p可通過作用于NOR-1 mRNA 3′非翻譯區降低其表達,逆轉PDGF誘導的PASMCs增殖及遷移,改善肺血管重塑,降低APE 死亡率。
APE病人病情危重,漏診率高,及時識別并給予有效診治對改善預后非常關鍵。臨床常用的D-二聚體及CTPA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新型生物標志物miRNA則為APE早期診治提供了突破性的進展,期待更多研究結果實現其真正地應用并指導臨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