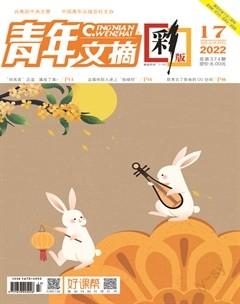一個矮個子的樂觀主義
靜思

我的身高是我父母內心很深的遺憾,即使這只是我完美地遺傳了他們的基因所得。
從小到大——包括現在——我爸媽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唉,咱要求也不多,閨女要是能再長高5厘米就好了,那和現在的境界就絕不一樣了。”其實,再長高5厘米,我也還是矮,但在父母的腦海里,好像那5厘米就是助我人生走上巔峰的青云梯。
我對身高展開的搶救工作,可以譜寫一部智商稅史。
小時候,看見高樂高廣告,上面的小孩子喝完幾杯后個頭瞬間就往上噌噌地飆,然后父母摸著他的頭笑得一臉欣慰。為了這個開懷的笑容,以及“高樂高”這么充滿美好愿景的名字,我媽沒少讓我喝。但個頭不見長,體重倒是不客氣。
后來,有一陣特別流行增高鞋,90年代就賣300多元一雙啊。廣告上那個矮小的孩子,穿上鞋子后腳底開始泛藍光,然后神奇般地增高了5厘米。我媽看完后當即拍板:買!鞋定勝天!在我穿壞兩雙增高鞋但身高絲毫不見長后,我媽終于認清了現實:這與街邊攤三五十元一雙的運動鞋無異。
再比如,不知誰說的打羽毛球能增高,我爸媽知道后就天天早上逼著我去打半小時羽毛球。所以,每天我七點背著書包、扛著拍子、站在操場上拉人陪我練球,以至于有段時間我同學都以為我要考體校。
最讓我感到“恥辱”的一項增高運動是籃球。我爸說打籃球能長個子,于是在高二的暑假給我買了個籃球,每天吃完晚飯趕著我去學校的籃球場練球。我們學校有兩個露天籃球場,前后挨著。于是,經常出現這樣一幕:一個籃球場上,一堆身高1.8米以上的男生光著膀子激烈對決,周圍叫好聲一片;另一個籃球場上,一個身高比他們矮一頭起的小女生孤獨地拍拍球,然后吃力地把球扔向那個永遠也投不進的籃筐。
有一次,我被自己扔出去的球砸中,暈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恰好被旁邊正在打比賽的人看到,他們中止比賽跑過來看我要不要緊。人生頭一次被一堆體格健碩的男生圍著,我一時不知是羞是喜。
再后來,我爸媽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個民間秘方——吊單杠,說吊單杠能拉伸骨骼,讓人變得瘦長。
然后,我就開啟了課間吊、放學吊、體育課吊、晚自習也吊的吊杠模式。直到有一次吊的時候實在沒堅持住,摔下來把左胳膊弄脫臼了,我短暫的業余體操生涯才算結束。
人類對身高的崇拜,據說是因為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要通過圍獵來維持生存,而高個子的人在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能給人提供更多安全感,所以這項優勢被保留在了我們后代的基因里。
在一個對男士崇尚高大威猛、對女士崇尚高挑纖細的社會里,生而矮小的人總會有意無意被鄙視。比如,從小被冠以“小不點兒”“小矮人”這種不太體面的綽號;比如,拍集體照、排座位時你總會被擺弄到靠前的位置……個子小,本來是基因問題,最后卻被歸類成類似缺陷的問題,催生出了身材歧視。這個世界不僅看臉,還看身高。
不過,個頭矮的人也有很多“身高不觸底”的人難以體驗到的好處。比如,通常身材矮小的人,臉也顯得比較年輕。我在上初中時就被別人認作小學生,高中時被人認作初中生,大學時被人看作高中生。
再比如,身材矮小的人買衣服和鞋子真的省錢。買衣服,大碼童裝搞定;買鞋,大童鞋搞定,一樣的做工和樣式,價錢比成人碼數便宜了20%。而且因為身材不高,如果你看開一點,作為女性這輩子基本可以免受高跟鞋帶來的痛苦了。一雙“恨天高”踩在腳下,并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個高挑之人,還不如安安心心踩著平底鞋踏踏實實走好自己的路。
學會愛自己是一件辛苦而又浪漫的事。我們的身體雖不完美,卻閃爍著獨一無二的光,那是我們之所以成為自己的重要印記。
花花//摘自三聯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本刊有刪節,四季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