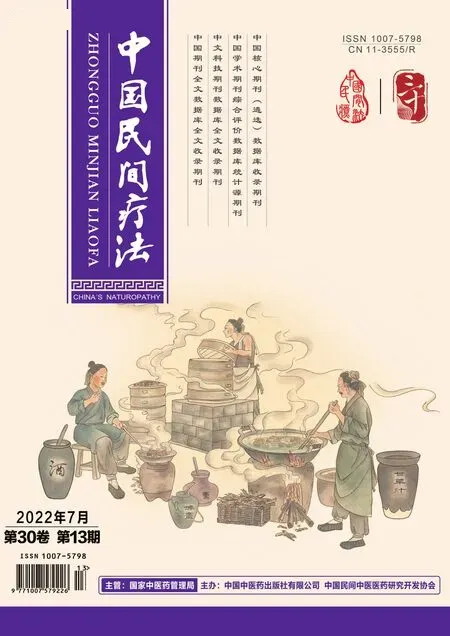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研究淺論※
郭晉斌,楊路庭,王懷昌,司二琴,馬昱紅
(山西省長治市中醫研究所附屬醫院,山西 長治 046000)
醫案是醫師臨床思維活動與醫療實踐活動的記錄。從古至今,岐黃之術傳承不息,醫案與其他形式的醫著共同呈現了中醫發展的軌跡,承載了中醫仁術的精神。醫案生動地反映了民生需要、臨床療效、辨證思維,向來為醫林所重視,醫案中往往理法方藥具備,示人以圓機活法。研讀醫案如同與醫家共診切磋,對于后之學者開拓臨證思路、提高辨治能力頗有裨益。筆者在前期中醫腦病醫案研究的過程中,對元代以前的中醫腦病醫案形成了一些粗淺的認識,現總結如下。
1 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的篩選
醫案之作由來已久,殷墟甲骨文中載有某疾愈或不愈,《周禮·天官》中載有“稽其醫事”。漢·淳于意傳診籍載于《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歷代文獻陸續記載醫案,有收入史籍列傳者,有收入筆記、方志者,有收入醫學專著者,迭有佳作,蔚為大觀。筆者著眼于傳統文化,在經史子集間多方搜求查找,在總量豐富的文獻資料中篩選出符合研究要求的腦病醫案,進行了從文本考證到演變源流、從文理校讀到醫理詮釋、從學術思想到臨證經驗的多方面探討。
中醫腦病學是在中醫不斷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其臨床實踐自古即有,如《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論之薄厥,《素問·至真要大論》《素問·脈解》《素問·病能論》等所論之癲狂。至元代設分十三科中就有了專門的風科,這與現代中醫腦病學學科有密切的關系。在王永炎、張伯禮主編的《中醫腦病學》中,明確給中醫腦病學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即“現代中醫腦病涵蓋了神經系統疾病、精神疾病及某些疾病引起的神經精神癥狀”[1]。古代文獻中有許多病證和癥狀的描述是符合這個內涵界定的。依據這個內涵界定,筆者從元代及以前的古代文獻中輯錄出腦病領域的醫案,包括中風、眩暈、頭痛、癇病、痙病、痿病、麻木、不寐、癲狂、郁病等病證,符合上述內涵的醫案即作為研究對象。在醫家選擇方面,遴選出姚僧垣、許智藏、許胤宗、甄權、秦鳴鶴、紀朋、錢乙、龐安時、杜壬、郝允、楊介、竇材、許叔微、孫琳、徐文中、張從正、李東垣、羅天益、朱丹溪、倪維德、滑伯仁21位有代表性的元代以前的醫家。
2 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的流傳演變
筆者對于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的文本流傳演變情況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查考。醫案終末文本以《名醫類案》《續名醫類案》《古今醫案按》等通行的醫案匯編著作所載文本為準,同時以之為線索,通過查考其最早的古文獻源頭以考察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的流傳演變情況,包括文本的校對和訓詁考證,部分內容結合文理與醫理的考證等。在詮釋文義的基礎上,對諸位醫家的學術背景、學術思想、診療經驗、醫案思路、涉及方藥及腧穴等方面進行初步分析與探討,筆者認為中醫腦病醫案總的變化趨勢是由史傳性質、事件敘述逐漸向探求源流、申明醫理轉化。通過文本梳理,也明確了其脈絡,即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的文本流傳由史籍向醫籍逐漸轉變,而且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的文本流傳演變情況也較為復雜。
2.1 由史籍向醫籍的逐漸轉變 早期的中醫腦病醫案依賴于史籍的記錄而保存。從最早的《史記》記載的淳于意診籍,到《周書》《北史》記載的姚僧垣醫案,《隋書》《北史》記載的許智藏醫案,《舊唐書》《新唐書》記載的許胤宗醫案、甄權醫案、秦鳴鶴醫案等,均記載于史籍中。這些記載基本上都是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附屬物被記錄下來的,并不能構成獨立意義上的中醫腦病醫案。宋·錢乙、許叔微等首先在其醫學著作中附載驗案以佐證其論述[2],其后金元明清諸醫家多有效仿。清·周學海在《讀醫隨筆》中說:“宋以后醫書,唯醫案最好看,不似注釋古書之多穿鑿也。每部醫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處,潛心研究,最能汲取眾家之所長。”這也反映了中醫醫案由簡向繁、由史籍向醫籍的發展過程。
北宋以后的醫案分為兩類。一類是醫名顯著而未著作或著作未能流傳下來的醫案,依賴于筆記文獻。例如龐安時(約1042—1099年)的醫案見載于宋·張耒(1054—1114年)所著的《明道雜志》中,杜壬(生卒年不詳)的醫案見載于宋·葉夢得(1077—1148年)所著的《避暑錄話》中,郝允(生卒年不詳)的醫案見載于宋·邵博(?—1158年)所著的《邵氏聞見后錄》中,楊介(生卒年不詳)的醫案見載于宋·趙與時(1172—1228年)所著的《賓退錄》中,孫琳(生卒年不詳)的醫案見載于宋·龐元英(生卒年不詳)所著的《談藪》中,徐文中(生卒年不詳)的醫案見載于元·徐顯(生卒年不詳)所著的《稗史集傳》中,等等。古代筆記是指隨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包涵古代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至宋代,筆記完成了從志怪傳奇向注重社會現實的轉變,并且數量龐大,所以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學術價值。盡管筆記中所載部分人物生卒年不詳,但記錄者與被記錄者基本生活在同一時代,所以這些記載內容的可靠性還是較高的。存在的問題是筆記所載內容的醫理敘述較為簡略,而醫事作為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記述的故事性較強,文學色彩較為濃厚。
另一類是醫名顯著而著作流傳影響巨大的醫案。例如宋·錢乙的醫案主要見載于其兒科專著《小兒藥證直訣》中,宋·竇材的醫案見載于其所著的《扁鵲心書》中,宋·許叔微的醫案見載于其所著的《普濟本事方》中,金·張從正的醫案見載于其所著的《儒門事親》中,金·李東垣的醫案見載于其所著的《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醫學發明》《蘭室秘藏》中,金·羅天益的醫案見載于其所著的《衛生寶鑒》中,元·朱丹溪的醫案見載于其所著的《格致余論》《丹溪心法》《丹溪先生治法心要》中。這些記載構成了較為成熟的中醫腦病醫案,病史描述、病機探討詳細,理法方藥基本完備,完成了向探求源流、申明醫理的轉化。
2.2 文本流傳過程中變化復雜 與其他古代歷史文獻相似,元代以前的中醫腦病醫案文本在流傳中也會發生變化,其根本原因是后世在引用時,多數情況下會根據需要做一些調整。第1種情況是因文風或文本體例需要,敘述主體會有變化,同時使文本篇幅也發生相應變化。例如姚僧垣治竇集病風案,原載于《周書》中為71個字,《北史》記錄簡要為49個字,《續名醫類案》引用時改變敘述主體,用75個字記錄。第2種情況是因文學色彩較重,轉敘時由文理偏向醫理。例如朱丹溪治一女病郁案,為了以怒解郁,需要激怒患者,戴良在《九靈山房集·丹溪翁傳》中記載為朱丹溪親自“入而掌其面者三”,至《古今醫案按》則記錄為“其父掌其面”,《名醫類案》則避開主體,側重目的,記錄為“令激之大怒而哭”。第3種情況是文字義近,因引用者理解不同而發生變化。例如秦鳴鶴治唐高宗風眩案,《舊唐書》記載為“苦頭重不可忍”,《資治通鑒》記錄為“苦頭重不能視”,《針灸資生經》記錄為“秦鳴鶴針高宗頭風”,《醫說》記錄為“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筆者理解唐高宗所患應為頭暈昏重,程度較嚴重。
另外,醫案涉及的人物也會發生變化。第1種情況是醫者發生變化。例如紀朋治一宮人病狂案,《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根據《明皇雜錄》記載為紀朋,而《太平廣記》《吳郡志》則根據《明皇雜錄》記載為周廣,但《明皇雜錄》傳至宋代已無完本,故孰是孰非無法考證。第2種情況是患者發生變化。例如許胤宗治柳太后病風案,《舊唐書》記錄為柳太后病,而《新唐書》記錄為王太后病,結合《陳書》所載南陳世系,當為柳太后,至《古今醫案按》引《舊唐書》。
還有醫案中部分文字因形近致訛誤。例如姚僧垣治宇文邕病風案,“臉垂覆目”當為“瞼垂覆目”,“臉”字在魏晉時期出現時只表示兩頰的上部,而“瞼”表示眼皮。再如錢乙治八太尉病急驚抽搐案,“更坐石杌子”,有版本訛誤為“更坐石機子”。
3 研究中發現并提出的新問題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例如關于文獻所載足太陽膀胱經在背部第1、2側線諸穴的定位問題存在爭議[3]。《類經圖翼》《醫宗金鑒》均言:“脊骨內闊一寸。凡云第二行夾脊一寸半、三行夾脊三寸者,皆除脊一寸外,凈以寸半三寸論。故在二行當為二寸,在三行當為三寸半。”這里就提出文獻所言“一寸半”“三寸”是以后正中線為起點(去脊中),還是以內闊一寸之脊骨邊緣為起點(去脊)的問題。《針灸大成》云:“背部……第二行,夾脊各一寸半,除脊一寸,共折作四寸,分兩旁。第三行,夾脊各三寸,除脊一寸,共折作七寸,分兩旁。”支持“去脊”說。《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九》《千金翼方·卷第二十六》所言各穴皆謂“在第某椎下兩旁各一寸半”“在第某椎下兩旁各三寸”“在第某椎下節間”;《針灸資生經》所言各穴皆謂“在某椎下兩旁各寸半”“在某椎下兩旁各三寸”;《針灸聚英》所言各穴皆謂“某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五分”“某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均支持“去脊中”說。以上定位問題均需要進一步研究。
關于針灸禁忌的穴位或部位,《素問·刺禁論》曰:“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在秦鳴鶴治唐高宗風眩醫案中,就是刺腦戶出血而獲效,這說明古代醫家并未囿于文獻所述。晉代《針灸甲乙經》明確列出了神庭、上關、顱息、左角、人迎、云門、臍中、伏兔、三陽絡、復溜、承筋、然谷、乳中、鳩尾14處針刺禁忌的穴位或部位,以及頭維、承光、腦戶、風府、喑門、下關、耳門、人迎、絲竹空、承泣、脊中、白環俞、乳中、石門、氣街、淵腋、經渠、鳩尾、陰市、陽關、天府、伏兔、地五會、瘈脈24處艾灸禁忌的穴位或部位。后世醫家不斷進行總結,針灸禁忌的穴位或部位也不斷發生演變。明代《針灸大成》在實踐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增至22個穴禁針、45個穴禁灸。至清代《醫宗金鑒》增至23個穴禁針、47個穴禁灸。《針灸甲乙經校注》指出:“所謂刺禁,亦系古人經驗之總結,其義有三,一者絕不可刺,一者禁深刺,一者禁多出血。另有些禁刺穴,由于后世對針具的不斷改進,造成針傷的可能性減少,加以審慎從事,亦可酌情施針……所謂灸禁,指直接灸而言,其義有三:一者頭面部穴位,恐誤損美容;二者臨近重要臟器及大血管等,恐誤為內傷;三者個別穴位,可引起功能改變,如石門女子禁灸等。推而論之,凡與上述三者有關之腧穴,直接施灸時,均當注意。如必須施灸者,后世有非直接灸法,如隔物間接灸,或用艾卷相隔一定距離之灸法等,均可變通施用。”[4]筆者認為,隨著對針灸禁忌的穴位或部位結構與功能認識的不斷深入,針灸禁忌的穴位或部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臨床中,可以探索采用新的針灸方法或新的針灸工具或介質在一些前人認為是絕對禁忌的穴位或部位上進行針刺或艾灸治療。如激光針灸是采用低強度激光,利用其生物作用刺激腧穴進行治療,激光聚焦進行“針”,激光擴束作為“灸”,此方法還具備無痛及避免感染的優勢,可消除患者對傳統針灸的恐懼[5-6]。
4 對諸家腦病診療學術特點的探討
筆者共篩選了南北朝至元代的21位醫家的近百例腦病醫案,其中有13位醫家僅有少量腦病醫案甚至孤案存世,難以反映其診療腦病的學術特點;其余8位醫家有較多的腦病醫案存世,筆者對他們的醫案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其共同點首先是尊經重經,且都有深厚的儒學基礎,有些還擔任了政府要職。例如錢乙從其姑父習儒學醫,擔任太醫丞;許叔微于紹興二年(1132年)中進士后任翰林學士,人稱許學士。其次是師承或家傳醫學。例如張從正三世業醫并師從劉從益、姜仲安,李東垣師從張元素,羅天益師從李東垣,滑伯仁師從王居中、高洞陽等。諸醫家在腦病診療方面各具學術特點,如羅天益在防治中風方面辨證分類,區別腑臟,分經論治;因時制宜,注重四時變化;忌過汗過下,重視預防中風;內外兼治,多施針灸[7]。朱丹溪集諸氏之大成,重視氣血,并貫穿中風辨治全程,左右分辨痰與瘀,病初活用汗、吐、下法,善后調養用和法[8]。滑伯仁則儒道融合,基儒學醫終歸道,治則尊經,臨證重脈,合參諸家,淵源深厚,療效出眾。
5 小結
近代張山雷在《古今醫案評議》中說:“醫書論證,但紀其常,而兼證之紛淆,病源之遞嬗,則萬不能條分縷析,反致雜亂無章。唯醫案則恒隨見癥為遷移,活潑無方,具有萬變無窮之妙,儼如病人在側,馨咳親聞。所以多讀醫案,絕勝于隨侍名師而相與晤對一堂,上下議論,何快如之!”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指出:“中醫之成績,醫案最著,名家工巧,悉萃于是。學者欲求前人之經驗心得,醫案最有線索可尋,循此鉆研,事半功倍。”筆者將校勘、翻譯、詮釋等 文獻研究與人文歷史、典章制度等社會背景及中醫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對元代以前中醫腦病醫案有了初步的認識,為下一步研究中醫腦病醫案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