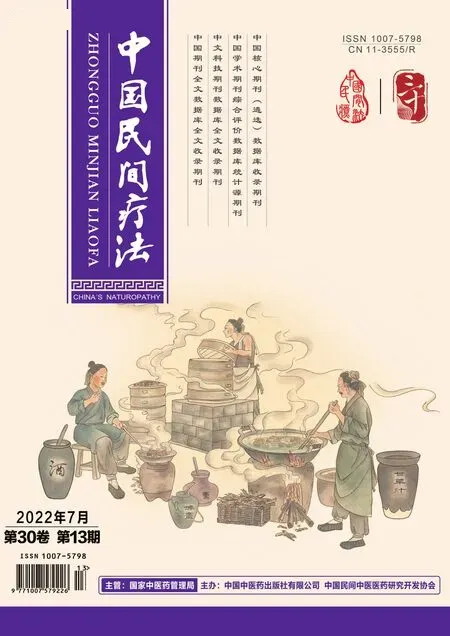毫火針排針淺刺聯合拔罐治療妊娠期急性帶狀皰疹的經驗探析
王博偉,郭玉峰
(1.重慶市永川區中醫院,重慶 402160;2.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帶狀皰疹是由于人體感染水痘-帶狀皰疹病毒后引起的病毒性皮膚病,臨床以皮膚皰疹、神經疼痛為特征,好發于免疫力低下人群[1]。妊娠期女性處于特殊的生理時期,當免疫力低下時可能易患帶狀皰疹。帶狀皰疹以抗病毒、抗炎、止痛、營養神經等對癥治療為主,但由于此類藥物可能對胎兒產生不良影響,故臨床用藥受限。筆者采用毫火針排針淺刺聯合拔罐治療妊娠期急性帶狀皰疹效果顯著,現將臨床體會分享如下。
1 病因病機
引起帶狀皰疹的病原體是水痘-帶狀皰疹病毒,這是一種與單純皰疹病毒相關的雙鏈脫氧核糖核酸(DNA)病毒。多數人在兒童時期感染帶狀皰疹病毒導致水痘發作,免疫系統最終將病毒從大多數位置清除,但它在毗鄰脊髓的神經節或顱底的三叉神經節中仍然處于休眠狀態,當病毒因各種原因由休眠狀態再度恢復活性時,會沿著神經造成全身感染并引起帶狀皰疹[2]。病毒再活化的危險因素包含免疫功能低下、嬰幼兒期有水痘病史、高齡等[3]。帶狀皰疹屬于中醫“蛇串瘡”“纏腰火丹”等范疇,痛如火燎,遷延不愈,對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本病多因正氣不足、情志失調、飲食不節致臟腑功能失調,兼感毒邪而發病,病機為火毒、濕熱之邪侵入肌膚,致經絡不通,氣血不暢,發于肌膚則表現為紅斑、皰疹,以胸部、腰肋部較為多見,有刺痛感[4]。
2 治療方法
臨床治療帶狀皰疹的主要目的是減少疼痛,誘導皰疹快速愈合,避免并發癥發生。帶狀皰疹確診后,應立即進行抗病毒治療,可有效降低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的發生風險,也可使用皮質固醇類激素控制疼痛和皮疹,其他的治療方式包括隔離患者并清潔局部皮膚損傷。臨床治療急性帶狀皰疹的抗病毒藥物有阿昔洛韋、泛昔洛韋和萬昔洛韋,這些藥物有助于減輕疼痛,促進皮損快速愈合,并預防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的發生。全身用皮質固醇類激素常用于治療急性帶狀皰疹疼痛、亨特綜合征和眼部并發癥,當與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時,皮質激素可獲得更好的療效。妊娠期帶狀皰疹在臨床上雖不多見,但由于妊娠期處于特殊的生理時期,如處理不及時或治療方法不當,會對母嬰結局產生不良后果。在治療上,西藥可能存在不良反應,因此選擇一種適宜的治療方法尤為關鍵,既要保證母嬰安全,又要能快速解決患者痛苦。中醫認為,急性期帶狀皰疹以標實為主,治療以祛邪為主,多以清熱解毒、行氣活血、通絡止痛為治則。有研究顯示,針灸治療帶狀皰疹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均較高,且可避免藥物對孕婦及胎兒產生的不良反應,適用于妊娠期婦女[5]。火針作為針灸的一種治療方法,在改善帶狀皰疹疼痛、縮短疼痛時間、降低后遺神經痛發生率等方面效果顯著,在即時止痛方面有明顯的優勢[6-8]。
2.1 火針的原理及應用 火針又稱為燔針、焠針,治療前先將針尖燒紅,然后迅速刺入穴位,刺激病變區域,以達到溫經、行氣、發散之功。《靈樞·官針》云:“焠刺者,刺燔針則取痹也。”火針療法綜合了針法和灸法的療效,既可用其火力外瀉壅結的火毒,又可溫通經脈以促進氣血運行,達到通而不痛的效果。火針療法基于“火郁發之”理論,利用其溫熱效應作用于局部,以激發經氣運行,暢通氣血,氣行則郁伏之熱得以疏散,在溫通經絡、行氣活血的同時,以熱引熱,散邪外出,強開門戶給賊邪以出路,使熱得清,毒得解,邪出正復,防止閉門留寇[9]。
火針基于熱效應改善微循環的理論[10],用加熱的針具點刺皮損區,可使針具接觸部位皮膚炭化,促進治療區皮膚血管擴張,改善局部血液循環,刺激健康組織細胞再生,以修復病變組織[11]。火針刺激可提升局部皮膚疼痛閾值,同時能增強機體免疫力,阻斷機體炎性反應,緩解疼痛[12]。帶狀皰疹病毒在高溫下可直接被殺滅,達到抗病毒的作用[13]。臨床研究報道,火針聯合拔罐治療可加速緩解急性帶狀皰疹患者局部神經痛,并下調血清P物質等炎癥因子水平[14-15]。
2.2 毫火針排針淺刺的原理及應用 毫火針排針淺刺法在傳統火針療法上進行了針具、刺法的改良,選用0.35 mm×40 mm一次性不銹鋼毫針,持10根針灸針整齊排列成一排,即排針刺法。與傳統火針相比,一次性針灸針針尖細小,對皮膚損傷小,快速燒灼皮膚時不易產生疼痛,且針刺深度為1~2 mm,以不超過皰疹基底為度,針刺后出血、感染風險降低。每次治療使用10根針灸針,可擴大刺激面,增加刺激密度和強度,增大的針刺截面可防止進針過深,從而提高其安全性。施針者操作時持針的手要穩,針尖垂直刺入皮膚時快進快出,一般連續點刺3次后燒針復刺。需要注意的是,毫針燒至通紅再行操作,不紅則無效,毫針燒灼后出現彎曲應及時更換。如《針灸大成·火針》云:“燈上燒,令通紅,用方有功。若不紅,不能去病,反損于人。”
毫火針具有針法和灸法的雙重作用,既有針的刺激,又有灸的溫熱效應,可直接激發人體陽氣和經氣,產生灼熱、疼痛針感,緩解病灶引起的疼痛。《素問·皮部論》記載“皮者,脈之部也”“欲知皮部,以經脈為紀”。因病位在皮膚,治療上應遵循“在皮守皮”“刺皮無傷肉”的治療原則,即采用淺刺法。淺刺法治療可直接刺激皮部,具有疏通表里經絡、通暢氣血、協調陰陽的作用。
現代醫學認為,毫火針可刺激下丘腦分泌一種類似嗎啡樣的鎮痛物質并傳遞至痛處,以提高機體的痛閾值,達到鎮痛的效果。有報道指出,毫火針比藥物能更有效地降低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的發生率[16];毫火針可緩解癌癥晚期患者的中、重度疼痛,減少止痛劑用量,降低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17];毫火針治療急性期帶狀皰疹可使周圍組織壞死,機體免疫系統反應啟動后,促使正常組織細胞再生,促進原有結構的恢復[18]。
2.3 拔罐的原理及應用 拔罐是將產生負壓的火罐吸附于局部皮膚上,使其充血或起泡,可促進局部血液循環,加速血液中炎癥因子的代謝,并作用于神經末梢,阻斷疼痛。
研究顯示,在毫火針疏通病灶局部氣血的基礎上聯合拔罐療法,可加速濕濁、瘀血、熱毒的排出,起到清熱解毒、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的功效[19]。火罐的吸附作用可使皮損處污血、膿液排出,取其“在皮者,汗而發之”之理,是為因勢利導,所以能加快疾病恢復進程,改善預后[20]。此外,拔罐產生的溫熱作用對改善局部微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有積極作用,有效避免代謝產物滯留體內,繼而減輕炎性反應,加快受損組織恢復的速度[21]。郝蓬亮等[22]研究指出,急性期帶狀皰疹患者經刺絡放血拔罐聯合圍刺治療后,其末梢血及皰疹局部血常規中性粒細胞水平升高(P<0.05),淋巴細胞水平降低(P<0.05),這可能是其抗病毒的作用機制之一。
3 病案舉例
患者,女,27歲,2020年6月16日初診。主訴:停經39周,右肩背發現成簇皰疹伴劇烈疼痛1周。孕期產檢無異常。患者1周前自覺右肩背瘙癢疼痛,如蟲咬感,未行診治。就診3 d前右側肩背部相繼出現紅斑、水皰,疼痛加重。2020年6月13日于當地醫院皮膚科診斷為帶狀皰疹,予干擾素噴劑、復方黃柏液涂擦,治療后皰疹仍持續增多并蔓延至右腋下,伴劇痛難忍、夜寐不安,遂來求治。刻診:右肩背部及右腋下水皰密集成簇,面積約巴掌大小,基底發紅,皰壁緊張,皰液澄清。予以毫火針排針淺刺聯合拔罐治療。患者取坐位,充分暴露病變區域,用碘伏棉簽常規消毒病變區域,醫生左手持止血鉗,用止血鉗夾取95%酒精棉球,點燃酒精棉球后向針刺區域靠攏,右手持10根華佗牌不銹鋼毫針(規格為0.35 mm×40 mm)排成一排,針尖置于火焰上燒至通紅亮白后,迅速垂直點刺,進針深度1~2 mm,連續點刺3次,針尖變暗后,燒針、復刺同前。先刺早發皰疹,后刺新發皰疹,在無明顯丘皰疹、水皰但疼痛顯著處,用毫火針進行均勻點刺。將所有皰疹刺破后,選合適的部位拔罐,留罐10 min,起罐后用無菌棉簽清理局部皮膚,常規消毒。告知患者針刺處24 h內不能沾水,脫痂后復查。患者治療后疼痛即刻明顯減輕,夜可安睡,第3日皮損結痂而痛止。因2020年6月20日患者入院分娩,后未再行治療。半年后隨訪,患者自述治療1周后開始脫痂,治療兩周后全部脫痂,無遺留神經痛,亦無瘢痕遺留。
按語:本例患者處于妊娠晚期,由于妊娠期婦女精血下注沖任以養胎,易致血虛肝旺,化熱化火;機體相對氣陰不足,衛外不固,致毒邪乘之;加之妊娠晚期胎體較大,氣機阻滯,易形成氣滯濕郁,從而發病。運用毫火針排針淺刺聯合拔罐治療,以熱引熱,散邪外出,可起到清熱解毒、消腫止痛之功,從根本上解除患者病證,對患者順利分娩起到了積極作用。
4 體會
綜上所述,毫火針排針淺刺聯合拔罐具有清熱瀉火、通絡止痛之功,用于治療妊娠期急性帶狀皰疹療效顯著,且無明顯不良反應,充分發揮了中醫外治法的優勢,且操作簡便,具有較高的推廣價值。
在毫火針排針淺刺治療時,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疼痛,對于妊娠期尤其是妊娠晚期婦女,易使其產生緊張、焦慮情緒,可能誘發不適宜的宮縮,故操作過程中需注意以下幾點。①治療前應與患者充分溝通,一方面進行疾病相關知識的宣教,提高其對疾病的認知。另一方面向患者講解毫火針排針淺刺的操作方法,以及可能出現的感覺及注意事項,緩解其對治療的恐懼和抵觸心理。②毫火針排刺法增加了針刺截面,防止進針過深,可有效減輕疼痛刺激。在治療的同時可與患者聊天或播放音樂,使其分散注意力,降低疼痛主觀感受,并囑患者行深呼吸,使肌肉放松,減輕疼痛反應。在治療過程中應嚴密觀察患者的宮縮情況,確保母嬰安全。③治療后做好治療部位皮膚的護理,勤換衣物,尤其是臨近預產期的患者,治療后進入產褥期,汗出較多,注意保持治療處皮膚的干燥、清潔。穿著寬松衣物,避免摩擦損傷。囑患者避免撓抓,局部紅暈、紅腫未消退時切忌洗浴以防感染。告知患者結痂后要待其自然脫落,避免因擔心遺留瘢痕影響美觀而自行撕落痂皮。因妊娠期、產褥期女性為增強營養或促進乳汁分泌,易多食補益之品,可能會有助火生熱之弊,告知其忌服人參、黃芪等補品,以免影響疾病的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