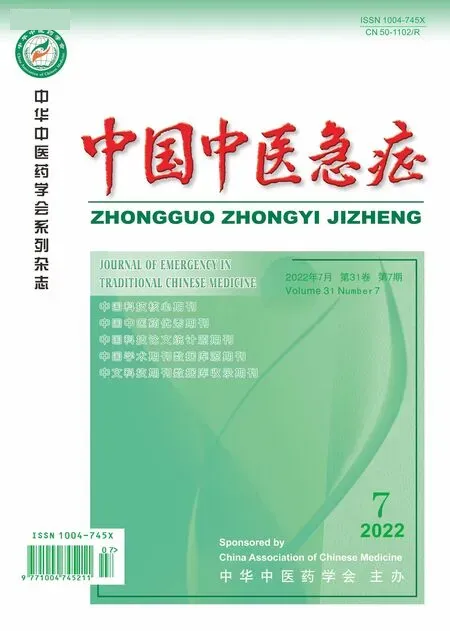從盧云乘醫案分析傷寒重癥治療特色*
李 龍 蔡永敏
(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 鄭州 150046)
盧云乘(1666年-約1739年),字鶴之,號在田道人,古黟(今安徽黟縣)人,新安醫派代表醫家。盧氏精于傷寒之學,臨床擅長治療各種外感、內傷夾雜的傷寒兼證、重癥等。該書載錄盧氏四十余則傷寒病醫案,且多數為傷寒重癥醫案,患者或在內傷病的基礎上合并傷寒,或患傷寒經多次誤治,致使病情垂危,出現抽搐、譫語、昏厥、吐血、耳聾等諸多危急癥狀,盧氏處方用藥,常有桴鼓之效,值得今人借鑒。另外書中醫案包括患者信息、病史、脈證、方藥、分析等,翔實完備,極具研究價值。該書現僅存古代刊刻本,尚無現代影印本或校注本。本書被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項目“《中華醫藏·傷寒金匱類》編纂”所收錄,計劃對古籍原書進行影印出版。本研究以清乾隆三年(1738)得一堂刻本《傷寒醫驗》中的醫案為主要研究對象,結合盧氏對證治方藥的理解,剖析盧氏傷寒重癥治療特色,以期為臨床應用提供參考。
傷寒重癥指一切外感熱病重癥。外感熱病的病因有風、寒、暑、濕、燥、火,其中暑、火、燥統屬于熱,容易出現重癥;寒邪致病嚴厲,亦可出現重癥;風、濕致病多較輕緩,不易出現重癥。故盧氏傷寒重癥醫案中病因多為寒邪及熱邪致病,無風、濕邪氣致病醫案。以下將傷寒重癥分寒邪重癥、熱邪重癥分別論述。
1 寒邪重癥
寒邪重癥是由于寒邪侵犯人體,或傷人陽氣、或閉郁氣機而形成的諸多危急重癥,為傷寒重癥中主要病因之一。盧氏遇此證緊緊抓住表寒重閉、陽氣亡脫兩種主要病機,分別予以發散解表,溫陽固脫之法治療,并在診斷及治療方面多有獨到之處,可供臨床參考。
1.1 表寒重癥,治宜發散解表
表寒可致重癥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病因,然而盧氏極其重視。寒邪從體表入侵,正氣奮起抗邪,若不能驅除邪氣,則形成寒邪閉表。一般認為,寒邪閉表常見于普通感冒,臨床可見發熱、惡寒、流涕、咽癢等輕微癥狀表現;但若寒邪嚴厲,氣機閉阻極重,則會出現傷寒重癥。盧氏醫案中多有因表寒所致的重癥,出現諸如神昏、耳聾、麻木、身腫等危重癥狀。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正邪僵持,邪氣從體表入侵,人體正氣為保護機體而抗邪于表,若正氣或邪氣力量差距過大,則形成一邊倒的狀態,或者邪氣被驅除,或者邪氣入里,只有當正氣和邪氣力量相當,正氣既不能祛除邪氣,邪氣也因正氣充盛而不能進入臟腑,則會在體表形成一種邪正僵持的病理狀態。其二,正盛邪實,若正氣餒弱,邪氣輕微,即便正邪僵持在體表,疾病的癥狀表現也相對輕微,只有正氣充盛,邪氣嚴厲,正邪交爭才會激烈,才會出現嚴重的癥狀表現。因此,在表寒重閉的病機條件下,正邪僵持、正盛邪實兩個條件都具備,才會出現傷寒重癥。
表寒重閉可致傷寒重癥,其病機古人早有論述,但今人往往不察。張仲景《傷寒論》第46條說“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1]。條文中太陽病出現了無汗、發熱、身疼痛、脈浮緊的傷寒表實證,給予麻黃湯治療后出現了“發煩目瞑”的癥狀表現,有學者認為這是中醫在治療中所出現的“瞑眩反應”[2]。但如果以另一個角度考察,傷寒表實證提示邪氣充盛,“服藥已”提示患者因服下辛溫發散的麻黃湯,正氣被大量向體表調動,因此體表的正氣充盛;“微除”指服下麻黃湯后表邪稍微解除一些,但正氣并未戰勝邪氣,在表的邪氣依然充盛,提示此時正邪僵持于體表。當正邪僵持、正盛邪實兩個條件同時滿足,體表正邪斗爭劇烈,處于一種表寒重閉的狀態,出現“發煩目瞑”的癥狀。“目瞑”指目視不明,視物昏花[3],同“發煩”一樣都是正邪斗爭較輕微的結果,若更加嚴重則可出現神昏甚至昏厥。現代醫學認為皮膚具有分泌和排泄功能,人體可通過出汗的方式排泄體內代謝產生的廢物,若皮膚排泄功能受到抑制,則可出現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影響體溫調節,使產熱大于散熱,代謝廢物無法排出,進而嚴重危害人體。表寒重癥即是由于寒邪嚴重閉阻體表之氣,致使皮膚分泌和排泄功能受到抑制,出現諸多危重癥狀。
此證盧氏予以發汗解表之法治療,常用散表羌活煎(羌活、防風、蒼術、陳皮、山楂、細辛、川芎、甘草)、荊防敗毒散(荊芥、防風、羌活、獨活、柴胡、枳殼、前胡、茯苓、川芎、桔梗、甘草)加減。盧氏認為今人稟賦弱于古人,麻、桂發散力度較大,易發泄真氣,故多用羌活、防風和川芎,以其性溫而不燥,發散力度較大且不易耗傷真氣,不論風寒風熱都可以應用,較之麻、桂更為安全。
此證病機容易理解,難在臨證時不易識別。如盧云乘治一丁姓傷寒患者,人事昏沉,兼發熱、頭身痛、目黃、口燥渴等癥,盧氏抓住寸脈微浮,關尺俱緊數,認為表邪不解,予散表羌活煎發散解表,兩劑諸癥悉退。此案目黃、口燥渴等里證表現較為明顯,臨床中若出現這些里證癥狀,醫者很多時候會忽視表證的存在,再加上神志方面的危重癥狀,便更不會考慮從表證論治。面對這種情況,盧氏多在脈證合參的基礎上,憑脈辨證。其表證的脈象判斷標準有二:其一,單寸脈或雙寸脈有力,搏指而動,余脈或緩和、或數急、或沉數、或弦滑,然必充實不衰;其二,脈三部浮緊,或弦或數,重按有力。臨床上遇到傷寒重癥患者,若出現這兩類脈象,并兼有表證出現,可以考慮以解表散寒論治。
1.2 亡陽重癥,治宜溫陽固脫
亡陽是傷寒重癥的重要病機之一。盧氏認為此證多因患者陽氣素虛,體質素弱,又兼飲食休息不慎,感受寒邪,重傷陽氣;或因患傷寒病后經醫生誤治,汗下太過,重傷陽氣而致。陽氣暴亡則失其溫煦、推動、固攝的作用,臨床可見神志昏聵、語言錯亂、肢體厥冷、口鼻息冷、身熱面赤、煩躁不安等亡陽表現,重者可見汗如雨下,二便失禁等陽亡陰竭之癥,相當于現代醫學的心衰、呼衰等臟器衰竭病。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三十一》指出“大病之后,復為風邪所乘,則陽氣發泄,故令虛寒,汗多亡陽”[4],張景岳《景岳全書·陰陽篇》則認為“水性本寒,使水中無火,其寒必極,寒極則亡陽,而萬物寂滅矣”[5],馮兆章《馮氏錦囊秘錄·論傷寒可不可下》認為不僅汗多容易亡陽,“下多亦亡陽”[6]。3人從不同方面指出了亡陽證的病機,與盧氏觀點有相合處。
盧氏認為此證病機乃傷寒邪傳三陰,陽氣孤危欲脫,此時非溫陽不能散其陰霾,故仿仲景白通湯、四逆湯等回陽之意處方成劑,且必以附子為君。若陽氣大虛,但無明顯亡脫之象,僅見四肢厥冷、唇甲青黑、惡寒蜷臥等陰寒內盛之癥,法當溫陽通經,以救陰理中湯(附子、干姜、半夏、桂枝、當歸、蘄艾、陳皮、細辛、炙甘草)等加減治療。若陽氣亡脫,陰氣欲竭,兼見喘汗之癥,非收斂不能固其真元,擬溫陽固脫之法治療,多用急救回陽飲(人參、附子、炮姜、麥冬、五味子、甘炙草)加減治療。若陽亡陰竭之重癥者,于溫陽固脫法中重用山茱萸等固脫之藥,可取捷效。盧氏溫陽固脫之法脫胎于仲景四逆法,在四逆湯溫陽的基礎上,合用生脈散固脫。這種治療思路和當代名中醫李可的破格救心湯在治法上有異曲同工之妙,李老以四逆湯合張錫純來復湯,治療一切心源性、中毒性、失血性休克等急癥導致的循環衰竭[7],盧氏則將此法用于傷寒重癥亡陽證的治療,都取得了極佳的臨床療效。
此證本為陰證,但其諸多癥狀表現與陽證相似,在臨床中實難分辨。盧氏分別從脈、癥上予以辨別。以癥狀而言,面赤煩躁而不光澤,渴欲飲水而不能咽,大便不通而不燥結,小便閉塞而其色淡黃,譫語而奪氣,氣上逆而喘促,咽痛而脈細數無力等皆為陰證似陽,切不可作陽證論治。另外脈象是盧氏判斷陰證的主要依據,包括脈證相應和脈證不應兩個方面。若出現沉細無力,按之欲絕,細滑如絲等陰證脈象,同陰證的病機吻合,可確診陰證,此為脈證相應。若脈見浮數、洪大、革大或尺寸浮大等類似陽證脈象,而外癥兼有身熱面赤、煩躁不安等表現,此時最容易誤診為陽實熱證,必尋按至底,若其脈雖浮取洪、數、大、革,然沉取或無力,或細微,可知其雖似陽脈,本為陰證,此為脈證不應。臨床中遇到傷寒重癥,可參考盧氏診斷陰證的脈、證經驗,考慮用溫陽固脫之法。
小結:盧氏遇傷寒重癥,常常詢問患者素體健康狀況,再與病情結合,仔細分析后方才處方用藥。大抵平素體質虛弱之人難耐病邪,寒邪稍重則陽氣潰敗,病入三陰,易致亡陽重癥;平素體質壯實之人陽氣旺盛,抗邪能力強,卒遇暴寒則邪正交爭劇烈,容易出現表寒重癥。故盧氏每以溫陽固脫之法挽虛人傷寒;以發散解表之法救實人傷寒,這兩組病機和治法為盧氏治療寒邪重癥的主要思路。
2 熱邪重癥
熱邪重癥多由人體感受暑、燥、火邪氣,體內邪熱過盛,或郁閉于內,或充斥內外而成。盧氏認為素體陰虛患者感受熱邪,或熱證大量誤用溫補藥多導致熱邪重癥的出現,在辨證治療上尤其重視熱厥和熱盛的區別。熱厥為熱邪阻結于內,不能外達;熱盛乃熱邪充斥內外,傷及陰血。
2.1 熱厥重癥,治宜清泄里熱,透達郁陽
熱厥是熱邪重癥的重要病機之一。盧氏認為熱厥即為陽厥,此證病機為陰血不歸于陽氣之中,內熱如焚,反現假寒于外;病因多見于身體壯實之人感受風寒之氣,或熱證誤用熱藥致寒熱相抗,導致熱厥。《黃帝內經·素問》認為“陰氣衰于下,則為熱厥”[8],指出熱厥的病機為陰虛。《傷寒論》則認為熱厥病機為“陰陽氣不相順接”[1]。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認為“陽厥即熱厥”[9],并指出熱厥表現出四肢厥逆,身熱面赤,唇燥大渴,口干舌苦,小便赤澀短少,大便燥結,不省人事等陽極似陰證,闡述比較全面。虞摶《醫學正傳》認為“熱厥者,此人必醉飽入房,精氣中虛……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能滲營其四肢也”[10],指出熱厥病機為精氣損耗。
盧氏治熱厥用清泄里熱、透達郁陽之法,常用清里明粉煎(玄明粉、紫菀、枳殼、木通、麥冬、柴胡、澤瀉、甘草)和仿古承氣湯(厚樸、枳實、柴胡、澤瀉、玄明粉、紫菀、甘草)加減治療。這兩張處方針對的熱厥程度不同。清里明粉煎治療的熱厥程度稍輕,僅見神志昏聵,手足厥冷等癥,其脈寸浮而關尺沉數有力,故以柴胡、澤瀉、枳殼、木通解散邪熱,以玄明粉、紫菀攻下邪熱,從表、里兩條路徑泄熱。仿古承氣湯治療的熱厥程度較重,常見昏迷不醒、嘔血傾盆等危急之癥,其脈寸關洪大,僅尺部沉數有力,熱厥已極,此時盧氏主要倚仗下法收功,故方中加厚樸、枳實等藥助玄明粉、紫菀瀉下,并撤去枳殼、木通等藥,使瀉下之力不受牽制。
盧氏對此證的認識符合仲景“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之旨,然仲景以白虎湯為代表的清法治療熱厥,而盧氏治療熱厥尤重泄下之法。盧氏下法與仲景下法在具體應用上有所不同。仲景擅用大黃、芒硝攻下,苦寒直降,斬關奪門。然盧氏則認為硝、黃之性直下,直至下焦,與上中二焦結熱兩不相涉,若用之不當,既不能瀉中上焦結熱,又易傷及下焦真元,故尊仲景“下不厭遲”的原則,主張攻下之旨,不攻下焦,惟開中焦,變仲景“下法”為“潤法”,以紫菀、瓜蔞等辛潤下氣之品代替硝、黃。諸潤下藥中,盧氏尤其推崇紫菀。《中藥學》將紫菀僅作為潤肺化痰之藥[11],而《神農本草經》言紫菀治“胸中寒熱結氣”[12],盧氏采其說,提出“潤下之藥非紫菀不能取效”,認為紫菀治“寒熱結氣”不限于胸中,中焦、下焦之結氣亦可使用。現代學者賈志新等通過實驗,認為紫菀可能通過提高TChE活力對抗復方地芬諾酯所導致的M樣癥狀,從而起到通便的作用[13],國醫大師朱良春亦有用紫菀通便的臨床經驗[14],可見盧氏關于紫菀的論述并非閉門造車,乃經驗之談。
2.2 熱盛重癥,以清熱養陰為大法,隨證施治
熱盛是熱邪重癥又一重要病機。熱邪充斥人體內外,燔灼氣血,可現壯熱口渴、神昏譫語、大便燥結、喘息鼻煽等一派陽盛癥狀。歷代醫家對此病證治論述較為豐富,如《傷寒論》中以大承氣湯治療“譫語”“如見鬼狀”“搓空理線”等神志方面的重癥,《溫病條辨》則以三甲復脈湯、大定風珠等治療熱盛真陰耗竭之證等[15]。本證治療大法無非清熱、養陰二途,然而盧氏具體處方用藥極其靈活,他隨證施治,將清熱養陰的治療大法細化,切于臨床應用。以下將熱盛重癥的具體治法及適應證簡要歸納,并對其治療原則進行分析。
2.2.1 熱盛無結滯,宜辛寒清熱,兼用養陰 熱邪在里,而無氣、血、痰、食之瘀滯,證見高熱神昏、口渴舌干,大汗淋漓,其脈多洪大而數或沉而有神,當以辛寒之劑清里散火。盧氏多以石膏兼用柴胡、葛根、紫蘇、前胡等清揚辛潤之藥,以清理之劑兼解表之藥,欲急急透散邪熱,防臟腑受其煎熬。若陰傷較甚則仿仲景白虎加人參法,配伍人參化生津液。若方中須用黃芩、黃連、梔子、玄參等苦寒之藥,盧氏必兼用陳皮、枳殼、山楂、甘草等藥開豁中脘,兼制苦寒。
2.2.2 熱盛結滯在上,宜清熱兼和解 熱盛結滯在上者,當忝合表里為用,以清熱之品為主,隨證加減施治。若熱盛食滯中脘,可見脘腹脹痛,喘息嘔惡,神志昏昏等癥,治當清熱導滯,盧氏于清熱之品中加山楂、陳皮、枳殼、麥芽等消食導滯藥。若熱盛痰滯上脘,證見熱盛神昏,痰聲如鋸等,則當清熱化痰,于清熱之品中加入半夏、瓜蔞、枳實、香附、桔梗等理氣化痰,漸次展開胸中之結,則熱自散。若瘀血與熱相結,阻于上焦,證見徹夜不眠,如見鬼狀等癥,當清熱散瘀,于清熱之品中加入延胡索、丹參、桃仁、紅花之類。
2.2.3 熱盛結滯在下,當攻下結熱,兼以養陰 熱盛結滯在下,則為陽明燥結之證,其舌必黃燥,且腹痛拒按,當遵仲景之法,急下存陰,盧氏常以紫菀、玄明粉、厚樸、枳實等攻下實熱。然考慮到熱盛陰傷,盧氏常在攻下之外,另加生地黃、麥冬、當歸、玄參等清熱養陰之品,以救將亡之陰。
2.2.4 熱盛耗傷真陰,當徑投養陰 熱盛耗傷真陰,致孤陽獨亢,龍雷之火上越,可見口渴、煩躁、譫狂、斑疹、吐血等癥,脈多見沉細數,或寸關大而尺數。盧氏認為惟水可以制火,地黃乃滋陰上品,壯水之主非地黃無濟其用。故遇久熱不退者,盧氏徑投養陰,恒以地黃為君,引領麥冬、沙參、牡丹皮、當歸等,諸藥聯合施治。
2.2.5 熱盛血瘀,當泄熱逐瘀 盧氏所謂熱盛血瘀即仲景所言熱結膀胱證,其證熱與血結,癥見腹痛、譫妄等,盧氏仿桃核承氣湯之法,以紫菀、玄明粉、枳實攻下實熱,并用桃仁、當歸、赤芍、莪術等大隊活血之品散血逐瘀,較仲景桃核承氣湯,活血力量更大。
針對熱盛重癥,盧氏以清熱養陰為治療大法,在具體治療上大體遵循以下3個原則:其一,依據熱邪和陰傷的程度確定清熱藥和養陰藥的配伍關系。熱盛則傷陰,熱愈盛則陰愈傷。盧氏處方用藥極其重視熱邪和陰傷的程度,若邪熱充盛,未傷真陰,則以石膏等清熱藥為主,而僅以黨參化生津液;若陰傷較重,則石膏與麥冬、生地黃等養陰藥并用,清熱養陰;若耗傷真陰,則撤去氣分之藥,徑投養陰。其二,根據熱邪所在部位選用不同的藥物清除邪熱。熱邪在上在外者,多見中、上二焦熱證,以石膏等清熱藥配伍葛根、紫蘇等解表藥,辛寒清熱,意在從表驅邪;熱邪在下在內者,多見中、下二焦熱證,以紫菀、玄明粉等配伍厚樸、枳實等,苦辛寒并用,意在從里驅邪。其三,根據不同兼證隨證施治。由于患者個體差異,臨床中熱盛重癥往往夾雜不同的兼證,即無形之熱邪夾雜有形之瘀血、痰飲、宿食等病理產物。若只考慮無形之熱邪或有形之實邪某一方面,則方不對證,難以獲效。盧氏依據兼證表現,以清熱為治療大法,隨證摻入活血、化痰、消食藥等消散實邪,方能切中病機,取得預期治療目的。
小結:對于熱邪重癥,盧氏抓住熱厥和熱盛兩種主要病機。熱厥重癥病機為邪熱內熾,不得透散,外癥多見手足厥冷等寒證表現,治宜清泄里熱,透達郁陽;熱盛重癥病機為熱邪充斥內外,傷及陰血,外癥現一派熱盛陰傷之癥,以清熱養陰為治療大法,隨證加減施治。
綜上,寒邪重癥和熱邪重癥是盧氏醫案中傷寒重癥的兩大類別。盧氏治寒邪重癥緊扣表寒重閉、亡陽兩大病機,分別予以發散解表、溫陽固脫法治療。治熱邪重癥則抓住熱厥和熱盛兩大病機,并以清泄里熱、透達郁陽之法治療熱厥重癥;以清熱養陰為大法治療熱盛重癥,并隨證施治,將清熱、養陰的治療大法細化。盧氏在以脈象判斷病機的經驗、對紫菀攻下的認識以及對清熱養陰法的細化等諸多方面的認識頗有獨到之處,可為今人在傷寒重癥的研究和治療方面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