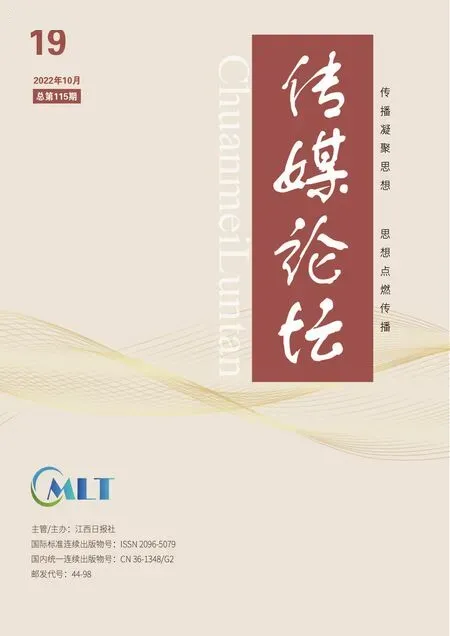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與引導
吳智敏 翟 敏
信息時代下,社交媒體不僅是大眾生活中重要的信息來源,還賦予了其更自由的表達權。當社會熱點事件發生后,參與公共輿論討論的聲音將不可避免的在社交媒體上相互交織,富有個人情感色彩的表達使公共輿論格局變得愈發多元、復雜。
一、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
安東尼·梅菲爾德將“社交媒體”界定為“用戶享有極大參與空間的新型在線媒體”。從這個概念中可以看出社交媒體最大的特點即受眾享有極大的傳播自主權,輔以社交媒體交互、即時、開放的媒介特點,注定形成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多維化局面。
社交媒體中病毒式傳播的內容多是充滿感情的,此類內容易讓受眾產生共鳴以獲得情感體驗[1]。無論是“神舟十三號”成功對接空間站點燃的國民驕傲,還是袁隆平院士逝世引起的舉國悲慟,抑或是掀起民眾抗議的河南營養餐事件,社會事件能發展為公共輿論并引發熱議的共同點在于:激起大眾情感價值。當某一社會事件觸發了大眾的情感刺激,人們會趨于通過表達來抒發自我情感,而社交媒體就成為了大眾情感表達的絕佳場所。因此,社交媒體中的公共輿論大多伴隨著大眾情感的發酵而發展。
以新浪微博為例,不少輿論事件通過微博擴散傳播、引發討論、得到解決。但從微博官方管理員定期發布的“社區公告”中能看出因在社交媒體上盲目跟風、隨意捏造的情感表達而造成的公共輿論場紊亂的事件屢次發生,這與期望的公共輿論情感表達的“烏托邦”仍存在著不小差距。因此,引導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朝良性、健康方向發展迫在眉睫。
二、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存在的問題
在社交媒體的勃興為普通大眾搭建了意見交流平臺的同時,但其存在的弱把關機制、網民素質參差不齊以及傳播主體匿名等問題也讓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出現痛點,其中感性主導理性、煽情夸大事件、情緒放任自由是亟待解決的三個問題。
(一)后真相時代,感性主導理性
“后真相”的“后”字表明真相已經放在了事件的次要位置上,當參與討論的公眾只注重情緒化觀點的輸出,更渴望從公共輿論事件中追求感官的刺激、細節的離奇,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就會出現脫軌、偏差。從當下的輿論環境來看,社交媒體之上的情感表達面臨著一個“大眾言論自由意識不斷覺醒”與“所發之聲缺乏理性”的矛盾。
在社會事件的傳播中基于社交媒體的弱把關機制,網友們極富主觀色彩的描述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匯聚、粘合,感性的風潮徹底蓋過了尋求事件真相理性的一方。通常在調查結果未出前,習慣短視頻等信息獲取方式的受眾更是看了某些自媒體捕風捉影的標題就下結論,使并未跟進了解的受眾形成富有情感色彩的思維定勢。
(二)注意力時代,煽情夸大事件
赫伯特·西蒙曾提出一個觀點——注意力經濟,即隨著信息的發展,有價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2]。社交媒體時代印證了這一觀點。為了吸引公眾注意力,部分傳播者在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時往往煽情夸大事件。
以2021年“廣州方圓小學學生受體罰吐血”事件為例,家長發文強調“運動量是要殺人”等觀點,加上孩子“血衣”照片,觸目驚心的內容使網友的注意力被吸引,情緒迅速被點燃。網民在社交媒體中的言論發表多為“這樣的老師就該下地獄”等極具情緒化的偏激表達,加速了傳播鏈的下一輪滾動;同時,一些媒體為了吸引網友的關注目光,在報道中將事件貼上“師生關系”“師風師德”的標簽,事件上升至為當下的社會痛點“教育”上來,公共輿論隨即爆發。最后查明,該事件中的家長夸大了事實,且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也不可忽視。
無論是從個人層面抑或是社會層面,此類事件的影響都不容小覷,如何對社交媒體上為了吸引注意力而進行公共輿論炒作帶來的社會影響進行控制勢在必行。
(三)匿名化時代,情緒放任自由
社交媒體的匿名傳播特點使得偏激、暴力的言論肆意擴散,由于被匿名狀態掩飾的個體處于極度松弛狀態,他們感受不到社會約束力,該情景下個體的社會責任感被極大降低。因此,社交媒體中的公眾更易做出實名狀態下不會進行的有違社會規范的沖動行為,從而造成公共輿論中情感表達的亂象[3]。
公共輿論往往具有明顯的情緒化特征,公眾的表達動機中夾雜著強烈的怨懟情緒。匿名傳播下的語言暴力行為迎合了狂歡式的意義消費,網友甚至只是借由敲擊鍵盤吐槽、辱罵的方式來排遣生活中的不平。社交媒體上情緒的匿名化匯聚傳播常常使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偏離正確軌道。
三、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存在問題的原因
在傳統媒體時期,報社、電視臺等媒介組織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規范標準[4]。一篇放到公眾面前的輿論事件一定要經過記者、編輯重重把關。傳統媒體以其強大的議程設置功能影響著大眾生活中的議題,部分主觀色彩極濃的報道影響著大眾怎么去定義這個議題。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傳播技術的成熟為大眾搭建了情感表達的平臺。基于傳播上具有跨越時空的自由,大眾的群體心理發生轉變,同時當下存在的社會矛盾也進一步催生了公共輿論情感表達問題的出現。
(一)媒介技術勃興搭建情感表達平臺
社交媒體時代下,各媒介平臺的研發登場與5G通信技術的突破為公共輿論的形成提供了平臺與技術支撐,有私密性強的微信,有圈層性開放的微博,還有以抖音為代表的具有視聽優勢的短視頻平臺。
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大眾的情感表達得到了落地點,公眾在社交類媒體上分享對生活的感悟、在政務類媒體平臺控訴社會不公現象、在救助類媒體平臺上進行自身情況的描述從而尋求社會的幫助。社會熱點事件通過諸多平臺的擴散傳播得到萌芽而后形成公共輿論。在此過程中,媒體平臺擔任了匯攏更多地區、更多階層情感意見的角色。
(二)群體心理筑牢情感表達極化基礎
勒龐曾提出“群體心理”的概念:聚集成群的人易將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個方向,形成群體心理。處于社會大環境中的多數人在意見傳遞中為了不顯得其“標新立異”往往會選擇趨同,少數人的意見在討論的過程中被多數意見所吸收而湮沒[5]。
2021年9月,一則“長沙采耳大媽用采耳工具摳腳”的視頻引起廣大網友關注。其間有網友指出那并非采耳工具,但大多數網友的厲聲指責裹挾了這一理性意見表達。事發后經記者證實摳腳的東西只是敲打叫賣工具。當社會事件在社交平臺上發酵傳播時,多數的意見并不是經過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僅僅是某些極具煽動性言論的跟隨。如果事件的討論產生了情感引導理性的基礎,事件的意見表達就變得復雜起來,不可控的因素也會增加。
(三)社會矛盾激化情感表達極端化傾向
在社會轉型的浪潮下,各領域都存在著改制與革新,社會矛盾進一步增多,醫療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能夠時刻觸發大眾的感官神經。社會大眾著重思考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如何讓政府機關看到自己的訴求。但當大眾需求的表達與政府對大眾需求的實現之間存在偏差,基于理想與現實的不同,大眾容易對所處的社會環境、階層產生焦慮感,焦慮感催生非理性的偏激心態,因此在情感表達上易表現出極端化傾向[6]。
相較上層建筑的有關事件,代表基層群體利益的公共事件更能夠激起大眾的集體表達欲,如陳春秀高考被頂替事件反射出的教育矛盾、河南營養餐集體嘔吐事件代表的食品安全問題、商洛扶貧造假事件反映的部分基層干部欺上瞞下的工作作風,此類社會民生事件成為社交媒體上公共輿論情感表達極端化的重災區。此類輿論事件情感表達的大眾大多是社會中低階層的普通百姓,他們沒有社會諸多領域的特權與捷徑,所以該群體極度渴望公平。因此,政府面對社交媒體上大眾關于社會矛盾極端化的情感表達應進行合理疏導,并及時做出回應,這是維護輿情環境穩定的重要一步。
四、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的引導策略
除了把握傳統輿論場的風向外,對社交媒體的公共輿論的管控與引導也不容忽視。若不對社交媒體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進行及時規范的疏導,勢必會激化社會沖突,沖刷社會穩定的基石。
(一)政府:實時體系監測,正視公眾情感訴求
不同于傳統媒體上公共輿論的發展,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病毒噴霧式”的傳播特點要求政府部門必須建立體系化的公共輿論監測機制,利用云社區、大數據等新型智能網絡技術監測實時的大眾情感態度,通過檢索事件中情感表達的高頻詞、發表地等關鍵信息在第一時間掌握公共輿論的風向與基調。
對公共輿論情感表達的檢測完成后,應正視公共的情感訴求,及時發布官方權威的信息,面對大眾提出的問題應切實回答,空話、套話、虛話都不應出現,并在源頭扼住因大眾情感表達偏激而造成的流言與謠言,只有受眾及時了解公共輿論事件的根源及走勢發展,才能避免民意的阻塞,讓公共輿論渠道暢通發展,樹立公眾心中政府的公信力。
(二)意見領袖:發揮中堅力量,合理表達輻射公眾
意見領袖作為引導社交媒體情感表達的中堅力量,其立場和態度極大的影響著甚至直接決定了公共輿論的走向,如何發揮意見領袖的力量引導公眾情感表達成為肅清公共輿論大環境的重要議題。
社交媒體上意見領袖的地域分布、圈層代表廣泛多樣,面對社交媒體上眾多的意見領袖首先應進行篩選,并對其進行社交媒體基本素質的培養,而后借助意見領袖的影響力來引領社交媒體上其他受眾的表達立場[7]。相關部門要密切關注意見領袖的情感表達,對其偏軌的言論及時勸導、更正;對情感表達立場促進社會共識整合的意見領袖進行精神與物質上的鼓勵嘉獎,培養其榮譽感從而促進公共輿論的良性發展。
除了對社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進行組織引導外,在傳統大眾媒介中發展起來的意見領袖同樣需要跟上時代潮流。由于受眾對傳統媒介的接觸率大幅下降,傳統媒介中意見領袖的觀點抵達率隨之降低,其社會影響力也不如從前,組織傳統媒介中發展起來的意見領袖學習社交媒體,使其進行通過社交媒體情感表達引領公共輿論發展。如著名軍事評論家張召忠先后在新浪微博、嗶哩嗶哩開通賬戶后,憑借其在傳統媒體上建立起的影響力,在社交媒體上也吸引了不少受眾的關注。
(三)公眾:理性批判思考,規范自身情感表達
在海量信息翻滾的社交媒體時代,沒有信息批判意識的建立,注定被淹沒在巨大信息量的虛假泡沫中[8]。在正確解讀信息的同時進行理性、客觀的情感表達是每一個社交媒體應用者都應該具備的能力。
目前來看,大部分公眾已能夠熟練運用社交媒體,但在真實性、全面性都有待商榷的公共輿論信息前并不具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在意見的情感表達上并不成熟。作為公共輿論受者時,要求公眾在合適正確的角度上理解媒介信息所傳達的真正含義,經過理性思考后再進行個人思辨性的情感表達;作為公共輿論的傳者時,也應避免為了擴大傳播效果而添油加醋、顛倒黑白,這是公眾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情感表達必修的一門課程。
五、結語
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給公共輿論的情感表達打開了全新的發展格局,在這樣一場充滿機遇與挑戰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揮社交媒體的傳播優勢,正視大眾的情感需求,借力科學技術對公共輿論情感表達進行監測,以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帶動大眾的情感表達向真實、客觀的方向發展,同時注重培養大眾自身情感表達的規范意識,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社交媒體中公共輿論情感表達環境風朗氣清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