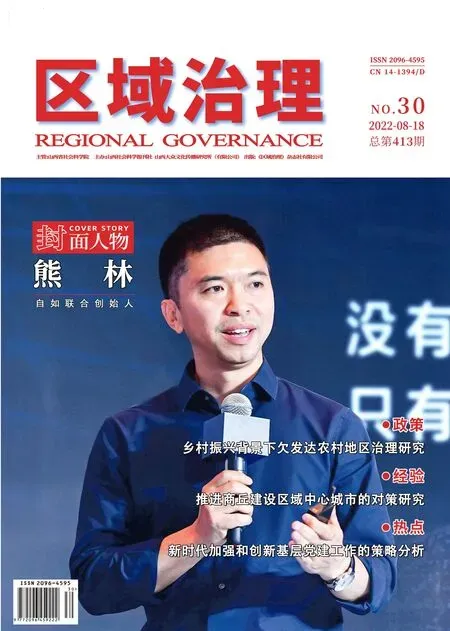論居住權的制度價值
天津工業大學 趙晞蒙
一、居住權的歷史沿革
居住權的制度是一個較為古老的制度,最早出現在羅馬法中,時代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促使以德國、法國為主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羅馬法的影響下,都將居住權制度加入了民法典中。
二、居住權制度的設立
(一)設立居住權的方式
(1)合同。合同是雙方當事人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誠實守信的基礎上達成合意后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條規定:設立居住權,當事人應當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居住權合同。設立居住權的雙方一般存在著特殊關系,如親屬關系,且相較一般的商業交易,居住權合同的交易復雜程度較低,風險較小。
(2)法律規定。法律規定中對設立居住權作出了明確規定。
(3)遺囑或遺贈。房屋所有權人遺囑中設立了居住權,目的是為其生存的配偶設立,同時該房屋也可以由子女繼承。尊重遺囑人生前對其財產的安排,這樣保全了各方利益。
(4)法院裁判。在離婚案件中設立居住權的情況很多,涉及的問題也十分突出,雖然可以依照司法解釋,但實踐中該如何操作依舊是一難題,法院裁判更多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同時對象不確定,就操作而言,法院裁判的方式相對來講具有較大的靈活性。
(5)如下案例更好地詮釋了設立居住權。
【案例1】涉案房屋原為公有住宅,實際居住人多為歷史原因及政策原因取得單位福利分房的職工及家屬,因原產權管理單位無力負擔修繕費用,產權歷經多次無償或低價轉移,但每次產權轉移過程中都對實際居住人的居住問題有所約定,或約妥善管理、或約妥善安置、或約不得強攆,均保障了實際居住人的居住權益。最后一任具有房屋產權的單位對外負有尚未還清的債務,將涉案房屋產權經司法程序直接劃歸本案原告某公司所有,以抵償其所欠債務,原告某公司因此取得涉案房屋的產權,原告某公司亦應妥善處理原有實際居住人的居住問題,綜合保障其居住權益。被告郭某一家經單位調換住房至涉案房屋中居住,其居住權益亦應得到相應的綜合保障。因此,原告某公司要求被告郭某一家騰退涉案房屋、并拆除自建房以及支付占有房屋使用費,此依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2】相關司法解釋規定:“離婚時,一方以個人財產中住房對困難者進行幫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權或者房屋的所有權。”該規定可表明,夫妻雙方離婚時,一方因生活困難并無居住地,有房一方可以設立居住權予以幫助。該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居住權的主體,屬于特定主體,僅指離婚案件中的夫妻一方。相關法律規定:婚姻存續期間居住的房屋屬于一方所有,另一方以離婚后無房居住為由,要求暫住的,經查實可據情予以支持,但一般不超過兩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居住權是以離婚時某一方無居住地為前提而存在,根據上述法律規定以及一般日常生活經驗,婚姻法司法解釋雖然沒有將居住權明確規定為是臨時還是長期,但一般情況下居住權不可能無期限長時間存在。離婚時一方為另一方設立居住權、出于好意給予另一方幫助,這與夫妻共同生活時的互相扶養義務的性質不同。夫妻共同生活時互相扶養是因夫妻關系產生的法定義務,但夫妻雙方離婚后此項義務也隨之消滅,然而離婚時設立居住權并不屬于法定扶養義務的延伸,系因原婚姻關系所產生的臨時性幫助,附有條件與期限。本案原、被告雙方沒有明確約定居住期限,現原告楊某要求被告伍某搬離,被告伍某有勞動能力卻主張無期限居住構成權利濫用(擅自改變房屋的結構、用途,不當使用房屋亦能在本案構成權利濫用),但原、被告雙方離婚時間不到一年,如原告楊某想居住在訴爭房屋內可對三樓進行裝修,也可依法解除與一樓承租人的租賃合同,原告楊某未舉證證明被告伍某無房居住的生活困難的情形已經消失,亦無證據證明具有其他阻卻被告伍某行使居住權的事由[1]。
(二)設立居住權是否需要登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條規定,設立居住權的,應向登記機構申請居住權登記。居住權自登記時設立。居住權歸類于用益物權,居住權人享有對所住房屋的支配力及管領力,希望運用物權請求權保障自身的合法權利。房屋居住權登記之后就具備對世性,能夠起到對抗第三人的作用,對居住權人的利益也能盡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因此,若房屋的居住權必須登記的話,即使所有權人將設立居住權的房屋出賣,居住權人仍然可以對抗該房屋受讓人,這樣就能避免因所有權人處分房屋導致居住權人無法實現自身權利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條規定,居住權不得轉讓、繼承。設立居住權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居住權帶有人身屬性,屬于人役權,一般情況下居住權是無償設立的,但當今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養老需求與日俱增,養老方式也在發生著各種變化,如今還出現了以房養老的新方式,當事人可以自行協議約定有償使用該房屋以滿足老年人養老需求。其次,居住權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居住權不能發生轉讓與繼承。同時,一般情況下居住權人不能將設立居住權的房屋出租,但當事人雙方之間有特殊約定的除外。因為有些情形如以房養老,因老人的生活較為困難,法律允許雙方形成居住權人以出租房屋的方式來取得收益的合意[2]。
(三)居住權的消滅
居住權是為居住權人提供住宅居住及其他相關的權益權利,也有可能權利濫用,根據現實中反映出居住權人濫用權利的情況主要包括未經居住權人的同意進行違法改建房屋、違法出租房屋、違法買賣等。由于不同情況的濫用造成的損害也不同。然而筆者認為在居住權人濫用情況下影響房屋正常使用,居住權應該予以滅失[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條規定,居住權期限屆滿或者居住權人死亡的,居住權消滅。居住權消滅的,應當及時辦理注銷登記。居住權消滅有兩種情況,一是居住權約定期限到期,二是居住權人死亡;上述兩種情況出現一種即可。發生上述情況之一時,居住權會就此消滅,消滅之后應當及時到相關部門進行注銷登記,但注銷居住權登記并不是其消滅的必要條件,這不同于居住權的設立登記。
三、居住權與其他權利的沖突
(一)居住權與抵押權
居住權與抵押權均是需要設立登記,居住權是以占有為前提的用益物權,抵押權是不得轉移占有的擔保物權,均屬于物權。因此兩者若發生沖突的解決思路是可以根據登記時間先后順序來進行判斷。如若設立居住權的房屋抵押,分別為居住權已登記或居住權未登記,抵押權不能排除居住權人權利,僅限帶居住權拍賣[4]。如抵押權登記先在抵押房屋上登記設立,住宅上并未設立居住權,抵押權優先于債權,可排除居住權對住宅進行處理。理由如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條規定:居住權無償設立,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設立居住權的,應當向登記機構申請居住權登記。居住權自登記時設立。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百零二條規定:以本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的財產或者第五項規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應當辦理抵押登記。抵押權自登記時設立。居住權和抵押權均需設立登記。其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百零五條規定:抵押權設立前,抵押財產已經出租并轉移占用的,原租賃關系不受該抵押權的影響。如若在買賣法律關系中,先成立租賃權不得強制排除。
(二)居住權與所有權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規定: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所有權包含著占有、處分、收益、使用等權利,二者會存在著權利重疊,因此會發生沖突情況。居住權通過合同或遺囑來訂立,而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在意思自治基礎上簽訂合同或遺囑。合同簽訂對雙方具有約束力。除非合同到期或者解除合同情形,否則發生沖突時應以居住權優先。
【案例1】居住權與所有權的對抗。上訴人(原審被告)姜某、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高某之女。位于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區10-2-201房屋原為拆遷安置住房;高某及妻殷某、高某之子及妻姜某,一同居住在該房屋,某年高某之妻殷某病故,同年某月高某購買了此房屋,系為該房所有權人。同年某月,高某之子及妻姜某登記結婚,姜某婚后與其母、其子一直居住上述該房屋。
高某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姜某騰出該房屋。同年,高某因涉嫌詐騙被逮捕。高某在涉嫌詐騙案審理過程中死亡。但高某生前留有公證遺囑,指定該房屋由高某之女一人繼承。高某之女于同年某月經申請參加本案訴訟。同年某月,房屋所有權進行變更。高某之女為此房屋所有權人,參加本案訴訟,請求法院依法判姜某騰退房屋及交出該房屋鑰匙。而姜某則辯言:高某已在訴訟中死亡,應中止訴訟。應確定遺囑繼承人高某之女和高某之子是否會到庭參加本案訴訟、繼續進行訴訟程序。高某之子已經因病多年臥床不起,其患有繼發性精神障礙、腦梗塞后遺癥、失語等重大疾病;因此高某之女所提供的高某生前遺囑并非為高某的真實意思表示,遺囑應當無效;姜某還認為上述該房屋也應有一部分屬于其丈夫(高某之子),并不同意高某之女的訴訟請求。
原審法院在審理中認為,姜某在訴訟中并沒有提交新的證據可以推翻高某之女所提交的公證遺囑,該房屋所有權人系高某之女。因此高某之女對該房屋具有占有、使用、處分等權利。如今姜某未經房屋所有權人高某之女的同意,居住于該房屋,侵犯了高某之女的合法權益。因此,判令姜某騰退該房屋及房屋鑰匙交還給高某之女。原審判決作出后,姜某對原審判決表示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要求中級法院撤銷原審判決。
二審法院審理案件后認為,訴爭的房屋原性質為拆遷安置房,后高某購買該房屋系房屋所有權人,高某之子對該房屋享有居住權利,屬于被安置人。姜某與高某之子婚后一直在訴爭房屋內居住,其與高某之子婚姻存續期間,享有在該房屋居住的權利。姜某提供的證據不當然具有否定公證遺囑的有效性。則高某之女依照高某遺囑繼承了該房屋的所有權,但是不應該因此剝奪高某之子、姜某居住的權利。高某死亡后,由遺囑繼承人高某之女參加本案訴訟,符合法律規定。綜上所述,二審法院作出判決撤銷了原審判決,并改判姜某應騰退該房屋客廳北側一間、南側東一間交還給高某之女,姜某可在客廳南側西一間房屋內居住,其余部分廁所、廚房、客廳雙方共同使用。
就本案例分析,兩級法院對審判程序組織合理合法、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判決結果卻截然相反。原審法院基于傳統物權,根據遺囑認定該房屋所有權人系者高某之女,據該物享有完整權屬。認定其訴爭房屋實際占有人姜某侵犯了高某之女高某所有權屬,判姜某敗訴。二審法院依舊確認高某之女根據有效遺囑繼承系該房屋的現在所有權人,同時肯定了姜某作為高某之子的妻子對該房屋享有依法居住的權利。這一權利在此案例中取得了“絕對權之王”的稱號。
四、居住權制度的作用
居住權具有構建美麗和諧社會、減少家庭生活矛盾的重要作用。居住權是在家庭、夫妻、朋友關系等一系列特殊身份的基礎之上產生的制度,在緩和關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樣在撫養未成年人和贍養老人等方面也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住權具有物權效力,因此,該制度幫助確認了非房屋所有權人能夠使用房屋的權利,起到了保護老人、未成年人合法合理在他人房屋居住的作用。其次,居住權保護弱勢群體的作用是建設法治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5]。而居住權是充分體現這一精神的法律之一。居住權解決了即年邁的父母,離異后一方暫無居所等居住問題,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重點在于保障他們的生存權,要解決弱勢群體中無居住場所的問題是最基本的問題。
居住權制度也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理念。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不動產需要留給子孫后代,設立居住權制度,則是為解決這些糾紛提供有效途徑,該途徑能夠加強大眾人民的法律思想,強化公民法治觀念,將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緊密結合,從而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與完善。
五、結語
當今社會的飛速發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帶來了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因此,根據現實需要,應當通過立法提供制度保障,而法律往往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及時修訂和完善法律變得非常重要。居住權制度的設立,提供了新的模式解決現有問題,符合現實生活的需要。同時,為應對和有效解決各種居住權的爭議和糾紛,并借鑒現代各國居住權領域所取得的立法和學術成果,更好地完善我國居住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