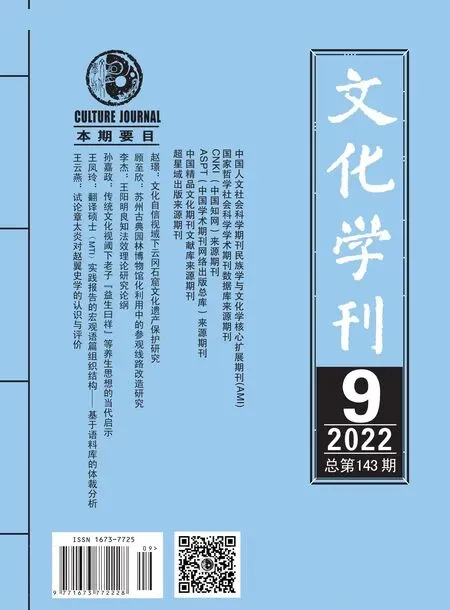修辭觀視角下西方哲學與文學問題
于 航
在西方的傳統思想文化中,修辭手法其實是普遍存在于語言文化中的一種藝術,而文學出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產生某種精神方面的效果,從而引發人們對于某一事物的思考,通過文字語言的組合產生一種美感。一直以來,在西方文化的視角下文學與修辭之間本身就存在著一種天然性的關系。然而另一種思想認為修辭手法其實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一種語言搭建的技巧,這種技巧本身就不屬于知識的范疇,可以說,修辭手法的存在會破壞哲學和真理。但是隨著修辭觀念的持續性改變,在19世紀末期關于哲學與文學關系的探討也發生了轉變。尤其是到20世紀后,隨著修辭觀念的復興以及后現代形而上學批判思潮在文學領域中的盛行,傳統的修辭觀點更是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而哲學一直屹立于文學之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戰。那么,如何從修辭的視角下來探討文學與哲學之間關系的變化呢?針對這一問題,本文主要從修辭觀念變化的角度作為切入點,集中探討了西方思想界哲學與文化之間關系的變化歷程,同時也為這一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和判斷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系。
一、遠離真理的修辭觀念下哲學與文學之間的對立關系
在古希臘,智者柏拉圖將修辭作為一種技術與烹飪技術和裝飾技術并列呈現,這也說明了修辭與哲理之間毫無關聯性。但是,柏拉圖卻發現,利用修辭手法能夠提升訴訟過程中的說服力,可見修辭手法對于創建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幫助。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修辭手法是不依賴于實踐而存在的,僅僅是通過模仿而形成的一種表面現象,因此,修辭手法與辯證的哲學之間是對立關系。而蘇格拉底認為,修辭和演講作為一種技藝并不是真正從知識角度出發的技藝,修辭的存在只是為了達到某種記憶而產生的一種勸說技巧。也就是說哲學是一種揭露善惡,通過啟迪人們依照本性行善所追求和描述的一種理想生活。而基于修辭術的語言學只是能夠讓人們產生某種滿足和快樂的技巧。因此,在古希臘時期,人們主張修辭必須要服從于哲理,認為理想的修辭方式就是從哲學中得出的智慧然后再反作用于文學知識,通過這樣的修辭觀念來闡述文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
而到中世紀之后,修辭就變成了一種學術方面的活動,修辭與語法和邏輯共同構成了中世紀語言學科中的三大類目。這一時期的修辭學不僅僅是用在演說方面,更多的是應用在書信描寫方面,而修辭學也更加關注文字本身的風格和特征。到啟蒙時代后,又有學者認為真理需要對事物的本身進行成熟的思考后才能得出,而不是需要通過人為的措辭方式和辯論結果得出,也就是說人為的措辭和辯論不能稱之為真理。這一時期的學者認為修辭作為一種技術遷移和應用在文字語言的表現手法中只是一種語言表達方式,但是這種表達方式卻會迷惑人們的判斷。而在詩歌界,人們普遍認為詩歌與修辭手法之間相互聯系,是充滿欺騙和嘲諷的謊言,與哲學之間相互對立。柏拉圖曾經說過,我們不能太認真地將一首詩歌當作真理。在那一時期的學者眼中哲學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引導人們在普遍獲得的真理下形成一種理性且正義的生活方式,而詩歌則是以修辭手法為基礎達到一種煽動人們情感的目的。因此,修辭的存在對于理性原則來說是一種違背和挑戰,修辭在意識理論方面不真實和不可靠的特性,容易引導人們誤入歧途。一方面,這些學者將語言藝術當作哲學和理論的注腳,為當代社會中的思想體系或哲學提供了語言論述方面的幫助,卻抹殺了文學獨立性的特征。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學者又將藝術作為了自身理論的替代,使藝術永遠蟄伏于普遍性理論之下。也就是說,在遠離真理的修辭觀念下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對立的,在這一階段文學始終蟄伏于哲學之下。
二、以真理觀念為基礎的修辭觀下,文學能夠反映哲學
關于真理與修辭之間的關系,還有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真理與修辭之間保持著某種聯系,修辭應當以哲學知識為基礎,并且以社會普遍道德作為根基,建立在真理與語言邏輯的基礎之上。亞里士多德在后來糾正了柏拉圖一些極端的思想,亞里士多德將修辭視作了一種勸說方式以及觀察的能力,并且對不同的修辭手法進行了區分[1]。亞里士多德將通過演講進行的勸說分為了三種方式,一種是取決于演講者本身的人格;另外一種是取決于聽眾心態和演講詞中內容的一種修辭手法;第三種就是演講過程中的理論道德、情感表達以及邏輯表達這三方面的結合體。事實上演講過程就是理論道德、情感共鳴以及邏輯表達三位一體的體現。由此,亞里士多德也將修辭與詩歌、政治學、辯證法、邏輯學以及心理學之間相互連接,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將修辭與人類所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直接聯系了起來。在詩歌學中,亞里士多德專門探討了不同的詩歌措辭風格,并且提出詩歌中措辭體現出的最佳價值就在于其清晰和條理的表達方式。除此之外,亞里士多德還專門提供了修辭與演示邏輯和哲學之間的聯系,并以哲學理性思維看待了修辭學,將哲學中的不同分支與修辭學之間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從這一點來看,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之間的觀念存在顯著的差異性。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的過程其實就是演講和辯證的過程,因此,修辭學就相當于辯證學,而修辭學還可以通過增加語言的多樣性來提升哲學的真理體現價值。
昆體良認為,一個完美的辯論者應該在了解哲學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完美的辯論和解說。首先,一個辯論家必須要具備一定的道德和品行,也就是說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成為優秀的辯論家。辯論家首先需要學習道德原理,了解社會中一系列關于公證的相關真理,但是辯論家所學習的知識只能從哲學中去尋找。昆體良認為,哲學中擁有的知識是多方多面的,因此,辯論家也應該是具備哲學品質的人,換句話說,哲學也是構成演講和辯論知識的根基和道德源泉。昆體良這樣解說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拯救當代社會下的哲學思想,因為昆體良認為,許多專心于雄辯以及演講的人們都放棄了對于哲學和真理的追求。除此之外,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許多哲學家都選擇遠離公眾和社會進行生活,這在昆體良看來也是一種缺憾,因此,昆體良才認為,未來的雄辯家必須是與社會生活貼近的且具有良好哲學理論基礎的雄辯家[2]。
朗吉努斯認為,崇高的哲理不僅帶來了美感,同時,還具備了真理的價值。一些具備崇高美感的文章,總是能夠潛移默化地提升我們的靈魂。朗吉努斯將文章中崇高的風格確認為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分別是偉大的文字概括能力、慷慨激昂的情感、具有邏輯性的修辭手法、高尚的措辭方式以及人的尊嚴和高雅,這五個方面相互融合才能夠構建真正具備崇高價值的文章。在這五個方面中,前兩種是屬于寫作者的天生技能,但后三者就屬于可以通過后天學習的技巧性技能。尤其是在修辭方面,朗吉努斯認為,修辭的手法不在于去勸說別人,而是在于能夠通過語言的組織方式去引導別人[3]。
與上述觀點相互對應,在這一時期人們普遍認為文學與哲學之間是相互關聯的,但是社會中的主流思想仍然以哲學作為指導,哲學的存在就在于揭示真理。亞里士多德首先肯定了文學對于哲學的價值,他認為,詩歌的本質其實就是在探討嚴肅的哲學問題,是人類在哲學理性思考下的產物。而這一時期的學者們,也大多數認為文學依然會受到哲學的支配。一方面,許多學者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應該具備自身獨立的系統,但另一方面,這些學者仍然將文學歸屬到了哲學中的理論部分。因此,在這一時期中,人們將修辭手法的誕生歸功于真理,認為修辭是在真理基礎上所產生的一種技術。而在此背景下,將文學看成了哲學的一部分,文學也成為了反映哲學并且歸屬于哲學的重要構成部分[4]。
三、修辭與真理視角下,哲學與文學關系的統一
到19世紀,關于真理和修辭以及哲學和文學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著名學者尼采認為,站在西方形而上學真理觀念和理性主義語言觀念的批判者立場下,修辭本身就是具備一定美學價值的。在尼采看來,哲學家們稱之為真理的東西,其實就是這些哲學家先入為主,將真理當作永恒來探究一系列社會現狀和宇宙之謎的絕對規律[5]。但是這些所謂的永恒,只不過一瞬而逝,當許多社會中的哲學家在為這些真理辯護時,這些哲學家也成為了改頭換面的辯論者和律師,只是為自己具備先入之見的真理而進行狡辯。尼采將當代的哲學家比喻為律師,表明這些哲學家只是在為具有主觀意見的言論進行辯護,這也相當于尼采將哲學家所說的真理和哲學與演說和修辭是為了具備同樣本質的話語。而哲學家們所謂的真理,只不過是將世界中的普遍現象根據自己的觀點和選擇進行了擬人化,并且將之信奉為永恒的理念,從而形成的一種抽象概念。也就是說,所謂的真理就是哲學家個人對于世界進行觀察而得到的結果,如果將修辭比作是一種謊言,那么真理最終的本質也是謊言[6]。而尼采關于修辭和真理之間的關系也為20世紀新出現的修辭學和真理奠定了基礎。20世紀后,新的修辭學中轉變了修辭長期以來只作為一種語言工具的固有概念[7]。道格拉斯認為,那種將修辭視為話語中的調料的觀念應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修辭普遍存在于人類的一切語言傳播活動中,修辭能夠規范并且組織人們的語言表達方式。由此可見,新的修辭學修辭的概念從傳統的政治視角下引入到了一切以語言表達為象征性的交流活動中,這也讓修辭學本身的認知性得到了確認。羅伯特指出真理并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固定的,真理的存在需要適應周邊的社會環境并且能夠被不斷創造,而在人類處理各類型事物的過程中修辭學是一種了解事物本質的方式,修辭學具有認知性。由此可見,在后現代的修辭學理論觀念下,真理不再是一種永恒的且絕對的思辨規律,真理是相對的,會隨著社會的變化以及環境的變化不斷被創造。這一階段中的學者認為,對真理的發現和創造是通過主體間性體現出來的[8]。主體間性也就是所謂的交流,而交流中不可避免地會運用到修辭手法。在對真理探討且創造的過程中,現實社會中的各類型事物被賦予了多樣性以及彈性空間,而不同的主體對于現實生活的感知和參與方式的不同,也會造就不同的真理以及不同真理的存在方式。因此,哲學的出現以及哲學的研究與修辭學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這也證明,哲學不再是以知識或永恒的真理探究作為己任,而修辭的功能也不僅僅局限于對于語言的支持和贊同,而是可以用于各類型語言交際的環境中[9]。
如果真理的本身與修辭之間相互聯系,那么哲學就不再是既定的和永恒的,哲學也就失去了高于文學藝術的地位和優勢,而是能夠與文學和藝術之間相互統一[10]。在尼采看來,藝術其實就是以變相的形式講述著真理,但藝術始終圍繞著真理,是一種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幻想;藝術雖然沒有哲學那樣具備理性,但是藝術可以通過更加感性的方式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認知,正是憑借著藝術的存在,人們才能更加真實地體會生活。而美國文學理論家保羅德曼認為修辭是普遍存在于哲學話語中的,一切哲學的推論和演變都離不開修辭。
四、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真理與哲學、修辭與文學之間的特殊關系,給予了人們看待哲學與文學之間關系的新視角。通過修辭觀念變化的角度看待哲學與文學的關系,也是通過一種理性的辯證方法進行的一場討論。但是僅僅憑借理論上的辯證還是無法真正得出在修辭視角下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只有真正地將修辭應用在哲學文本和文學文本中進行實踐考察,才能進一步判斷在修辭視角下哲學與文學之間存在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