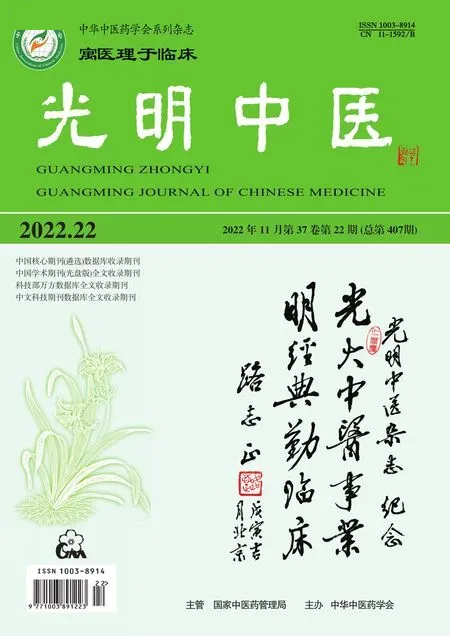慢性蕁麻疹的六經八綱辨治
李宏軍
六經是指太陽、陽明、少陽的三陽,和太陰、少陰、厥陰的三陰而言。《傷雜病寒論》雖稱之為病,實則為證,來自于八綱。八綱就是陰證、陽證、表證、里證、寒證、熱證、虛證、實證八種基礎證。經方辨證主要是六經八綱辨證,辨證論治亦主要是在六經八綱基礎上制定治療的準則,所以對于經方辨證施治的研究,則六經和八綱是首應探討的核心問題。六經八綱辨證是以八綱辨證為基礎,根據陰證、陽證、表證、里證、寒證、熱證、虛證、實證八種基礎證的組合而成的復合證。從病位來說分為表證、里證、半表半里證。從病性來說可以分為陰證和陽證兩大類證。具體而言,就是太陽病是陽證、表證、熱證、實證;少陰病是陰證、表證、寒證、虛證; 少陽病是陽證、半表半里證、熱多寒少、虛實夾雜偏于實證;厥陰病是陰證、半表半里證、寒多熱少、虛實夾雜偏于虛證;陽明病是陽證、里證、熱證、實證; 太陰病是陰證、里證、寒證、虛證。對于六經病的辨治規律:太陽病,病在表宜發汗,不可吐下,如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等均屬太陽病的發汗劑。少陰病,雖與太陽病同屬表證,亦宜汗解,但發汗須酌加附片、細辛等溫性藥,如桂枝加附子湯、麻黃附子甘草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均屬少陰病的發汗劑。陽明病,熱結于里而胃家實者,宜下之,但熱而不實者,宜清熱。下劑如承氣湯;清熱如白虎湯。陽明病不宜汗。太陰病,虛寒在里只宜溫補,汗、下、吐均當嚴禁。少陽病,病在半表半里,只宜和解,汗、下、吐均非所宜,如柴胡湯、黃芩湯等,皆少陽病的解熱和劑。厥陰病,雖與少陽病同屬半表半里,法宜和解而禁汗、下、吐的攻伐,但和宜溫性強壯藥,如當歸四逆湯、烏梅丸等均屬之。
蕁麻疹是皮膚科常見病,而慢性蕁麻疹,病程短者數月,長者數十年,往往夜間發作,白天消退,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西醫治以抗組胺劑甚者激素、免疫抑制劑等,往往停藥即發。近年來,中醫治療慢性蕁麻疹的優勢日益受到重視[1]。本文就慢性蕁麻疹的六經八綱辨治體會做一分析,與同道探討。
1 太陽病
太陽病是六經八綱辨證中的表證、陽證、實證。此型多見于體質壯實之男性蕁麻疹患者,證見:風團以上半身為多,顏色可紅可白,遇冷加重,尤常見眼瞼臉面浮腫,頭部身上常少汗,脈象常有力,偏浮緊。可伴有過敏性鼻炎、咳喘等。病機為外受風寒侵襲,津液充斥于體表抗邪外出,故見風團以上半身為多,同氣相求,故遇冷加重。《傷寒雜病論》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治療以祛風散寒,發越在表之廢水為法。常用麻黃類方,如葛根湯、越婢湯等。
典型醫案:趙某,男,38歲。因患慢性蕁麻疹 8年遍用抗過敏西藥效果不佳,于2019年10月9日初診。證見:上半身多發風團瘙癢,面部水腫明顯伴胸悶,怕熱,二便可。舌淡紅苔薄黃,脈數。六經辨證屬太陽陽明合病。予越婢湯加減:麻黃10 g,石膏30 g,生姜 18 g,大棗20 g,炙甘草12 g,荊芥10 g,防風10 g,炒蒺藜15 g,炒苦杏仁15 g。5劑,水煎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患者當日風團消退,3 d后有反復,1周后恢復正常,后隨訪半年未復發。
按:患者脈數,怕熱,體質壯實,兼有里熱,但尚未成陽明腑實,故加入苦杏仁,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之意,經表里雙解而愈。
臨床中用麻黃劑,患者常常風團有一過性加重,多出現在服藥第3天,一般持續4 d左右會逐漸消退,出現此種現象為臨床佳兆,往往自此病入坦途,甚至不需再服藥即愈。正如《傷寒雜病論》:“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這是正氣旺盛,驅邪外出的表現,正邪交爭,正勝邪負,故有此癥。另外麻黃劑容易導致入睡困難,故睡覺前服用麻黃類方宜提前。
2 陽明病
陽明病是六經八綱辨證中的里證、熱證、實證、陽證。蕁麻疹本為表證,不會單獨出現陽明里病,往往是以合病的形式出現,但有偏表偏里之不同。此型多見于體質壯實者以及喜歡肉食的兒童,膽堿能性蕁麻疹多見此型。證見:身起風團,上身為重,色紅居多,多伴有手足溫,多汗不惡風,怕熱,口干口苦,大便偏干或者便秘等。病機為外邪不解,里熱漸盛。治療以解表清里為法。常用方劑為防風通圣散、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白虎湯等。
典型醫案:張某,男,17歲。因患慢性蕁麻疹4個月,于2020年1月16日初診:證見:上半身多發風團瘙癢,早晚發病,嚴重時伴有胸悶,舌淡苔黃膩脈滑有力。六經辨證屬太陽陽明合病。予防風通圣散加減:麻黃6 g,防風10 g,荊芥10 g,薄荷6 g,黃芩15 g,梔子10 g,石膏30 g,甘草10 g,桔梗12 g,連翹15 g,赤芍15 g,炒枳實15 g。5劑,水煎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未服用西藥,藥后偶發風團,效不更方,共服藥19劑治愈。
按:患者內熱未成實,故去大黃、芒硝,川芎、當歸、白術過于溫燥,也減去。仲景臨證使用下法時若表證未解,即使有可下之征,也不可單純使用下法,否則易使病邪深陷于里,導致病情惡化,而應先解表后攻下或表里雙解[2]。清熱通下的著眼點還是為了解表,故此型患者,需斟酌清熱通下藥物的使用,寧少毋濫,寧遲勿早。
3 少陽病
少陽病是六經八綱辨證中半表半里證、虛實寒熱錯雜偏于陽證。中年女性及偏食的兒童常見此種類型。證見:風團伴有頭暈口苦咽干,胸悶腹脹,食欲不佳等癥狀,往往體型偏瘦,女性常伴有精神焦慮,睡眠障礙,月經量少等。病機為表證未解,津液已傷。上焦郁熱,中焦胃虛,下焦飲逆。治療以和解少陽、調和營衛為法。常用柴胡類方,如小柴胡湯、柴胡桂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等。少陽病為主的蕁麻疹患者,因為胃虛,津液不足,里不和者外不協,常常伴有桂枝湯證,往往需合用桂枝湯以調和營衛。
典型醫案:呂某,女,31歲。因患慢性蕁麻疹8個月于2020年1月6日初診。證見:上半身多發風團瘙癢,早晚發病,精神飲食睡眠一般,舌淡苔薄白脈弦細。口服氯雷他定片控制不佳。六經辨證屬太陽少陽合病。予柴胡桂枝湯加減:柴胡24 g,黃芩12 g,黨參12 g,清半夏12 g,生姜18 g,大棗24 g,炙甘草12 g,桂枝18 g,白芍15 g,荊芥10 g,防風10 g,炒蒺藜15 g。5劑,水煎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依巴斯汀片每3 d口服5 mg,可控制。二診大便偏干,上方加生白術30 g,5劑。三診停西藥,上方繼續口服10劑治愈。
按:《傷寒雜病論》:“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臨床中慢性皮膚病遷延日久,大多有正虛邪戀的病機,正因為柴胡證是半表半里證、虛實寒熱錯雜偏于陽證,故柴胡類方臨床上使用十分廣泛,且藥性平和,無論是兒童或者哺乳期婦女,辨證準確,均療效確切。臨證時需注意太陽病和少陽病的表里偏重而斟酌用藥劑量。
4 少陰病
少陰病為六經八綱辨證中表證、虛證、寒證、陰證。慢性蕁麻疹此種類型最為常見。常見于中青年女性患者,平時貪涼喜食生冷水果,熬夜等[3]。患者病勢遷延日久,醫者不察,屢屢投以清涼之劑,更傷津耗氣,亦可成此證。證見:風團量少,多為皮膚色,但遇冷加重,晨起及睡前多發。精神困頓,睡眠不佳,平時很少感冒,即使感冒也一般不發熱,無論多汗或甚少出汗,多伴有畏寒怕冷,夜尿頻多,過敏性鼻炎等,舌淡胖苔薄白,脈沉細無力。病機特點為患者素體陽虛津虧,發病即陷入虛寒陰證。治療以溫陽解表為法,常用方為麻黃附子甘草湯、麻黃附子細辛湯、桂枝加附子湯等。
典型醫案:張某,女,42歲。因患慢性蕁麻疹于2021年1月8日初診。證見:風團瘙癢遇冷加重,乏力,腰疼,腳冷出汗,大便可,多尿。舌淡苔薄白脈沉細無力。六經辨證屬少陰病。予麻黃6 g,炙甘草12 g,附片6 g,桂枝18 g,赤芍12 g,茯苓15 g,白術15 g,鹽杜仲20 g,鹽巴戟天15 g,牡蠣18 g。5劑,水煎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二診,諸癥減輕,加當歸12 g,細辛5 g。共服藥20劑治愈。后囑其口服1個月金匱腎氣丸善后。
按:此種類型常常用少量附片以溫陽散寒,表虛有汗者合桂枝,表實無汗者配以麻黃,但麻黃用量宜小,且中病即止,不可久服,多在三五劑之間即可,后期可更換為荊芥、防風等風中潤藥為宜。因方中常常附片、麻黃同用,故患者藥后往往會病情一過性加重,需提前告知患者,勿停藥,可短期配合口服抗組胺藥,一般1周左右即可好轉。病愈后亦需注意勿貪涼,常予金匱腎氣丸口服鞏固數周以防復發。
5 太陰病
太陰病為六經八綱辨證中里證、虛證、寒證、陰證。中年男性慢性蕁麻疹患者多見此種類型。癥見:風團晨起、睡前多發,遇冷加重,多伴有乏力、嗜睡、腹瀉。舌淡胖苔薄白,脈沉細無力。病機特點為患者調養不慎,中焦胃氣受損,水飲內生,外邪乘虛而入,外濕引動內濕,漸成外邪里飲而發病。濕為陰邪,同氣相求故而遇風寒、貪涼飲冷可加重病情。治療以溫陽利水解表為法,常用桂枝加黃芪湯、腎氣丸、真武湯、四逆湯、甘草干姜湯、腎著湯等。
典型醫案:胡某,女,52歲。因患慢性蕁麻疹2個月于2020年9月7日初診。證見:平素喜食水果。常怕冷、頭暈、面腫,風團瘙癢,位置不定,舌淡苔白脈沉細。六經辨證屬少陰太陰合病。予桂枝加黃芪湯加減:桂枝18 g,生姜18 g,大棗24 g,炙甘草12 g,生黃芪15 g,荊芥10 g,防風10 g,炒蒺藜15 g,茯苓24 g,蒼術15 g。 5劑,水煎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配合依巴斯汀片,1日5 mg口服。二診患者不起風團,停西藥,改為上方合金匱腎氣丸方5劑口服。三診仍未發病,繼服上方5劑鞏固治療。囑患者平素忌食生冷,勿貪涼。
按:《傷寒雜病論》曰:“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此種類型患者,保護胃氣去除廢水為一貫的原則,本為陰證,津液已明顯不足,不足以溫煦腠理,故不可再大量發汗,更傷津耗氣。須嚴格限制水分、生冷水果的攝入,并注意保暖。病愈后常予口服歸脾丸鞏固數周以防復發。
另外,附子劑治療過程中,患者可能會出現腹瀉和風團一過性加重的現象,《傷寒雜病論》曰:“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系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鄭欽安醫書闡釋·服藥須知》云:“此是陽藥運行,陰邪化去,從下竅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數日,飲食懶餐,三五日自已”[4]。這也是正常現象,類似于“瞑眩反應”,可提前告知患者,勿怪。
6 厥陰病
厥陰病是六經八綱辨證中半表半里證、虛實寒熱錯雜偏于陰證。慢性蕁麻疹患者病程長,用藥龐雜,也多見此種類型,多表現為上熱下寒者或者太陰陽明合病者。證見:除風團之外,多見口苦、咽干、心煩失眠多夢、小腹冷、腰以下冷、足冷、多尿、便溏等。病機特點為虛實寒熱錯雜,病位在半表半里。治療以調和寒熱,燮理陰陽為法。常用方有烏梅丸、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生姜瀉心湯、柴胡桂枝干姜湯[5]等寒溫并用方劑。
典型醫案:李某,男,15歲。因患慢性蕁麻疹2個月,于2020年10月15日初診。證見:風團瘙癢伴有口渴,胸滿脘痞,腹瀉,舌苔黃厚膩脈沉弦。六經辨證屬厥陰病。予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甘草瀉心湯加減:柴胡24 g,黃芩15 g,牡蠣18 g,桂枝18 g,炙甘草12 g,干姜6 g,黨參12 g,清半夏12 g,黃連6 g,大棗24 g,荊芥10 g,刺蒺藜15 g。5劑,水煎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二診,腹瀉停止,偶發風團。舌苔黃膩偏干,上方去干姜加生薏苡仁18 g,炒枳實18 g。繼服5劑后痊愈。
按:厥陰病的治療過程中,存在著厥熱往復的變化,如果方證相應,疾病向愈的過程中,可以陰證轉陽,里邪出表,出現太陽病、少陽病、陽明病等,需要及時調方,“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陰證治療過程中都會出現這種變化。
張仲景六經八綱辨證是一個圓融的辨證體系,用藥精煉,藥少力宏。柯韻伯《傷寒來蘇集》云:“仲景之六經,為百病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制”。俞根初《通俗傷寒論》說:“以六經鈐百病,為確定之總訣”。故人身病位不過表里,病性不過陰陽,病邪侵入人體,人體正氣抗邪,疾病不除,斗爭不已,則六經八綱便永續無間地見于疾病的全過程,成為凡病不逾的一般的規律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