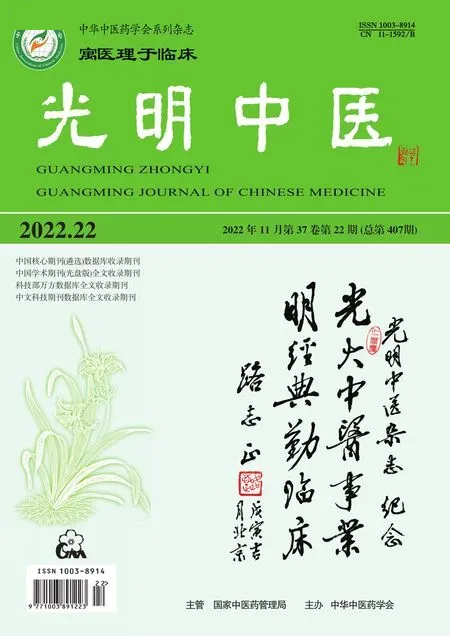張池金主任醫師中藥治療帶狀皰疹后假疝經驗
孫建橋 趙凱樂 周 菲 張池金
帶狀皰疹(Herpes zoster,HZ)是由潛伏在脊髓后根神經節或顱神經節內的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VZV)再次激活引起的皰疹性病毒感染性皮膚病[1],是皮膚科多發病、常見病,中醫現稱之為“蛇串瘡”或“火帶瘡”,因其多發生于胸脅部、腰部,故明代醫籍《證治準繩》又稱之為“纏腰火丹”。帶狀皰疹患者中有13%~47%會出現并發癥或后遺癥[2], 并發癥以神經系統受累為主,最常見的并發癥為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而運動神經受累約占所有并發癥中的5%[3],如面癱、Ramsay-Hunt綜合征或四肢節段性麻痹等,帶狀皰疹后假疝,又稱帶狀皰疹后節段性帶狀皰疹腹部運動神經麻痹較為罕見,發生率約為0.17%,受損神經多為T10~T12皮節[4]。
1 概述
帶狀皰疹后假疝又稱帶狀皰疹后節段性腹部運動神經麻痹、帶狀皰疹后腹壁疝或腰疝及帶狀皰疹后腹壁膨出。被稱為假疝的原因是這種類型的單側腹壁膨出不是因為腹壁結構缺陷及腹腔腫物、積液引起的,而是因為帶狀皰疹侵犯運動神經導致的肌肉麻痹。1886年,Broadbent報道了第1例由帶狀皰疹引起的腹部肌肉麻痹。節段性腹壁肌肉麻痹的癥狀通常在皮疹出現后 2~6 周內出現[5],部分患者伴有內臟神經的受累,受累神經麻痹影響膈肌、泌尿系統和消化系統,導致尿潴留、膀胱炎、麻痹性結腸梗阻及便秘,其中最常見的為便秘[4,5],存在腹部運動神經麻痹的患者僅55% ~ 75%能在2~18個月內完全康復[5],預后較好,但也存在永遠無法康復的病例。西醫現未有明確治療方法,一般采用與帶狀皰疹治療相似的抗病毒及營養神經治療,文獻報道可加用復合維生素制劑及皮質類固醇激素以抗炎治療幫助受損神經盡快恢復;有報道采用 0.5% 利多卡因 3 ml 和曲安西龍 40 mg 進行椎旁阻滯注射治療帶狀皰疹后神經痛、運動神經受累導致的腹壁假疝、內臟神經受累導致的便秘和腹脹,注射 1 d 后皮膚疼痛消失,5 d后其余癥狀基本消失[6]。張池金主任醫師通過采用內服中藥治療帶狀皰疹后假疝,可明顯改善患者癥狀,臨床效果顯著,現將典型醫案1則介紹如下。
2 典型醫案
患者男性,63歲。2021年11月6日初診。右側腰腹部疼痛2個月余出現腹部膨隆8 d。患者2個月前因右側腰腹部簇狀紅斑水皰伴疼痛7 d就診于當地醫院,行腹部B超未見明顯異常,考慮為“帶狀皰疹、帶狀皰疹性神經痛”,當地醫院予營養神經及抗病毒等對癥治療,經治患者皮疹漸消,仍有皮膚疼痛等自覺癥狀。8 d前患者因大便干燥,用力努掙后出現腹部右側膨出,自覺脹滿不舒,故就診于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門診,現患者右側腰部及肋下可見簇狀褐斑,局部時刺痛,腹部右側膨出(就診時腹部束有壓力帶),大便日行1次,納可,夜寐差,疼痛脹滿感嚴重,不能入睡。舌暗紅苔薄白,脈弦。診斷:帶狀皰疹腹部運動神經麻痹。中醫診斷:蛇串瘡,辨證為氣滯血瘀證,治以理氣疏肝、涼血活血。方藥:柴胡 10 g,赤芍 15 g,丹參15 g,牡丹皮10 g,郁金10 g,珍珠母(先煎)20 g,香附10 g,鬼箭羽10 g,黃芪15 g,厚樸10 g,合歡皮15 g,生龍骨(先煎)20 g,首烏藤20 g,地骨皮 15 g,佛手10 g,桃仁 6 g,炙甘草10 g。共7劑,每日1劑,水煎服,早晚分服,囑皮損處保持清潔干燥,但避免過度頻繁清潔。囑節飲食,調情志,規律作息。2021年11月13日二診:腰腹部右側可見淡褐斑,疼痛較前改善,腹部右側脹滿不適改善,大便日行1次。納可,夜寐欠安,舌紅苔薄白,脈弦。前方去合歡皮,加柏子仁20 g,玄參15 g,生牡蠣(先煎)20 g。12月3日三診:腰腹部右側可見少量褐斑及色素沉著,疼痛較前改善,腹部右側膨隆緩解明顯,大便日行1次,夜寐安,納可,舌淡紅苔薄白,脈弦。去赤芍、地骨皮加炒萊菔子 10 g,白芍 15 g,雞血藤 20 g。12月11日四診:腰腹部右側可見少量褐斑及色素沉著,偶有疼痛,腹部膨隆已完全好轉,大便日行1次,夜寐欠安,納可,舌淡紅苔薄白,脈弦。去白芍,加桑寄生 15 g,杜仲 15 g。12月17日五診:腰腹部右側可見色素沉著,疼痛基本消失,腹部膨隆未見反復,大便日行1次,夜寐欠安,納可,舌淡紅苔薄白,脈弦。去雞血藤,加合歡皮 15 g,葛根 20 g。后患者繼服2周,疼痛及腹部膨隆脹滿均已消失,夜寐安,納可,二便調,遂停止治療。2個月后回訪癥狀未反復。
按語:帶狀皰疹的特征為沿單側周圍神經分布的紅斑、水皰,常常伴有神經痛,根據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其發病率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的趨勢,其中50歲開始發病率上升明顯,中國大陸≥50歲人群,帶狀皰疹的每年發病率約為(2.9~5.8)/1000人年[7],85歲以上人群有多達一半的人不止1次患有帶狀皰疹[8],帶狀皰疹后遺癥的危險因素也與年齡有關,患者年齡越大,帶狀皰疹后遺癥的發生率越大[9],而早期的抗病毒治療并不能完全預防帶狀皰疹后遺癥的出現[10]。隨著迅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帶狀皰疹及其后遺癥的治療應更加予以重視。帶狀皰疹后假疝雖有自我恢復的可能,但也存在部分患者終生無法痊愈。應用中藥對癥治療可針對個體患者辨證治療,使患者無力、疼痛及便秘等臨床癥狀更快緩解,減輕患者痛苦,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張池金主任醫師通過對帶狀皰疹后遺節段性腹壁運動神經麻痹的中醫病因病機分析,具體辨證施治,總結出此病治法以疏利氣機貫穿始終,前期加以清熱涼血,活血化瘀,后期治以扶助正氣、調和氣血。分期治療,隨癥加減,為此病的中醫治療提供一種新的診療思路。
3 討論
3.1 病因病機張池金主任醫師認為患者情志不調,肝經氣滯,疏泄不利,郁而化火,肝經火毒壅盛發為蛇串瘡,此病進一步發展,肝經火熱煎灼津液,以致氣血凝滯,經絡不通,絡脈失養發為疼痛、麻木。肝脾不和,致脾氣虛弱,中氣不足,無法固攝,出現腹壁膨隆。年老體弱者,素體氣血不足,遇肝火太盛,乘克脾土,脾胃虛弱,升降失司,氣血生化無源,使氣血更虧,氣為血之帥,氣虛不能行血致瘀,血虛則血行不暢亦可致瘀,肝經余熱灼津使氣血凝滯,三者并行使經絡不通、絡脈失養更甚,故年老體弱者發此病癥狀較常人更重,恢復時間更長。
3.2 治療原則此病的治療為疏利氣機貫穿始終,前期應加以清熱涼血,活血化瘀,后期以扶助正氣,調和氣血為主。在此病的治療中,以疏泄氣機不利最為重要。氣機的調暢在人體正常生命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脾胃的升清降濁,肝肺的升發清肅,心腎的相交相濟,都有賴于人體臟腑氣機的調暢,氣機失調可阻遏中焦氣機,肝木乘克脾土,影響脾胃的升清降濁;情志不遂氣機失調可影響肝之疏泄,肝疏泄不及,肝郁化火,肝木反侮肺金,灼傷肺陰,影響肺之肅降;氣機失調影響心火下降腎水上升,使心腎既濟失調水火不濟。由此可見氣機調暢在治療疾病上是尤為重要的一環,張池金主任醫師認為,調暢的氣機除了可以平衡臟腑氣血陰陽外,理氣導滯使脾胃升降功能恢復正常,也可促進內服中藥湯劑的吸收,使藥物更好地發揮效用;氣的有力推動還能通過一些引經報使藥物更好地引藥至病所,是皮膚病治療中不可缺少的。應在疏利氣機的基礎上,前期的治療中,兼以清熱涼血并活血化瘀。肝經火熱仍存,氣血凝滯未解,加入涼血活血藥物,清其肝經余火,解其氣血郁滯。為避免寒涼太過凝滯氣血,不選用大苦大寒藥,而選擇使用微寒、微苦藥,且涼血藥與活血藥搭配使用,可達到涼血而不留瘀的目的。此病至后期,皮疹已經消退,肝經余火已清,氣血仍凝于經絡,經絡不通,此期的治療在理氣活血基礎上加以顧護正氣,調和氣血,適當加用健脾益氣、養陰滋血微溫之品,使氣血生化有源,配合理氣導滯藥與活血化瘀藥,使補氣血而不斂邪,活氣血而不傷正,調和氣血,使氣血和順,經絡得暢,病邪自去。
3.3 醫案分析此案患者經過西醫治療已2個月余,皮疹大部分消退,仍遺留疼痛,8 d前出現腹壁肌肉無力、腹部膨隆等不適。患者肝經郁滯化火,年歲已高,素體氣血不足,患病日久,氣血更虧,再加火熱灼津,氣血阻滯經絡,經絡不通,絡脈失養,遺留疼痛不適經久不消,患者易出現焦慮痛苦、情緒不暢、睡眠不佳,使肝經郁滯更進一步加重,肝脾不調,脾虛下陷,無力固攝,在大便困難用力努掙時出現腹壁膨隆。肝經余火未清,故選用柴胡為君藥,取其入肝膽經,且體質輕清,擅升陽理氣,透邪達表,疏肝解郁。丹參活血祛瘀,涼血消癰止痛;赤芍為肝家血分要藥,味苦能瀉,味酸入肝,專瀉肝火,與牡丹皮相需配伍,牡丹皮能清血分之實熱且散瘀活血,使涼血不留瘀,加強清肝涼血活血之功;香附通行十二經,重于行氣解郁,而郁金行氣且活血,兩藥相須為用,共奏行氣理血之功,赤芍、牡丹皮、郁金、香附行氣解郁,涼血活血共為臣藥,共奏清熱涼血、行氣解郁止痛之功。鬼箭羽性辛苦味寒,力專破血,善破血通經,又善活血解毒消腫,《名醫別錄》言其:“主中惡腹痛,去白蟲,消皮膚風毒腫,令陰中解”,地骨皮清熱涼血,鬼箭羽與地骨皮合用可消內外表里之余熱;珍珠母平肝潛陽,清肝安神;合歡皮可活血解郁安神,還可以皮走皮,引藥直達病所;龍骨鎮靜安神;夜交藤入肝經養心安神,四藥并行,平肝安神,調和陰陽,提高患者生活質量,調暢情志,有利于疾病恢復。佛手疏肝理氣,化痰寬胸,入肺、脾、肝、胃四經,為脾胃氣滯要藥;黃芪歸肺、脾二經,為補氣之圣品;厚樸溫中下氣,三者合用,使補中焦之氣而不留滯,消脾胃氣滯而不傷正,改善腹部脹滿不適癥狀。桃仁活血祛瘀,兼能潤腸,加強本方潤腸通便之力,改善患者大便努掙之苦。炙甘草緩急止痛,調和諸藥為使。后隨癥加減,二診患者夜寐欠安,加入柏子仁、牡蠣加強安神之功。三診患者腹部脹滿好轉,舌淡紅苔薄白,余火已清,去地骨皮、赤芍,加入白芍、雞血藤、炒萊菔子,加強行氣活血,養陰生血之力,四診患者僅遺留腰腹部疼痛不適,加入桑寄生、杜仲,滋補肝腎,兩藥也符合循經用藥,可引藥至腰腹部,增強療效。此案治法從理氣解郁、清肝瀉火、涼血化瘀入手,佐以平肝安神,行氣消導,后期治以扶助正氣、調和氣血,療效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