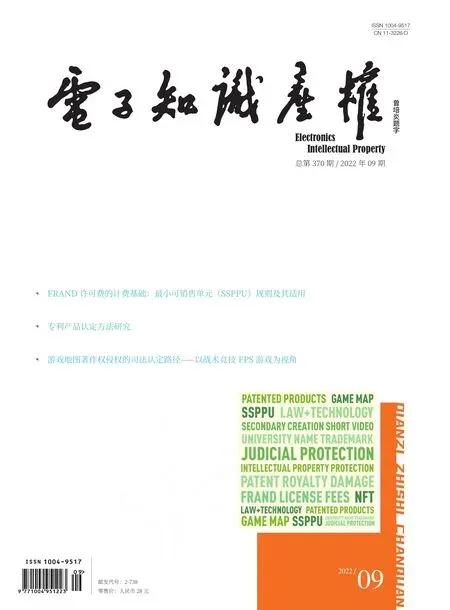基于“法律+技術”財產權模式對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規制的研究
文 / 汪賽飛
一、新無形財產權模式的形成
(一)“法律+技術”的二元結合保護模式
一般來說相較于可被直接占有的物權,無形財產權的實現更加依賴于國家強制力。依照卡梅框架下財產權實現的視角,無形財產權尤其訴諸財產規則(property rule)中的“禁令”救濟以達到對財產交易能否發生、對定價權的控制等。1. See Lemley Mark A., Weiser Philip J., Should Property or Liability Rules Govern Information. Texas Law Review, 2007,Vol.85, Issue 4: 783-784.然而技術的發展打破了權利人以往的國家強制力(法律)依賴僵局,當互聯網空間成為無形財產權尤其是作品的主要傳播空間后,權利人可以通過信息技術加強對互聯網空間的管理與控制,并以“法律+技術”的手段實現自己的財產權訴求。
“技術+法律”的財產權模式達到了以往權利人所不能達到的無形財產權客體控制效果,具體的產權實現模式如下:第一步,權利人先訴諸法律對“財產權”本身進行保護,打擊侵犯財產權行為;第二步,權利人訴諸法律對“技術手段”進行保護,打擊破壞技術手段的行為。新無形財產權模式最為典型的就是著作權領域出現的各類加強對作品控制與管理的“技術措施”,包括“接觸控制措施”與“版權保護措施”。2. “接觸控制措施”,其作用在于防止他人擅自以閱讀、收聽、收看等方式“接觸”作品內容。如視頻網站對于收費影視劇設置的用戶名和密碼,那些未付費的用戶將無法登錄網站并在線欣賞影視劇,即無法“接觸”作品。“版權保護措施”,其作用在于防止他人擅自對作品實施復制和傳播等受專有權利控制的行為。例如,視頻網站采用只允許在線觀賞影視劇,而不允許下載的技術措施。參見王遷:《技術措施保護與合理使用的沖突及法律對策》,載《法學》2017年第11期,第9頁。為了強化這種通過技術手段對作品的控制,權利人訴諸立法,將對技術措施本身的保護納入法律進行規定,如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2013)第4條第2款對“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技術措施”的行為進行規制。
的確隨著網絡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當對作品等無形財產傳播的主要方式轉移到了網絡空間后,著作權網絡侵權行為的發生更加容易,這對網絡空間的治理帶來了挑戰。但在短短二十年不到的時間內,經營著視頻、音樂、游戲等涉著作權產品的企業通過技術相較于消費者與潛在“侵權人”占據了更高的作品控制優勢地位,大企業逐漸與著作權人聯盟,并以某種壟斷與強勢的姿態出現在文化產業市場上,此時立法者若只看到“法律+技術”財產權模式對著作權人利益保護帶來的好處,而無視版權市場上壟斷的危險與新模式可能對社會公眾利益的侵蝕是有失偏頗的。
當對“技術措施”的保護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已經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后,通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技術措施構建的“法律+技術”著作權保護模式已經不僅僅被用于應對著作權侵權行為,如“用戶觀看影視劇本身不是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但是若破壞技術則會使得付費觀看這一經營模式下所能獲得的報酬流失”。3. 參見王遷:《技術措施保護與合理使用的沖突及法律對策》,載《法學》2017年第11期,第13頁。總之“法律+技術”的財產權模式著眼于權利人對權利客體的控制,維護的是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利用作品并從中獲益的權利。然而新模式的發展對既有的著作權權利限制制度發起了挑戰,合理使用等制度的實現建立在社會公眾能接觸作品的前提之上,但技術卻可以自動阻斷第三人對作品的接觸。
隨著“版權強制性過濾技術”的出現與成熟,新的“法律+技術”的財產權模式正在襲來,這對著作權人和社會公眾的影響十分深遠。由于該技術的引入對傳統“通知-刪除”規則的正當性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筆者認為立法者要以更加慎重的姿態,通過更為精妙的制度設計,吸收“技術+法律”財產權模式的優勢,在強化著作權人對作品控制的同時平衡社會公眾乃至二次創作者的利益。
由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的《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中規定:“依據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基本標準,短視頻節目及其標題、名稱、評論、彈幕、表情包等,其語言、表演、字幕、畫面、音樂、音效中不得出現以下具體內容:……93.未經授權自行剪切、改編電影、電視劇、網絡影視劇等各類視聽節目及片段的。”隨著版權強制性過濾技術的發展,通過技術讓可能侵權的二次創作短視頻從網上消失逐漸可以實現,但筆者認為對該技術的引入和對該技術的法律規制都應當慎重與靈活。
一方面,若簡單將版權強制性過濾技術引入并同時提高網絡服務提供商的注意義務,這種規定可能有損“合理使用”等著作權限制制度以及作者本身的“意思自治”。但另一方面,利用現有的信息網絡技術在堅持“財產規則”的前提下,通過以流媒體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建立降低交易成本的網上協商或議價機制,將能更有效地保護與促進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的發展。
(二)對引入“法律+技術”保護模式的爭議
“法律+技術”財產權模式的出現依賴于技術的發展與成熟,在技術尚未發展到可以幫助強化權利人對智力成果的控制,甚至相反使得侵權行為泛濫的時代,法律自身發展出一些平衡多方利益主體的法律機制,最典型的就是在互聯網領域以美國1998年《數字版權千年法案》為代表的“通知-刪除”規則與紅旗規則,以降低網絡服務提供商注意義務的方式平衡各方利益。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這種前信息技術時代下的規則產物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認為技術的發展催生了網絡主體對作品的控制力與監管能力,再繼續堅持“通知-刪除”規則必然不利于對著作權人的保護和新技術對著作權保護的適用,以歐盟為代表的事前審查義務規則開始出現,尤其是隨著2019年《歐盟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指令》的通過,其第17條對網絡服務內容提供商施加了一個以“成熟過濾技術”出現為前提的注意義務。美國與歐洲這兩條路徑的選擇恰好是對如何發展“法律+技術”產權保護模式的回應。
以崔國斌教授為代表的學者支持引入版權強制性過濾機制,其認為新技術降低了平臺的監管成本,著作權人也能通過與平臺企業合作加強對自己作品的控制,“技術進步為著作權人和網絡服務商合作打擊盜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4. 崔國斌:《論網絡服務商版權內容過濾義務》,載《中國法學》2017年第2期,第219頁。
當然僅僅是為著作權人帶來益處并非引入該機制的絕對理由,理由還包括技術發展使得傳統“通知-刪除”規制對平臺企業注意義務降低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平臺企業可以依靠盜版獲利并在與著作權人的談判中處于優勢地位,有必要將這一規則上升為法定義務,該技術通過大規模復制對企業施加的成本有限,“技術的發展使得錯誤過濾的可能性較低,并且輔之以適當的人工舉報和糾錯機制,侵犯用戶言論自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等。5. 參見崔國斌:《論網絡服務商版權內容過濾義務》,載《中國法學》2017年第2期,第219頁;張吉豫:《智能社會法律的算法實施及其規制的法理基礎——以著作權領域在線內容分享平臺的自動侵權檢測為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第6期,第89頁。
但在以萬勇教授為代表的學者看來,引入該機制是有爭議的,強制性過濾機制不能解決“價值差”問題,即試圖通過該技術彌補權利人在互聯網時代的權利損失是做不到的。6. 萬勇:《著作權法強制性過濾機制的中國選擇》,載《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第190-191頁。立法者希望通過廢除避風港規則而提高版權保護水平的方式來增加版權收入未必行得通;即使真的存在“價值差”問題,該問題也是由于著作權人與網絡服務提供者談判地位不對等所導致的,應在反壟斷法層面解決這一問題;該制度還會損害競爭,給初創企業施加過大的負擔。7. 萬勇:《著作權法強制性過濾機制的中國選擇》,載《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第193頁。
毋庸置疑,“法律+技術”的財產權模式賦予了著作權人以及互聯網企業對無形財產權更強的控制力,但是一味強調對著作權人的強保護而忽視整個市場的發展乃至后續的創作創新行為,就如已經納入立法的版權技術措施對合理使用制度的挑戰。制度若設計不當,加強權利人控制力的新型財產權保護模式可能最終未必有利于市場發展與著作權人的根本利益。筆者認為對于“法律+技術”模式對保護著作權人的利益有可取之處,但考慮到著作權法與民法的價值取向——促進創新、意思自治——對新模式的制度設計必須更加精細與慎重,下文筆者將對該模式會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
二、技術被納入無形財產權控制手段的影響
(一)技術對法律執行成本的影響
法律成本是法律運行的費用,有學者認為其在性質上屬于交易費用的一種,具體包括在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各個環節中當事人實現權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和承擔責任所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資源。8. 參見鄭智航:《法律成本論》,載《當代法學》2003年第2期,第14頁。通常來說法律的執行成本都是有害的,若訴訟的成本過高且效益不夠理想,社會成員將難以建立良好的訴訟預期,就有可能放棄權益追償。9. 參見魯籬:《論法律成本》,載《現代法學》1994年第1期,第53頁。但在注重利益平衡的著作權法領域,法律的執行成本卻成為了和保護期、合理使用、法定許可等著作權限制制度共同起作用的工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防止權利的過度擴張,在一些學者看來合法的權利也有被濫用的可能,需要被限制。
對于法律的執行成本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價值早有學者提出,如莫杰斯教授認為“法律的執行成本”在權利人和社會公眾之間建立了一個緩沖帶,10. 參見[美]羅伯特·P.莫杰思:《知識產權正當性解釋》,金海軍等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466頁。權利人可能宥于權利實現成本過高,主動選擇捐獻或者默示放棄部分自己的權利,或者延遲實現自己的權利,這種選擇從結果上為社會的后續創作行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法律的執行成本在客觀上維護了社會公眾的利益,其讓“法律理論上賦予作者的權利”和“作者實際實現的權利”之間有一個特殊區域,由于法律的執行成本,著作權人在面對侵權行為時有了各種各樣的選擇可能,社會也可以在這些特殊區域內獲利。當然這種“獲利”未必是合法的,其很有可能是介于“著作權侵權”與構成“合理使用”之間的行為,試想各種處于合理使用模糊地帶的利用作品的行為——如電子游戲直播——這一行為在無形中甚至產生了游戲直播行業這一新型市場,豐富了社會的娛樂產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法律的執行成本讓那些新興市場的產生有了可能,讓那些有生產性的第二作者(productive second authors)有了生存空間。法律一定的執行成本產生了一種保持著作權人與社會公眾間利益平衡的效果,新技術的發展確實可以起到降低法律執行成本、更好地維護權利人的利益的效果,然而維護權利人利益的背后意味著對現有利益平衡現狀的破壞。
隨著“法律+技術”財產權模式的出現,法律的執行成本得到了控制,版權過濾技術的發展使得著作權人在財產規則下求助“禁令”獲得權利控制更加及時高效,無論是盜版圖片、音樂、視頻,新技術都能快速識別出來進行刪除或者下架,侵權產品的傳播可以被有效遏制,但帶來的效果就是非侵權產品或者說屬于合理使用的那部分內容有可能受到影響,那么構建新產品、新市場的作品利用行為生存的土壤也會受到影響。這并不是說為了維護已有的利益平衡現狀就要抵制新技術的引入,相反筆者認為可以利用新技術,重新設置一個以“法律+技術”保護模式為基礎的版權市場,在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內以更合理的市場機制分配二次創作帶來的收益,使得社會公眾、原創作者、二次創作者都能從中獲益。
(二)技術對個人意思自治的影響
技術以及“法律+技術”的財產權模式很有可能影響個人意思自治的實現,最為極端的情況是權利人原本默許“侵權行為”的發生,因為這一行為可以幫助傳播其作品、提高其聲譽,而通過技術刪除所有未經許可的二次加工視頻卻剝奪了權利人原本意思自治的實現。
莫杰斯教授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把放棄財產權作為選項,正是任何財產制度的一個核心特征。許多潛在的知識產權的所有人放棄他們尚未成熟的權利主張,以支持共享性、協作式的參與,但是這不會削弱知識產權在初始的合理性。相反,它恰恰是支持其合理性的。”11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作品被修改與傳播變得異常容易,人們常常擔心在這樣一次影響深遠的數字革命中作者對自己作品的控制力下降,擔心作者喪失利用作品獲益的機會,有損著作權法激勵創作目的的實現。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但若因此而一味強調知識產權的強保護,以父愛主義關愛權利人,卻忽略了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自治與市場對資源的自發配置功能,效果未必盡如人愿。對于知識產權這一特殊財產權,降低財產流轉的成本,促進市場交易的發生,使得財產能在科斯定理所描述的“零成本”世界中自發轉移到其最高價值用途的主體手中,才是發揮作品價值的更好手段。12. See 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89, Vol.18. (1): 47-48.
無論是為了促進作品傳播而將許多行為納入“合理使用”的抗辯或者為了強保護而杜絕他人利用作品的行為,都忽略了作者的自治意志與自治能力。在尚未形成一個有效的市場來配置這部分新的利用作品的行為產生的新利益時,作者完全有可能為了推廣自己的作品、積攢自身的聲譽、維持自己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等原因,允許這些剪輯自己作品并傳播的行為存在。
隨著技術的發展,法律與技術的結合確實擁有了代替人類自己做決定的能力。以嗶哩嗶哩、抖音為代表的網絡服務提供商也逐漸擁有了監測各類未經許可利用作品行為的技術能力,如“版權內容過濾技術”,通過該技術,“網絡服務商事先建立正版作品數據庫;網絡用戶對外傳播作品時,網絡服務商通過技術措施掃描該作品內容,確定是否含有正版作品數據庫中的內容;如有則阻止用戶的傳播行為。”13. 參見崔國斌:《論網絡服務商版權內容過濾義務》,載《中國法學》2017年第2期,第215頁。在避風港規則有所搖動的今天,若是依照《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的要求對網絡服務提供商提出不得出現“未經授權自行剪切、改編電影、電視劇、網絡影視劇等各類視聽節目及片段”的要求,或許不會給企業帶來很重的負擔,但卻會對著作權人的財產權自治造成不良影響。在低成本的版權許可市場尚未形成的今天,法律強制要求二次創作者向著作權人獲得使用作品的授權,必然會降低二次創作的積極性,使得交易成本高于二次創造行為所能帶來的收益,交易不再發生,無形之中剝奪了作者自己的選擇與自治能力。
此外,對“版權過濾技術”的擔憂與人們對算法的依賴和與“黑箱技術”、“算法權力”的思考有關。算法很有可能輔助甚至代替公權力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算法決策。14. 參見張凌寒:《算法權力的興起、異化及法律規制》,載《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第65頁。算法黑箱的出現挑戰了人類決策的知情權與自主決策,版權過濾技術中對算法的運用使得“不透明的算法——而非人——成為決策主體”,當不加檢驗地以機器決策代替人類決策時,人類的自主性可能面臨嚴峻考驗。15. 參見丁曉東:《論算法的法律規制》,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第139頁。實際上在技術發展尚未足夠成熟的今天視頻審核依舊無法離開人的參與。在視頻剪輯領域存在大量屬于合理使用的作品利用情形,而對于合理使用的判斷是主觀性很強的,無論是大陸法系的封閉式立法還是美國的四要素判定法,法官都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利用視頻過濾技術讓算法代替法官作出具有公權力效果的決定值得深思。
三、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中賦權規則的構建
(一)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之簡析
伴隨著互聯網視頻平臺的發展以及各類視頻制作軟件的普及,個人也能制作優質的“短視頻”,法律意義上的“短視頻”不同于傳播學意義上市場較短的視頻,主要指基于在先影視作品制作形成的視頻。16. 參見陳紹玲:《短視頻版權糾紛解決的制度困境及突破》,載《知識產權》2021年第9期,第18頁。未經許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若不屬于合理使用等抗辯理由規定的情形,必然屬于著作權侵權行為,那么按照嚴格意義上對著作權這一絕對權的保護,需要將作品刪除即“停止侵權”的救濟以維護財產權的實現。因此傳統上學者都將爭議點聚焦于行為是否可能構成“合理使用”以維護這一新興視頻市場的繁榮。這里的是否屬于合理使用的有爭議的二次創作短視頻主要包括兩類:其一,將不同類型的作品包括視頻、音樂、圖片等進行拼貼;其二,在原視頻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
嚴格按照傳統版權市場先許可再使用的規則與互聯網上的“效率”取向并不契合,有學者提出如果對于互聯網上“隨手可取”的視頻資源逐一事前協商并獲得許可后方能使用,網絡技術帶來的傳播效率優勢將無法發揮。17. 參見熊琦:《“視頻搬運”現象的著作權法應對》,載《知識產權》2021年第7期,第48頁。為緩解作品先許可后使用帶來的交易成本和互聯網產業發展對效率追求之間的矛盾,學者們紛紛提出訴諸“合理使用”或“建立新型交易機制”的辦法,非常巧的是,前者對應的是卡梅框架下的“責任規則(liability rules)”,后者對應的是卡梅框架下的“財產規則(property rules)”:前者相信當市場失靈、交易可能因成本過高而無法發生時,應允許第三人未經許可進行交易;后者則堅持對權利人的保護,相信市場可以構建一套成熟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在保證權利人利益的同時讓新市場繼續運行。當然,通過法律降低交易成本的法定許可或合理使用制度,與尋求新技術、構建交易場所降低交易成本的兩種方法各有其稱道之處,那么針對不同的二次創作短視頻場景完全可以配合使用兩種賦權規則,輔以“法律+技術”的財產權新模式達到維護權利人利益、促進文化產業創新繁榮的結果。
(二)責任規則的選擇
1.市場失靈理論
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學家表示,一個人對一種資源的貨幣價值的評價將反映出這個人對該資源的使用將給社會帶來的價值,因此個人間資源的自愿轉移將創造一種社會所希望達到的理想資源分配模式。但是單個市場要實現價值最大化需要滿足幾個“完全競爭的條件”,溫蒂·戈登教授將其概括為三點,包括:交易和成本發生在交易內部不由外部人承擔,潛在交易者具備足夠的評價產品的知識,不存在交易成本。18. See Gordon, Wendy J. Fair Use as Market Failure: A Structu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etamax Case and Its Predecessors.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1983, Vol. 30, Issue 3: 1605-1608.但是這些要素在二次創作短視頻這一新興市場上要實現卻很難,首先是交易成本問題,原創作者和潛在的二次創造者之間達成許可授權的交易成本很大,業余創作者確定并找到著作權人、與著作權人擬制合同、確定利潤分配等等都會產生足夠高的交易成本阻礙交易的發生。其次,這一新型市場的利潤具有外部性,二次創作者本身能從二次創作中獲得的收益有限,其與大型公司之間沒有雇傭關系,而視頻平臺公司卻能通過將視頻匯集在平臺上獲得針對原創作者和二次創作者之間的外部性收益。
總而言之,在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上市場失靈現象是十分明顯的。以溫蒂·戈登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市場失靈是適用“合理使用”抗辯的重要考量因素,其認為合理使用制度是第三人與著作權人對作品進行交易成本太高,甚至高到無法進行正常交易形成市場時知識產權制度的一個回應。19. See Gordon, Wendy J. Fair Use as Market Failure: A Structu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etamax Case and Its Predecessors.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1983, Vol. 30, Issue 3:1614-1615. 在該文中,除了“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作為考量因素外,還包括“平衡損害與獲益(Balancing Injury and Benefit)”和“相當程度的損害障礙(Substantial Hurdle)”兩個額外的考量因素,詳細見該文第1615-1622頁。若嚴格按照傳統的財產權理論施加禁令,甚至輔以信息與算法技術,這一市場將會因為交易成本過高而消失,這也是為何針對二次創作短視頻有學者認為其屬于合理使用的原因,不僅在于大量新的視頻屬于“轉換性使用”,更在于這些具有創造性的演繹作品所在的市場存在一個市場失靈的現象。
2.類專利挾持
在專利法領域當涉及技術市場時,傳統財產規則的適用受到了巨大的挑戰,一個產品可能包含多個專利,若因為一個侵權專利而對整個產品施加禁令必然不公平或者說超過了“比例原則”下對專利權保護與貢獻相適應的要求,因此在越來越多的專利權糾紛案件中法院選擇不頒發禁令而僅僅是判處賠償金。由于知識產權的特殊性,調整禁令救濟使其保護的部分不涉及非侵權部分是很難的,此時權利人很有可能會利用獲得禁令救濟的能力采取“拖延策略(holdup strategy)”,以達到一個超乎其損害的協議(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專利挾持或專利流氓)。這樣的結果是不公平的,超過了財產規則原本所能帶來的益處。20. See Lemley Mark A., Weiser Philip J., Should Property or Liability Rules Govern Information. Texas Law Review, 2007,Vol.85, Issue 4: 784.
二次創作短視頻的市場和技術市場非常相像,一個視頻中可能蘊含多個作品,對這些原作品權利人而言,有的人可能通過放棄或默示許可的方式允許他人使用,有的宥于法律的執行成本而不在知識產權的緩沖地帶實現自己的權利,有的人則希望能積極打擊這類改編權等所覆蓋的侵權行為,此時嚴格按照財產規則施加禁令而下架作品就會發生在專利權領域已經頻繁出現的類專利挾持狀況。從技術市場已有的不發放禁令的案例來看,二次創作短視頻領域也值得引入責任規則,法院或其他機構僅施加賠償金而不頒發禁令、刪除作品,這對于整個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上的各個權利主體更為公平也更可行。
(三)財產規則的選擇
有學者相信,“市場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形成,特別是當一項新技術的突然出現,打斷了已經建立的商業模式時,當前的市場參與者可能需要花費一段時間,才能開始理解新的現實情況。”21. 參見[美]羅伯特·P.莫杰思:《知識產權正當性解釋》,金海軍等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454頁。即短暫的市場失靈不是適用責任規則的理由,市場失靈完全可能被修復,包括新技術和新的交易場所都有可能讓新的市場正常運轉。
隨著技術的發展在文學藝術領域總會有新的市場產生,例如電影技術的發展為文字作品的作者尤其是小說家拓展了新的收入渠道,作者能夠在電影市場上與導演這些二次創作者分享新市場的利益。同樣的,視頻剪輯與傳播這一現象產生于剪輯軟件的普遍與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新技術對行業與市場的改變當然不能簡單認為是在損害權利人的利益。相反,筆者認為新市場在醞釀與成長階段的前期必然伴隨一定的市場失靈,但新市場對于原創作者來說意味著新商機,這種有利于原創作者分享利益的新商機值得被引導與維護,而不應被簡單認為是侵權行為。
當達成和執行交易的成本低于預期的交易收益時,市場就會形成。對于原創作者和潛在的二次(業余)創作者來說,建立一個交易成本更低的權利清算場所,共同分享新型市場中的收益將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降低雙方之間的交易成本,技術或許是關建。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機制已經在市場催化下開始形成,如致力于通過信息技術解決文學藝術著作權許可問題的知識共享組織(Creative Commons,CC),再如YouTube的內容身份系統等,該系統甚至能夠讓著作權人事先選擇對于侵權作品是將視頻靜音、屏蔽視頻、許可繼續使用并獲得廣告分成或僅僅是追蹤視頻的瀏覽統計數據,22. 參見張吉豫:《智能社會法律的算法實施及其規制的法理基礎——以著作權領域在線內容分享平臺的自動侵權檢測為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第6期,第91-92頁。在這種新型權利清算機制下,著作權人擁有了上文談到的對自己財產的自治能力。對于嗶哩嗶哩等網絡服務提供商來說,與其被動的成為著作權共同侵權人,不如更好的服務于這些內容提供者,在原創作者和潛在的二次(業余)創作者之間搭建一個交易成本更低的許可平臺。
按照Calabresi 和Melamed的理論,交易成本決定了對合適的賦權規則的選擇,當交易成本很高時,責任規則會成為選項,但在高交易成本的情形下,工業參與者也有動力投資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或場所。因此,至少在某些情形下,由一個強有力的財產規則引起的議價成本會逐漸在市場上形成一個行政機制(administrative structure),其能產生法定責任規則相同的功能,故而可以在不犧牲大多數強有力的財產規則的前提下,就獲得降低交易成本的好處。23. See Robert P. Merges. Of Property Rules, Coa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lumbia Law Review. 1994, Vol. 94, No. 8:2661-2662.上文所說的知識共享組織與YouTube的內容身份系統就代表了這一趨勢。我國也有學者提出面對許可效率與傳播效率的矛盾,“允許互聯網平臺成為著作權集中和大規模許可的新主體,發揮其在數字權利管理信息的標準化上的技術優勢,將互聯網平臺與著作權人之間的合規授權作為重點規制的法律關系”。24. 參見熊琦:《“視頻搬運”現象的著作權法應對》,載《知識產權》2021年第7期,第49頁。當然在技術尚未發展到彌補許可效率的當下,堅持純粹的財產規則未必是最有效的著作權保護模式,互聯網平臺完全可以與著作權人達成協議并使其從侵權人的獲利中分享收益,這其實就是混合了責任規則下“法定許可”的產權保護模式,只不過是由企業代替法院作出賠償金的裁判,即平臺審慎地行使讓作品下架的“禁令(財產規則)”,更多的讓作者獲得“賠償金(責任規則)”。而隨著技術的發展,企業很有可能通過大數據與算法相結合的方式計算出合理的許可費用,從而兼顧原作者、二次創作者、消費者以及網絡平臺本身的利益。
四、結語
“法律+技術”財產權模式的出現解決了傳統知識產權幾乎完全依賴國家強制力實現財產權的機制,但是技術發展對產權的強保護未必完全利于產權市場如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的發展,無論是傳統著作權法中的技術措施,還是隨著算法技術發展出現的版權過濾措施,對于這些技術的使用與法律保護都引發了學者們的爭議。制度若設計不當,加強權利人控制力的新型產權保護模式最終未必有利于市場發展與著作權人的根本利益,會讓著作權人損失從新興市場獲益的可能。
技術手段的引入一方面降低了法律執行成本,影響了知識產權緩沖帶內新型產業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以算法為主的技術手段影響了權利人的意思自治代替了權利人自決,若立法技術不能跟進將很有可能打破現有的知識產權利益平衡局面。立法者應審慎發展“法律+技術”的產權保護模式,在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結合責任規則與財產規則各自的優點,建立互聯網平臺與著作權人之間的合作機制,有限制地采取版權過濾措施,輔以類“法定許可”機制,通過大數據與算法技術計算出合理的許可費或賠償金,在符合網絡效率要求的基礎上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二次創作短視頻市場的持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