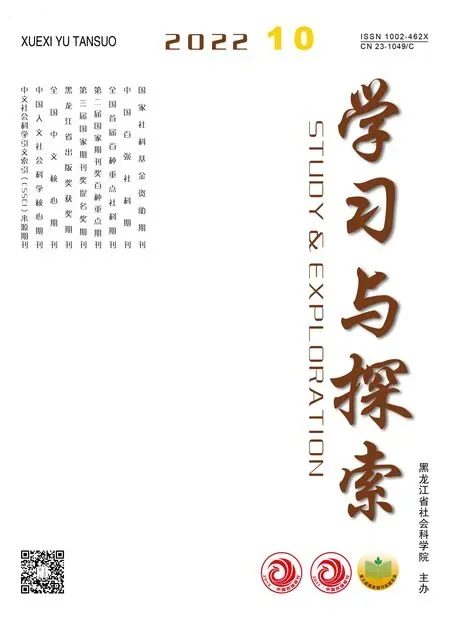加速資本主義社會時間結構批判
于 天 宇
(吉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長春 130012)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具有著一種生命價值以外的特殊意義,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人們對于時間的緊缺現象備感焦慮。這表現在主體用于體驗的時間,因可體驗事務的不斷增加而越發感到貧乏。為了盡可能多地不錯過可體驗事務,主體必須縮短閑暇時間,同時加快體驗的速度,甚至在同一時間內體驗多事務。然而,人們越發加速,則越發忙碌,對于這一問題的成因、后果及解決策略予以分析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義所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275資本的增殖邏輯不斷刷新著社會評價標準,同時改變了主體生命的時間結構,在此意義上,資本權力通過對人自由時間的剝削,徹底控制了人。
一、商品普遍化與勞動力商品時間化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2]47正是這種“龐大的商品堆積”使商品之于人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改變,因為這種普遍化的存在,一方面構成了社會財富本質內容,另一方面使人與人的關系逐漸發生物化。對于商品價值而言,勞動復雜程度是充分條件,勞動者所投入的勞動時間是充分必要條件。勞動時間決定勞動量,最終決定商品的價值量。正如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中所言:“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做尺度。”[3]51對于社會總體而言,全體勞動者投入的勞動時間總量越多,他們為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資本量就越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介入,使得一切的具體勞動在資本的框架內同質化,這既包含了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關系,同時也包含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關系。五花八門的商品、不同種類的勞動,都被商品的價值所掩蓋住了,“生產一件特殊商品所花費的時間,以一種社會普遍的方式被中介,并被轉化為一種規定了產品價值量的平均值”[4]223。在此意義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規范,具有一種客觀的社會必要性。“由作為一種客觀普遍中介的勞動所構建的社會整體性具有一種時間性質,其中,時間變成了必要。”[4]223因此,所有商品生產者都竭盡全力地達到或超越這一商品交換場域內的公共尺標,一切勞動的意義都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
勞動時間是勞動力商品的表現形式,資本家購買工人勞動力商品是以勞動時間為單位的。最大程度上占用工人的時間是資本家滿足其致富欲望的有效途徑。工人異化勞動與非異化勞動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之間的矛盾。資本家希望購買到工人更多的勞動時間,這就要求工人的閑暇時間必須不斷轉化為勞動時間,并在勞動生產率的作用下提升剩余勞動時間,在此意義上,工人的生命時間本身具有了商品的性質。對于資本家而言,購買到更多的工人閑暇時間,就意味著可實現更大程度的剩余價值增殖。資本剝削從絕對剩余價值到相對剩余價值的發展,說明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渴望。當剩余勞動時間不能直接延長時,資本家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方式無償竊取工人更多的剩余勞動時間。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言:“必要勞動的縮短要與剩余勞動的延長相適應,或者說,工人實際上一直為自己耗費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要轉化為資本家耗費的勞動時間。”[2]364資本家通過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占有,實現了其對工人剩余勞動的占有,并無償的獲得了由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同時解釋了價值規律與資本總公式即W—G—W與G—W—G′之間的矛盾,因為資本家購買工人勞動時間的過程并非等價交換,工人付出了額外的勞動時間,即剩余勞動時間。
剩余勞動時間是資本增殖的充分必要條件,在排除如通貨膨脹等因素引發的商品交換停滯的情況外,只要盡可能多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資本家就可實現更大程度的資本積累,資本就可實現更大程度的增殖。“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剩余勞動的相應延長。”[2]369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事實上正是用于購買工人的勞動時間,勞動時間的商品化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直接表現形式,工人想獲得更多的收入,就必須出賣自身更多的勞動時間,就必須將更多的閑暇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就必須犧牲更多的自由,雖然在所謂的閑暇時間中,他們也無法體驗到真正的自由。因此,可有效用于勞動的時間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唯一的出賣品,這是在資本邏輯內在驅動力和資本市場外在競爭壓力的雙重作用下而形成的。時間的商品化使勞動者具備了徹底喪失自我的“選擇”與可能。然而,無論資本家如何提升勞動生產率,無論工人勞動時間內的工作強度被如何增加,顯性的勞動時間總有上限。因此,為實現資本的無限增殖,資本家必須設法占據工人額外的時間,換句話說,必須使勞動突破固有的勞動時間框架,因為生命本身已被抽象成了純粹的時間,勞動力商品表現為時間的凝結。顯然,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在這一方面的剝削不斷發展。
二、資本的時間邏輯與社會加速
資本與時間的關系不僅表現在時間向資本的轉化,同時也表現在資本增殖過程中所依賴的時間效力。在G-W-G′的循環過程中,資本的周轉速率同樣影響著資本增殖的速度,在資本存在的每一種形態中,都渴望增加流通速度,縮短流通時間。因為在商品普遍交換的商業社會中,時間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勞動者唯一可用于出賣的商品,同時體現在資本自身的增殖過程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指出:“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是一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在這里,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5]資本正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增殖,在此意義上,“時間就是金錢”的更進一步表達是“速度就是金錢”,這既是資本的本質,更是資本主義社會加速的原因。資本時間邏輯的本質是將工人盡可能多的閑暇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同時將工人盡可能多的必要勞動時間轉化為剩余勞動時間,并在勞動生產率提升的幫助下提升單位剩余勞動時間內生產商品的價值量。在此意義上,資本的時間邏輯是資本增殖邏輯的現實表現,使時間物化。更快速的生產、交換、流通,以實現更快速的增殖。當然,資本對于增殖速度的渴望,需要依賴于時間的高效利用,在這一點上,精確化的時間為消除時間的“浪費”提供了一種積極的思路,至少在理論上,時間可以獲得不斷強化的使用方式。這種方式既為資本獲取勞動者更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可能,同時也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加速創造了條件。
資本對剩余價值的渴望使資本占有時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雖然時間本身并不是商品,只不過因為資本購買了勞動力商品,勞動才能以時間的形式凝結在商品之中。但這無形中造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加速的現實情境,并使原本的時間結構(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的分配比例)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被不斷打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的問題本質上是資本增殖的問題,不斷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是資本增殖的唯一方式,更是資本的唯一目的。在此意義上,資本邏輯的本質是資本不斷加速的增殖欲望。資本家是資本的“代理人”,資本的增殖欲望在資本家身上體現為一種具有增漲性的致富欲望,伴隨著貨幣的出現與商品交換的普遍化,“貨幣作為致富欲望的對象”[6]425,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全體人的直接目標,這同時形成了貨幣與商品的兩極對立。馬克思認為:“作為財富的一般形式,作為起價值作用的價值而被固定下來的貨幣,是一種不斷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過程。”[6]502貨幣量的增長,這種直觀的體驗要求資本權力為市場創造出更多的合理化消費場景,進一步講,更多的合理化消費,即商品與貨幣間更廣泛的交換依賴于廣大消費者的消費欲求。因此,消費者不斷激增的消費欲望同樣成為了資本滿足其增漲性致富欲望的必要條件。資本為滿足其不斷增殖的本性,使消費者困陷于不斷增漲的被資本制造出來的消費欲求中,資本為了實現更多的增殖與掠奪,則必須依賴于更多的需要。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現實描述:“每個人都指望使別人產生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犧牲,以便使他處于一種新的依賴地位并且誘使他追求一種新的享受,從而陷入一種新的經濟破產。”[7]223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也同樣揭示了這種被資本制造出來的消費欲望的虛假性,他認為:“我們擁有的不是浪費而是‘消費’,是永遠的被迫消費。它是不足的孿生姐妹。”[8]消費者消費欲望的滿足依賴于生產,因此,生產必需加速,科技發展必須加速。總之,資本增殖欲望的加速,刺激了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加速,“仿佛在某個時刻,我們共同決定,要比祖先們更貪婪”[9]。這種貪婪的表現被日本學者森岡孝二描述為:“每個人在消費方面都有攀比心理,都喜歡和別人比富、像別人炫耀。”[10]由此帶動了生產加速與科技加速。在此意義上,科技已然由人類改造自然的工具,轉化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由科技發展所解決的問題,本質上都是關于資本增殖的問題,在這種關系中,人已經不再處于主體性地位,而機器成為資本統治人的工具。“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2]469
如上所述,科技進步加速的根本目的在于幫助資本實現加速增殖,但也因此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節奏與存在方式。首先,科技進步加速帶來了社會本身的加速,這是由社會變遷的速率提升所帶來的,這造成了態度、價值、生活風格、時尚標準、階級、環境、語言、習慣等多方面形式的改變。哈特穆特·羅薩借用哲學家呂柏的“當下時態萎縮”概念對此作出了詮釋:“‘當下’這個時態不斷地萎縮得越來越短暫。”[11]17因為過去代表著不再奏效,未來代表著還沒奏效,而當下正是經驗范圍和期待范圍發生重疊的時間區間。由社會本身的加速所造成的這個時間區間的不穩定,使得人們無法準確依賴于以往的經驗來描繪未來,這增加了經驗衰退的速率,使人們感受到比以往強烈的變化趨勢。“可以說社會制度的穩定程度和實踐的穩定程度可以當作一個判斷社會變遷加速(或減速)的準繩……在晚期現代當中制度穩定程度的普遍下降,在理論方面和經驗方面都可以找到證據。”[11]20其次,社會變遷加速帶來了生活步調加速。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主要表現在亟待解決的事件量的不斷增加,人們試圖體驗更多、消費更多、占有更多,因此就必須在更短的時間內做更多的事。這種客觀上的時間匱乏甚至造成了人們主觀上的“錯過恐懼”。對錯過重要的事物的害怕并且因此產生加快生活節奏的愿望,是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生活步調加速作為對社會變遷加速的呼應,使人們對時間的精細化與利用強度要求更高。然而,人們即便不斷加速生活,卻仍然無法應對不斷涌入生活的事件,因此,生活步調加速期望科技進步更快加速。也就是說,人們希望通過更高的科學技術以實現他們更多的體驗追求。這一問題的直接后果是,科技繼續加速,社會變遷繼續加速,生活步調繼續加速,至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一種不斷加速的循環邏輯。伴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加速前進,固有的時間結構被不斷打破,更多的閑暇時間被迫變成了勞動時間。加速資本主義并不具有一個鮮明的開端,或者說,加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因為增殖是資本的本性。
三、加速資本主義社會時間結構與時間匱乏
資本的增殖邏輯打破了固有的時間結構,在自由競爭的作用下,一方面通過科技進步引發社會加速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催逼了主體閑暇時間向勞動時間的加速轉變,這既是加速資本主義社會時間結構的本質,也是資本時間邏輯的表現,更是造成主體時間匱乏的根源。在此意義上,科技加速發展的目的不再是使主體從繁忙的工作時間中獲得解脫,而是使人們陷入到一種時間貧困的境地。
一方面,從資本增殖的表象邏輯來看,資本增殖邏輯的加速激發了主體不斷增漲的欲望,欲望的無止性使得其滿足過程不斷延長。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滿足人類新的需要的過程,“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58-159。然而,資本為了加速增殖,同時也加速了人類的需要生成,“自然的需要”不斷變成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形成的需要”,并使真實需要發展成了虛假欲求。資本的加速增殖是通過主體的欲望加速以實現的,在資本權力的作用下,加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完成了由“生產欲望”到“欲望生產”的轉變。資本使全體人陷入一種“他者的欲望”之中。滿足欲望的過程占據了主體的全部時間,而不斷加速的欲望又使得主體所期望的真正滿足遙遙無期。“產品和需要的范圍擴大,要機敏地而且總是精打細算地屈從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來的欲望。”[12]224在此過程中,科技發展、社會變遷速率、生活步調都發生了加速,主體困陷于體驗事件的堆積與錯過事件的恐慌。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結構,伴隨社會加速速率的提升,不斷被打破,形成了科技越發展、時間越匱乏的緊張局面。
另一方面,從資本增殖的隱性邏輯來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的競爭邏輯,使全體人時刻處于備戰狀態。競爭邏輯決定了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邏輯,想要獲得更多且更具有競爭力,就必須在競爭中獲勝。“維持競爭力,不只是一種讓人們能夠自主地規劃人生的手段而已,而且它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唯一目的。”[11]33-34工人為了維持競爭力必須拼命工作,資本家為了維持競爭力必須拼命剝削,這就使主體的生活狀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首先,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人通過出賣自身固定的勞動力的方式換取工資維持生計,伴隨資本的不斷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不斷激增的相對過剩人口形成了這樣的事實:每個工人都必須要比其他工人工作的更多,才能維持他的競爭力,才能成為他有資格被資本剝削的理由。因此,事實上工人渴望著出賣更多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其次,資本家為了不被其他資本家吞并,也必須加速生產、加速流通、加速剝削,研發科技、更新設備、擴建廠房等手段都服務于鞏固其競爭力。資本家渴望更多剝削的本性,使其渴望著更多的工人勞動力商品。剩余價值產生于工人的剩余勞動,剩余勞動依賴于剩余勞動時間,工人用以交換的剩余勞動時間越多,則資本的增殖空間就越大。“現在資本主義企業家從他們的雇員那里買下的是‘時間’本身,而不再是他們的勞動所生產的產品。”[13]資本家期望著占有工人的全部時間,使工人無休止地為其工作,但在制度、法律的約束下,工人的工作時間有著明確的規定,且難以打破。雖然,資本家可通過高額的“加班工資”直接購買工人的時間,但這種方式顯然無法填補資本巨大的增殖胃口。
如前所述,在工人固定的勞動時間框架內,資本通過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方式,實現更快速的資本增殖。“資本本身是處于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資本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以便增加剩余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因此,越來越使剩余勞動時間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條件——生死攸關的問題。”[14]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條件是提升勞動生產率,這就促使科技進步成為資本增殖的必要前提,并由此全面地開顯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加速景象。但是,無論必要勞動時間如何縮短,在明確的作息制度框架內,資本仍舊無處突破,更多的剩余勞動時間永遠是實現資本加速增殖的充分必要條件。當時間框架不能被直接解構,資本通過制造更多的事件,隱性地剝削著主體的閑暇時間,科技進步無疑是資本增殖的幫兇,使主體在閑暇時間內仍舊可以工作,而加速的社會本身又使得主體在閑暇時間內主動渴望工作。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情況是:必須拼命奔跑,才可能留在原地。
在資本加速增殖改變時間結構的過程中,表象的欲望邏輯根源于隱性的競爭邏輯,在給予主體豐富體驗的同時,也形成了時間匱乏的社會現實。在滿足欲望與維持競爭的目的下,人們不斷將自身的閑暇時間主動轉化為勞動時間,伴隨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斷加速,實際的勞動時間越多,實際的閑暇時間越少,時間匱乏的體驗感越強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簡稱《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競爭不過是資本的內在本性,是作為許多資本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而表現出來并得到實現的資本的本質規定,不過是作為外在必然性表現出來的內在趨勢。”[15]資本的競爭本性與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的時間匱乏具有必然關聯。“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3]269資本主義社會加速的過程,正是資本不斷吮吸閑暇時間的過程,在不斷加速競爭的過程中,資本不斷消解又不斷重塑了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結構。加速資本主義社會時間結構的變化過程,實質上是主體自由時間向異化勞動時間轉化的過程。
四、加速資本主義社會時間結構消解與自由勞動
資本的時間邏輯改變了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結構,造成了社會中全體人的體驗壓力與時間匱乏。面對不斷加速的社會節奏與生活步調,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們幸福感不斷降低,并在繁忙的事件之中迷失自我。奧地利學者赫爾嘉·諾沃特尼在《時間:現代與后現代經驗》中認為: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被制造成稀缺資源后,對時間的剝削首先導致了對未來更美好的希望的痛苦磨損”[16]。在“自由競爭”的游戲規則內,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是加速的“競賽社會”,而人們參賽的資格與獲勝的砝碼是向資本展現出他們的利用價值,并隨時可犧牲這些利用價值。“在此意義上,資本成了萬物的尺度,一切都必須在資本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放棄存在的權利。”[17]競爭使人們勇于犧牲,而對于自由的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來說,唯一的犧牲品是自由時間。許多觀點認為,自由時間等同于閑暇時間,都是指非勞動時間,然而,事實上兩者具有本質差別。閑暇時間可理解為業余時間,是人們不需要勞動與生產的時間。閑暇時間供人們消費、娛樂、休息、追求藝術等,是參與勞動后人體身、心調劑的過程。在此意義上,閑暇時間確實等于非勞動時間,閑暇與勞動相對。對于自由時間來說,它的反義詞是非自由時間,認為自由時間等同于閑暇時間的觀點,先在地接受了非自由時間存在的事實。在資本權力的控制下,人們的確存在于一種非自由的狀態之中,但是,這種觀點的根本問題在于將“非自由”等同于“勞動”。勞動的異化與非自由是由資本后天造成的,而并不應該表現為一種先天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勞動并不應該就是非自由的,這既不是一種先天的設定,更不應是一種后天的約定,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自由時間應該包括勞動時間。因此,應該使勞動成為自由的勞動,而并非作為一種控制人、束縛人、異化人、痛苦人的方式。在此意義上,自由時間是主體本該擁有的全部生命時間,包含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不斷將閑暇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在資本增殖邏輯與社會競爭邏輯的壓力下,閑暇時間向勞動時間的轉化突破的固定工作時間的范疇,改變了時間結構。無論是勞動時間,或是待轉化為勞動時間的閑暇時間,本質上都是非自由的時間,都是受制于資本的時間。在資本權力的宰制下,人們甘愿犧牲的是其全部自由時間。
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自由時間的缺失是與主體自由的缺失相伴隨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主義以競爭的自由取代了全體人的自由。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了“把自由競爭看成是人類自由的終極發展,認為否定自由競爭就等于否定個人自由,等于否定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生產”[18]180這種荒謬的理論。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自由是建立在資本統治的基礎上的,這種自由是有局限性的,所謂的人的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于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采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本身而獨立的物”[18]180-181。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全部問題,都始因于資本權力對人的自由的剝奪,這造成了需要的異化、消費的異化、生產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科技的異化與時間的異化。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競爭貫穿在我們的全部生活關系中,造成了人們今日所處的相互奴役狀況。”[7]84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競爭原則根植于每個人的內心世界,資本增殖的唯一性,使每個人將獲得更大利益視為其發展過程中的終極目的。因為利益可轉化為價值、身份、標簽與認同,是滿足主體被資本制造出來的虛假欲望的唯一手段,這也確證了資本主義利益共同體的虛假本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是虛假的共同體,其實質是以資產階級為核心的階級利益共同體。在資產階級內部,個體追求“純粹”利己利益所形成的相互競爭,使階級共同體同樣具有虛假性。人們在資本所營造的廣泛的競爭中,相互逐利,而資本成為了坐享其成者。資本增殖是以人的自由為代價的,主體自由的喪失導致了其并不能真正擁有自由時間,而伴隨資本加速增殖造成的時間結構改變——閑暇時間向勞動時間的轉化,這一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性體現。因資本增殖欲望的無限性,使得社會加速是必然的,主體必須承受將更多的時間用于異化勞動也是必然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做不了自己的主”,本就從屬于資本,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代理人”“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2]205,這正說明了資本家與勞動者作為人的主體性的雙重喪失。而資本只是通過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進行剝削,以維護其“文明社會”的形象。由此可見,加速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時間問題,是資本發展的必然。任何只拘泥于時間匱乏現象本身的分析,都無法真正帶來改變。對于資本而言,主體的時間屬于勞動還是閑暇不過是“左手倒右手”,本質上都是非自由時間。因此,必須使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都轉變為自由時間。主體想獲得真正自由時間的前提是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就必須要求擺脫資本權力的束縛,走出資本主義虛假共同體,并結成以現實的人的真實需要滿足為目的的真正共同體。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聯合體”,是自由人的自我實現聯合體,是自由人的勞動需要聯合體。“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2]53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自由是標配屬性,這一屬性的前提是真正共同體對資本主義虛假共同體的超越,是無產階級聯合的力量對資本權力力量的超越。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的形成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對立面而存在的,當資本主義被徹底瓦解后,無產階級也將不再存在。在他所暢享的新社會中,國家、階級都會消亡,人將實現真正的自由解放。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12]47在主體獲得真正自由的基礎上,勞動回歸了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主體的生命時間真正成為受自身意志支配的自由時間。此時,無論是勞動時間還是閑暇時間本質上都是自由的。
一方面,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滿足真實需要的過程中,主體自由自覺地從事勞動,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異化形態。在此意義上,勞動成為了“吸引人的勞動,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18]174。勞動作為主體自我實現的方式,完成著主體的真實需要,主體為生計奔波,不再需要通過被迫的勞動去交換他們的所愿,而是將通過勞動本身獲得。人們不再困陷于“他者的欲望”之中,并跳脫出了被資本制造出的虛假欲望迷霧。如果說在這樣的社會中仍然存在競爭,那么競爭的對象只可能是自己——每個人希望自身獲得更好的發展,以完成更大程度上的自我實現。個人的發展并不會招來他者的攻擊與嫉妒,并形成彼此間的惡性競爭,因為滿足個人的需要是滿足全體人需要的前提。人的自由使勞動成為自由勞動,使勞動時間成為自由時間。
另一方面,每個人都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全面發展是建立在自由發展基礎上的,在自由基礎上的全面發展使社會中的每個人可以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時間,而非在普遍競爭的恐慌中,被迫將閑暇時間用于工作。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閑暇時間是真正的自由時間。勞動與閑暇的自由切換,才是良性的時間結構,在這樣的共同體中,人的全面發展才具有可能性。勞動時間的自由與閑暇時間的自由,使主體不再被禁錮于某一種固定的身份之中,即擺脫了由分工所限定的個體特殊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7]537范圍的限定源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分裂,人本身的力量在資本權力的宰制下成了異己的、限制人的力量。人無法驅動這種力量,卻反而被這種力量驅動。然而,在自由人聯合體中,全體人自由的復歸,使全體人可實現對受資本操控的主體身份框架與時間框架的突破。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言:“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7]537總之,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的雙重解放,使主體不再掙扎于加速資本主義的時間結構之中,加速既是資本增殖的本性,又是資本發展的桎梏。
結 語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個階級享有自由時間,是由于群眾的全部生活時間都轉化為勞動時間了。”[2]605-606資本主義在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打破了以往一切的限制與束縛,使自身“按它自己的規律運動”[18]180。資本的規律正是在運動中完成價值增殖的循環過程,在加速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通過對主體時間結構的控制與調節,滿足其自身的增殖欲望。大衛·哈維在對《資本論》第二卷的研究中說道:“如果第二卷的論述有一個主題,那就是資本循環始終有不斷加速的動力。”[19]伴隨商品經濟的普遍化發展,資本主義使個人必須融入于廣泛的商品交換關系之中,而資本無限的增殖欲望,要求商品交換頻率加速,這同時對“買”“賣”雙方提出了考驗。一方面,資本通過對主體虛假欲望的制造,創造出了廣闊的買方市場;另一方面,資本通過對主體自由時間的剝奪,生產出了更多用于出售的商品。如馬克思所言:“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18]196勞動時間本應在主體的自由時間范疇之列,由主體自由選擇支配,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成為了勞動者唯一可以出賣的東西。資本通過生產絕對剩余價值與相對剩余價值的方式,使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最大程度上轉化為剩余勞動時間。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競爭邏輯使社會加速加劇,不斷被打破的時間結構,使人們甘愿被迫將更多的閑暇時間轉化成勞動時間,進而被資本剝削更多的剩余勞動時間。“資本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18]199于是,人必須從屬于他的勞動,因為勞動時間是衡量財富的尺度。在資本的宰制下,人并不真正擁有自由,更不真正擁有自由時間。資本不僅剝削了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更剝削了勞動者的閑暇時間。馬克思所暢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都真實擁有自由,同時享有自由支配時間的權利。自由時間是同剩余勞動時間相對立的存在,“那時,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18]200。時間不再成為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阻礙,而是人獲得自我實現的有利條件。那時,必要勞動的性質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勞動成為一種需要,即成為體現人的個性與本質力量的需要”[20]。因此,為擺脫資本權力對人的統治,達到實現自由個性的新社會,首先必須探索一條超越資本邏輯的路徑,即以制度力量駕馭資本力量,使資本力量成為幫助人發展的力量,而非限制人發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