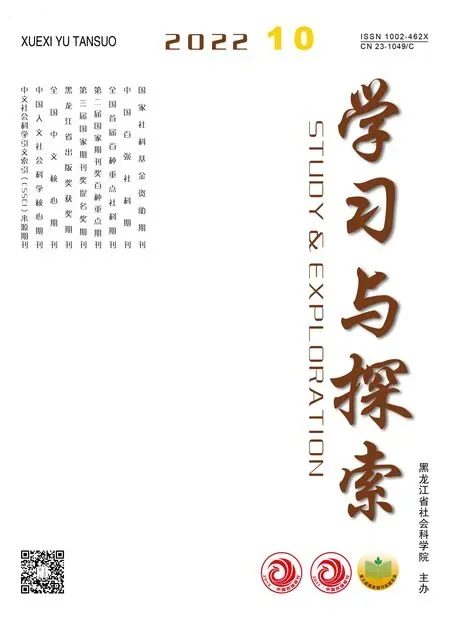風(fēng)景:復(fù)雜的思維軌跡
金 鋼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xué)院 文學(xué)研究所,哈爾濱 150028)
從20世紀(jì)80年代初開始,來自哈爾濱的馮晏便登上了詩壇,在內(nèi)地和香港都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她早期的詩作散見于《人民文學(xué)》《詩刊》,以及香港的《星島晚報》《新晚報》等報刊上,《星島晚報》還連續(xù)發(fā)表評論文章推介她的作品,認為她的詩歌是舒婷、北島等新一代詩人之外又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聲音。馮晏的詩歌創(chuàng)作以新世紀(jì)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以《原野的秘密》《馮晏抒情詩選》等為代表,偏重抒情,受普希金、萊蒙托夫、雪萊等詩人的影響較為明顯,語言也比較淺白。在20世紀(jì)90年代,馮晏停筆了幾年,2000年又重新開始寫詩,陸續(xù)出版了《看不見的真》《紛繁的秩序》《鏡像》《碰到物體上的光》等作品集,以及民刊“詩歌哈爾濱”系列詩集《小月亮》《邊界線》《意念蝴蝶》等。馮晏2000年之后的詩歌可以看成她的后期創(chuàng)作,作品的抒情成分逐漸消隱,而哲思性卻在不斷增強。這種變化是脫胎換骨的,顯示了馮晏對詩的本質(zhì)的不懈追尋。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指出,“如果僅僅描寫自然事物,或者僅僅敘述自然情感,那么無論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足以構(gòu)成詩的最終目的和宗旨……詩的光線不僅直照,還能折射,它一邊為我們照亮事物,一邊還將閃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圍的一切之上”[1]。經(jīng)過停筆幾年的沉潛,馮晏對詩的本質(zhì)與復(fù)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詩不僅是寫景抒情,還閃耀著人類思想的光輝。馮晏新世紀(jì)的詩歌更加睿智、深邃,能夠使讀者體察到新世紀(jì)漢語詩歌的多維時空建構(gòu),也給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闡釋空間。
一、從風(fēng)景空間到符號世界
《復(fù)雜風(fēng)景——致維特根斯坦》是馮晏自己最喜歡的詩作之一。她在詩中寫道:“你思維的軌跡,猶如/成群螞蟻爬過的/白色細沙,驚人的密紋/足夠我用破解密碼的焦慮/去觀察一生的。有多少/酷愛哲學(xué)的學(xué)友,蝸牛般/正在你的壟上穿越。”[2]71這里的“復(fù)雜風(fēng)景”是動態(tài)的,從某種程度上看,風(fēng)景在馮晏筆下從名詞變成了動詞,風(fēng)景不僅是一個物體或文本,而且是一個過程,詩人的主體身份通過這個如螞蟻、蝸牛般的思維爬行過程形成。米切爾認為,“風(fēng)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種微妙的力量,引發(fā)出廣泛的、可能難以詳述的情感和意義”[3]1。看起來,馮晏發(fā)現(xiàn)了這種微妙的力量,并沿著復(fù)雜的、多向度的思維軌跡,用她的詩歌把“難以詳述的情感和意義”表達出來。
對馮晏新世紀(jì)詩歌思維軌跡的探索應(yīng)從空間開始。不管是在阿赫瑪托娃的廚房、新圣女公墓,還是百慕大,風(fēng)景在馮晏的詩歌中總是以空間的形式出現(xiàn),詩人在空間中找到或者迷失自己。馮晏曾談及俄羅斯文學(xué)是她無法繞開的情節(jié),“俄羅斯文學(xué)始終貫穿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憂患”,“一個憂郁的民族對我的文化好奇心具有更加強大的魅力”[4]169-170。當(dāng)詩人來到圣彼得堡,親身拜訪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的阿赫瑪托娃的故居博物館時,她從中發(fā)現(xiàn)了什么?或許是源于女性特有的敏感,詩人發(fā)現(xiàn)了廚房這一角落,“廚房,猶如一枚書簽夾在暗處”[2]18。藉此書簽,詩人翻開了俄羅斯文學(xué)的大書,并實現(xiàn)了從現(xiàn)實的小空間向詞語的大空間的穿越。在《新圣女公墓》中也是如此,詩人徜徉在這片埋葬著俄羅斯眾多歷史文化名人的墓園,與果戈理、契訶夫等偉大的俄羅斯靈魂相遇,“為了果戈理,特朗斯特羅姆用詩句/打碎過圣彼得堡/猶如打碎一只水晶玻璃杯”[2]30-31。龐大的城市在馮晏的詩歌世界里被輕盈地打碎,穿透現(xiàn)實的城墻對靈魂來說輕而易舉。
劉小楓在《詩化哲學(xué)》中談道:“人之為人,并不只是在于他能征服自然,而在于他能在自己的個人或社會生活中,構(gòu)造出一個符號化的天地,正是這個符號化的世界提供了人所要尋找的意義。”[5]對于一位詩人來說,可能符號化的詞語世界比現(xiàn)實世界更為重要,個體生命是有限的,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空間也是有限的,而詞語的世界是無限的,就如馮晏寫阿赫瑪托娃“在時間上死去,詞語下活著”。詩人生命的價值或許在于竭盡全力把那種茫然無措的情感轉(zhuǎn)變?yōu)樵娫~的真實可靠的力量,如此我們大概能夠理解馮晏為什么會踏上百慕大的航程。在很多人看來,百慕大意味著颶風(fēng)、海龍卷以及神秘的艦船失蹤事件,是一個未知的、讓人恐懼的地方,而正是探索未知的誘惑,讓馮晏懷著內(nèi)心的恐懼在百慕大的航船上度過了五夜,飽覽了百慕大的奇異風(fēng)景,寫出了引起評論者廣泛談?wù)摰拈L詩《航行百慕大》。
如果說百慕大意味著未知與神秘,那么“航行百慕大”便是對未知空間的探索。《航行百慕大》呈現(xiàn)為五個夜晚的抒寫,第一、三、五夜是從容優(yōu)雅的詩行,表達了詩人智性的思考,第二、四夜卻是連綿不斷的長句,有的句子甚至一百多字沒有間斷,仿佛奔流不息的潛意識。如果說第一、三、五夜是詩人思維的陽面,那么第二、四夜就構(gòu)成了暗面。在陽面是“我”的理性節(jié)制地冥思,“未來,我們是否存在,/只有詞語知道”;在暗面則是“你”洶涌的情感和詞語的洪流,“你在他們的文字未來中深陷沉迷,仿佛承擔(dān)了被塑造過的宏大預(yù)知盡管你感覺自己突破甚微,整個舊時光似乎依然在你新發(fā)現(xiàn)的真理中重復(fù)。除了在百慕大海域的神秘消失人類那種無聲大過有聲”[4]113。在陽面與暗面的交替進行中,馮晏實現(xiàn)了對詩歌意緒的多向度探尋。《航行百慕大》的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形式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對詞語緊追思維的多重表達。
馮晏對符號世界有著自覺的追求,她認為寫作是“為破解詞語所蘊含的最小粒子的突變與體力較勁”[4]2。于是我們看到,她在《一百年以后》中寫道:“寫作是蛇脫掉的皮。/如果幸運,詞語可以穿過鱗。”[2]3對詩人來說,寫作如蛻皮一樣,艱難同時也意味著新生。馮晏新世紀(jì)的詩歌體現(xiàn)出了她高強度的思維能力和對潛意識的靈活運用,她所構(gòu)筑的詞語世界既讓人困惑,又會激發(fā)讀者破解謎題的好奇心。
二、作為媒介的風(fēng)景
在馮晏新世紀(jì)的詩歌中,我們可以讀到世界各地的風(fēng)景,除了圣彼得堡、百慕大,還有卡蒙斯的塑像、倫敦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新疆浮雕以及那輛開往圖們的綠皮火車。“夜晚,乘坐一列綠皮火車/去圖們。黑色車窗猶如幾處缺口/向曠野蔓延著。此刻/你不走動已在路上。”[4]73“你不走動已在路上”,旅客并沒有走動,卻已隨火車奔向遠方,恰如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命運,在不知不覺中被歷史的車輪滾滾推動。在這個高鐵、飛機四通八達,網(wǎng)絡(luò)全面覆蓋的時代,馮晏精準(zhǔn)地找到了綠皮火車這一具有歷史感的景象,透過車窗依稀看出時代的變化與記憶的裂痕。在馮晏的詩中,“風(fēng)景是人與自然,自我與他者之間交換的媒介。在這方面,它就像金錢:本身毫無價值,但卻表現(xiàn)出某種可能無限的價值儲備”[3]5。通過風(fēng)景這一媒介,馮晏實現(xiàn)了詩歌中地理圖景、空間經(jīng)驗與精神場域的結(jié)合。
隨著經(jīng)濟條件的改善、交通工具的便捷以及旅游產(chǎn)業(yè)的推動,新世紀(jì)以來的旅行詩歌、見聞詩歌大行其道,馮晏的詩歌能否避免這種流行的俗套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馮晏曾說她與寫作伴隨的另一種興趣就是旅行,“旅行所打開的眼界對于一位詩人具有著知識被膨化的作用,真理產(chǎn)生于真知灼見。是語言讓萬物作為萬物而存在。作為詩人,我希望對事物的描述精準(zhǔn)、細膩、視角遼闊”[2]184。詩人在與自然、與他者的聯(lián)系中,直接經(jīng)驗是不可缺少的,對事物的判斷如果僅僅建立在間接經(jīng)驗上,往往會淺薄、會出現(xiàn)偏差,而馮晏詩中的風(fēng)景,是她在現(xiàn)實生活中深入游歷的圖景,也是她在不同地理空間、文化空間碰撞下的詩思迸發(fā)。新疆與黑龍江同樣遼闊,卻又有完全不同的地域風(fēng)情,“一條皮鞭沉默著,讓我了解羊群的天堂/就在白云之上!游牧的居所喜歡在內(nèi)心建筑/天大的屋宇,取之不盡的光線/我正慢慢接近一份世紀(jì)遺產(chǎn),像進入/一只飽滿的香梨,正在接近感知的核”[4]132。同樣是北方,黑龍江的風(fēng)景是良田萬頃,新疆卻是戈壁、沙漠、牧民的羊群和甜美的水果。馮晏對生態(tài)自然有著敏銳的認識,她認為“自然,是視覺的遠方,是苦悶的釋放之地,是生活乏味的逃避場所,也是詩中情感被提醒以及抒發(fā)的最終指向”,“自然是詩歌永恒的依賴”[2]123-125。從生態(tài)自然方面看,新疆是與黑龍江截然不同的世界,于是走過新疆的詩人寫道,“我仍在地球上生存卻像我從地球歸來”。
除了不同的自然生態(tài),異域風(fēng)景還包含著路德大教堂、古老的水塔、島上的燈塔等西方宗教化的場景,以及奧林匹克廣場、西貝柳斯故居、赫爾辛基書店等帶有繁復(fù)文化功能的建筑和公共空間。當(dāng)一位來自東方的女詩人置身于這些異質(zhì)空間中時,她由此生發(fā)的陌生感和追問是意味深長的。“思維無法越過黑暗,不快的風(fēng)景。/一張靜止的合影照,空缺部分,/時間在流過,生命之間的沖突/將到何時?一個詩人在身體里/安睡著兩個國家,或者更多。”[4]100-101馮晏表現(xiàn)出一種知性而又偏執(zhí)的態(tài)度來面對歷史與時代,詩人可以包容不同的國家與文化,而“那時代的真相”,顯露在語言的“逆行部分”中,也就是說,詩歌“要離開一個又一個語言或語感的故鄉(xiāng)”,“在一個信息嘈雜、心靈被阻隔的時代,以往語言的輕柔已經(jīng)無法讓你抵達深處的靈魂”[4]168。詩人是時代的審視者,在看清了時代之后,尋覓最恰當(dāng)?shù)脑~語與時代進行碰撞。
即便是馮晏這樣一位從容的詩人,她的詩歌中仍或多或少流露出對當(dāng)下時代的焦慮。當(dāng)詩人身處異域時,祖國、漢語仍是她詩中不斷出現(xiàn)的詞語。“這時國內(nèi)電話/一座新松浦大橋尾部垮塌/瞬間,道路成為深淵/死去的人,靈魂正迷失在途中”[4]137。詩歌從赫爾辛基奧林匹克廣場突然轉(zhuǎn)回家鄉(xiāng)發(fā)生的慘劇,表現(xiàn)出詩人此時的痛心與震驚。馮晏的詩歌在極具哲思性的同時,是不乏現(xiàn)實感的,現(xiàn)實感“來自于一種共時性的作家對生存、命運、時間、社會以及歷史的綜合性觀照和抒寫”[6]。這種觀照和抒寫除了與當(dāng)下時代緊密相關(guān)之外,也延伸到普適性的人的內(nèi)心,馮晏說“真實是內(nèi)心唯一宗教”(《北歐旅行片段·芬蘭最南端,漢高小城》),她在充滿了“懺悔”的異域風(fēng)景中反思當(dāng)代中國的命運與個體的命運,就如《一只黑色甲蟲》里那只旅途中的甲蟲,不厭其煩地翻越一座座“山峰”,卻仍然要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三、城市風(fēng)景與城市文化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馮晏新世紀(jì)的詩歌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詩歌雖然具有很強的哲思性,但并不完全是玄之又玄的。比如,有關(guān)馮晏生活的城市哈爾濱的只鱗片羽時常浮現(xiàn)于詩中:暴風(fēng)雪、露西亞、中央大街、波特曼西餐廳、呼蘭河、蕭紅以及仍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詩友張曙光等,會讓熟悉哈爾濱的讀者會心一笑。在城市化迅速發(fā)展的今天,我們生活的城市是另一種風(fēng)景呈現(xiàn)的形式,對城市的書寫日益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重要部分。馮晏新世紀(jì)詩歌的思維軌跡密布在哈爾濱這座東北城市里,而城市風(fēng)景的書寫,在馮晏新世紀(jì)的詩歌想象中不僅是背景、環(huán)境,而且深入了城市文化、城市精神。
哈爾濱這座因中東鐵路的修建而興盛的東北邊疆城市,具有濃郁的俄羅斯文化風(fēng)味。以至于馮晏初訪圣彼得堡的時候,竟覺得那里與哈爾濱非常相像,產(chǎn)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發(fā)展過程使得哈爾濱具有了與北京、上海等國內(nèi)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氣質(zhì)。俄日殖民統(tǒng)治、左翼文化思潮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重工業(yè)基地的興衰等,都對哈爾濱的城市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筆者看來,馮晏新世紀(jì)詩歌所呈現(xiàn)出的哈爾濱城市文化特征主要有三點:其一,因地處東北大平原中心,水陸交通四通八達而產(chǎn)生的廣闊、包容的氣質(zhì);其二,大量俄羅斯僑民長期居留此地而形成的俄羅斯文化風(fēng)味;其三,老工業(yè)基地衰落之后的銹跡斑斑的工業(yè)城市形象。
馮晏曾談道:“哈爾濱處在北方遼闊地域的中心,遼闊本身對于詩人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自然教育,猶如東西方文化或者思想對于詩人的教育一樣重要。”[4]207這種地域的遼闊性在馮晏的詩歌中也有較為充分的表現(xiàn),如她所寫的《暴風(fēng)雪》:“一層玻璃隔開嚴(yán)冬,/窗外冰河如白紙,/足跡讓給平原。”[2]11暴風(fēng)雪落得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凈,如一張無邊的白紙,人的足跡走在上面就像一行詩。由于太過遼闊,《暴風(fēng)雪》顯得空曠,甚至孤獨。風(fēng)雪本是紛繁密集的,詩中卻說像“一只綿羊在草原追趕離散的白云”,綿羊應(yīng)是成群的,詩中卻只出現(xiàn)了一只。《暴風(fēng)雪》所寫極廣闊,又極單調(diào);極紛擾,又極寧靜,在動靜之中寫出了地域的特色和詩人的心境。哈爾濱的春天因其短促而讓人覺得特別珍貴,《立春》透露出春天生機勃勃的氣息,“立春,轉(zhuǎn)動著鑰匙。/是時候放出被困在思想里的獅子、海豹了,/以及沙漠、花園和蜥蜴。/在解凍之季通往海市蜃樓的夢境里”[2]9。春回大地,詩人的思想也解凍了,釋放出各種各樣奇妙的詞語和意象,甚至靈魂都“騎上一只野兔”,穿過枯草和荒原。
20世紀(jì)初大量俄國僑民和殖民者來到哈爾濱,他們在建設(shè)哈爾濱的時候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圣彼得堡。模仿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重要手段,不僅是建筑,寫作也是如此,藝術(shù)創(chuàng)作往往是在模仿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創(chuàng)新。馮晏在《復(fù)制或模仿》中寫道,“旁邊的中央大街始終像俄羅斯,/街上新增一個畫街景的雕塑,/繼續(xù)著偉大的模仿”[4]86。詩歌既展現(xiàn)了哈爾濱的俄羅斯文化風(fēng)味,又進行了深入的哲理思考,“經(jīng)驗是創(chuàng)意的敵人。/復(fù)制是逃脫之繩打起的結(jié)”。詩歌寫作離不開經(jīng)驗,杜威認為藝術(shù)即經(jīng)驗:“經(jīng)驗本身具有令人滿意的情感性質(zhì),因為它擁有內(nèi)在的、通過有規(guī)則和有組織的運動而實現(xiàn)的完整性和完滿性。”[7]“詩是經(jīng)驗”是當(dāng)代漢語詩歌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作觀念,李琦、張曙光、趙亞東等詩人都以豐富的詩作詮釋了這一觀念,而馮晏的創(chuàng)作并不滿足于經(jīng)驗,她的寫作是超驗的,她試圖把普通的詞語帶到更高的、更完美的層次。就如在《波特曼西餐廳》中,“我們背靠著印有列寧和葉卡捷琳娜頭像的俄羅斯椅子”是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語言爆破像一場儀式”[2]64則是超驗的。與北京、成都等城市的茶館文化不同,俄式西餐廳可以說是哈爾濱的城市名片,華梅、露西亞、波特曼等俄式西餐廳常在文藝作品中出現(xiàn),構(gòu)成了哈爾濱城市的一個重要文化空間。在《波特曼西餐廳》中,文化空間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被詞語的超現(xiàn)實爆破打碎,然后又重新組合成超驗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詩句。
現(xiàn)代城市是鋼筋水泥的森林,看起來是缺乏詩意的,特別是在哈爾濱這樣一個擁有“三大動力八大軍工”的老工業(yè)基地城市,但從另一方面看,這座城市的煙塵和銹跡同樣存在著詩意,這需要詩人發(fā)現(xiàn)的眼睛。馮晏對哈爾濱的抒寫不是單純地寫風(fēng)景,而是把時勢寓于風(fēng)景之中。在《五月逆行》中,“道路擁堵猶如浮腫的腿”。在《這座城市有些偏遠》里,“加入的車流,仿佛穿越一場戰(zhàn)役。/擁堵甚至?xí)恢鄙钊肽愕膲糁小?我時常夢見氧氣在天邊,成為商品,/夢見驚恐,身體丟失在心靈的后面。”[4]93擁堵是現(xiàn)代城市的頑疾,不管修多少馬路、立交橋、地鐵,在特定的時間段里,城市還是擁堵得讓人絕望,“甚至?xí)恢鄙钊肽愕膲糁小薄!秲?nèi)部結(jié)構(gòu)》有著對現(xiàn)代城市病的系統(tǒng)批判,空氣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等社會問題在詩中不斷出現(xiàn)和累積。“都市,霧霾一次次越過母親/新贈送給你的護身符,血管里/后來流進什么,父母一無所知/就像他們的血液,生你時/大自然還潔凈”[4]145,這是詩人在煙塵滾滾的城市中的悲鳴。“殺蟲劑在空中,雨里/和泥土深處,任由你血液/迎來送往”,這讓我們想到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與卡遜女士一樣,馮晏相信人類應(yīng)該敬重自然,人類的生存與自然生態(tài)的平衡息息相關(guān),而不像有些狂妄的人那樣覺得人類能夠統(tǒng)治自然。
在世界日益扁平化、同質(zhì)化的今天,詩人如何提供個體經(jīng)驗,展開獨特的想象與思考,成為衡量詩歌品質(zhì)的重要因素。具體到城市書寫中,城市不僅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產(chǎn)物,它還有各自的地理特征與歷史文化脈絡(luò),以及城市人靈魂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有研究者認為,哈爾濱是“國內(nèi)為數(shù)不多的以詩歌獲得認同的城市”[8],而馮晏以其對城市文化精神的思考,以及起伏跳動的詞語想象,為新世紀(jì)城市詩歌寫作提供了難得的范本。
四、鏡中風(fēng)景
馮晏對哈爾濱城市的書寫,不像李琦、張曙光、桑克等詩人那么直接、完整,而是隱晦、破碎的,需要讀者去重新拼接。應(yīng)該看到,城市形象、城市精神并不是馮晏書寫哈爾濱的終點,她對城市文化精神的書寫仍是詩歌的表象,她的思維軌跡并沒有停留在倫理化的城市空間,而是強力地探入到城市人的內(nèi)心。評論者多強調(diào)馮晏新世紀(jì)詩歌的哲思性與潛意識等深層次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哲思對詩歌的影響,或詩歌對哲思的反映并不是以直接方式進行的,而是以“鏡像”的形式迂回展開。馮晏認為,“對于一首好詩來說,其中一點就是怎樣把思想隱藏好”[4]2。在馮晏的詩中,她的思想是隱藏的,不那么直露的,概念性的思考轉(zhuǎn)化為了意象的蝴蝶,需要讀者去耐心地捕捉。詩集《鏡像》的封底選取的是《鏡子》中的兩句詩,“鏡子里的我是精細的,/她聽到生活發(fā)出撕紙的刺耳聲。//然而,粗糙是一種誘惑,始終都是”[4]3。這兩句詩大概可以看成馮晏新世紀(jì)詩歌的自況,她的詩歌雖然是精細的,卻是粗糙生活與復(fù)雜內(nèi)心的鏡像,詩人通過鏡像的折射去追求真理。
夢是馮晏新世紀(jì)詩歌里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仲夏夜之夢》中,“一條花蛇從夢中向外張望”;《旅行在凱恩斯》里,“她隨幻覺出海,反而從夢中驚醒”;《灰空氣》里,“你夢見視線穿透屋頂,比昨夜夢見翻過烏云尋找星星還要低”。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大致能夠看出,“夢”所包含的象征意義對詩人的重要性。夢是人類思維的隱秘部分,每個夢都是有意義的,詩人試圖通過夢境來解析人類的潛意識,就如她在《走進夢境》中所表達的,對于一個超現(xiàn)實主義者來說,夢與現(xiàn)實互為表里。在《清晨的局部速寫》中,馮晏引入了“捕夢網(wǎng)”這一意象,捕夢網(wǎng)源自18世紀(jì)的印第安人,傳說好夢能從網(wǎng)中的圓洞流出來,而噩夢會被困在網(wǎng)中,并在清晨陽光的照射下徹底消失。這一奇妙而又美好的意象讓人印象深刻,并且恰恰指明了夢處于真與假的邊界,從夢境出發(fā),真實與想象、過去與將來、家鄉(xiāng)與遠方、生與死等不再相互對立,這或許是超現(xiàn)實主義提供的一種超真實。然而,若想在超現(xiàn)實主義的詩歌里尋找一個確定的支點,那恐怕是徒然的,就如馮晏所寫,“夢境對神經(jīng)系統(tǒng)進行解密,/研究,最終是徒勞的”[2]8,我們所能發(fā)現(xiàn)的只是若有若無的定位的希望而已。
馮晏新世紀(jì)詩歌中所描寫的景象大多是生活的細節(jié),是詩人的經(jīng)歷以及旅途印象等。這些細節(jié)是真實可感的,但細節(jié)之間的現(xiàn)實關(guān)系卻被詩人用夢境化的手法打碎,我們大致能夠感受到夢境的色彩,卻理不清夢境的邏輯。詩人甚至有意制造了觀察的困境,“鏡子里的我剛穿過夢中瀑布”,我們需要通過瀑布、夢、鏡子三重阻隔來觀察詩人的內(nèi)心,這種多重阻隔帶來神秘的效果。馮晏曾說,“我確認每一個真正的詩人的內(nèi)心深處都有一個與神秘主義的區(qū)域相接通的路徑,一首理想的詩作給寫作者本人帶來的欣喜不可言說,只能體會。”[9]詩人有意營造的錯位、顛倒、迷失等等,可能正是夢境的迷惑,它將讀者引向縫隙之下的深淵,一種深層的、超驗的真實。在《縫隙與日月》中,“鉛字已經(jīng)深陷在縫隙里,/仿佛不合時宜的幽靜生活。/還有筆記,被追憶拉直的橫與豎,/撇和捺的飛揚時光,她都留戀。”[4]66詩人甚至不滿足于意象與詞語的破碎,連漢字都要拆解為筆劃,從而在漢字的縫隙中發(fā)現(xiàn)真理。或許詩歌的真理就在于以字詞的重新拼接來抓住事物隱藏在縫隙中的核心,詞語的力量是巨大的,“幾個詞就能劃傷全部,這并不夸張”(《漸行漸遠的日子》)。
在新世紀(jì)以來的漢語詩歌中,日常性、歷史性、敘事性等是較為常見的詩歌審美范式。與這些范式不同,馮晏的詩歌帶有強烈的超驗色彩,執(zhí)著于探索詞語的奧秘,表現(xiàn)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她認為,“詩歌寫作就是讓詩人去體驗發(fā)現(xiàn)奇跡的感覺。你的才華需要在每一首完成的詩歌中去被時間檢驗。雖然有些無情,但給出的標(biāo)準(zhǔn)一定是真理”[4]166。馮晏在她的詩中并沒有給出真理的明確定義,但我們大致可以認為,她通過詩歌的鏡像所進行的迂回的詞語與思想的創(chuàng)造,就是她詩歌的真理所在。
結(jié) 語
不管怎么說,馮晏新世紀(jì)的詩歌是晦澀、難懂的,在閱讀、闡釋她詩歌的過程中,常會想到阿倫特所說的:“討論詩歌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任務(wù)。詩歌可以引用,卻不宜用來討論。”[10]但我們也應(yīng)該認識到,詩歌的“晦澀”不能僅歸咎于詩人所采取的表現(xiàn)手法。“詩歌的‘晦澀’有它的認識論方面的來源。人的認識本身就包含著‘晦澀’的成分。而詩歌作為一種人的認知方式,只不過比其他的認知方式更強化了其中的‘晦澀’成分。”[11]馮晏新世紀(jì)詩歌的思維軌跡構(gòu)成了復(fù)雜的風(fēng)景,猶如一座迷宮,不過,馮晏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又一個迷宮的入口,比如新疆“大巴扎市場一塊小玉的裂縫”,又如波特曼西餐廳“被縫合后又重新開啟的唇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