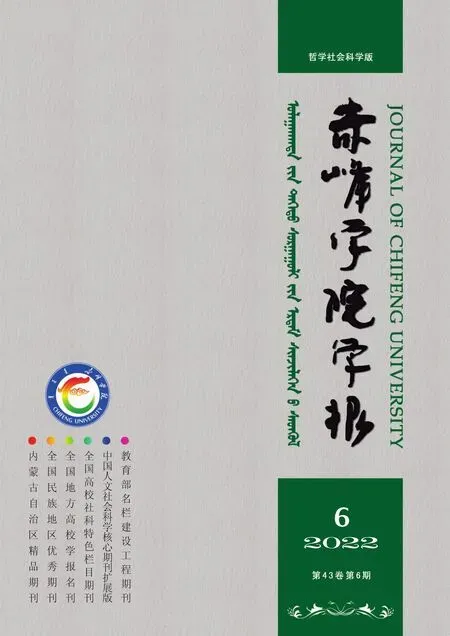清末新政時期新疆財政及捐輸問題
海爾汗,特爾巴衣爾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北京 100872)
一
在清末之前,清政府財政收入來源主要以地丁銀為主,同時還有錢糧、關稅、鹽課等幾項稅收。但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宣布“將丁銀固定,對于五十年以后的新增人口不再增收丁銀、不征錢糧,且多丁之戶也只需交一丁錢糧。”使國庫歲收失去了擴張性。加之關稅、鹽課都有征收的標準與規定,使清政府國庫在應對國家危難、社會危機時有驟然虧空的風險,且容易入不敷出。為了應對突發狀況,清政府在咸豐之前采用歲余儲存和臨時號召捐輸的方式來支撐財政支出。
捐輸,猶捐獻、輸納,指將個人財物捐獻給國家的行為。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亂,康熙帝開捐納實官之例以籌措兵餉。雍正朝之后有了“常例捐納”,書生可通過捐納得職銜,官員則可以通過捐納來加爵晉升。乾隆元年 (1736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捐納銀占戶部總收入銀數在15.7%左右。嘉慶七年(1802年)至二十四年(1819年),捐納銀占戶部收入銀數在53.3%左右。道光元年(1821年)至二十九年(1849年),捐納銀占戶部總收入銀數在38%左右。①嘉慶到道光時期,國運漸衰,最初官民百姓尚有余力上交財物以響應政府捐輸號召,但隨著社會動蕩的不斷加劇、財政不斷虧空,使得社會財政收入日漸萎靡,政府收取的捐輸銀也在減少。清政府為了填平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賠款而造成的國庫財政空洞,頒布了一種 “臨時籌款方式”,名為厘金。
最初厘金制度只是一種變相的“捐輸”,被稱之為 “捐厘”。由副都御使雷以誠于咸豐三年(1853年)在揚州首先推行,②后逐漸推行至全國各地,新疆地區則于咸豐六年(1856年)始推行厘金。③厘金實際上是一種值百抽一的商業稅征收,此類變相的收稅使得民商百姓的負擔再度加重,也有官員趁機中飽私囊,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清政府在后期雖出臺了一些管理限制政策,④但是遵循條例的地區很少,沒有明顯成效。盡管厘稅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但是在財政危機的情況下,清政府也不得不采用這種辦法填充支出。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戶部奏:“和議既成,賠款已定。無論如何窘急,必須竭力支持。臣部職司度支,固屬責無可卸,各省值此艱巨,尤當勉為其難,亦惟有于出款力求裁減,入款再求加增,庶幾湊集巨款,屆期歸償。”[1]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清政府開始加征附加稅,以賠款捐輸的名義加征稅糧。⑤除繼續推行厘金制度之外,對于工商業的各項稅款進行償款加價、海防籌餉加價等[2]。厘金、捐輸成為清末新政時期清政府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政府表面鼓勵進行自主捐輸,實際上用設定指標、設立相關財政管理部門等方式進行強制收款。這種方式雖然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是對于社會穩定產生了不利影響。
清末新疆財政也頗為困難。在光緒初期,中央政府將協餉制度改為“大致視各省財力以攤派各省定額協款”[3]。新疆作為受協省份,協餉有了一定保證。新政期間,清政府為了向列強交付賠款,填補推行新政以來的財政空洞,讓全國各省分擔賠款,舉全國之力償還債務。新疆雖然經過建省后的革新,社會經濟狀況有所緩解,但是整體來看經濟水平依舊十分低下,社會結構也較為脆弱。自建省以來,新疆大部分財政收入來自山西、河南等省份向新疆所解的餉銀。然而隨著封建王朝逐漸衰落,中央財力的逐漸減弱,地方省份不再按時按數將餉銀解給甘肅,而是留銀自用,導致新疆所受協餉大幅減少。
新疆攤派庚子賠款數額四十萬兩,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時任新疆巡撫的饒應祺上奏:“近際時艱,庫款支多存少,殊形竭蹶,玆因賠償洋款,臣與布政司支光熟商,將每年……共請每年短解協餉四十萬兩以湊賠款,從此來源較減餉款益形奇絀。”⑥新疆首任巡撫劉錦堂曾明確提出對于田賦“統于此次一律核定,作為永額。”[4]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新疆攤派賠款“數鉅期迫,由協餉發還,愈形艱窘”,故而準備仿照內部省份對田賦加收耗羨,復開華稅。⑦新疆在縣城中設立總局,征收的稅率為值百抽三,所有華商稅務照一起一落征收。光緒三十年(1904年),戶部籌辦“百貨統捐”,時任新疆巡撫潘效蘇以現征華稅與統捐無異為由上奏,并仍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稅收章程收稅。
咸豐六年(1856年)新疆對吐魯番進行過一次棉花厘金的收取[5],但后期是否還有相關厘金的抽取已經不詳。再度抽取厘稅是在光緒四年(1878年)左宗棠平復新疆之后,并一直持續。光緒八年(1882年)五月,新疆奉上諭停止抽厘,曾設的抽厘局卡一律裁撤。盡管新政時期新疆征稅沒有用“厘金”的名號,但是華稅征收名目和方法與厘金無異,商民苦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新疆巡撫聯魁批準改辦百貨統捐,新疆的厘稅收入又有了一定程度增長[6]。
二
中國歷史上的捐輸現象由來已久,漢唐時期偶有發生,至宋明時期,捐輸主要用于災荒賑濟。到了清代,封建社會的經濟生產走向末路。在經歷政權危機與社會動蕩后,國家財政往往會出現危機。這時捐輸成為備受清政府青睞的一種政策。除基本的地丁、田賦、關稅等收入外,捐輸成為地方公共工程建設、賑濟以及戰時的軍餉籌備等經濟支出的重要財政補充手段,為政府短期內籌集大量白銀提供了可能。
清政府為擴大捐輸渠道,一般會采取地方官向民勸諭捐輸和獎勵捐輸等方式。雖然前期取得一定成效,但隨著清政府的沒落,開捐愈加頻繁,甚至有時還出現了各捐輸項目一同開捐的現象。為了在限定時間提高收捐的效率,多地不惜“打折收捐”,導致“所捐實銀計不過舊例十成之一”[7]。而清政府內部腐敗嚴重,已經十分有限的捐款還會被地方官員層層克扣,甚至中飽私囊,最終收捐的錢糧極為有限。
1.1 基本資料 收集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間,在廣東省婦幼保健醫院就診正常聽力孕前/產前婦女13 452例,年齡15~45歲,受檢對象主要來自廣州及其周邊地區(包括24例外籍人士)。在對患者進行耳聾知識宣傳后,自愿進行晶芯TM 9項遺傳性耳聾基因檢測試劑盒進行突變熱點的初篩。
清末新政期間新疆的捐輸,以參與者身份劃分為外部捐輸與內部捐輸兩大部分。
外部捐輸以地方和官吏個人捐輸為主,或以新疆整個行政區為單位向清廷捐輸。新政期間,清朝政府為了籌措巨額賠款、維持戰爭以及實施新政,不斷向地方索取經費,新疆也無法幸免。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開始,清政府以籌備“新海防”的名義給各省下達了捐輸指令,并給予了一定的捐輸標準。新疆在新海防捐輸中數額有增有減。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至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新疆巡撫饒應祺一共提交了16次有關新海防捐輸的奏折,其中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共有連續11次請求減一成捐輸的奏折,而到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的5次奏折,則都為請求加一成捐輸的奏折[8]。清政府對于新疆的捐輸標準一直較為寬松。光緒三十年(1904年),中央免除新疆每年應解的七萬兩練兵經費。但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為了節省經費,戶部決定裁減甘、新兩省的餉銀,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始實行。同一時間,各省欠解新疆的餉銀越來越多,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始,按照規定新疆巡撫每年應得協餉為2,501,450兩,但是由于各省的財政壓力增大,導致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到三十三年(1907年),各省欠解新疆的餉銀總量已經達到183萬余兩,平均每年欠解的銀兩大約占應得餉銀的18.1%。⑧
在新政推行之時,邊疆官吏積極向朝廷捐輸個人財產。清政府給歸順朝廷的天山南路統治者的待遇十分優越,不僅授予他們對本部的行政管理權,給予豐厚的養廉銀,還賜予一定數量的土地,以維持他們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這里的統治階層為了贏得朝廷的信任和豐厚的獎賞,熱衷于捐輸。為了補充軍餉等開支,清政府自咸豐朝開始便鼓勵這些官員以及王公伯克捐輸錢糧,并且制定了具體的伯克捐輸獎敘議程[9]。新疆哈密扎薩克和碩親王(九世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就向朝廷捐輸銀兩,而被清廷加賞三眼花翎,獲乾清門行走;于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捐助軍餉而被“賞敘”[10];又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再度捐餉酬防而請獎。⑨新疆吳進回部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至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先后三次向朝廷捐金,并向朝廷請獎。⑩
捐輸在名義上是一個自愿的行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積極參與捐輸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朝廷對于中央及地方官員的捐輸激勵,實際上屬于層層攤派或者說是勒派[11]。這一現象在清末已經十分常見。在推行捐輸過程中,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都任意勒索攤派,“名曰勸捐,按其實到勒捐也……每開一例,即遍傳殷實之戶及家僅小康者派定捐數”“且小民之畏捐亦有故,今日勒捐,明日即按戶之名勒借。”?二是官員為了表達對朝廷的忠心,是感激朝廷恩德的報效之舉。如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是否響應咸豐帝捐輸的號召,代表了是否對皇上忠誠,故而無論自身的家境好壞,所有官員都在想盡一切辦法籌得捐款。這也是咸豐二年(1852年)捐輸達到高潮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邊疆地區官員捐輸的動機和性質與內地有所不同,清代伯克以及清代蒙古王宮貴族捐輸的原因除了強制攤捐外,也是出于對清政府的感激,向朝廷效忠的一種方式。
新疆的內部捐輸以民間捐輸為主,主要目的在于支持新疆當局的財政,以進行社會建設和推行改革。一般包含以捐輸為名而增添的稅收、為征集建設省內公共事業的資金而開展的捐輸、與新疆地區商業貿易有關的捐輸這三個部分。
新政時期,新疆為了籌措各項經費,出現了很多種捐稅。對于田稅,新疆當局設置南北兩路:北路辦畝捐,以每畝收銀二分五厘來征收;南路辦草捐,以每百斤收銀五錢征收。宣統二年(1910年),由于清軍馬隊營長槍殺弁兵,在迪化引發了聚眾放火事件,使170家商戶商鋪盡毀,損失慘重。后賑災救濟的費用,由公家出資三十余萬兩白銀墊付。宣統三年(1911年),時任巡撫袁大化決定,在統捐內,每百兩加收二兩五錢白銀,用以補公家的墊款,于是開始了“二五商捐”,這項稅收一直到民國才被廢除[12]。
新疆當局還出現了捐廉、捐產興學、捐田興學等,用來支撐開設農業、工業技術培訓等。新疆振興農業、開辦實業等措施雖然在最初卓有成效,但是這些改革措施大多都沒有延續下去,甚至有部分政策只停留在了提議階段,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去推行。
除了為農業生產與公共事業建設而開展的捐輸,新疆當局也對商業開展了捐輸活動。庚子事變之后,巡撫饒應祺復開華稅,新疆的厘稅收入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時,有90,876兩白銀,到了三十三年(1907年)共有77,314兩[13]。盡管為新疆的財政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是厘捐實際上與稅收無疑,本質上還是強制性的征收措施,長此以往給新疆民眾帶來了不小負擔。
民間開展捐輸的因素大致有二。一是民眾通過捐輸的方式向當地政府官員賄賂,從而獲得一定的特殊優待或者便利[14]。但是對于商人這一群體捐輸的主要動機,目前學界存在一定分歧。?另外,民間捐輸中的勒捐現象極為普遍,收上來的錢糧被貪官污吏克扣,中飽私囊,“若輩貪黠性成,未免以動用并非官帑,更恣侵吞,罔知顧忌。”[15]
三
新政期間,新疆的財政支出除籌練新兵外,又增加了實業費、學堂費、機構經營費等,支出驟然增多。僅是伊犁地區籌練新兵一項,每年開支就達到五十七萬四千余兩,再加上新政開辦公司企業的支銷,每年大概需要八、九十萬兩白銀[16]。新政期間新疆創辦了各式學堂,創辦每一所學堂需一萬兩千兩,常年經營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兩[17]。而且為了開辦實業,培養人才,新疆還送學生去往北京、俄國學習。還有官商合辦實業公司,官商兩方要各出一半資金支撐公司運轉。除了省城有可靠的經濟來源外,地府州縣都需自行籌款,使新政措施在地方的推行并不順利。光緒二十六年(1901年),新疆烏蘇地區由于協餉減少,當地公共事務幾乎無力維持,故奏請新疆當局對于其財政短缺進行補助,然而新疆當局的財政同樣短缺,故而對于此等請求有心無力。?
由于落后的經濟和社會生產力,面對中央政府的攤派和捐輸錢糧的財政任務,新疆將重擔壓在民眾身上。光緒二十三年(1898年)五月,新疆喀什當局向巡撫饒應祺提出酌辦裁兵節餉,以減少當地財政支出。?由于不斷增加賦稅,新添各種稅款、捐輸,在新政期間新疆地區百姓的負擔反而更加沉重。以宣統三年(1911年)為例,新疆稅收有二百一十六余萬兩,而此時全省人口不到二百一十六萬,人均負擔一兩以上的稅款,而在建省初期,每人稅款僅在0.3兩左右[18]。經濟生產不穩定、財政危機和官員腐敗貪污,導致民不聊生,物價飛速上漲。到宣統二年(1910年),吐魯番民眾由于當地糧價過高發生了社會暴亂,焚燒搶劫,放火攻城[19]。新政期間,民眾的生活壓力反而比新政之前的還要重。
清政府在開始推行改革時,改革事宜多交給總理衙門等中央政府部門兼管,在這過程中沒有一個統一規劃,造成各省在推行新政時方法不一,中央集權受到影響,地方權力逐漸擴大。在后期地方政府往往漏報、少報以留存本地財政剩余,再加上各地官員貪污腐敗,層層克扣,導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下降。
新政推行之時,清政府管理國家事務已經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牽制。再加上清政府昏庸無能,百姓對清政府的統治愈加不滿。當時的商人群體憤而指責商部:“不曰開統捐,即曰加關稅;不曰勸募紳富慷慨助金,即曰招徠南洋富商責令報效。”[20]對清政府廣收稅錢,強征捐輸表達了強烈的不滿。而且清政府在鼓勵創辦實業、推行改革的同時,以各種明目增加苛捐雜稅,使全國各地的財政壓力不降反增,從而降低了地方推行改革的積極性和生產積極性,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從本質上看,清政府出現政策失誤的原因主要在于落后的封建專制政權已經不能適應社會近代化的發展。我們不能否認清末新政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推動了中國近代化思想的萌發,但是新政同時也成為清朝覆滅的原因之一。
注 釋:
①根據羅玉東《中國厘金史》歷朝戶部銀庫收入表,本文數據結果通過將歷朝每年的捐納銀占戶部收入銀數百分數進行平均值計算方法得出.
②見《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41第1頁:“咸豐三年,金陵失陷,餉源枯竭。太常寺卿雷以誠治軍揚州,始于仙女鎮倡辦厘捐。”
③見《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41第5頁:“六年奏準,……又奏準烏魯木齊、吐魯番地方,抽取棉花厘金。”
④見《湖南厘務匯纂》卷1第21頁:“戶部遵議厘稅大減餉糈不繼酌擬章程八條疏,咸豐十一年二月。”
⑤據李帝《清末新政財政改革論述(1901-1911)》第17頁:“四川1901年派地丁‘賠款捐輸’達100萬兩,江西1903年地丁和漕糧的隨糧捐歲曰30萬兩。……山西1901年的畝捐每畝加征銀一錢五分。”
⑥見 《新疆巡撫饒應祺稿本文獻集成》第13冊第55-66頁《新疆餉項支絀疑請復辦華商貸稅以資補救折》.
⑦見 《新疆巡撫饒應祺稿本文獻集成》第15冊,第115-124頁《新疆現疑仿照內省錢糧加收耗羨折》.
⑧[清]聯魁《聯魁新疆奏稿》,見馬大正,吳豐培.清代新疆稀見奏牘匯編 (同治、光緒、宣統朝卷)[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⑨見 《新疆巡撫饒應祺稿本文獻集成》第1冊第111-114頁《哈密回部親王沙木胡索特捐餉籌防請獎片》.
⑩見《新疆巡撫饒應祺稿本文獻集成》第6冊391-396頁、第8冊134-138頁、第9冊489-494頁《吳進回部貢金折》.
?孫翼謀.請除近日流弊疏,見[清]盛康輯,盛宣懷編.皇朝經世文牘編·武進盛氏思補樓,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卷25.
?有學者認為商人捐輸是完全自主的行為,取決于“內在超越性的商業精神”,見馬麗.區域社會發展與商人社會責任關系的歷史研究——基于明清揚州徽商捐輸活動的考察[J].社科縱橫,2012(01).
?見 《新疆巡撫饒應祺稿本文獻集成》第22冊第30頁《致烏蘇游府徐 協餉多奏請停解公懸之缺仍緩補》.
?見 《新疆巡撫饒應祺稿本文獻集成》第21冊第413頁《致喀什提臺 請酌辦裁兵節餉事、裁兵節餉案均照尊議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