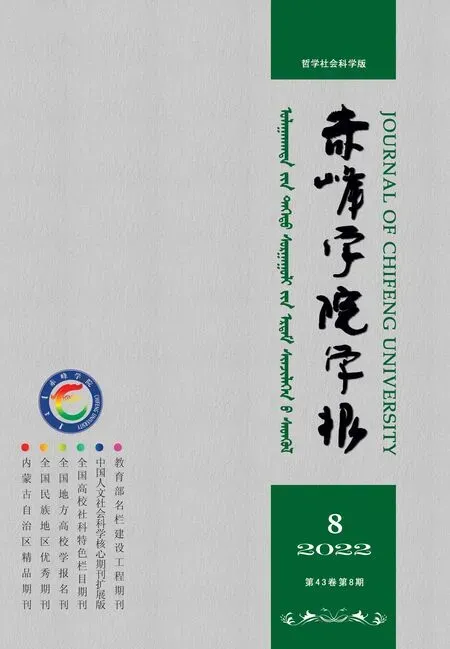GATS框架下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模式研究
胡倩一
(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 400031)
馬來西亞被無國界高等教育觀察組織(OBHE)稱為“新興競爭者”,靠著低廉的學費和語言優勢(英語),在2006年占到全球國際學生市場約2%的份額[1]。同時,馬來西亞被還列為“地區學生中心”,對亞洲地區學生,特別是中東和非洲國家學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2]。雖然馬來西亞僅在《服貿易總協定》的金融和其他服務方面作出了承諾,并未提供教育服務方面的承諾,但由于其渴望成為世界級知識經濟和區域教育中心,一直以來對教育貿易都秉持積極的態度。
一、關于《服務貿易總協定》
《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1995年由世貿組織通過,涉及到12個不同的服務部門,目的是使貿易自由化,減少或消除貿易壁壘。教育被明確地作為一種服務類商品,支持者認為GATS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機遇和催化劑,反對者則擔心教育商業化挑戰了傳統教育理念,同時帶來了各種風險如破壞文化傳承、文化同質化、麥當勞化[3],加劇教育不平等和人才流失等。《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12種服務的四種交付方式,在教育方面的解釋如下[4]:
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是指提供者從一成員國的國境內向另一成員國的國境內提供服務,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沒有實際的流動。如遠程教育、在線學習、虛擬大學。跨境交付主要是通過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尤其是互聯網來實現,目前有著巨大發展潛力;
境外消費(Consumption Abroad)是指提供者在一成員國境內向來自另一成員國的消費者提供的服務。主要表現為學生的流動,如出國留學。這是最常見的傳統國際化形式,目前在全球教育服務市場中占有最大的份額,并在不斷增長;
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是指提供商在另一個國家建立商業設施以提供的服務,主要表現為機構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如衛星校園,雙聯合作伙伴關系,特許經營安排等,這種交付方式在未來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
自然人流動(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是指作為以個人身份進行的服務提供者的臨時跨境流動,主要表現為服務提供者的流動,即人的流動性(如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不包括學生),這種流動通常是臨時性的;
GATS希望通過貿易逐步自由化,最終達到國家之間沒有貿易障礙的狀態。盡管目前僅有1/3的國家對GATS做出了有選擇性承諾,但跨境貿易已經影響到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并且這種貿易正在穩步增長。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并不能完全壟斷教育,所以公立教育也會受到GATS的影響。馬來西亞有著繁榮的私立教育,同時也積極對公立教育進行企業化改革,《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四種交付方式在馬來西亞都有充分體現。
二、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國際化具體表現
(一)跨境交付
跨境交付在高等教育中主要表現為遠程教育、在線學習和虛擬大學等形式,后兩種形式在廣義上可以歸入遠程教育。遠程教育并非新生事物,最早的遠程大學是成立于1969年的英國開放大學(UKOU),70年代后,這種彈性教育形式被大多數英語國家采用,并迅速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東南亞國家。如果說早期遠程教育一直面臨著形象問題,被認為質量差、不合格,是二流教育的代表[5],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遠程教育已經完全擺脫傳統形象,成為替代傳統教育的更具成本效應的方式。
馬來西亞的遠程教育開始于70年代左右,當時僅有少部分學校提供相關課程或文憑。9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提出“2020宏愿”,旨在把馬來西亞建成發達工業國家。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就必須要有豐富知識和嫻熟技能的人力資源的支撐,需要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馬來西亞當時有1100萬工人,其中40%-60%的人僅為高中水平[6]。為了改變這一現狀,馬來西亞在第七個五年計劃(1996-2000)[7]中決定進行更大規模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的技能培訓,以便提供更多受過良好教育、具備高技能和積極性勞動力。1998年,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多媒體超級走廊”國家計劃(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簡稱MSC),這項宏偉計劃包括開辦一流的學校教育和發展最有效的遠程學習系統[8]。在這項計劃的支持下,從2000年到2008年,馬來西亞境內的互聯網使用人數增加了300%,互聯網接入率排名東南亞地區前列[9]。
教育是馬來西亞政府優先關注的問題,馬來西亞遠程教育的優勢在于政策支持下信息技術、基礎設施以及信息化人才的充分保障。目前,馬來西亞幾乎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有在線學習管理系統,尤其是國際學生可以很便捷地獲取校園公告、課程資料、學習資源,參加在線論壇討論等。GATS框架規定成員國服務提供商能夠自由使用公共網絡,保證信息自由、安全地在境內外流動,相對較少地受到貿易壁壘的限制,在這一積極的學習環境中,馬來西亞傳統遠程教育的愿景、目的、形式和規模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服務提供者和學習者均不用身體移動的前提下,遠程教育不再是僅僅學生進修學位課程的手段,成為馬來西亞教育國際化重要推動力。
(二)境外消費
境外消費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主要形式是學生流動,出國留學是教育國際化最傳統的形式。2000年以來,全世界出國留學的學生人數呈指數級增長。但隨著教育參與者的不斷增加和多樣化,高等教育公共資金的減少,以及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后對外國技術勞工需求量的增加,國際學生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10]。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外國學生的入學率均在下降,渴望成為地區教育中心的亞洲和中東地區正在成為教育市場的新參與者。
90年代前,馬來西亞主要以學生出國留學為主,屬于教育輸出國。馬來西亞社會有著復雜的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差異,1969“5·13”種族騷亂后,政府推行“新經濟政策”,通過各種平權行動維護馬來土著人的特權。在教育方面則實行種族配額制,即以民族而不是成績作為大學的入學標準(土著和非土著入學比例為55:45),當時的馬來西亞僅有一所公立大學(馬來亞大學),直到1995年前還沒有私立大學,這些原因直接導致了大量非土著學生在國內求學無門,據統計,1985年有68,000名馬來西亞學生在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留學[11]。
90年代中后期,馬來西亞接收了大量國際學生,逐漸發展成教育輸入國。這一轉變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教育需求的不斷擴大。馬來西亞在90年代初對基礎教育進行了改革,將學期從9年延長到了11年,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中學教育開始民主化,這些改革導致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12];其次是經濟發展的需要。馬來西亞政府提出“2020宏愿”,開始承認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出臺并修訂了《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法》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法律法規。到2000年,馬來西亞出國留學的學生已減少到5萬名,其中30%是受資助的學生。從2002到2013年,馬來西亞共接收了70多萬名國際學生,成為“地區學生中心”。
在境外消費模式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馬來西亞逐漸轉變為高等教育凈出口國,學生流動方式由輸出變為輸入,節省了大量外匯流失,大量的外國項目為馬來西亞創造了巨大的貿易利益。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過程中,馬來西亞始終把國家意志放在首位,以確保國家目標的實現和國家認同貫穿其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人員、機構、項目等外在層面,在高等教育自身的制度和功能等內在層面變化相對有限,這很好地解釋了馬來西亞對GATS承諾持謹慎態度的原因,很顯然,在馬來西亞,社會和文化目標比市場目標更加重要。
(三)商業存在
商業存在在高等教育中主要表現為建立海外分校。20世紀以來,高等教育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大學和商業組織一樣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世界大部分國家都試圖將自身打造成卓越高等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13],各國政府普遍認為,外國機構以商業存在方式進入本國有助于防止國內外匯流失,增加貿易機會,節省高等教育機構的基礎設施資源,從而減少對政府資金的依賴。海外分校的數量從2002年的24家增加到了2017年的300多家[14]。70年代初,馬來西亞政府就允許外國大學以提供課程的方式進入馬來西亞。到90年代后,在大力發展經濟的背景下,馬來西亞的海外分校迅速發展,截至目前共有13所外國大學分校[15]。
和韓國、新加坡等國接近自由的監管方式不同,馬來西亞的教育國際化注重風險防控和質量保障。馬來西亞對海外分校有著詳細的準入規定和全面的質量保證框架。海外分校進入馬來西亞有兩種方式:1.與當地公司或當地機構的合作;2.租用非常經濟的土地[16]。馬來西亞將海外分校作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監管,采取的是雙重質量保證的方式,海外分校需要同時接受馬來西亞資格認證機構(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簡稱MQA)的質量保證監測和東道國的授權機構的資格審查。
盡管商業存在的風險和挑戰很高,馬來西亞仍然通過降低稅收和租金等優惠政策吸引國外頂級教學資源,海外分校的建立同時吸引了大量國際學生來馬來西亞學習,促進了境外消費交付方式的蓬勃發展。一方面,通過修改或增加本土課程以滿足本國校園要求,另一方面,加強風險防控和注重質量保障。馬來西亞通過這兩項措施建立了均衡的跨境教育體系,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四)自然人流動
自然人流動在高等教育中主要表現為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的跨國流動,由于涉及到國際服務貿易和移民問題,和其他三種交付方式相比,自然人流動相對難以追蹤和理解。盡管自然人流動模式早在1986年烏拉圭回合就開始了,但它在服貿總協定下的自由化承諾并未完全兌現[17]。據世界銀行統計,自然人流動占服務貿易總價值不到2%。2012年東盟經濟部長簽署了《自然人流動協定》,該協定主要針對熟練勞動力的自由流動[18]。在馬來西亞,占據區域流動主導地位的是非技術勞動力,專業技術人員的流動只占到很小的部分。
隨著馬來西亞經濟持續增長,勞動力市場特征由勞動力過剩轉向勞動力短缺[19],馬來西亞已經成為熟練勞動力的凈進口國[20],在對專業人力資源需求迅速增長的同時,面臨著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21]。對于馬來西亞來說,在自然人流動模式下還有諸多努力的空間。從短期的角度來看,馬來西亞需要關注當前的勞動力需求缺口,促進外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馬來西亞需要加強高等教育和行業間的聯系,在自然人流動框架下,通過鼓勵國際師資的自由流動提高教育國際化水平。尤其是馬來西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因為有著英語語言優勢,對聘請外國人擔任教師更有吸引力,成熟的雙聯課程和學分轉移等形式也將為大量專業人員的“非永久”入境和“臨時”停留提供了可能。
三、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國際化迅速發展的原因
《服務貿易總協定》關心的是貿易,而不是教育。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高等教育經歷了劇烈重組,國家、大學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正在被重新定義。在“2020宏愿”的框架下,馬來西亞教育系統體現出民主化、私有化和權力下放的特點。教育部轉變了對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整體交付體系的看法,更關注成果和績效,并注重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總的來看,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模式主要是,在成為世界級知識經濟和區域教育中心的愿景下,致力于確保教育系統順應全球趨勢而不斷動態發展,在GATS的框架下開放高等教育市場,并保持高度的風險防范意識。其高等教育國際化迅速發展的原因有:
(一)將教育質量作為高度優先項
在內部質量保障方面,馬來西亞有著制度和機構雙重保證,《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法》《馬來西亞質量框架》等系列文件規定,商業存在中的海外分校被認定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需強制性地符合馬來西亞本國的評估程序。在外部質量保障方面,馬來西亞有著東道國和本土雙重質量保證。
(二)積極構建高等教育服務市場
馬來西亞積極擁抱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靈活多樣的教育國際化形式。從GATS的角度來看,四種交付方式在馬來西亞均有充分體現,且都蓬勃發展。馬來西亞致力于教育服務輸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是主力軍,其主要形式有內部方案、跨國方案和外部機構授予資格方案等[22],其中雙聯課程、學分互換等方式甚至吸引了大量來自發達國家的留學生,促進了GATS框架下四種交付方式的不斷發展。
(三)不斷完善風險應對機制
在海外分校的設立和監管方面,馬來西亞的市場準入原則和GATS的規定并不一致。馬來西亞規定新的外國大學分校只能在教育部長的邀請下設立,且必須由一家擁有馬來西亞人多數股權的公司來運營,政府可以限制私立大學的數量和類型,且外國大學分校與當地私立大學遵守相同的規定,并設立《民族語言》《馬來西亞研究》和《伊斯蘭研究》等文化必修課程。在語言和本土課程的規定方面的努力,是規避文化風險,建立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