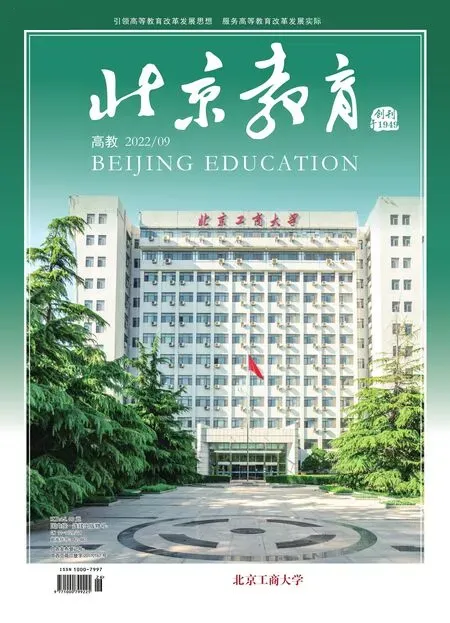高校教師職業倦怠問題與應對
——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與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的視角
□ 文/甘羅嘉
高校教師職業倦怠是一個常見問題。關于教師職業倦怠,有很多從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展開的研究,提出提高教師工資待遇、緩解教師工作壓力等應對建議;還有從教育哲學方面的思考,如清華大學的石中英教授(2020年)“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異化勞動的思想,認為教師職業倦怠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師與教育活動關系的異化,喪失其自由自主的類本性。具體的原因包括:教師在選擇從教時并非源自自己的興趣愛好,教育教學過程中專業自主權喪失以及教育教學改革中的邊緣化、客體化和工具化等”[1],提出“解決教師職業倦怠需要從教師招聘的源頭及促進教師職業流動入手,落實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并發揮教師在教育教學改革中的主體作用”[2]的策略。
本文嘗試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與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的視角重新審視高校教師職業倦怠這一普遍問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認為“其行為與活動的動機和需要是多種多樣的,從低級到高級,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如果我們將教師職業發展視為教師個人滿足、個人需求與最終實現自我的一個連續過程,那么運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能夠解釋職業倦怠的成因,并能在獲取應對方法中受到啟發。赫茨伯格“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將組織中影響成員的各個因素分為兩大類:保健因素(也稱為亞當需要,不滿足這些條件會導致員工的不滿)和激勵因素(也稱為亞不拉罕需要,滿足這些條件會讓員工得到激勵)。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讓我們更深刻地從教師個人角度去理解職業倦怠,雙因素理論則能讓我們更好地觀察學校等外部環境對教師職業倦怠的影響。
高校教師職業倦怠的問題成因
高校教師作為社會眾多職業中的一種,因其工作相對自由、教書育人富有成就感、能發揮創造性、職業發展路徑清晰以及社會地位較高等優勢而受到推崇。然而,如果對上述優點分別進行深入分析,將會呈現高校教師職業的另一種真實狀態。
“工作自由”一般理解為無須坐班,有課程教學安排時才需要到校授課;然而這種理解,一方面,忽視了備課、課外輔導等一系列課堂外的教學環節;另一方面,也忽略了高校教師科研工作的考核壓力。“工作自由”實際上是一種長時段甚至是24小時在線的工作狀態。“教書育人富有成就感”一定程度上是教師職業備受尊敬的主要原因之一,“桃李天下”是教師個人對社會的重要貢獻;然而,要真正完成“負責任、有良心”的“教書育人”工作,需要教師投入永無止境的精力于教學工作中。“能發揮創造性”是所有科學研究工作的共同特點,創造性的高水平發揮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投入,與專門的科學研究崗位相比,這就對需要同時從事教學、社會服務等其他工作的高校教師提出了更高的時間需求。“職業發展路徑清晰”是社會公眾對高校教師職業發展存在的較大誤解之一,大家往往認為每位高校工作者或者高校教師最終都能成為“教授”。
以筆者所在的C大學為例,C大學是一所教育部直屬、中等規模,在其特色領域有兩個A+學科的大學。在C大學里教學、科研人員不到全部職工的50%,擁有教授或者副教授職稱的教師在所有教學、科研人員中不到80%,即能在教學科研崗位發展到“副教授”以上的人員不到全部職工的40%。再以北京大學為例,北京大學網站上公示了截止到2020年12月的學校教職工數據[3],該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全校教職工11,694人,專任教師中擁有正高級與副高級職稱的教師數為3,034人,從這些數據看:北京大學的“教授”與“副教授”只有全部職工的26%。誠然,在北京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教學輔助人員等人員中也有高級職稱人員(如實驗室的高級工程師、校醫院的主任醫師、圖書館檔案館的研究館員等),但是即便加上這部分人員,也不會超過職工總數的一半。北京大學和筆者所在的C大學尚且有一半以上的教職工不能沿著職業路徑發展而獲得較高的專業技術職稱,全國眾多高校的教師在職業發展上則面臨更大的困難。高校教師“社會地位較高”源于“成就他人、犧牲自我”的奉獻精神,源于改革開放以來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不斷深化理解;現實中除去少數工程與經、管、法、藝學科專業人員,大部分高校教師還是相對清貧的,即高校教師職業具有“社會地位較高+收入偏低”的交織屬性。
當我們以上述視角回顧之后,我們能發現高校教師工作呈現“工作時間緊張、發展壓力較大”的突出特點,而高校教師的職業倦怠正是基于這些特點而產生。誠然,一個“不負責任、無所謂教學科研事業進步”的“躺平”教師是不會發生職業倦怠的。但是,一方面,教育與學術界管理越來越規范、考核越來越嚴格,“躺平”幾率越來越小;另一方面,“負責任、積極進取”的高校教師是絕大多數,加之教育與學術行業發展越來越迅速,高校教師的職業倦怠問題呈現日漸突出的態勢。
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與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的觀察
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人的最終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高校教師職業倦怠的終極原因在于“自我實現”的艱難甚至無望。第一,“自我實現”目標遠且難,如前文所述,一所大學里超過一半的教師(教職工)可能一直無法獲得較高水平的專業認定,其教書育人的成就感與外界社會評價難以被正確認可,久而久之,不是“倦怠”就是“躺平”。第二,“自尊的需要”在高校教師進入社會工作一定時間后有了新的認識與理解,這些理解往往與之前的認知有偏差。具體來說,高校教師工作的前述所有“優點”逐漸褪去了光環,還原為“社會資源有限+收入待遇較低”的現實,這與其過去十幾年的“學霸”生涯及自己的高期待未來有較大落差,“自尊的需求”受限。第三,即使從“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來重新審視高校教師工作,在競爭激烈的當下,都存在不確定性。源自歐美的“非升即走”政策在現今的國內高校有了異化的表現,華南、華中地區的兩所“985高校”,高達90%左右的淘汰率讓所有在校的青年高校教師不僅失去了“安全與歸屬”,而且失去了從事學術與科研工作的動力。上述所有一切都讓高校教師的工作從一份崇高的、值得奉獻終身的“事業”變成了一份普通的養家糊口的“工作”,而這一點也促成了高校教師職業倦怠的關鍵轉變。
如果我們運用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來分析,也能視野更開闊地了解這一問題。當前社會階段,大部分學校能夠提供給高校教師的“保健”條件相對有限,準確地講,大部分學校只是為學校教職工提供了一個基本“生存”條件。“保健”因素的不健全導致了部分高校教師對教育事業與教書育人工作的不滿意,這些不滿意突出地體現在考核與評價機制不夠合理(“科研有用、教學無用”等)、工資收入與其他福利待遇有待提高等。大部分學校能夠“激勵”教師積極進取的因素也不夠,物質激勵方面,高校副教授跳槽到中小學從教偶有發生,經濟欠發達地區高校教師跳槽東部沿海地區企業工作也不算罕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高校物質激勵條件有限;其他激勵措施方面,“感情留人、事業留人”某種程度上成為停留在宣傳層面的口號,大部分高校也無法給教師帶來很高的社會聲譽與受尊重程度;教育事業的社會價值方面,部分大學本科學習的“散養放羊”狀態以及研究生階段導師與學生關系異化為“老板與員工”的情況降低了高校教師的社會評價美譽程度,教師教書育人的成就感在逐步降低。
因而,從上述兩個理論的視角出發觀察,我們可以對高校教師職業倦怠問題的認識有了一種假設性的理解——高校教師工作某種程度上成為“意義微小與未來渺茫的低價值重復勞動”。
應對高校教師職業倦怠的建議與策略
高校教師工作的“價值回歸”是應對職業倦怠的良藥。為高校教師工作重新確立可以達成的目標和可以實現的意義,讓從教人員能夠通過教師工作實現每個人自我的“安全、歸屬、自尊與自我實現”是讓絕大部分高校教師避免長期處于職業倦怠狀態的終極方法。這個方法需要解決幾個問題:
1.高校教師工作的目標和意義重定位
立德樹人、為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是教師工作的基本目標,將其現實化為每個高校教師工作的意義和目標則是管好教師自己班級與課程的每位學生,讓他們學有所得并順利畢業或者結課,即將遠大崇高的終極目標具象化為每日的具體工作安排,從而增加教師工作的充實感和成就感,以應對職業倦怠。
2.教師職業成長路徑的多元化
并不是每位教師都適合教書育人工作,那么如何退出或者轉換賽道?這首先涉及到教師本人對自己意愿、能力和可獲得的機會與資源的一種客觀認識,即教師“愿意干什么”“適合干什么”“當前有什么”的矛盾統一。絕大多數情況下,想做一名高校教師并不意味著其適合做一名高校教師或者能獲得一個高校教師的崗位。如果已經成為高校教師,那么需要解決的其實是“想不想做好一名教師”與“是否適合做一名教師”的關鍵問題,如果“不想做”或者“不適合”,就需要學校提供一種機制讓教師轉換為純粹的科研工作者、教學管理工作者、教學輔助工作者等,讓他們能在其他職業發展路徑上向前進步—找準自己的位置,看到努力的方向與成長的希望是緩解職業倦怠的重要方法。
3.對個人發展中的困難與努力奮斗必然性的再認識
任何“激勵”下的個人奮斗以最終“自我實現”的道路必然是困難重重和曲折艱苦的。所有短期的職業倦怠都意味著正處于“量變”的積累期,無法超越而發生“質變”皆因為積累不夠,尚未到達轉折點。因而,將職業倦怠視為成功前必經的“黑暗”,將有助于堅定意志、從容應對。
4.高校提高“保障”待遇,加大“激勵”力度
大部分高校的物質條件有限,因而提高“保障”待遇和加大“激勵”力度只能是創造良好的教學科研環境讓高校教師能集中更多精力在教學科研工作上,不被或者少被各種不必要的其他事務打擾或者妨礙;創新政策鼓勵教師從學校外部引入社會資源或者鼓勵教師進入社會參與競爭,利用社會資源“激勵”教師實現個人與學校的共同發展。
總的來說,高校教師職業倦怠問題目前普遍存在且日益嚴重,一方面,倦怠源自較大的工作壓力;另一方面,則主要根源于教師對個人發展前景不明朗的憂慮。高校教師的職業倦怠問題深層次地反映了高校教師個人對教師職業的價值再認識。只有努力創造條件,通過促進“價值回歸”來實現教師職業倦怠感的降低與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