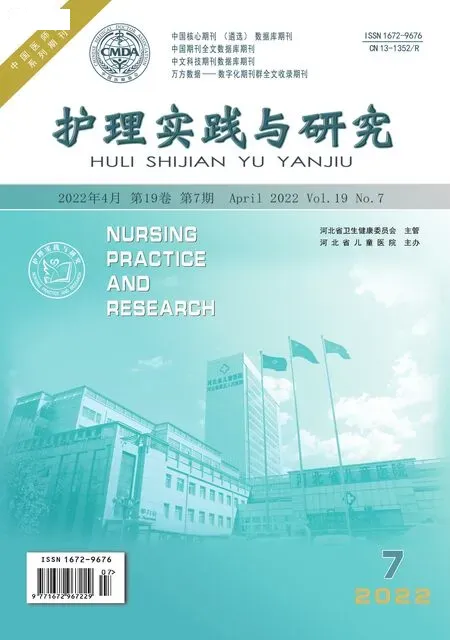免疫缺陷合并膿毒血癥致右手壞疽性膿皰瘡患兒護理1 例
春曉 龔媛媛 李敏
作者單位:510623 廣東省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兒童重癥監護室
原發性免疫缺陷病(PID)是一組由基因缺陷導致的免疫功能異常為特點的臨床綜合征,在起病時或病程中多伴有皮膚癥狀[1-2]。皮膚是原發性免疫缺陷病最常受累的器官之一,也是最直觀的癥狀,往往是早期識別免疫缺陷病的重要臨床表現[3]。PID 相關的皮膚改變包括皮膚軟組織感染(如真菌、細菌和病毒感染)、濕疹樣皮疹、凍瘡樣皮疹、蕁麻疹樣皮疹、魚鱗樣皮疹、紅皮病、皮下出血、膿皰型銀屑病或其他自身免疫/自身炎癥和蛋白酶活性相關皮膚癥狀等[1-2]。PID 引發的膿毒血癥意味著感染的嚴重性和全身性,且PID 患兒的皮膚感染較正常人癥狀表現更加嚴重,病程遷延,治療效果不佳,且易反復[4]。本例為1 例PID 合并嚴重膿毒血癥致右手壞疽性膿皰瘡的患兒,經過制訂符合患兒病情的分階段創面管理方案以及數次清創與功能性敷料換藥,傷口愈合,現報告如下。
1 病例介紹
患兒,女,2 歲2 個月,主因“發熱、皮膚破潰化膿2 周余,加重2 d”于2020 年8 月3 日17:00收入院。入院診斷:①免疫缺陷待查;②膿毒血癥;③支氣管肺炎;④呼吸衰竭;⑤軀干皮膚感染(全身皮膚);⑦G-6-PD 缺乏。患兒在新生兒期因“①新生兒敗血癥;②腸炎;③休克;④腦室出血;⑤遺傳代謝病待查”住院,予抗感染、抗休克、抗癲癇治療后好轉出院,后生長發育正常。父母均體健,患兒哥哥1 歲余齡時因“①膿毒血癥;②多器官功能障礙;③大皰性魚鱗病樣紅皮病;④免疫缺陷待查;⑤營養不良”,搶救無效過世。患兒入院前1 個月開始發熱(39 ℃以上),外院查血常規,感染指標高,三系降低,建議到上級醫院就診,家屬未就診,逐漸出現軀干及四肢皮疹,瘙癢,抓撓后皮疹處出現破潰化膿、瘀點瘀斑、結痂等。入院前1 周再次出現發熱(39 ℃以上),于我院急診就診,三系降低未見改善,軀干及四肢皮膚破潰較前加重,建議轉血液腫瘤科治療,家屬拒絕。入院前1 d 再次發熱(38.9 ℃),急診再次就診后收治入院,我院就診查血常規示感染指標高、三系低,氣促、呼吸費力,軀干及四肢皮膚破潰較前加重,全身散在紅色斑丘疹、黑色焦痂、破潰化膿等。入院第1 天仍發熱(39 ℃)、氣促加重轉兒童重癥監護室(PICU),轉入時患兒神志清楚,自主體位,表情痛苦,反應差,呻吟呼吸,雙側瞳孔等圓等大,直徑3 mm,對光反射靈敏;體質量8.5 kg,身長64 cm,BMI18.4;體溫39 ℃,心率171 次/min,呼吸70 次/min,血壓113/54 mmHg。入室后立即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擴容、抗感染、血管活性藥物改善循環等對癥支持治療。治療期間反復輸注紅細胞懸液、血小板、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等藥物支持治療,根據體溫、感染指標、病原學檢查結果不斷調整抗感染藥物治療方案,入院第15 天,患兒反復發熱癥狀好轉,感染指標下降,凝血功能較前好轉,繼續給予藥物支持和抗感染治療。入院第40 天,患兒病情較穩定,感染及凝血功能均較前好轉。入院第55 天,患兒雙肺感染較前加重,雙肺進行性破壞,多發肺膿腫、肺氣囊產生,血常規三系進一步降低,給予胸腔閉式引流、輸注血制品等對癥治療。入院第75 天,患兒出現血尿,全身皮膚出血點增多,血壓及血氧飽和度進行性下降,經調整血管活性藥物、調整呼吸機參數、輸注血制品等治療后無明顯改善。入院第76 天,患兒血壓及血氧飽和度再次出現進行性下降,家屬經過慎重考慮后放棄治療,患兒最終死亡。
2 護理
2.1 護理評估
2.1.1 全身評估 患兒入院第2 天傷口小組首次接診時,患兒在芬太尼、咪達唑侖持續靜脈輸注維持下,處于淺鎮痛鎮靜狀態,體溫36.5 ℃,心率102 次/min,機械通氣輔助下呼吸頻率50 次/min,膿毒性休克狀態,于持續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持續靜脈輸注維持下血壓85/42 mmHg。營養狀況評估正常,處于同年齡同性別患兒的25%~75%,四肢皮下脂肪層正常,皮膚彈性可,暫禁食,血清白蛋白正常。患兒合并肺部感染、膿毒血癥、三系降低、G-6-PD 缺乏等,C 反應蛋白>200 mg/L,紅細胞計數2.18×1012/L,白細胞計數0.1×109/L,血小板計數12×109/L,血紅蛋白61 g/L。全身皮膚稍蒼黃,全身散在紅色圓形皮疹,皮疹中心可見點狀黑色結痂,全身可觸及散在淋巴結,四肢有多發小面積皮膚破潰化膿,部分結痂,皮溫高,破潰處周圍皮膚紅腫。請皮膚科會診,血培養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建議使用莫匹羅星軟膏外涂破潰處抗感染[5]。患兒家庭經濟狀況較差,但家屬對傷口治療表示支持。
2.1.2 局部評估 傷口小組首次傷口評估見右上肢腫脹較左側明顯,皮溫較高;右腋窩下可觸及一腫大淋巴結,約5 cm×5 cm。右手背可見一2.8 cm×3.2 cm 表面凹凸不平、100%黑色焦痂覆蓋的傷口,為全身最大面積傷口;傷口邊緣形狀不規則,未見滲液,觸及無波動感,未聞及明顯異味;周圍皮膚紅腫,手指更明顯,皮溫高,手臂嚴重腫脹;疼痛評估應用FLACC 評分法,安靜及處理傷口時評分均為3 分(輕微不適),予持續芬太尼鎮痛。
2.2 分階段創面管理
2.2.1 早期緩慢清除壞死組織,局限感染灶,防止擴散 通過對患兒的全面評估,確定早期傷口護理難點在于全身情況較差,凝血功能差,全身感染嚴重,治療護理以全身支持治療挽救生命為主,傷口保守處理避免出血,局部抗感染預防感染灶繼續擴大。右手背傷口請骨科專科會診,考慮傷口面積較大且有壞疽,深度未知,若手術探查有截肢可能,但患兒基礎情況差、凝血差,目前無手術條件,建議保守治療。所以右手背傷口選擇持續予碘伏濕敷及10%聚維酮碘乳膏外涂抗感染,每日換藥。入院第16 天,傷口大小約4 cm×3.5 cm×0.5 cm,部分焦痂脫落可見75%創面基底紅色,25%黑色焦痂覆蓋,傷口邊緣形狀不規則、腫脹,滲液為血性,稍黏稠,傷口觸及易出血。查血常規凝血功能較前好轉,且已輸注血制品改善凝血功能,遂右手背予鑷子保守銳性清創,后以10%聚維酮碘乳膏持續濕敷。本例患兒對于傷口敷料的選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患兒存在G-6-PD 缺乏,不能使用含磺胺的銀離子等敷料,且患兒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當前全身治療花費已較大,所以使用價格較低廉的聚維酮碘乳膏抗菌抑菌、軟化焦痂緩慢清創。聚維酮碘具有較好的抗炎、止痛的療效,能夠促進創面的肉芽生長,促進皮膚組織在生長過程中的DNA、RNA 的生產,縮短創面愈合的時間,而10%聚維酮碘軟膏對常見的感染性創面具有較好的抑菌作用[6]。
2.2.2 后期創造濕潤環境,滲液管理,促進愈合患兒傷口創面后期的護理重點包括預防感染、滲液管理、預防出血等,可應用功能性敷料促進傷口愈合;同時也應密切觀察,早期識別傷口感染。患兒為原發性免疫缺陷,肺部感染難以控制,不斷加重,但傷口創面后期未出現明顯感染。創面一級敷料應用藻酸鹽,創造微酸無氧或低氧、適度濕潤的傷口環境,促進壞死組織的溶解,促進生長因子釋放,刺激細胞增殖,加快表皮細胞的再生和爬行,同時緩解傷口疼痛[7],部分可釋放鈣離子,促進凝血酶原激活物的形成,加速止血。二級敷料使用標準型水膠體敷料,如滲液量較少且出血減少,可僅使用水膠體敷料覆蓋,保證濕性愈合的環境,同時吸收滲液維持濕性平衡,促進創面肉芽組織生長和爬皮。入院第44 天,患兒病情較穩定,感染及凝血功能均較前好轉;患兒右手背傷口3 cm×2.5 cm×0.3 cm,表面凹凸不平,創面基底75%紅色,25%黃色,無明顯滲液,創面觸及易出血;傷口邊緣形狀不規則,部分上皮邊緣內卷,右手臂紅腫較前明顯消退,干燥脫屑,皮溫正常;兩次傷口膿液細菌真菌培養顯示無菌生長。以鑷子去除壞死組織,碘伏和生理鹽水依次清洗創面,紗布拭干創面,予藻酸鹽填塞傷口,表面予水膠體敷料覆蓋。換藥頻率以滲液及傷口情況按需調整,一般3 d 換藥1 次。入院第65 天,患兒右手背傷口面積1.5 cm×1 cm,創面基底表面平整,100%紅色;滲液為黃色伴少許血性,稍黏稠,濕潤狀態;周圍皮膚部分色素沉著,干燥脫屑,右手臂無紅腫,皮溫正常。予清洗創面,拭干后以標準型水膠體敷料覆蓋。入院第69 天,患兒右手背傷口0.7 cm×0.5 cm,創面基底表面平整,100%紅色,滲液少,濕潤狀態;周圍皮膚部分色素沉著,干燥脫屑,皮溫正常。入院第73 天患兒右手背傷口已完全愈合。創面分階段管理要點為采取保守治療與積極干預相結合,循序漸進地進行綜合管理。前期患兒治療以穩定病情為主,創面采用保守治療,后期病情穩定應用功能性敷料采取清創、降低細菌負荷、滲液管理等“創面床準備”方法處理。功能性敷料可以為創面提供密閉或半密閉濕性環境,能有效控制液體滲出,促使創面角化細胞增多,提高上皮細胞再生能力;其材質利于新生上皮爬行擴展,揭除敷料時不會損傷新生肉芽組織[7]。
2.2.3 減少右上肢腫脹,緩解皮膚干燥 患兒入院第16 天右手臂紅腫較前加重,皮溫高,行腋窩彩超及CT 均見淋巴結腫大,部分膿腫形成,淋巴結活檢考慮免疫缺陷病相關淋巴結改變;抬高患肢,予硼酸溶液濕敷,減輕腫脹,肢體干燥處外涂魚肝油軟膏。入院第25 天患兒右手臂紅腫較前明顯消退,皮溫正常,皮膚干燥脫屑;繼續抬高右上肢,干燥處外涂魚肝油軟膏。患兒四肢其他部位可見多發點狀皮膚破潰化膿,部分已結痂,使用莫匹羅星和10%聚維酮碘乳膏持續外涂,逐漸愈合。
2.3 全身治療
PID 患兒全身治療核心是提高其生存質量,因此對于皮膚感染的治療要求較高。抗感染治療總原則包括:早期識別癥狀,準確定位感染部位,通過影像學、血培養和組化等檢測來確定感染病原[8-9]。本例患兒病程長,遷延不愈,且合并較多基礎病,全身抗感染治療方案根據體溫、病原學結果及感染指標不斷調整。創面管理必須建立在全身治療的基礎上,一項對慢性傷口愈合的影響因素研究[10]也指出,血紅蛋白水平和皮膚狀態是其獨立的預測因子。另外,當營養不能滿足機體需要時,會引起機體免疫功能低下,機體修復和維持自身穩定的能力也隨之下降,傷口不易愈合,皮膚屏障功能減弱,增加了皮膚損傷的風險[11-12]。本例患兒感染重、凝血較差、三系均顯著下降,需在做好氣道護理、全身抗感染,血管活性藥物改善循環、輸注紅細懸液、血小板、免疫球蛋白、人血白蛋白等支持治療的基礎上,不斷評估患兒全身情況。另外,為患兒提供最佳照護應結合最佳證據、患兒及其家屬的意愿以及醫護的經驗能力等。本例患兒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并且有G-6-PD 缺乏癥,在創面管理方案選擇上應考慮患兒經濟因素及疾病因素。
3 小結
本例患兒為1 例免疫缺陷合并膿毒血癥致右手壞疽性膿皰瘡,且合并G-6-PD 缺乏、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等,感染指標高、血液三系低。經過制定符合患兒病情的分階段創面管理方案,保守換藥和清創相結合,遵循預防感染、滲液管理、預防出血等創面處理原則,以及數次清創與功能性敷料換藥,傷口愈合。雖然患兒因基礎疾病預后較差,免疫缺陷使感染難以控制,死亡難以避免,但最終全身面積最大的右手背傷口愈合,治療期間避免了截肢、手術、植皮等更大的有創操作,不僅減輕了患兒痛苦,緩解其臨終不適,也給予家屬一定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