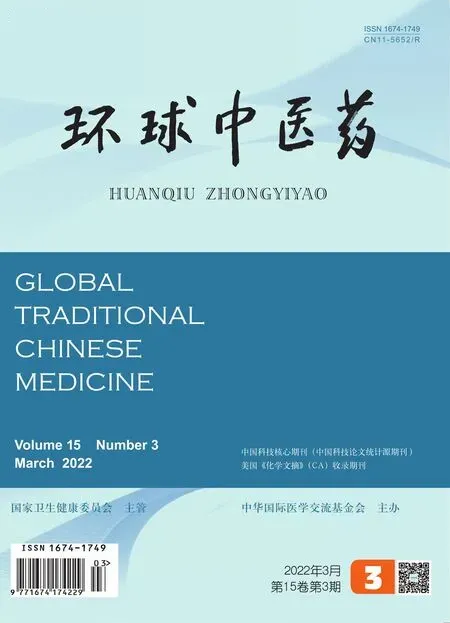丹參酮IIA對免疫細胞的調節作用研究概述
徐連潔 陳文慧 張玉蓉 劉瀟 孟卓然 張珊
T lymphocytes; Regulatory effect
丹參為唇形科植物丹參SalviamiltiorrhizaBunge.的干燥根及根莖,始載于《神農本草經》,具有活血祛瘀、通經止痛、清心除煩、涼血消癰的功效。丹參及其成分可擴張冠狀動脈,預防心肌缺血,改善微循環,減少心肌耗氧,被廣泛用于治療心臟疾病,如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冠心病、心肌病、心律失常等。丹參酮IIA(tanshinone IIA,TIIA)為丹參中活性最突出的脂溶性成分,因其具有多種生物活性而被廣泛研究。這些生物活性包括抗氧化、抗炎、抗血管生成和抗腫瘤等。TIIA對炎癥性疾病、膿毒癥、腫瘤、糖尿病、肥胖等的治療潛力屢見報道。而上述疾病的免疫調節機制日益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并且近年來的國內外研究也顯示TIIA對免疫細胞的發育、激活和功能均有調節作用,可參與先天免疫反應和獲得性免疫反應。本文就TIIA對不同免疫細胞的調節作用進行綜述,并分析其在不同疾病中的作用機制,以期為TIIA的臨床擴展應用和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1 TIIA對中性粒細胞的調節作用研究概況
1.1 中性粒細胞概述
中性粒細胞是先天免疫系統的主要效應細胞之一,來源于骨髓祖細胞,是外周血中數量最多的白細胞,通常也是首先被招募到炎癥部位的白細胞。在正常情況下,中性粒細胞處于未激活狀態,一旦機體發生炎癥反應,骨髓中的中性粒細胞分化、成熟,并釋放到血液中,在多種介質的作用下,激活的中性粒細胞經過邊集、捕捉、滾動、粘附、滲出等復雜過程,向炎癥部位進行趨向性移動[1]。滲出到組織中的中性粒細胞的作用方式主要為吞噬、脫顆粒、生成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以及形成和釋放中性粒細胞胞外誘捕網(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等[2]。
1.2 TIIA通過調節中性粒細胞活性治療炎癥性疾病
Roberston等[3]通過斑馬魚實驗證明了TIIA加速炎癥消退的機制是通過中性粒細胞逆向遷移實現的,而不是減少損傷部位募集的中性粒細胞數量,而這種遷移是TIIA加速了中性粒細胞對其趨化環境敏感性的喪失,而不是通過定向遷移程序將中性粒細胞從炎癥部位趕走,這比單一清除中性粒細胞以達到抗炎目的的干預手段明顯具有優勢。Bernut等[4]也發現,在囊性纖維化跨膜電導調節劑缺失的斑馬魚模型中,過度的氧化反應促使中性粒細胞向傷口募集,而TIIA可以通過誘導中性粒細胞的凋亡并促進中性粒細胞的逆向遷移從而促進炎癥的解決和組織修復。此外,Xu等[5]發現,TIIA可以顯著降低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誘導的小鼠急性肺損傷中肺組織中性粒細胞的浸潤、髓過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活性以及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這些結果表明,TIIA可以通過抑制小鼠炎癥反應來減輕LPS誘導的急性肺損傷。Liu等[6]發現,在人類和小鼠結腸炎中,總是觀察到腸黏膜的顯著中性粒細胞浸潤,包括中性粒細胞穿過腸上皮的遷移、募集、大量ROS的釋放和炎性細胞因子的過度產生。然而,過度或持續的中性粒細胞浸潤是不利的,可導致腸黏膜損傷,腸黏膜損傷又會進一步刺激中性粒細胞的浸潤,從而形成炎癥。因此,組織中性粒細胞的清除對于炎癥的解決和組織穩態的維持至關重要。而在給予TIIA治療的小鼠結腸組織中,中性粒細胞浸潤和活化顯著減少。同時ROS和炎性細胞因子水平降低,這一結果表明TIIA可以改善葡聚糖硫酸鈉誘導的小鼠結腸炎。另外,Zhang等[7]實驗研究發現,在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疾病發生過程中,中性粒細胞滲出血管并聚集到關節部位;NETs可促進瓜氨酸化自身抗原的產生,抗瓜氨酸蛋白抗原導致RA炎癥的持續存在。而TIIA可以抑制中性粒細胞向炎癥部位的遷移、聚集,抑制其活化,并促進活化的中性粒細胞適時凋亡,以促進炎癥的解決;也可以抑制NETs的形成和NETs形成過程中MPO、彈性蛋白酶(neutrophil elastase,NE)的釋放,從而減輕弗氏完全佐劑誘導的RA炎癥反應和組織損傷。
2 TIIA對巨噬細胞的調節作用研究概況
2.1 巨噬細胞概述
巨噬細胞是廣泛分布的先天性免疫細胞,在器官發育、宿主防御、急慢性炎癥、組織穩態等多種生理病理過程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不同的環境條件和特定的病理條件下,巨噬細胞可以通過極化分型發揮不同的生物學作用[8]。巨噬細胞根據表型譜和局部微環境分為兩類:“經典活化”的促炎M1型巨噬細胞和“交替活化”的抗炎M2型巨噬細胞[9]。M1型巨噬細胞通過產生促炎細胞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氧自由基等,促使炎癥反應加重,介導ROS誘導的組織損傷,損害傷口愈合和組織再生。M2型巨噬細胞通過分泌抗炎細胞因子如IL-10、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等可發揮抗炎作用并具備組織修復,參與血管生成和成纖維化等功能[10]。
2.2 TIIA通過調節巨噬細胞極化緩解動脈粥樣硬化
目前研究認為AS的發生是一個慢性的炎癥反應過程,主要為脂質沉積于血管內膜,導致單核細胞募集并被刺激分化為巨噬細胞吞噬脂滴形成泡沫細胞逐漸發展成為粥樣斑塊。因此,巨噬細胞在疾病的進展中起著關鍵作用。Tan等[11]發現,TIIA能顯著增加巨噬細胞源性泡沫細胞ATP結合盒轉運蛋白A1的表達,增加細胞內膽固醇的流出,抑制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ox-LDL)誘導的泡沫細胞的形成。有研究顯示,穩定斑塊組織中主要由M2型巨噬細胞組成,M1在不穩定斑塊中的比例不斷增加,M1與M2型巨噬細胞的比例可以決定病變的嚴重程度和進展[12]。陳萍等[13]研究發現,TIIA可有效誘導AS斑塊中巨噬細胞從M1型向M2型極化的過渡,降低斑塊內的炎癥反應,從而延緩AS化斑塊的進展。同時,他們還發現通過上調p-STAT1/NF-κB信號通路可誘導巨噬細胞向M1型極化,而TIIA可有效激活p-STAT6磷酸化,誘導巨噬細胞向M2型極化,從而降低炎癥反應,提高AS斑塊的穩定性。Chen等[14]研究發現,TIIA可以激活大量M2型巨噬細胞,以減弱M1型巨噬細胞極化引起的炎癥反應,增加抗炎細胞因子的產生,有效地發揮修復和重塑受損組織的作用;TIIA還可以通過miR-375/KLF4途徑協調巨噬細胞自噬和M2極化的相互作用以減輕AS。由此可見,平衡M1和M2型巨噬細胞在AS不同階段的活化水平,可提高AS斑塊的穩定性。Yang等[15]發現,TIIA可以通過下調THP-1巨噬細胞miR-33的表達,抑制ox-LDL誘導的促炎細胞因子的分泌,從而發揮對AS的保護作用。此外,Wang等[16]發現,TIIA可顯著降低ox-LDL誘導的RAW264.7巨噬細胞中基質金屬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MMP-2)和MMP-9的表達水平來逆轉細胞增殖和遷移;還可抑制RAW264.7巨噬細胞中IL-1β、IL-6、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和TNF-α的表達,推測TIIA還可通過調節巨噬細胞中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來防治AS。
3 TIIA對肥大細胞的調節作用研究概況
3.1 肥大細胞概述
肥大細胞廣泛分布于全身的結締組織中,是最早與各種入侵病原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細胞之一,是IgE介導的超敏反應炎癥的主要效應細胞。肥大細胞可被多種刺激物激活,釋放多種生物活性介質(脫顆粒),從而調節機體的免疫應答。這些介質可以大致分為預形成的(儲存在分泌顆粒中,包括胺、蛋白酶、蛋白聚糖、溶酶體酶和細胞因子,如TNF-α和干細胞因子)和從頭合成的介質(包括白三烯、前列腺素、細胞因子、趨化因子、NO和ROS)兩大類[17]。
3.2 TIIA通過調節肥大細胞脫顆粒防治過敏反應
在正常情況下,肥大細胞在組織中保持恒定的數量,在過敏反應的晚期可以觀察到肥大細胞的數量增加,肥大細胞的異常增生和聚集可導致多種疾病[18]。有研究發現,IgE誘導的肥大細胞激活受Sirt1-LKB1-AMPK途徑的負調節,Li等[19]通過體內外實驗研究發現,TIIA可以通過激活Sirt1-LKB1-AMPK途徑,在體外抑制IgE受體(FcεRI)介導的肥大細胞活化,在體內抑制肥大細胞介導的過敏反應,因此TIIA可能成為由肥大細胞介導的過敏性疾病的一個新的藥物。此外,目前認為過敏性鼻炎的發病機制是過敏原誘導的IgE抗體與肥大細胞表面的高親和性FcεRI結合激活肥大細胞,進而誘發細胞內信號級聯反應,所以肥大細胞可能是治療過敏性鼻炎的一個潛在靶點。于是,黃鑠等[20]通過體內、外實驗研究TIIA對肥大細胞介導的過敏性鼻炎的影響,結果顯示,TIIA可以緩解模型小鼠組胺釋放、IgE產生及血管舒張等過敏性鼻炎反應,并抑制肥大細胞的脫顆粒,抑制NF-κB通路的激活下調炎癥因子TNF-α和IL-4的表達,這表明TIIA通過抑制NF-κB通路的激活從而緩解由肥大細胞介導的過敏性鼻炎反應。另外,王文君等[21]采用體外培養的RBL-2H3肥大細胞來研究TIIA對肥大細胞功能的影響,結果顯示,TIIA對肥大細胞增殖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并能明顯促進細胞凋亡,且對RBL-2H3細胞活化脫顆粒有較強的抑制作用,這可能是丹參臨床可用于哮喘和抗過敏治療的原因。有研究發現,氣道上皮的炎癥變化會導致過敏性哮喘,哮喘的特征是免疫細胞浸潤增加,細胞因子水平升高,以及氣道黏膜的結構變化。因此,Heo等[22]用大鼠RBL-2H3肥大細胞研究TIIA對過敏性哮喘的作用,通過體外測定β-己糖胺酶活性來評估抗原誘導的脫顆粒,結果發現,TIIA可以抑制抗原誘導的肥大細胞脫顆粒,這可能有助于TIIA的體內藥效。
4 TIIA對樹突狀細胞的調節作用研究概況
4.1 樹突狀細胞概述
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是功能最強的抗原呈遞細胞,其作用是捕獲來自病原體的抗原,并呈遞至T細胞進行免疫應答[23]。DCs可分為三類:常規樹突狀細胞(cDCs)、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pDCs)和單核細胞衍生樹突狀細胞(moDCs)[24]。在穩定的環境下,由于DCs位于外周組織,缺乏共刺激分子的表達,很少分泌細胞因子,因此是不成熟的抗原提呈細胞。但在粘附分子(CD54、CD58、CD11a/CD18、CD50)、共刺激分子(CD40、CD80、CD86)和抗原提呈分子(MHC I、MHCⅡ、CD1)表達上調、吞噬和抗原處理能力減弱的過程中,DCs逐漸成熟。而成熟的DCs向T淋巴細胞提呈抗原的能力會大大增強[25-27]。
4.2 TIIA通過調節樹突狀細胞成熟防治免疫性疾病
研究發現DCs的抗原呈遞能力及成熟狀態,可直接干預機體的免疫調節,影響機體穩態。成熟的DCs可以誘導并加重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發展,如多發性硬化、RA。因此選擇藥物抑制DCs成熟狀態已經成為改善多種免疫性疾病的突破口。夏金華等[28]發現,TIIA可以通過抑制DCs功能及成熟度,從而影響T細胞分化,導致體內抑炎性因子分泌增多,炎性因子分泌減少,從而起到減緩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作用。最近研究發現,在AS血管中出現大量聚集的成熟DCs,而斑塊中的多種元素可能影響DCs成熟和促炎功能,這表明DCs成熟與AS的進展有關。因此,Li等[29]通過實驗研究發現,TIIA可劑量依賴性地下調共刺激分子(CD86)、粘附分子(CD54)和主要組織相容性因子(HLA-DR)的表達,抑制DCs成熟,減少促炎因子IL-12和IL-1的分泌,同時削弱其刺激T細胞增殖和細胞因子分泌的能力,表明TIIA可能通過抑制DCs介導的獲得性免疫來抑制AS病變的進展。此外,有研究顯示,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的功能可以控制實驗性自身免疫性腦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EAE)反應,而TIIA可以通過驅動DCs中的TGF-β1信號通路來增強Treg細胞的分化,從而有效抑制EAE的進展,并且TIIA治療的EAE小鼠中病理(炎癥和脫髓鞘)的減少與Treg亞群頻率的增加相關。在體外和體內實驗中,TIIA誘導的Treg細胞顯示出與TGF-β1極化Treg細胞相當的有效抑制活性,這表明TIIA作為治療神經炎癥疾病的治療劑可能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30]。由此可見,TIIA可以通過抑制DCs介導的適應性免疫和獲得性免疫來削弱免疫系統疾病的發展過程。
5 TIIA對T淋巴細胞的調節作用研究概況
5.1 T淋巴細胞概述
T細胞及其亞群是機體免疫功能發揮作用的主要載體,可通過分泌細胞因子及信號通路間的相互調節、相互制約而維持機體免疫動態平衡,其按照功能不同可分為細胞毒性T細胞(cytotoxic T cells,Tc)、輔助性T細胞(T helper cells,Th)及Treg。此外,T淋巴細胞根據其表面標志物不同主要分為CD4+T淋巴細胞和CD8+T淋巴細胞兩大亞群,其中CD4+T淋巴細胞是重要的免疫調節細胞,能夠促進B細胞、T淋巴細胞和其他免疫細胞增殖、分化。大多數活化的CD4+T細胞可以刺激細胞因子的聚集,并分泌IL-12、干擾素-γ(immune interferon-γ,IFN-γ)等,最終導致炎癥[31]。CD8+主要存在于Tc及抑制性T細胞(suppressor T cell,Ts)表面,其中Tc主要參與抗病毒免疫、抗腫瘤及抗移植排斥反應,而Ts可通過分泌抑制因子而達到抑制免疫應答活化的作用。
5.2 TIIA通過調節T淋巴細胞參與多種疾病的免疫機制
T淋巴細胞在AS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主要是由于輔助性Th1或Th2細胞分泌的促炎細胞因子。Kang等[32]研究顯示TIIA以劑量依賴的方式顯著抑制Th1細胞IL-12、INF-γ的產生,抑制AS的形成,穩定斑塊。CD40L和CD40相互作用可激活T淋巴細胞表達CD40L,進而促進組織因子和MMPs的表達。Fang等[33]發現,TIIA可使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增強,降低丙二醛水平,從而降低CD40的表達和MMP-2的活性。由此可見,TIIA的抗氧化抗炎作用可能是其治療AS的潛在機制之一。另有證據表明,病毒感染引起的過度活躍的炎癥反應和自身免疫反應已成為病毒性心肌炎(viral myocarditis,VMC)心肌細胞損傷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直接的病毒感染,而Th亞群分泌的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與VMC的發病機制密切相關。因此,調節炎癥反應被認為是VMC的一種潛在治療策略。Guo等[34]研究采用BALB/c小鼠腹腔注射柯薩奇病毒B3株(CVB3)建立VMC動物模型,在給予TIIA治療后發現,TIIA可以通過抑制炎癥和顯著下調小鼠Th1細胞因子的水平,上調Th2細胞因子的表達,即調節Th1/Th2的平衡,從而有效地保護CVB3誘導的心肌炎。另有研究用小鼠卵清蛋白誘導的過敏性哮喘模型測試TIIA的療效,結果發現TIIA可以減少肺部粘蛋白的產生和炎癥,降低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和肺組織中Th2細胞因子(IL-4和IL-13)的表達和分泌,由此可見,TIIA在抑制小鼠過敏特征方面顯示出顯著的功效,由于TIIA對Th2細胞因子有抑制作用,表明TIIA的抗過敏活性源于抗炎作用,這可能為抗過敏療法提供新的證據[22]。Qin等[35]發現,TIIA可提高T淋巴細胞亞群CD3+、CD4+和CD8+的比率,降低炎性細胞因子(IL-2、IL-4、INF-γ和TNF-α)的水平,同時提高抗炎細胞因子IL-10的表達,從而對免疫性肝損傷具有保護作用,因此TIIA可能成為治療肝損傷的潛在候選藥物。此外,Yu等[36]采用大鼠皮膚移植模型,測定TIIA對延長同種異體移植皮存活的作用,發現TIIA可使炎癥細胞向同種異體移植物的浸潤減少,以及受體大鼠外周血中CD4+T細胞和CD8+T細胞的百分比降低,這表明TIIA可作為同種異體移植排斥反應及Th1細胞主導的免疫疾病的新的治療選擇。
6 結論和展望
綜上所述,TIIA可通過調節中性粒細胞的浸潤,促進中性粒細胞的逆向遷移,誘導中性粒細胞的凋亡及抑制NETs的形成對肺部炎癥、結腸炎及RA等炎癥性疾病產生療效;可通過誘導M1、M2型極化,抑制巨噬細胞的增殖,遷移和浸潤,抑制巨噬細胞中的炎性因子的表達來緩解AS形成過程中的炎癥反應;可通過抑制肥大細胞活化,脫顆粒來防治鼻炎、哮喘等過敏性疾病;可通過抑制DCs成熟,降低DCs表面共刺激分子表達及細胞因子分泌等來治療AS及神經炎癥性疾病;可通過調整T細胞亞群的活性及Th1/Th2的平衡來治療AS、VMC、免疫性肝損傷等疾病。因此,探討TIIA對免疫細胞的調節及其在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及機制對其藥理作用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義,為TIIA的進一步擴展應用和開發提供依據。
doitsh G,Greene W C. Dissecting how CD4 T cells are lost during HIV infection[J].Cell Host Microbe, 2016, 19(3):28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