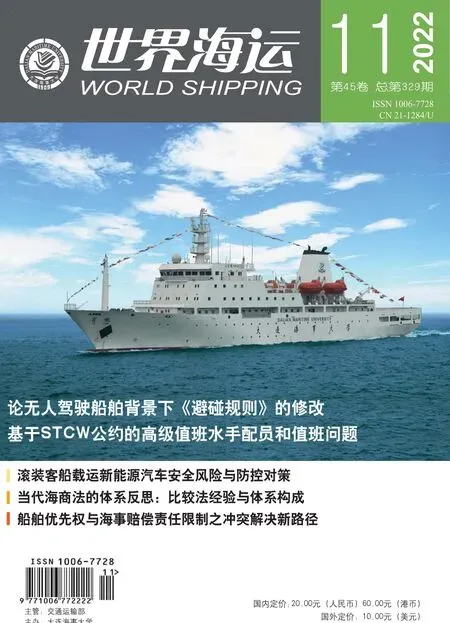包銷模式郵輪旅游的立法完善
——以郵輪旅游中存在的法律關(guān)系為切入點
董澤瑞
一、郵輪旅游包銷模式下的法律關(guān)系爭議
當前,大多數(shù)國家的郵輪旅游經(jīng)營采取郵輪公司直銷船票、旅行社分銷船票和旅游代理商分銷船票三種模式。與此不同,我國郵輪旅游普遍采用的經(jīng)營銷售模式為包銷船票,主要包括包艙和切艙兩種。具體來說,即旅行社要購買郵輪公司相應航次或相應時間下郵輪的全部或部分艙位,再將海上郵輪旅游觀光服務與包括辦理簽證、提供中轉(zhuǎn)運輸、進行岸上觀光旅游在內(nèi)的服務打造成包價旅游產(chǎn)品(package travel product)出售,旅行社的盈利為旅客支付的包價旅游費用與旅游服務成本之間的差價。[1]我國郵輪旅游市場之所以形成此種特殊的郵輪旅游經(jīng)營模式,是因為我國行政法規(guī)對運輸業(yè)務和旅游業(yè)務作了一定限制:在海上旅客運輸方面,經(jīng)營郵輪航線的經(jīng)營人必須具備相應的運營資格;①《國際海運條例》第11條規(guī)定:“國際船舶運輸經(jīng)營者經(jīng)營進出中國港口的國際班輪運輸業(yè)務,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guī)定取得國際班輪運輸經(jīng)營資格。未取得國際班輪運輸經(jīng)營資格的,不得從事國際班輪運輸經(jīng)營活動,不得對外公布班期、接受訂艙。以共同派船、艙位互換、聯(lián)合經(jīng)營等方式經(jīng)營國際班輪運輸?shù)模m用本條第1款的規(guī)定。”在旅游業(yè)務經(jīng)營方面,外籍郵輪公司不能經(jīng)營我國旅客的出境游業(yè)務,無法單獨開展我國居民境外郵輪旅游經(jīng)營活動。
我國郵輪公司要開展出境游業(yè)務,必須獲取出境旅游資質(zhì),即便具備出境游資質(zhì),國內(nèi)郵輪公司一般也會委托其他旅行社銷售船票。在郵輪旅游包銷模式下,旅客、郵輪公司和旅行社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法律關(guān)系。[2]
對于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合同的性質(zhì),學者之間的爭議焦點主要在于“承運人的認定”,形成了“郵輪公司具有承運人的法律地位”和“旅行社具有承運人的法律地位”兩種對立的學術(shù)觀點。[3]前一種觀點認為旅客與郵輪公司成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即旅客同時和旅行社、郵輪公司成立合同關(guān)系;后一種觀點認為旅客只同旅行社成立合同。上述兩種觀點分別被稱為“二元論”和“一元論”。[4]
目前學界占據(jù)主流的觀點是“一元論”,該觀點認為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只存在一個“郵輪旅游合同”,郵輪旅游合同包括海上旅客運輸部分和觀光旅游部分,是混合合同,且在種類上應屬于類型結(jié)合合同。①在合同數(shù)量上,混合合同是由數(shù)個典型或非典型合同的部分內(nèi)容構(gòu)成的合同,屬于一個合同。詳情參見崔建遠:《合同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頁。[5]“一元論”意味著郵輪旅游合同的標的是唯一的,[6]而“二元論”認為旅客、郵輪公司和旅行社三方之間分別存在三個基礎(chǔ)合同:旅客與旅行社之間存在郵輪旅游服務合同,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存在通過船票證明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郵輪公司和旅行社之間訂有郵輪船票包銷合同。[7]
二、郵輪旅游包銷模式下法律關(guān)系的厘清
(一)郵輪旅游包銷模式下法律關(guān)系爭議帶來的現(xiàn)實困境
將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中的郵輪公司認定為旅行社的履行輔助人不應有疑問,但是郵輪公司與旅客之間是否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卻不明確。因此,旅客在海上旅客運輸過程中遭受人身傷亡、財產(chǎn)損失的或者因旅游服務違約遭受損害的,并不能直接向郵輪公司主張賠償責任,即便旅客向其主張賠償責任,郵輪公司也會以自己是“履行輔助人”加以抗辯,導致旅客無法得到賠償,進而采取“霸船”的方式來維權(quán)。[5]如“831量子號霸船”事件,郵輪公司由于擅自變更航線而違約,雖然旅行社與郵輪公司簽有代理協(xié)議,但是旅客并不知曉該協(xié)議的內(nèi)容及具體的責任劃分,加之郵輪公司和旅行社的法律地位不明確、同旅客簽訂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主體是旅行社等現(xiàn)實情況,就導致在出現(xiàn)問題時旅客只能向旅行社尋求解決。旅行社則認為,自己無法干涉郵輪公司變更航線的決定,而只能向郵輪公司推諉責任,旅客覺得自己的權(quán)益受到侵害卻又無人負責,因此選擇了一種極端的維權(quán)手段。
在以運輸為目的的傳統(tǒng)海上旅客運輸下,旅客自登船到離船的時間段屬于承運人的責任期間并無爭議,因為旅客離船時便完成了行程,離船后不會再返回客船。但是,傳統(tǒng)的承運人責任期間并不適用郵輪旅游下的海上旅客運輸,因為旅客通常會在掛靠港下船游玩或者購物,而待郵輪啟航時重新登船。旅客也可能會因其他緊急事件離船,比如下船就醫(yī),現(xiàn)實當中就出現(xiàn)了旅客在船上發(fā)病,但因郵輪上醫(yī)療資源有限被迫送往岸上醫(yī)院救治而產(chǎn)生的責任期間認定糾紛。②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滬01民終10447號民事判決書。再者,關(guān)于旅客在岸上游玩的期間是否歸屬為承運人的責任期間也存有爭議。
在郵輪旅游的實踐安排中,各旅行社在開展業(yè)務時需要同旅客簽訂郵輪旅游服務合同,③郵輪旅游服務合同中必須附有出團通知、行程說明和安全須知等規(guī)定。旅行社應根據(jù)合同的約定滿足旅客所需要的旅游服務。[8]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的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由旅行社在包銷船票時同旅客一并簽訂,根據(jù)《上海市郵輪旅游經(jīng)營規(guī)范》(以下簡稱《規(guī)范》)第13條第1款可知,旅客在同旅行社簽訂合同后獲取包價旅游服務。④《規(guī)范》第13條第1款規(guī)定:“旅行社將郵輪船票和岸上觀光服務打包成包價旅游產(chǎn)品向旅游者銷售的,應當與旅游者簽訂郵輪旅游合同,并提供船票。”同時,《規(guī)范》規(guī)定了郵輪公司和旅行社成立的郵輪船票包銷合同在性質(zhì)上應認定為“銷售、代理合同”,即郵輪公司和旅行社存在委托代理關(guān)系,但當船票銷售同時包括岸上旅游服務內(nèi)容時,二者則不存在委托代理關(guān)系。筆者認為該認定標準存有不足,因為此種認定標準是“旅行社銷售的郵輪旅游產(chǎn)品是否包括岸上旅游服務項目”,忽略了以委托代理為基礎(chǔ)的代銷船票合同和特殊的包銷船票合同在合同內(nèi)容、合同性質(zhì)方面均存在差異。盡管《規(guī)范》對于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認定標準存在不足,但是其對于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法律關(guān)系的確定毋庸置疑,即旅行社與旅客和郵輪公司分別成立郵輪旅游服務合同和郵輪船票包銷合同。需要明確的問題是,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是否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如果存在,該合同主體如何認定?
(二)郵輪旅游包銷模式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證成
1.“登船憑證”的法律功能
我國《海商法》雖然并未明確船票的定義,①《海商法》第110條規(guī)定:“旅客客票是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憑證。”《民法典》第293條規(guī)定:“客運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但賦予了船票“證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功能,上海首次規(guī)定了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的“登船憑證”制度,旅客在進港、登船時必須持有“登船憑證”。此處的“登船憑證”是否同船票一致,具有“證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功能?有觀點認為不能將“登船憑證”看成船票,因為其僅賦予了旅客“持證登船”的權(quán)利,而并不具有船票的法律功能。[9]但是,旅客與郵輪公司是否成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應當依據(jù)合同體現(xiàn)的具體特征即包含的權(quán)利義務加以判斷,重點考察是否符合《海商法》下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7]根據(jù)登船憑證具有的“有權(quán)登船”功能可知,旅客持有“登船憑證”便有權(quán)上船、享受船上服務,“有權(quán)登船”實質(zhì)是船票具有合同成立證明功能的體現(xiàn),“登船憑證”的法律功能同船票一致,是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證明。即便“登船憑證”不能被認定為一般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下的船票,也不影響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海上旅客運輸合同關(guān)系的確立。
有觀點認為,“登船憑證之所以不是船票,是因為郵輪船票由承運人簽發(fā)出具,而登船憑證由郵輪公司簽發(fā)出具”[10]。此種觀點混淆了前提與結(jié)論,把“郵輪公司不是承運人”的結(jié)論作為論證前提。同時,有觀點認為,“旅客付款義務的履行對象已經(jīng)變?yōu)槁眯猩缍青]輪公司,郵輪船票已經(jīng)無法滿足證明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作用”[4]。筆者認為,盡管旅客與郵輪公司不直接締結(jié)合同——旅客給付對價的主體為旅行社、接受郵輪公司提供艙位的主體為旅行社,但是并不影響旅客同郵輪公司成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因為,在相類似的存在航空運輸?shù)陌鼉r旅游合同中,旅客給付對價款項的對象同樣是旅行社而非運輸方,但旅客與航空公司成立旅客運輸合同并無疑問,參考我國的司法實務可知,在發(fā)生包價旅游糾紛時,旅客有權(quán)向航空公司直接主張相關(guān)的權(quán)利,②參見(2015)南揚商初字第610號、(2017)滬01民終7067號、(2017)津02民終6908號、(2018)粵01民終15012號、(2019)粵0111民初20487號、(2020)京0105民初45554號、(2020)晉0105民初2723號、(2022)遼02民終4584號、(2022)遼02民終4584號等民事判決書。這體現(xiàn)了包價旅游的特征:總價支付。在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中,旅行社所交付的預付款項可以看成是其提前為旅客支付的旅游費用,郵輪公司接受了該預付款項就意味著要為旅行社所安排的旅客提供海上旅客運輸服務和旅游觀光服務。不同于一般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締結(jié)者與實際接受運輸服務的主體是相分離的。[1]
2.郵輪公司的承運人地位
有觀點認為,“在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中,郵輪運輸支撐整個郵輪旅游合同的履行,不同于普通旅游合同項下的運輸服務,郵輪旅游中的海上旅客運輸服務并不處于輔助地位。因此,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不存在單獨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6]。對此觀點,筆者認為,在郵輪旅游中,郵輪運輸確實不處于輔助地位,但旅客所享受的海上旅客運輸服務、郵輪休閑娛樂服務與岸上游服務是涇渭分明的,這兩類服務的提供主體也不同。前者是郵輪公司以及郵輪上的個體經(jīng)營者,后者是旅行社或旅行社安排的地接社,③我國《旅游法》第115條第5款對地接社的定義是“接受組團社委托,在目的地接待旅游者的旅行社”。從責任承擔方面來看,即使是地接社負責旅客岸上游部分,旅客也可直接要求旅行社承擔責任。因為郵輪船票很少會涉及岸上觀光旅游服務,加上旅客對地域的陌生和語言交流的不便,旅客也很少會選擇單獨進行岸上觀光旅游,岸上觀光旅游項目大多是由旅行社圍繞停泊港來組織、設計的旅游產(chǎn)品。
有觀點主張,“作為郵輪旅游服務的實際提供者,郵輪公司基于《海商法》或《1974年雅典公約》的規(guī)定也可以成為實際承運人”[4]。郵輪公司同時是承運人和實際承運人的觀點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實際承運人制度的“誕生”是為了解決轉(zhuǎn)船運輸過程中出現(xiàn)的運輸合同下的承運人與實際從事運輸?shù)闹黧w不同的難題,從而解決承運人承租船舶運輸?shù)膯栴}。當合同中約定的承運人與實際從事運輸?shù)某羞\人為同一主體時,實際承運人將喪失法律意義從而失去存在的必要。
綜上可知,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且合同雙方是旅客和郵輪公司,因此,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存在三個合同:郵輪旅游服務合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及郵輪船票包銷合同。郵輪旅游服務合同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在法律關(guān)系方面既各自獨立又存在關(guān)聯(lián),郵輪公司和旅客單獨成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同時,郵輪公司是郵輪旅游服務合同下旅行社的履行輔助人。[11]而郵輪船票包銷合同在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中作為連接旅客與郵輪公司的“橋梁”,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討論,探究其法律性質(zhì),從而完善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中關(guān)于此合同部分的立法。
(三)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利他合同法律性質(zhì)
在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中,通過郵輪船票包銷合同,旅行社有權(quán)請求郵輪公司向旅客履行特定郵輪航次下的旅游服務,旅行社行使的該權(quán)利在性質(zhì)上屬于請求權(quán)而非物權(quán)。[12]在郵輪旅游過程中,游客會使用郵輪配套的健身、娛樂設施進行娛樂活動,旅客在體驗娛樂活動時僅能依靠郵輪上的經(jīng)營者履行義務來實現(xiàn),在對方拒絕履行義務時,旅客有權(quán)向其主張違約責任,而不能像租賃合同、買賣合同那樣,請求對方移轉(zhuǎn)交付來實現(xiàn)對標的物的占有、使用。因此,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權(quán)利基礎(chǔ)是請求權(quán),[1]該請求權(quán)主要是針對郵輪艙位的給付使用,且需要借助海上旅客運輸服務給付、郵輪上觀光娛樂服務給付和岸上觀光娛樂服務給付等服務給付實現(xiàn)。
在美國聯(lián)邦密蘇里州法院審理的Stafford v.Intrav,Inc.一案中,①See Stafford v.Intrav,Inc,841 F.Supp.284(1994).法院認為,旅行社承租郵輪的,如果合同雙方在包(切)艙合同中沒有約定“對船舶進行管理、經(jīng)營與控制”等事項,且雙方實際從事的活動也未背離上述約定事項的,那么雙方不存在“光船租賃”的法律關(guān)系,也就不存在旅行社對郵輪經(jīng)營的實質(zhì)管理,②See Le Tran v.Celebrity Cruises,Inc.[2013]WL.雙方構(gòu)成獨立合同人關(guān)系。可以看出,在美國法下,光船租賃與其他類型的租船分類明確,而且雙方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也有不同,因此,美國法下將類似于我國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的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看作具有利他合同性質(zhì)的運輸合同。[13]
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符合為第三人利益,旅行社與郵輪公司成立郵輪船票包銷合同后,旅行社享有了郵輪艙位的給付使用請求權(quán)以及其他綜合服務請求權(quán),郵輪公司則作為義務履行主體,因此旅行社與郵輪公司存在債權(quán)債務關(guān)系。在郵輪公司與旅客之間,郵輪公司是在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基礎(chǔ)上向第三人旅客履行協(xié)議內(nèi)容,這種關(guān)系稱為債務承擔關(guān)系。
在實踐當中,旅行社與郵輪公司簽訂的船票包銷合同被稱為“郵輪船票銷售協(xié)議”,在該協(xié)議下,旅行社負責銷售郵輪公司的艙位,郵輪公司通過收取旅行社的訂金獲利,但是自負空艙的風險。在形式上看,該合同的內(nèi)容是旅行社為郵輪公司處理郵輪艙位售賣的事務,郵輪公司委托旅行社銷售船票、進行宣傳招攬旅客、開展郵輪旅游業(yè)務;在法律后果上看,旅客最終取得了對郵輪公司的郵輪艙位給付使用請求權(quán)以及其他綜合服務請求權(quán),從而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
三、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立法完善
為了提高交易效率、鼓勵包銷模式郵輪旅游的發(fā)展,應制定郵輪船票包銷的標準格式合同。這一方面有利于郵輪公司船票銷售的規(guī)范化,促進包銷模式郵輪旅游的規(guī)范化發(fā)展;[14]另一方面,能夠明確旅客在船票包銷合同下享有的權(quán)利,有利于解決甚至減少包銷模式下郵輪旅游的糾紛爭議。同時,在法律規(guī)范的配置方面,規(guī)制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法律規(guī)范應包括倡導性規(guī)范和授權(quán)性規(guī)范。③合同法下所調(diào)整的利益關(guān)系包括合同一方當事人與合同相對方之間的利益關(guān)系、合同雙方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利益關(guān)系、合同當事人與國家間的利益關(guān)系以及合同當事人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guān)系,以上四種利益關(guān)系分別對應的法律規(guī)范類型為任意性規(guī)范、倡導性規(guī)范、授權(quán)性規(guī)范(授權(quán)第三人的法律規(guī)范)、強制性規(guī)范。
(一)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倡導性規(guī)范
倡導性規(guī)范雖然在對交易當事人利益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中處于次要地位,但其具有提示風險的功能。[15]關(guān)于郵輪船票包銷格式合同的倡導性規(guī)范可以直接借鑒《規(guī)范》第12條,①《規(guī)范》第12條規(guī)定,郵輪公司與旅行社、國際船舶代理企業(yè)應當就郵輪船票銷售、代理簽訂書面合同,并對以下涉及旅游者權(quán)益的事項作出明確約定:(一)因不可抗力導致的航程變更、取消后的風險分擔標準;(二)發(fā)生違約或者給旅游者造成人身損害、財產(chǎn)損失情形的責任分擔;(三)糾紛解決方式;(四)向旅游者提供中文文本的船票、服務說明等資料的責任人;(五)其他與旅游者權(quán)益相關(guān)的事項。但需將其第1款中“應當就郵輪船票銷售、代理簽訂書面合同”改為“應當就郵輪船票包銷合同”;而關(guān)于郵輪船票銷售的法律規(guī)范則可以直接借鑒《規(guī)范》第10條。②《規(guī)范》第10條規(guī)定:郵輪公司在國內(nèi)設立的船務公司可以直接銷售郵輪船票,也可以委托有資質(zhì)的旅行社和國際船舶代理企業(yè)銷售郵輪船票。郵輪公司應當對外公布船票銷售指導價。同時,可以嘗試規(guī)定允許郵輪船票直銷的法律規(guī)范,允許旅客與具有直銷船票資格的郵輪公司締結(jié)郵輪旅游合同,避開旅行社這一民事主體,從而避免復雜的民事法律關(guān)系。
(二)郵輪船票包銷合同的授權(quán)性規(guī)范
民法所調(diào)整的交易主體間的利益關(guān)系,也包括交易關(guān)系當事人與交易關(guān)系外第三人間的利益關(guān)系,對此種類型利益關(guān)系進行調(diào)整的,需要借助授權(quán)第三人規(guī)范。[15]作為具有利他合同性質(zhì)的郵輪船票包銷合同,應受授權(quán)性規(guī)范的規(guī)制,保障旅客作為利益第三人享有的權(quán)利,即明確旅客在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下請求履行海上旅客運輸服務的權(quán)利、請求履行郵輪上觀光娛樂服務和岸上觀光娛樂服務的權(quán)利。同時,可以考慮為旅客設定必要的附隨義務,比如旅客應聽從旅行社或郵輪公司合理指示安排、履行個人必要信息報備等有利于郵輪旅游順利進行的義務。再者,郵輪船票包銷合同作為真正的利他合同,要賦予旅客直接請求郵輪公司承擔違約責任的“訴權(quán)”,以妥善解決郵輪旅游糾紛的訴訟主體問題。
四、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立法完善
(一)借鑒《規(guī)范》中的立法經(jīng)驗
《規(guī)范》作為地方政府規(guī)章,不具有法律適用的效力位階,不能作為解決郵輪旅游糾紛的法律依據(jù),但其對我國郵輪旅游的立法存在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借鑒其相關(guān)規(guī)定完善郵輪旅游法律規(guī)范的設立。[11]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立法是對現(xiàn)實迫切需求的回應,也是《海商法》對海上旅客運輸章節(jié)完善的需要,更是我國郵輪旅游法律制度確立、完善的需要。在立法方面,可以借鑒《規(guī)范》中的立法經(jīng)驗,明確郵輪旅游中海上旅客運輸部分能適用《海商法》海上旅客運輸章節(jié)。[16]詳言之,《海商法》海上旅客運輸章節(jié)對承運人、實際承運人在履行義務、承擔責任、享有免責事由和賠償責任限制權(quán)利等方面的規(guī)定,對郵輪旅游中的郵輪所有人、經(jīng)營人或承租人等主體也同樣適用。
由于《民法典》的編纂并沒有增加旅游合同部分,在對《海商法》進行修改時就需要對相應的旅游法律制度予以補充完善,以保證郵輪旅游法律制度的準確性和圓滿性。
(二)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法律規(guī)范配置
1.相關(guān)定義規(guī)范的明確
首先要明確“郵輪旅游”的概念,可以參考《規(guī)范》中郵輪旅游的定義,但是要做相應的修改予以完善。在郵輪旅游中,旅客的旅游場所和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僅限于郵輪,所以應將船舶限定為“主要的旅游場所和交通工具”。隨著郵輪旅游的發(fā)展,在未來旅游市場,郵輪旅游不僅僅只包括“出境游”,也會包括“沿海游”。[17]郵輪旅游所涵蓋的類型應有所擴大,同時兼具旅游與運輸。但在旅客運輸方面,不同于一般海上旅客運輸下實現(xiàn)旅客的海上位移,而在于向旅客提供海上旅游休閑一體化服務,絕大多數(shù)郵輪會在航程結(jié)束后返回到始發(fā)港,郵輪始發(fā)港和目的港相同。因此,在立法上也要明確郵輪旅游中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定義,筆者將在下文對此部分進行詳細討論。
岸上觀光活動也是郵輪旅游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該活動必須由旅客同旅行社在郵輪旅游服務合同中明確約定,因為當事人未事先約定的,岸上觀光活動作為獨立的旅游活動是與郵輪旅游相分離的。岸上觀光活動不僅要與海上旅客運輸服務和郵輪旅游觀光服務活動有時間上的銜接性,而且必須同其構(gòu)成包價旅游產(chǎn)品。因此,關(guān)于郵輪旅游的法律定義,可以直接借鑒《規(guī)范》第2條,①《規(guī)范》第2條規(guī)定:本規(guī)范所稱郵輪旅游是指以海上船舶為旅游目的地和交通工具,為旅客提供海上游覽、住宿、交通、餐飲、娛樂或到岸觀光等多種服務的出境旅游方式。但應做一定的改動,將“旅游目的地和交通工具”限定為“主要的”,將“出境旅游方式”改為“旅游活動”,并且將“岸上觀光”的定義明確為旅客在登船前或者在離船期間所參加的旅游觀光活動。
2.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強制性規(guī)范
對交易關(guān)系背景下民事主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調(diào)整,要依靠強制性規(guī)范。[15]在規(guī)定郵輪旅游服務合同強制性規(guī)范時,應規(guī)定旅行社、郵輪公司及旅客各自需要承擔的義務性規(guī)范。在規(guī)范郵輪旅游服務合同內(nèi)容時,不僅要考慮到一般旅游具有的因素,也要考慮郵輪旅游所具有的特殊海上因素:一般因素包括旅行社和旅游經(jīng)營者的告知事項,特殊海上因素包括旅行社、郵輪公司對旅客的賠償責任限制事項。
旅行社對旅客履行告知事項的義務規(guī)定見于《旅游法》第62條,而郵輪旅游下郵輪公司的告知義務卻不明確,因此在完善立法時,應關(guān)注郵輪公司的告知義務。關(guān)于郵輪公司告知事項和旅行社特殊告知事項的具體規(guī)定,可以借鑒《規(guī)范》第14條的規(guī)定。關(guān)于旅行社責任限制賠償?shù)囊?guī)定應考慮旅客所受損害的原因,當旅客所受損害是承運人原因?qū)е聲r,旅行社才可能承擔先付責任,從而有權(quán)援引賠償責任限制。關(guān)于郵輪公司責任限制賠償?shù)囊?guī)定,筆者將在下文詳細展開。
除了明確旅行社、郵輪公司的積極義務外,同時也應明確旅行社和郵輪公司的消極義務,即規(guī)定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禁止性規(guī)范,具體包括:不得強制旅客選擇旅游產(chǎn)品,不得對旅客進行捆綁消費,不得以任何形式的約定免除或降低自身應對旅客負有的保障義務和免除或降低因自身原因?qū)β每偷娜松怼⒇敭a(chǎn)造成的損害。
如前文所述,“登船憑證”可以作為海上運輸合同的憑證,在立法過程中,要明確其性質(zhì),建立正式的郵輪船票制度,落實旅客憑船票登船、享受郵輪旅游活動。對于旅客來說,除了前文所述應規(guī)定旅客的附隨義務外,也有必要規(guī)定旅客憑票登船的義務。船票應當包括紙質(zhì)票和電子票,明確包括船票在內(nèi)的郵輪旅游產(chǎn)品,并且對外界公布,保證旅客的知情權(quán)和選擇自由。
五、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立法完善
(一)《海商法》第5章對郵輪旅游規(guī)制的不足
郵輪運輸雖不同于傳統(tǒng)海上旅客運輸,但并未改變其海上運輸?shù)膶嵸|(zhì),郵輪作為航行于海上的船舶仍然要受海上特有風險的制約。[18]郵輪旅游利用海上的空間位移為旅客提供旅游休閑的愉悅和感受,其旅游必須通過運輸來實現(xiàn),其納入《海商法》項下調(diào)整應屬必要。[4]但是,與純粹的海上旅客運輸相比,郵輪旅游存在明顯的不同,僅適用于調(diào)整海上旅客運輸?shù)姆梢矡o法適用調(diào)整郵輪旅游活動,因為《海商法》第5章重點調(diào)整的是運輸行為,規(guī)定了承運人對旅客及其行李損害的賠償責任。郵輪旅游具有的旅游、運輸特點,勢必要求郵輪旅游配備特殊的法律規(guī)范,郵輪公司向旅客提供的服務不僅僅局限于海上旅客運輸下的服務,僅僅賦予其承運人的法律地位要求其接受海上旅客運輸相關(guān)法律規(guī)范的調(diào)整不能滿足現(xiàn)實需要。
(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法律規(guī)范配置
郵輪與一般的客輪相比,旅客人數(shù)更多,海上行程更長,旅客進行的活動更豐富,會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因此,對船醫(yī)和醫(yī)療器械的需求可以說是關(guān)乎旅客人身安全的重大問題。然而,無論是目前的國際公約,②《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在其“標準A4.1”中規(guī)定:載員100人或以上,通常從事3天以上國際航行的船舶應配備一名醫(yī)生負責提供醫(yī)療。國家法律或條例還應考慮到諸如航行的時間、性質(zhì)和條件以及船上船員人數(shù)等因素,規(guī)定哪些其他船舶也應要求配備一名醫(yī)生。其他海事國際公約也有類似規(guī)定,但筆者認為,對于郵輪來說其載員明顯超過了100人,而且旅游航程也遠遠多于3天,因此對其理應提出更高的配員要求。還是我國行政管理方面,均未明確郵輪要配備適量、具有資質(zhì)的船醫(yī)。③我國交通部在1990年發(fā)布的《船醫(yī)管理辦法》規(guī)定:“遠洋貨(油)船應設船醫(yī)一名;遠洋客船應設船醫(yī)、護士各一名;沿海客船和流動性大的大型施工船、救助船應設船醫(yī)一名;內(nèi)河800客位以上單航次超過24小時的客船應設船醫(yī)一名;旅游船應設船醫(yī)一名。”該規(guī)定的內(nèi)容顯然并不能直接適用于大型郵輪的情況,且該規(guī)定已被廢止。在立法層面,需要將郵輪承運人配備適量、具有資質(zhì)的船醫(yī)作為其重要義務,將該義務法定化,也符合郵輪旅游的現(xiàn)實需求。
郵輪旅游服務合同所涉及的“海上旅客運輸”部分法律規(guī)范主要涉及以下內(nèi)容:
明確其海上旅客運輸航程較一般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下航程的不同,可以在《海商法》第107條關(guān)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定義的基礎(chǔ)上稍做修改,增加郵輪旅游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定義,只需將原文中的“從一港運至另一港”改為“從起運點運至約定地點”。這也解決了“郵輪旅游是否能夠基于其運輸屬性而當然適用《海商法》第5章”的爭議,使“同港往返”下的郵輪旅游不再因形式要素而被否定適用《海商法》第5章。條款中“適合運送旅客的船舶”是郵輪的,還應當配置一定數(shù)量的具有資質(zhì)的船醫(yī)。
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中,判定合同何時成立,應以承運人向旅客給付船票的時間為標準,這也是船票具有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證明功能的應有之義。其次,為體現(xiàn)契約自由原則,旅客和承運人可以自由協(xié)商有關(guān)合同的成立時間。再者,行業(yè)之間、郵輪公司和旅客之間為了業(yè)務方便可能已形成了相關(guān)商業(yè)習慣,要對相關(guān)交易習慣予以尊重。因此,可以增加關(guān)于船票證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規(guī)定: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交易習慣的除外。
如上文所述,旅客在岸上觀光旅游時并不受承運人的實際管控,因此該段時間也就不能歸為承運人的責任期間,應當予以排除。在郵輪旅游下,旅客除了因岸上旅游觀光離船外,也可能會因其他事件離船,比如下船就醫(yī)。旅客在離船登岸進行觀光娛樂服務時,可能會隨身攜帶部分行李,如果該部分行李在此期間內(nèi)發(fā)生毀損、滅失,承運人不再負賠償責任,但是對于仍放置在船艙內(nèi)的行李,承運人仍負有責任。
關(guān)于郵輪公司的承運人責任期間條文,應在《海商法》第111條的基礎(chǔ)上予以完善修改,在該條第1款“自旅客登船時起至旅客離船時止”后增加“不包括旅客中途離船的期間”規(guī)定;同時,承運人對于旅客行李的責任期間也要完善,要在該條第2款后增加“包括旅客中途離船而自帶行李仍放置在船艙內(nèi)的時間”。
關(guān)于郵輪海上運輸航程變更的事項并未規(guī)定在《海商法》下,但是在郵輪旅游中卻出現(xiàn)了大量因航程變更而導致的訴訟糾紛,航程變更涉及的主要問題在于郵輪公司和旅行社的責任承擔,特別是在何種情形下可因符合不可抗力等免責事由而不必承擔責任,以及相應的告知、費用退還等隨附義務。[19]筆者認為,在我國法律體系下,郵輪旅游下的航程變更應受《旅游法》和《海商法》調(diào)整,《旅游法》下當旅游行程由于不可抗力等因素變更時,旅行社有權(quán)減輕或免除責任,但是應當告知旅客相關(guān)行程變更原因并且退還旅客相應的旅游費用;而在《海商法》下,卻沒有關(guān)于海上旅客運輸航程變更的規(guī)定。關(guān)于郵輪旅游下海上運輸航程變更的具體規(guī)定可以借鑒《規(guī)范》第16條、第17條規(guī)定。
六、結(jié)語
在我國,郵輪旅游主要以包銷模式的經(jīng)營方式存在,但是,學術(shù)界對包銷模式郵輪旅游的法律關(guān)系存在爭議,爭議焦點主要是: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下是否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若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合同主體如何認定?通過對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下“登船憑證”法律功能和郵輪公司具有的承運人法律地位的論證,可認定包銷模式郵輪旅游下存在三個合同:郵輪船票包銷合同、郵輪旅游服務合同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且郵輪船票包銷合同具有利他合同的法律性質(zhì)。在明確包銷模式郵輪旅游法律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我國郵輪旅游所涉三個合同立法完善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