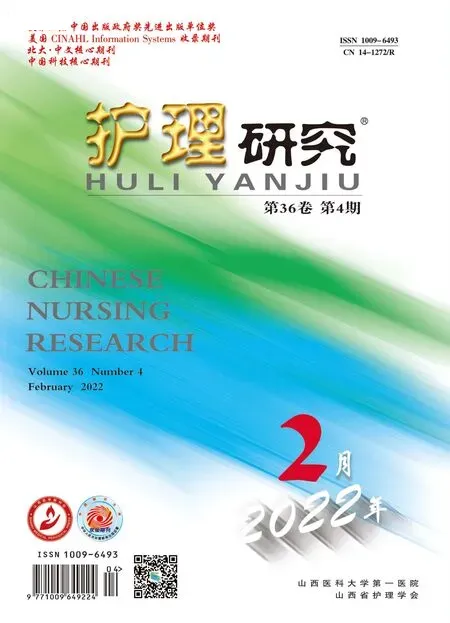癌癥病人創傷后成長縱向研究進展
宋媛媛,蔣曉蓮
四川大學華西護理學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四川 610041
癌癥是全球關注的公共健康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發布的最新研究數據顯示,2020 年全球約有1 929 萬人被診斷為癌癥,996 萬人因癌癥死亡[1]。診斷為癌癥、手術創傷、放化療導致的不良反應、經濟方面的沉重負擔、對預后的擔憂和不確定感等給病人帶來巨大的疾病創傷,影響其心理調適,降低其生活質量[2-4]。研究表明,關注癌癥病人的心理反應對于幫助病人應對疾病、回歸社會、重塑積極健康生活、提升其伴癌生存的生活質量有確切價值[5-7]。近年來,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關注癌癥病人所體驗到的積極變化,如創傷后成長(post traumatic growth,PTG)。較多證據發現,PTG 與癌癥病人的成功應對、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相關[8-11]。此外,對于癌癥病人來說,關注他們與疾病抗爭過程中的潛在資源和積極力量,挖掘個體及社會資源來幫助其成長,提高其伴癌生存的能力和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也為醫務人員開展相關心理干預提供了新視角。癌癥病人PTG 相關研究包括橫斷面研究、縱向研究、質性研究和干預研究。根據Tedeschi 等[12]提出的PTG 模型,PTG 并不是一個靜態結果,而是隨著創傷事件、時間等動態改變的過程。因此,目前使用最多的橫斷面調查研究可能難以發現PTG 的變化規律,縱向研究設計對于全面、深入了解個體的PTG 發展變化情況有著重要作用。對于癌癥病人來說,了解他們的PTG 變化規律可為重要的干預時間節點的選擇提供依據,形成更精準、高效、科學的干預方案。本研究圍繞PTG 相關概念、國內外相關縱向研究的研究對象特點、PTG 評估工具、資料分析方法、PTG 變化趨勢與測量時間點選取、PTG 產生與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以期為今后開展PTG 縱向研究及相關干預提供依據。
1 PTG 相關概念
1.1 創傷事件 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制定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 版,創傷事件是指直接經歷、目睹或聽聞涉及實際或威脅死亡或嚴重傷害的事件[13]。Calhoun 等[14]對創傷事件有更廣泛的定義,他們認為不是事件本身定義了創傷,而是它對圖式的影響,促使圖式重建。創傷事件不一定是危及生命的,而是一種高度緊張的、具有挑戰性的重大生活危機事件。他們關注的是事件后引起的根本性、變革性的改變,這一事件需要足夠重要,足以挑戰關于一個人的未來以及如何走向未來的基本假設,從而產生難以控制的巨大焦慮和精神痛苦。這些創傷經歷會使人失去所愛的人、失去珍視的角色或能力。在研究早期,創傷事件多是針對自然災害、意外傷害等,近年來,疾病創傷相關研究大量涌現,以癌癥人群為主。
1.2 PTG PTG 最 早 由Tedeschi 等[15]于1995 年 提出,被定義為個體在與創傷事件或情境進行抗爭后所體驗到的積極心理改變[12,16]。PTG 的概念是基于建構主義觀點,即人們創造了個體版本的用于理解經驗的基本認知范疇,以及關于自我、未來和世界的核心信念[17]。此外,PTG 的概念還受益于哲學和心理學中廣泛的存在主義傳統,這種傳統提供了一種關于苦難問題和一般人生哲學的視角,指導人們賦予事件和行動意義[18]。Tedeschi 等[12]認為PTG 可以表現在各個方面,如對生活的欣賞增加、人際關系改變、個人力量感增強、重要事物優先次序改變以及精神生活更加豐富。PTG 并不是創傷事件本身產生的,而是個體與創傷事件斗爭的結果。斗爭一開始并不是為了成長或改變,而是為了生存或應對。但是對這些個體而言,他們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經歷了意義深遠的變化,這是一種無計劃的、意想不到的情緒、認知或行為上的變化[16],他們的心理功能水平超越了危機發生之前[12,19]。除了成長或智慧建設,PTG 還會使個體做好準備或有韌性去面對未來可能的創傷事件。重要的是,痛苦是成長發生的必要條件,只有事件足夠有挑戰性或產生巨大影響,才能啟動成長所必需的認知處理機制。因此,持續的個人痛苦和積極成長往往并存。
2 癌癥病人PTG 縱向研究現狀
2.1 研究對象特點 癌癥病人PTG 縱向追蹤研究多以乳腺癌病人[11,20-28]為研究對象,還有研究以青少年和青年癌癥病人[29-31]、結直腸癌病人[32]、肝癌病人[33]、肺癌病人[34]、頭頸癌病人[35]、卵巢癌病人[36]等為研究對象。除單一疾病人群,還有研究納入混合人群,如結直腸癌病人與肺癌病人[37]、乳腺癌病人與前列腺癌病人[38]、乳腺癌病人與黑色素瘤病人[39]、乳腺癌病人和胃腸癌病人[40]。有些研究不僅考慮了癌癥病人本身情況,還納入了病人配偶或照顧者進行分析[23,33]。大部分研究是以治療期間的癌癥病人為研究對象,還有研究納入的是結束治療的康復期病人[20,26,31-32,41]和臨終的晚期癌癥病人[42]。
2.2 PTG 評估工具 癌癥病人PTG 縱向研究中使用到的PTG 評估工具不盡相同,其中使用最廣泛的是Tedeschi 等[43]于1996 年 編 制 的PTG 評 定 量 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包括新的可能性、與他人關系、個人力量、對生命的欣賞以及精神變化5 個維度,共21 個條目,量表信效度良好,目前已有中文版、西班牙語版、日語版、荷蘭語版等多種語言版本[44-49]。其他縱向研究采用了慢性病治療功能評估-靈性量表-12(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12,FACIT-Sp-12)、一線希望問卷-38(The Silver Lining Questionnaire,SLQ-38)和益處發現量表(The Benefit Finding Scale,BFS)評估癌癥病人PTG發展變化情況。FACIT-Sp-12由Davis 等[36]開發,用于評估慢性病病人靈性成長和生活質量,包括意義、平和、信念3 個維度,共12 個條目[50]。SLQ-38 由 英 國 學 者Sodergren 等[51-52]編 制,包 含38 個條目,主要測量病人疾病獲益的內容和程度。BFS 是美國學者Antoni 等[53]于2001 年編制,單維度,17 個條目,主要用于測量乳腺癌病人在獲知診斷和治療后的益處發現水平,之后也被用于其他癌癥人群和癌癥照顧者。以上3 個量表均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心理學測量性能良好。
2.3 相關資料分析方法 癌癥病人PTG 縱向研究使用到的資料分析方法主要有t檢驗[30,36,40,54]、方差分析[21,26-28,33,38,55]、線性混合模型[39,56]、時間序列路徑分析[22]、混合效應模型[31,42,57]、多層混合模型[34]、增長曲線模型[23]、組基增長模型[24,58]、潛類別增長模型[20]、潛在群組轉變分析[41]和增長混合模型[59],這些方法中目前使用最多的是方差分析。縱向追蹤研究在心理學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傳統的重復測量資料的分析方法,如t檢驗、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線性混合模型、時間序列分析。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也為縱向數據分析提供了一些能夠更加充分利用數據信息的建模方法,如混合效應模型、增長曲線模型、組基增長模型、潛類別增長模型、混合增長模型[60-63]。每種方法都有其特點和適用條件,研究者可根據研究目的和資料類型選擇合適的數據分析方法[61]。就縱向研究數據分析方法進展而言,縱向追蹤問題既往只注重分析總體平均發展趨勢,而后研究者們意識到研究樣本中的群體往往存在異質性,即并非所有個體均遵從相同的變化軌跡(即相同的截距和斜率),于是傳統的分析方法受到挑戰。將傳統的增長模型與潛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相結合的模型既能刻畫增長趨勢,又能考慮到群體的異質性,如潛類別增長模型、組基增長模型、增長混合模型,它們同時存在兩種潛變量:連續潛變量和類別潛變量,連續潛變量用來描述初始差異和發展趨勢的隨機截距和隨機斜率因子,類別潛變量則通過把群體分為互斥的潛類別亞組來描述群體異質性[60],是PTG 以及其他變量縱向研究數據處理主流及方向。
2.4 癌癥病人PTG 的變化趨勢和測量時間點的選取 癌癥病人多在疾病早期就報告了不同程度的PTG,大部分研究是探索疾病治療期間PTG 的變化情況。部分研究以確診或治療時間作為追蹤時間點的選擇標準,特點是所有研究對象測量的時間點和/或時間間隔具有較好的一致性,選擇較多的時間節點為確診時,確診1 個月、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24 個月,術前1 d,術后1 d、1 個月、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結束治療時、3 個月后等;還有一些研究以治療的階段作為追蹤時間點的選擇標準,因不同癌癥病人、相同癌癥類型但不同分期的病人治療方案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它們的特點是研究對象處于相似的治療狀態,但測量時間點和時間間隔不一定相同,如手術時、輔助治療時、治療結束6 個月,首次化療、末次化療。隨訪次數2~5 次[11,22,32,35-37,40-41,54-55]。追蹤時間最短的為2 個月[57],最長的為7 年[11,20]。目前,癌癥病人PTG 的縱向研究的時間點選擇在現有研究中差異較大,缺乏確切的理論和研究基礎。因患病人群、追蹤時間、測量時間點的選取異質性較大,因此對于癌癥病人不同階段PTG 的關系或者變化趨勢的研究結果存在較大的異質性。乳腺癌病人的縱向研究相對較多,Silva 等[28]的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病人在疾病早期表現出較高水平的PTG,直到治療結束后6 個月保持穩定。McDonough 等[26]對結束治療5 個月以內的乳腺癌病人進行了6 個月的隨訪,發現PTG 處于穩定狀態。馬麗莉等[64]的研究結果顯示,病人確診后1 個月、3 個月、6 個月PTG 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Manne 等[23]對乳腺癌病人的隨訪結果顯示,在確診后的1 年半時間病人的PTG 呈上升趨勢。Liu 等[27]對早期乳腺癌病人的研究結果顯示,確診后3 個月化療期間PTG 水平較低,而后的6 個月PTG 呈上升趨勢。高冉等[65]的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病人術前1 d 的PTG 得分最高,首次化療時最低,直到末次化療PTG 得分有所提高。少數研究利用上述能夠處理群體異質性的資料分析方法識別不同的PTG 變化軌跡,主要是針對乳腺癌病人的研究,如Wang 等[58]采用組基增長模型探索乳腺癌病人術后1 年PTG 的4 種變化模式,分別是高穩定型(27.4%)、高水平下降型(39.4%)、低水平上升型(16.9%)和低水平下降型(16.9%)。Danhauer 等[24]對653 例確診8 個月內的乳腺癌病人進行了18 個月的隨訪,使用組基增長模型確定了6種PTG 軌跡群,其中3種在不同PTG 水平上保持穩定,2 種呈緩慢增長,1 種大幅增長。
2.5 癌癥病人PTG 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因素 目前,癌癥病人PTG 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因素主要圍繞人口學因素、疾病相關因素、社會心理因素和伴侶相關因素4 個方面展開探索。人口學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文化程度、種族、性別、職業狀態等因素與PTG 相關,但各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Wang 等[58]的研究發現,乳腺癌病人PTG 高水平下降組和高穩定組病人的年齡較小,受教育程度較高。Danhauer 等[24]發現,不同PTG 變化軌跡的乳腺癌病人在年齡和種族方面有所不同,而婚姻狀況和教育程度在不同軌跡病人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usson 等[30]的研究結果顯示,高穩定PTG 病人的特征為年齡小、性別為女性。Chen等[29]將青少年和青年癌癥病人的情緒困擾和成長情況分為4 組,痛苦成長組的病人與彈性組或彈性成長組相比,更有可能處于工作或學習狀態。疾病相關因素:關于診斷時間、治療階段、治療方式等因素對PTG 的影響目前研究結果并不一致。Tanyi 等[38]學者發現,放療期間乳腺癌病人和前列腺癌病人的PTG 總分和4 個維度得分沒有顯著變化,只有精神改變維度在放療期間得分顯著增加,并在放療結束后4~6 周持續改善。Husson等[30]的研究顯示,PTG 維持高水平的青少年和青年癌癥病人多接受過化療。社會心理因素:多項研究結果發現應對方式[11,21,24,28,39-40]、社會支持[26,28]、認知加工過程(反芻性沉思、疾病侵入)[24,57]是癌癥病人PTG 的主要影響因素,積極應對、社會支持和反芻性沉思水平越高,PTG 越高。伴侶相關因素:Manne 等[23]的研究發現,乳腺癌病人的PTG 與其配偶的PTG、配偶的認知及情緒加工有關。
3 小結與展望
癌癥病人PTG 相關研究是癌癥心理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該領域目前的研究熱點。縱向追蹤研究多用于分析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以及探討數據間因果關系,在心理學相關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癌癥病人PTG 相關研究以橫斷面調查為主,縱向研究近年來增多,但仍相對缺乏,且此類研究在縱向時間點的選擇、數據分析方法等方面差異較大,使得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欠深入的特點,使人們對癌癥病人PTG 的縱向變化規律認識不足,難以為科學、有效的PTG 干預方案開發提供高質量證據。未來癌癥病人PTG 縱向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探討:①縱向研究的測量時間點選取應找尋相關理論基礎或者在既往同類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驗證和分析,以促進各研究結果的比較,為今后PTG 提升干預的時點選擇提供科學證據;②隨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一些能夠分析人群異質性的統計分析方法涌現,如潛類別增長模型、增長混合模型,應注意使用這類方法在刻畫病人PTG 總體變化趨勢的同時識別能反映群體異質性的潛在類別,這對重點干預人群的識別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③少數研究除了納入癌癥病人為研究對象,還納入了病人的配偶或重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在人際互動和相互影響的理念下得出更加豐富的研究結果。后續可進一步挖掘病人及重要他人的互動機制與路徑,為病人及其重要關系人共同成長的更高效、有益的PTG 干預策略構建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