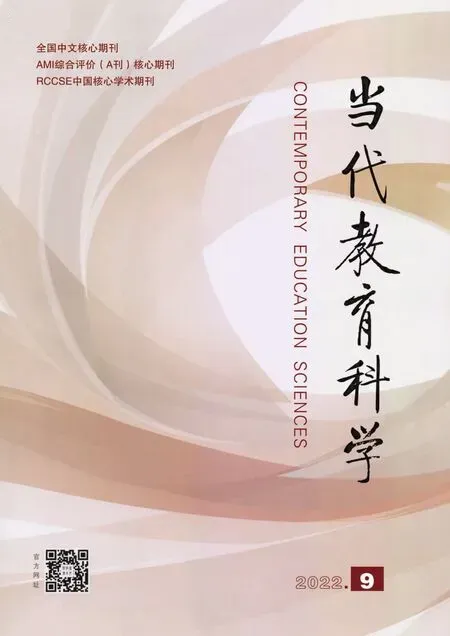他者性教育:教育的同一性批判與為他性重構
●盧紅 趙越
今天,由同一性所帶來的暴力彌漫在教育領域。在技術主義的宰制下,“教育”這種具有復合意義的詞匯已逐漸被“學習”“教學”等更加清晰而單一的詞匯替代,本該涉及人類靈魂的偉大活動被分解為一步步可量化、可操作的統一目標。在這種統一中,現代教育的弊端體現為:工具理性對批判理性的取代,多元思想的喪失,逃避自由的學生,單向度的人。而以列維納斯為代表的他者性理論,則從他者所具有的優先級出發,強調他者對于我的絕對他異性和不可同一性,以期實現傳統主體概念中“為我性”到“為他性”的根本轉變。這無疑為我們反思現代教育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接受他者的差異,學會與他者共生,成為教育新的時代呼喚。
一、對他者問題認識的三重變奏:從主體性哲學、主體間性哲學到他者性哲學
在西方語境下,“主體”(Subiect)一詞擁有雙重含義:一為自主、主動,強調主體的征服與同一;二為屈從、屈服,意指服從于外界的他者。但長久以來,西方哲學似乎只關注到了“主體”的第一重含義,主體和主體間性哲學占據統治地位。直到近現代以來,才有哲學家在反思主體主義的基礎上,從第二重含義出發,提出他者性理論,使他者的概念得以澄明。從主體性哲學到主體間性哲學,再到他者性哲學的轉變,既是人們對其自身主體性的不斷反思,也表明了在對待他者這一問題上的不同看法。
(一)主體性哲學:自我權能的無限膨脹
所謂主體,與客體相對,是“二元論”西方哲學話語體系下最根本的語詞。主體性,既是主體力量的彰顯,也是主體為宣示自身權能而對客體強行征服、改造與同一的過程。主體性哲學強調主體自身的權能,將客體(他者)視作有待同化和征服的對象,表現為絕對的排他性和獨占性。自伊奧尼亞最初的愛智者開始,哲學家們為了更好地解釋他者,不可避免地追求一種同一性,即將世間萬物歸結為一種或幾種最初的物質,以完成對他者的解釋,并將自我也融入這種同一性之中,借以確認自我與萬物的共在。至巴門尼德提出“存在是一”的觀念后,這種自覺追求同一性的傾向開始正式成為西方哲學的基礎。
在蘇格拉底這里,對他者同一性的探尋發生了重要轉向,即從外在物質世界轉向主體自身。其標志是蘇格拉底對“德性”以及“認識你自己”的追問,這也是主體性哲學的開端。近代,笛卡爾從“我思”出發,用普遍懷疑的方法試圖為人的認識找到一個毋庸置疑的起點和根基,然后再通過“我思”來證明外在(他者)的真實性,“我思”遂成為他者存在的根據以及對他者同一的工具。只有黑格爾敏銳地覺察到,自我意識的確立必須以承認他者的差異性為前提,“自我意識只有在一個別的自我意識里才獲得它的滿足”。[1]如果缺少“非我”(他者),則不能確立“自我”(主體),只有在他人的承認下,自我的認知和建構才得以可能。
主體性哲學致力于為他者去魅,將他者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消解,以維護主體自身權能的無限膨脹。在主體性哲學中,主體始終處于爭斗狀態,世界成為“每個人和每個人的戰爭”。薩特在《禁閉》中寫道:“他人就是地獄。”[2]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對于主體主義哲學下人與人畸形關系的隱憂。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以瘋癲作為文明的他者,以描繪瘋癲者遭受囚禁和流放的過程來詮釋主體對于他者他異性的排斥與拒絕。
(二)主體間性哲學:“先驗唯我論”的迷思
針對主體性哲學,胡塞爾提出“主體間性”的概念,希冀以此解決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即達成兩個主體間的平等互動。主體間性哲學以承認他者的存在為前提,探討主體與主體之間如何獲得認識上的統一。即通過移情將自我意識投射到他人身體里,使自我在感受他人的同時,也意識到自我正在被他人感受,自我與他人是兩個同樣平等的主體。主體間性哲學將人與人的關系從主客二元論的對立中解放,代之以較為平等的雙主體關系,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者的不可同一性。但在胡塞爾的語境下,他者的用詞依然是“他我”(Alter ego),對他者的理解只是主體自我意識的投射,未能走出“先驗唯我論”的迷思。
繼承主體間性,海德格爾提出了“我與你的共在”。他認為:“此在之獨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種共在中而且只能為一種共在而不在。”[3]這說明在個人的存在中就包含著對他者的領會,此在在世必然是與他者的共在,無論他者是否在場,都不可避免地規定著此在。馬丁·布伯認為人和世界即他者有兩種關系,一種是“我—它”的關系,一種是“我—你”的關系。在“我—它”中,他者不過是主體利用的對象;而在“我—你”中,則是二者真正靈魂的相遇。如他所說,“誰說了‘你’,誰就沒有在把什么東西當成對象”,[4]“所有的真實生活,都是相遇”。[5]哈貝馬斯提出“交往理論”,認為交往行動將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運作方式,而這種交往行動的核心即主體與主體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
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哲學的轉變,說明隨著現代社會公民生活范圍的逐漸擴大,他者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了人們的視域中,但是主體間性哲學其本質上依然沒有脫離主體性哲學的藩籬,依然是從自我出發來完成對他者的同一,只不過代之以對話或契約等較為平等的方式。從自我出發來解釋他者,極易陷入一個根本的矛盾之中,即如果想要確證他者存在的真實性,那么對他者的解釋就不能從“唯我論”出發,否則所謂的他者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他我”,即“我”的變異而已。
(三)他者性哲學:為他的倫理訴求
列維納斯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對他者問題作出系統思考的哲學家,他從批判西方傳統的主體主義和“唯我論”出發,將他者視作一個絕對差異性的存在,以反對在追求同一性過程中主體對他者所帶來的暴力,并由此將倫理學視作“第一哲學”。列維納斯認為,正是由于西方這種“唯我論”的哲學傳統,使得他者雖然一直存在,但其真正意義從未顯現。列維納斯對主體進行了重新定義,他認為“我”對他者負有一種不對稱的責任,“我”必須無條件地回應他者,對他者負責。在這里主體成為以他者為前提的主體,從追求認識論上的同一轉向為他的倫理訴求,也正是這種“為他性”,使主體獲得了存在的普遍價值與意義。
列維納斯認為在西方哲學史上歷來存在兩種他者,一種是“相對的他者”,可以被還原和同一;一種是“絕對的他者”,不可被還原和同一,是根本外在于我的異在。[6]而“為他性”體現的第一要義就是對他者他異性和不可同一性的承認,即承認他者對于主體的超越。針對此,漢娜·阿倫特強調:“人們,而不是一個人,生活在地球上,棲居于世界中。”[7]“我們進入世界基本上依賴于他者接納我們開端的活動。”同時,“自由僅存在于行動之中,而行動就定義來看,是與他者一起的行動。”[8]
他者性哲學將他者而非主體置于共同體的首要位置之上,借以打破主體存在的同一與孤獨,轉而使其通過他者走向無限與多元的做法,深深影響了人們對教育的認識與教育實踐的發展,正如格特·比斯塔提到的,“教育之責任就必須強調獨特唯一的存在進入世界”,并且“通過為他者的他性擔負起我們的責任的方式,我們作為唯一的、獨特的個體才得以進入這個世界”。[9]他者性哲學反對教育中的理性主義和知識本位論思想,將德性視作教育的第一要義,力圖將教育從同一性的怪圈中解放,重拾對于他者的接納與包容。
二、他者性教育的出場:他者性視域下的教育批判與教育超越
近年來,隨著他者性理論的興起與發展,他者性教育也得到了國內教育學界的重視。可以說,他者性教育是在他者性哲學視域下的某種教育批判與教育重建。它的出場,鮮明地彰顯了部分教育學人對現代教育中主體性及其同一性的批判,以及對理性及其理性共同體的反思,同時也表明,他們以他者的差異性為前提,正在教育中展開對主體性概念的重建工作。
(一)尊重他者的差異:對現代教育中主體性及其同一性的批判
主體性的發展曾一度代表了文明與進步,把人從自然和上帝的奴仆轉變為世界的主人。但是,主體性的過度膨脹也形成了對于他者的事實暴力,我們從自我出發去理解他者、定義他者,把“他們”變成“我們”,又在“我們”的同一中徹底抹殺了他者的差異。同一成為主體統攝萬物的手段,在其不斷的自我膨脹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唯我的孤島,自私與狹隘取代了對于他者所負有的責任。近年來,學校中惡性競爭、校園欺凌等事件的頻繁發生,使我們不得不去反思傳統主體性教育所帶來的危機。從其教育模式上看,無論是以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傳統“教師中心主義”教育模式,還是以杜威為代表的現代“兒童中心”主義教育模式,如果從“自我”的主體性出發,都不免將師生的交往變成某種主體對客體的征服和改造。在這種關系之下,學生與教師不可能達成真正的對話與諒解,更不必奢談“靈肉的交流”及“精神的契合”[10]。
他者性教育則要求我們必須為他者留有位置,我們無限地逼近他者,卻始終與他者保持距離,他者是絕對異于“我”的外在,即在“我”主體性之外的存在,不可被“我”同一。列維納斯認為,他者的這一差異正體現在他的“面貌”之中,“在他人之面貌中閃爍著外在性或超越的微光”。[11]面貌具有可見和不可見的雙重屬性,在可見的屬性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在不可見的屬性上,面貌預示著他者的無限,因為他者身上總蘊含著“我”所不可知點和不可理解之處。他者面貌所寫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不可殺人”。[12]“你不可殺人”代表了他者對“我”主體性和同一性的質疑。
只有從差異性而非同一性出發,教育活動才能擺脫傳統主體主義教學模式,轉向真正精神上的交往與靈魂上的契合,教師與學生也才能達成真正的平等與自由,在差異性而非同一性中獲得彼此的共鳴。學生是具有獨立意義的人,不以教師的意志為轉移,即是說把學生當成一個真正的他者;教師則要從關注學科轉向關注人,即成為一個“為他性”的存在。列維納斯在此指出:“他者的全部存在正是由他的外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他的他異性所構成的。”[13]“他人之所以是他人,并非由于其性格,或相貌,或心理,而是由于其他異性本身。”[14]對他者差異性的尊重真正體現了教育及其社會的開放程度。在他者性教育中,我們所尋求的不再是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即從自我出發而尋求同一性答案的求同式對話,恰恰相反,我們所尋求的是給予他者他異性充分關注的存異式對話。
(二)呼喚他者的到來:對教育理性及其共同體的反思
現代社會以理性作為人的本質,進而形成了排斥一切非理性行為的理性共同體。在理性共同體下,人與人的關系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同一性和排他性傾向,即每一個個體都必須受到理性共同體的承認才能夠“合法”地存在。作為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教育包含了人的社會化進程,在其中,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共同體的同化和改造。現代教育愈發制度化的特征,將培養人的效率提高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同時也將同一性演繹到極致。在其典型的班級授課制下,學生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排斥,失去了作為個體的獨特性特征,學校淪為知識的加工廠,學生淪為統一的商品,而教育則成為一條流水線。今天,我們的教育變得多么簡單和可操作,學生就變得多么狹隘和淺薄。他們用知識代替智慧,用記憶代替思考,看了很多卻不懂分辨,學了很多卻不懂運用;他們的思想不過是別人的復刻,他們的行為不過是別人的延續。而這一現象正是現代社會理性及其理性共同體在教育中的縮影。
教育的危機就體現在其育人本質的喪失之下:人不過是教育通過“文化再生產”轉而進行“社會再生產”的工具,人變成了手段而非目的。在這種教育中,學生時刻處于共同體“暴力符號”的統治之下,一切教育活動都被分解為有待完成的各項指標,并通過量化的方式加以評價和篩選。個體內在的生命與活力被指標化的“能力”替代,人成為可以被量化的東西,其價值和尊嚴也就遭到了徹底的否定。正如后現代主義者所批判的那樣,一是理性這一標準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考察了所有人的理性后所作出的客觀判斷;二是這種基于某種同一性去理解差異性的思維本身就暗含著對于他者的暴力,它使得人們為了各自的“是其所是”而爭斗,卻將他者所代表的“是其所不是”遺忘。理性本質的界定從一開始就完全是理性共同體中由少數人權力壟斷所導致的結果。列維納斯說:“唯我論既不是一種迷亂,也不是一種詭辯,它就是理性的結構本身”,“因此,理性從來就不曾發現另一種向其訴說的理性”。[15]
他者性教育則熱情地呼喚他者的到來,要求人們走出自身的狹隘與偏見,去無條件地面對世界和他者,并在與他者面對面的相遇中完成對自我本質的實現。在這方面,德里達一直雄辯地請求容納局外人,或者運用不同語言、不同視角來觀察他者。他要求我們“讓他者成為他者”——尊重他們的他者性,不要試圖把他們同化在我們自己的語言和故事之中。[16]我們的存在從來就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從來就是與他者的共在,他者是我人生所必須去面對而不可繞開的確然。因為“對自己來說,人是不充分的,如果生命不為自我以外的目的服務,如果生命對別人沒有價值,那么生命對人就沒有意義”。[17]在他者性教育中,人們必須超越自身理性認識的局限,轉而在對他者無私奉獻的倫理關系中來構建全新的、允許他者差異性存在的“他者共生體”。
(三)“為他”而存在:對傳統主體性概念的超越
批判是為了超越。對主體性的批判并非要徹底將其抹殺,而是為了優化與改造,以達到超越傳統主體性的目的。一方面,主體性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發生轉變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主體性也是人類得以建立文明與國家的基礎。但是在他者性教育中,主體必須經過改造,將其中的“為我”轉變為“為他”,將“自由”轉變為“責任”,將“同化”轉變為“回應”,以重塑教育神圣的理想,培養德性完滿的人。
近年來,教師侮辱、虐待、性侵甚至導致學生自殺的新聞屢屢曝光,而學生頂撞、毆打、殺害教師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我們不禁要問:在有著傳統“貴師重傅”文化的中國,為什么會不斷上演這樣的惡性事件?究其原因,便是主體性哲學中“為我”思想所導致的德性衰退。他們將彼此視作有用的物,而非需要負責任的人。對此,他者性教育直接指出,作為存在者的主體必須以“為他人”的責任作為存在條件。[18]我們原初的存在是一種與他者共生的存在——我們與他人同在比我們自身更早;在我們是某人之前,我們就是為他人存在的。[19]正是這種“為他人存在”使得“我”在與他人面對面的相遇中具有一種無條件關注和回應他人的責任。這里的主體成為真正意義上倫理的主體,“倫理的‘我’,就其在他人面前屈尊,為他人更原初的召喚而犧牲自己的自由而言,就是主體性”。[20]列維納斯使主體從傳統的自我走向了外在的他者,使主體在對他者的無私奉獻中克服了自身的權能,即同一與占有的欲望,轉而成為一種具有“為他性”的新主體。
在這樣的新主體理念下,師生才能進行“換位”,教育也才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學生主動與老師溝通和交流,尊重老師的教學成果,努力完成學業任務;老師則主動去了解和關注學生,尊重學生的差異,努力幫助學生實現自我的發展,師生交往徹底走出利益相符和彼此計算。在當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堅持對外開放的理念下,他者性教育將為培養國際性人才和以全球化眼光解決人類所共有的問題提供一種新的途徑。在以他者為前提的主體性概念下,主體與他者成為一個辯證的統一,別人對于“我”是他者,“我”對于別人亦是他者,同時在場與不在場的第三方還是一種他者。在此理念下形成的教育共同體,過于強調他者而對主體造成的不對稱性得到了彌補,因為“我”同時既是主體又是他者,“我”既有履行主體“為他性”的責任與義務,又有作為他者為自己提出平等訴求的權利,主體與他者在此過程中成為真正的共在與共生關系,而整個教育共同體也將因此而實現真正的教學相長。
三、他者性教育的澄明:現代教育的“為他性”重構
吸收他者性哲學的他者性教育,體現了其為他者發聲、為他者服務和為他者無條件奉獻的思想意蘊。基于此,現代教育急需一場超越同一性和確證為他性的思想革命。
(一)培育師生對他者負責的觀念和倫理關系
教育即學會如何尊重他者、回應他者,與他者共生、對他者負責。人必須通過教育才能成為人,故而“人之為人有何內涵這一問題,也可能首先是一個教育的問題”。[21]列維納斯提到,人的存在的意義與基石被指向他者,“人們在他們終極的本質上不僅是‘為己者’,而且是‘為他者’”。[22]因而,正是他者使存在的真實性得以可能。“從我到我自己終極的內在,在于時時刻刻都為所有的他人負責,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質。”[23]作為培養他者的教育,必須肩負起為他人負責的使命,幫助師生樹立“為他性”的思想觀念。
一是培養師生“對他人負責”的責任意識。他者的創造與付出是“我”發展的基礎,個體只有在對他者無限的倫理責任中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價值。使“我”出生的父母是一種他者,教導“我”的老師是一種他者,使“我”獲得友誼的朋友是一種他者……乃至于與“我”照面和未曾照面的所有人都是一種他者。他者組成了世界,而“我”就在世界之中。也正是這種“為他性”要求我們要尊重他者的差異而不強求一致,傾聽他者的聲音而不諱莫如深,在與他者的關系中打破孤獨的詛咒。從愛身邊具體的人做起,直至愛整個民族,愛整個國家,乃至愛全世界、全人類,在對他者的不停奉獻和責任中感受到生命的本質及其存在的價值,以克服虛無的侵腐。
二是重塑師生、生生的倫理關系。在以往的教育中,師生、生生之間的傳統倫理關系是一種對稱性的倫理關系,即“我怎么樣,你也應該怎么樣;我對你好,你也要對我好”。這種以自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倫理關系受到了他者性教育的質疑與拒斥,他者性教育主張用一種從他者出發而不求回報的非對稱性倫理關系進行替代。“作為公民我們是平等的,但是在倫理行為中,在我們和他者的關系中,如果我們忘記了我比其他人更有罪,正義本身將不能持久。”[24]“我”比他者更有罪的不對稱性恰恰說明了他者比“我”更重要。“那就是人在他的存在中更依賴他人的存在,而不是更依賴自己。”[25]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徹底轉變之中,在對他者負責任的回應中,師生、生生實現了“為他性”的倫理向度。
(二)讓師生“自由言說”與“自由行動”
傳統教育中,他者的不存在是常態。當我們不斷高抬教育地位的時候,我們一直強調的似乎也只是它工具理性作用下外顯于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等功能,而其內在本真的道德責任和批判理性卻早已被忽視。這是教育最終的宿命嗎?教育終將跟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一樣變成一種機械復制下的產物嗎?教育再也容不下反對的聲音了嗎?它終將在貌似的和諧中與其最初的信仰大相徑庭了嗎?
他者性教育正是基于此而產生的,以允許共同體中他者的存在為前提,使受教育者得以自由的言說與行動,并在這種行動中最終完成“為他性”的轉變。一方面,言說與行動是我與他者得以建立關系的紐帶,正是通過這種紐帶,“我”才能實現與他者生命的互動,才能作為一個全新的生命開端進入這個世界中。教育必須使他者能夠自由地入場、自由地言說與行動,允許他者的差異,同時給予他者必要的回應。在他者性教育中維護理性共同體的教育必須消失,從而使作為他者的受教育者能夠出現。教育權威必須向他者開放,接受他者的質疑和聲音,言說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言說,教育必須保障受教育者的話語權。否則,它將只能成為壓迫性的教育。
另一方面,言說與行動也代表了他者的他異性所在,因為我并不能準確預料到他者將對“我”進行怎樣的言說和行動,所以“我”只能無條件的去回應他者,即使“我”選擇了不回應,本身也是一種回應。作為“我”的主體在他者面前始終是一種被動性的存在,“我”成為他者的人質。“在傳統看來,主體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自主、自決,而這里的‘主體’概念則是徹底的被動性,是對‘他人’的無限責任。”[26]
(三)在“他者共生體”中形成好客的教育面容
他者共生體是在他者性視域下形成的,是與理性共同體相對立的,以保障他者自由言說和行動的共生體。傳統的理性共同體以同一為其目的,以同化和禁絕為其排斥他者入場的手段,在這種理性共同體中“人終將被抹去,如同大海沙灘上的一張臉”。[27]而以他者共生體為基礎的他者性教育,由具有“為他性”特征的新主體構成,這是一種真正好客的主體,歡迎他者的入場,要求教育者看到那些弱勢群體和少數學生,希望通過他者來超越自身的存在,去重拾那對于無限相異性的欲望。
在好客的他者共生體中,學生所說的話代表他自己而不是別人。他者共生體不是由冰冷的契約或利益組成,而是由具有超越性的愛與關懷所構筑。“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他就已是愛之在者。”[28]愛與關懷正是“為他性”的根基和超越理性共同體的最佳途徑。他的表達方式是“我想要”,而不是“我應該”。如此,教師得以無條件地傾聽和回應學生,學生們也不必非做同樣的事,說同樣的話,而是學會去尊重和包容那些不同的話和不同的事。
正是在此基礎上,好客的他者共生體強調對他者融攝的生命需求,強調在與他者達成生命共振的過程中正視他者的差異。在人類發展史上,因理性認識的有限而導致的交往不全面使人們一直懷疑個體是否真的可以實現彼此之間的通達。對此,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9]教育是培養人的學問,是聯系二者的實踐橋梁。對他者生命價值的尊重和關懷是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過程,對他人的尊重、接納與負責也是現代教育真正該有的倫理面容。人生意義必須在與他人的相遇中才得以顯現,“如果他不與別人分享意義,如果這意義不屬于其他人,他就永遠不能得到滿足,也不能認識到意義”。[30]當我們用好客的態度真正去尊重、理解與走向他者,個體生命間的融通也就有了實現的可能。
四、結語
他者性教育的出場,為現代教育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野和價值取向,促進了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他者性教育并不能包含教育的全部,也不能準確預示出教育的未來,畢竟教育始終是一門關于人的藝術,在人的不斷變化中,教育也將不斷變化。就目前來看,他者性教育至少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同一性悖論。他者性教育強調他者的差異,反對同一。但教育活動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同一性,這使得他者性教育陷入一個根本的悖論之中。一方面,這源于特定時代、特定社會對處在教育中的人所提出的特定要求,這種要求是具有同一性的;另一方面,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這種權利和義務針對于全體公民,不可避免地要求同一性。第二,對主體權利的忽視。在他者性教育中,他者與主體擁有不對稱的倫理關系,“為他性”代替“為我性”成為主體發展的根基。但他者的過度膨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主體自身,使主體只有在被當作他者時,自身權益才能夠得到有效維護,從而造成了對主體權利的忽視,他者成為新的霸權。第三,被動的責任。他者性教育以他者的責任代替主體的自由,將“我”視作他者的“人質”,“我”比他者更有罪,“我”必須無條件地為他者付出。但這種責任卻是一種被動的責任,是強加于主體之上的責任。對于主體來說,無異于是一種重負,只會使主體感受到疲憊與麻木,從而喪失道德活動所應當具有的神圣性和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