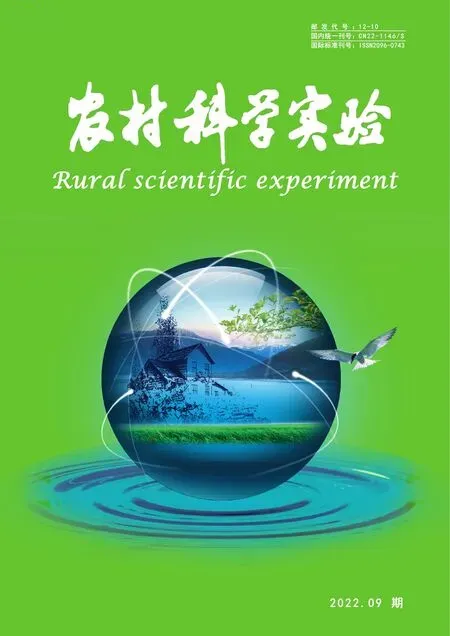北美五大湖七鰓鰻入侵問題及其治理
黨冠超
(山東師范大學,山東 濟南 250000)
隨著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狀況的改善,生物入侵成了世界范圍內越來越普遍的生態問題。北美五大湖區在20世紀遭遇了嚴重的外來生物入侵,本文試對20世紀五大湖區遭受七鰓鰻入侵的概況及研究人員采取的防治措施進行簡單的介紹。
1.七鰓鰻入侵五大湖區的條件及過程
北美五大湖位于美國與加拿大的交界處,是(自東向西)安大略湖、伊利湖、休倫湖、密歇根湖和蘇必利爾湖這五個淡水湖的總稱。五大湖被稱為“北美的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和地表水系統,總蓄水量達到226840億立方米,所蓄淡水占世界地表淡水總量的五分之一,占美國地表淡水總量的90%。五大湖總面積約245660平方公里,湖面廣闊,水量充足,蘊藏著豐富的漁業資源。
除安大略湖外,上游的四個湖泊高出海平面約180米,尼亞加拉大瀑布就位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間。安大略湖上游的急流和瀑布構建了一個生態屏障,阻擋水生生物由安大略湖遷徙進入其他的四個大湖,同時也攔住了來自大西洋的船只。反過來說,五大湖區中西部的貨船能夠在沿湖各個城市之間往返,卻無法進入大西洋。為了改善貿易條件,促進經濟繁榮,美國與加拿大都試圖通過開挖運河打通連接五大湖與大西洋的水路。1825年,伊利運河開通,它東起紐約州的奧爾巴尼,西至大湖區的布法羅,使得哈德遜河與伊利湖之間被暢通的水道相連。1829年,加拿大的韋蘭運河開通,它由40道船閘組成,使得船只可以經由運河穿越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間的丘陵地帶。此后,隨著貨船尺寸和噸位的不斷增長和船隊規模日益擴大,五大湖區的人工水道也相應進行了數次擴建。伊利運河和韋蘭運河的建成引領了經濟快速發展、城市迅速擴張的“運河時代”,為五大湖區工業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交通條件。
不過,隨著水路進入五大湖區的有些外國“貨物”并不受歡迎,它們的引入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可是當人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時,這些不速之客已經釀成了嚴重的后果。這些“貨物”就是經由人工水道從大西洋進入五大湖區的外來生物。運河的開通和拓寬使得曾經阻止它們擴展活動范圍的天險已經不再起作用了。
七鰓鰻(學名Lampetra japonica)是一種典型的溯河性動物,也就是說同大馬哈魚一樣,七鰓鰻也要在淡水河流或小溪中孵化出來并度過它生命的早期階段,然后遷徙進入海洋中,成長到性成熟之后再回到淡水河流或溪流中產卵,產卵后不久就會死去,如此完成一個生命周期。不過,如果這類溯河性動物運氣絕佳,在成長過程中能夠進入有著充足食物的大湖,那么它們也就不需要遷徙到海洋里了。因此,五大湖對于七鰓鰻來說絕對是一個營養豐富的饕餮樂園。
發育早期階段的小七鰓鰻以淡水中的有機物顆粒為食,而進入海洋之后發育完全的七鰓鰻則通過寄生魚類生活,它能夠用吸盤狀的嘴牢牢地固定在魚身上,然后用牙齒咬穿寄主的身體,鉆到寄主體內吸食體液和血肉。七鰓鰻的唾液中有一種抗凝劑,這種成分能使傷口難以愈合,以便于七鰓鰻持續取食。七鰓鰻的寄主很廣泛,包括鱒魚、白鮭、梭子魚、胡瓜魚、巖鱸、白鱘在內的許多水生生物都會慘遭它們的襲擊。
有研究者認為,一些原產于安大略湖和紐約州東部湖泊的七鰓鰻很適應終生在淡水中度過,無須進入海洋。然而也有許多學者相信,在伊利運河開通后,七鰓鰻才在湖泊里定居下來。不管怎么樣,這些七鰓鰻數量很有限,而且被尼亞加拉瀑布阻隔,無法繼續向西擴展活動范圍,所以并沒有對地區生態造成什么影響。即使在能夠跨越瀑布和急流的人工水道韋蘭運河開通后,七鰓鰻也沒有馬上就利用它進入上游的大湖。1921年,人們第一次在尼亞加拉瀑布上游的伊利湖發現了七鰓鰻。這件事在當時沒有引起關注,沒有人意識到,一旦這些七鰓鰻數量擴張,將會給五大湖的生態和漁業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七鰓鰻的種群難以在伊利湖擴大,因為伊利湖水溫相對較高,不利于七鰓鰻的繁殖,然而如果它們再向西游得更遠進入其他大湖,就會以驚人的速度增殖。1936年,密歇根湖有人捕獲到了第一條七鰓鰻,如野火蔓延般地,1937年和1938年分別在休倫湖與蘇必利爾湖也有七鰓鰻被捉到。然后,由七鰓鰻引發的生態浩劫開始了。
2.七鰓鰻入侵的危害
20世紀30年代末,休倫湖的漁民們開始抱怨他們捕撈到的湖鱒不但身上總是帶有丑陋的傷口,而且質量也遠不如從前了。1938年2月7日《基韋斯特公民報》上的一篇報道指出,在五大湖中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海七鰓鰻種群可能會對五大湖的商業捕魚造成巨大的威脅。這種擔心很快就變成了現實發生的災難。1939年后,休倫湖每年的湖鱒漁獲量都在創下最低紀錄,1935年休倫湖的漁民捕獲了多達174萬磅(約790噸)的湖鱒,而這個數字到了1943年則銳減為45.9萬磅(約208噸),1947年休倫湖全年僅捕到了12000磅湖鱒(不足5.5噸)。在密歇根湖,湖鱒漁獲量的逐年下降是從1943年開始的,這一年創造了密歇根湖近10年來的漁獲量峰值記錄(686萬磅,約合3112噸),然而之后漁獲量一路下滑,1947年僅為242.5萬磅(約1100噸),1949年在密歇根湖僅有34.3萬磅(155.6噸)湖鱒被捕撈上岸,而同一年休倫湖的湖鱒漁獲量已經只有1000磅(約450千克)了。據生活在密歇根湖北部沿岸的漁民反映,他們所捕撈上來的湖鱒有70%至90%帶有被七鰓鰻寄生留下的累累傷痕。湖鱒是五大湖捕魚業的支柱,因而它們的損失尤其引人注目,然而考慮到五大湖中白魚、鮭魚、鲇魚等在內的絕大多數魚類都會遭到七鰓鰻寄生,七鰓鰻的泛濫對五大湖漁業造成的損失根本無法計算。在1950年1月28日的《晚星報》中,一位記者莉蓮·考克斯·阿塞描述了這場由意外的入侵者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災難:
“……如今,密歇根湖里有數不勝數的死湖鱒。
從湖中被捕撈上來的魚當中有50%至70%帶有傷痕,這些受傷的魚多數體型較大,那些體長不足17英寸(約合43厘米)的魚則幸免于難。許多漂亮的大魚有一到五個傷口,其中有一些已經愈合了,有一些則是新的,還在流血。”
由于每一條雌性七鰓鰻平均會產下62500枚卵,而幾乎每條成年的七鰓鰻在追逐獵物的一年中能夠殺死40磅(約18千克)的魚,即使這些卵的成活率極低,它們也能在短短幾年內成長為令人膽寒的“吸血鬼”,在五大湖大肆屠戮。莉蓮在報道的結尾寫道:“種種跡象表明,七鰓鰻是很難纏的強硬對手。根除它們將會使我們付出許多。但是到目前為止,它們已經毀滅了數百萬條有商業價值的魚。”
3.治理七鰓鰻入侵的措施
如莉蓮所說,美國和加拿大的確要在治理七鰓鰻上花費許多,但是如果縱容七鰓鰻繼續泛濫,將會使兩國付出更大代價。為了避免五大湖的捕魚業徹底被摧毀,美國內政部于1947年劃撥兩萬美元用以在流入密歇根湖北端溪流中設置一系列的圍堰,這樣一來當七鰓鰻逆流而上尋找適合產卵的場所時就會被抓住。盡管七鰓鰻是一種兇猛殘暴的寄生生物,但它也有弱點。經過長期的實地研究和仔細觀察,學者弗農·阿普爾蓋特發現,七鰓鰻在其一生中最為脆弱的時期就是當它作為幼崽或即將前往開闊水域(如大湖或大海)開啟寄生生活的時候,以及進入產卵期之后,這些情況下它們的行動路線是固定的,考慮到休倫湖、密歇根湖和蘇必利爾湖只有有限的大約200條溪流適合七鰓鰻產卵,那么這種脆弱性就大大加強了——因為七鰓鰻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沿著固定的方向進入人們為它們精心準備的陷阱當中。阿普爾蓋特指出,在七鰓鰻產卵的必經之路上設置圍堰和堤壩捕獲它們是個有效的辦法。很快,用于圍捕七鰓鰻的圍堰、陷阱被廣泛地應用起來。這些設計精巧的工程為五大湖的魚類提供了方便它們躍過的平臺和支路,確保不會影響這些飽受七鰓鰻折磨的無辜生物。不過,這種措施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有些溪流中的地形不適合筑造圍堰和堤壩;其二,修造這些設施并加以維護需要較高的成本;另外,洪水可能會沖毀這些設施;最后是七鰓鰻依然有可能越過圍堰,逃脫陷阱,哪怕僅有少數七鰓鰻能夠到達預定的產卵場所,由于其繁殖潛力驚人,也能夠在溪流中產生足以維持其種群數量的后代繼續為禍一方。
另一個治理七鰓鰻的方法是使用電子屏障阻斷七鰓鰻的產卵路線。研究人員在七鰓鰻即將逆流而上的河水中布設了電子屏障,使用常規的110伏交流電就能有效運轉,在水中產生對七鰓鰻來說很強力的電場。這個策略在實踐中被證明對于成年的七鰓鰻很有效果,而且電子屏障在建設和操作上既經濟又便利。不過,對于正從溪流前往大湖展開寄生生活的“青年”七鰓鰻來說,電子屏障幾乎不起作用,這個階段的七鰓鰻對電流有很強的抵抗力。另外,電子屏障在復雜的自然條件下很容易出現故障,而且依然會被洪水沖垮。
由于五大湖位于美國和加拿大的交界處,除密歇根湖外,其他四個大湖均為兩國共有,要想解決五大湖的生態問題,美國與加拿大的合作必不可少。早在1947年,議員拉爾夫·丘奇就指出,七鰓鰻入侵造成的生態危機是一個“國際問題”,并敦促加拿大方面盡快采取相應的行動。很快美國和加拿大就進行了磋商。1955年,五大湖漁業管理委員會成立,在該委員會協調下,美國和加拿大漁業部門在治理七鰓鰻入侵問題上展開密切合作。
五大湖漁業委員會制訂的方案是使用化學制劑毒死七鰓鰻的幼崽。要想使用化學藥物清理七鰓鰻,就必須找到一種能夠毒死七鰓鰻幼崽,同時又不會對五大湖中的其他水生生物和人類構成危害的制劑。為了找到這種特殊的制劑,阿普爾蓋特等研究人員對5000種以上的化學藥品進行了長期的實驗。1957年夏天,阿普爾蓋特等人在實驗中發現了兩種藥物可以殺死七鰓鰻幼崽而不會對鱒魚和藍鰓魚幼崽產生危害。1961年,更加有效的試劑大量被灑進與蘇必利爾湖相連的溪流中。此時蘇必利爾湖已經是五大湖區唯一的鱒魚商業漁場了。根據加拿大方面的統計,“1961年(蘇必利爾湖)漁獲量僅為4.4萬磅(近20噸),而前一年為10.7萬磅(約48.5噸)。10年前漁獲量為138.9萬磅(約630噸)。”
經過一段時間的持續用藥,到1967年為止,研究人員認為他們已經成功將五大湖當中七鰓鰻的數量削減到峰值水平的十分之一左右。不過,藥物需要持續施用才能將七鰓鰻數量穩定在合理范圍內,因此至今加拿大和美國還需要定期對五大湖區的近兩百條溪流進行藥物處理,每年要花費大約2000萬美元的費用。此外,在控制七鰓鰻種群數量的同時,美國和加拿大也展開了大湖漁業資源的恢復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五大湖漁業從七鰓鰻入侵的打擊中緩慢地恢復了。
結語
當1921年七鰓鰻第一次在伊利湖被偶然發現時,誰也不會意識到,在20年后,這些入侵者竟然能夠將五大湖漁業資源摧毀殆盡,而為了避免這一災害死灰復燃,100年后人們依然要為這場生態浩劫的善后處理支付不菲的費用。其實,早在1932年,前文提到的記者莉蓮就向讀者們介紹了大海當中的七鰓鰻,并指出“由于七鰓鰻一直在捕獵魚類,它們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問題”。不過她沒能預見到如果有一天這種經濟問題降臨到五大湖區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如今,世界各國已經有了對外來生物入侵危害的充分認識和防范機制,一些國家在對抗外來生物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雖然在當今的嚴格管控下,跨過自然屏障遠道而來的外來生物已經不太有機會偷偷潛入陌生領域并建立起可觀的種群,但是問題在于已經成功入侵了的外來生物該如何清理。
不難發現,對入侵七鰓鰻的成功治理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和加拿大雄厚的科技、資金投入,另一方面也要歸功于兩國的通力合作。生物的遷徙并不會遵照政治邊界的限制。生態環境領域的問題往往會演變成區域乃至全球的共同問題。當今熱點的生態環境問題,不管是全球氣候變化、跨國污染,還是本文探討的外來生物入侵,都無法由哪個國家獨立解決,更不會有哪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1962年加拿大漁業研究委員會曾經抱怨,盡管加拿大方面在防治五大湖區七鰓鰻的攻堅戰中取得進展,但美國方面的管控不力使得加拿大的大量成果付諸東流。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要求面對危機的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負起責任來,切實投入自己的資源,攜手并肩面對自然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