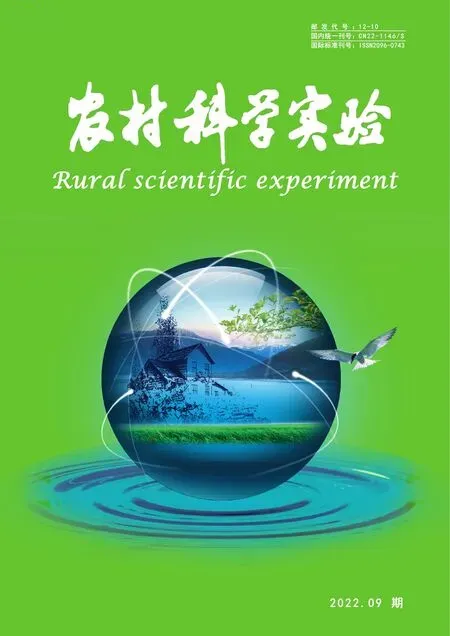人情社會的道義性對法治鄉村建設的抓手作用
——基于網格化管理理論的思考
姜 瑜 周 瑩 李 青
(山東政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1.相關概念界定
1.1 人情社會的界定
人情社會作為一種交換模式,其最基本的含義就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互動中,主要以人情作為交換媒介的社會。之所以把人情作為交換媒介,首先是因為人是情感動物,每個人生活在集體社會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與人進行交往,每個主體在社會關系網絡中都是一個交點,此交點與彼交點的鏈接就是人與人相互交往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需要表達自己對外部環境和人的情感,進而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和生存目標。其次,中國古人們講究“多個朋友多條路,多個冤家多堵墻”的思想觀念,這一思想從規避風險的角度來看就是,某一個體或團體的人情網絡越錯綜復雜、四通八達,當這一個體或團體遇到自身難以克服的困境時,就更為容易地通過檢索自己的人情網絡來尋找到能夠幫助自己的個體或團體,進而大大降低了自身囿于風險的概率,為我國古人所普遍接受。再者,人情關系網的形成對謀取不當利益具有明顯突出的作用。在我國古代,買官賣官在歷朝歷代都屢見不鮮,所謂的“找關系走后門”現象逐漸在人們的觀念中被優越化、正常化,因此人們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交際圈,將觸角不斷延伸至對自身有價值的交點,通過權錢交易等方式建立起聯系。
基于上述原因而建立起來的人情社會往往具有一定的通性。其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需求和利用價值成為人情關系網絡的核心,它決定著主體的行動方向并指導主體的行為模式;其二,因時因事的交往互動是維系人情網絡的傳統模式和主要途徑,并與結婚、喪葬等傳統禮俗和節日節氣緊密契合;其三,導致人情關系動態變化的自變量也是復雜繁多的,自變量與人情關系變化這一因變量的關系往往具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的特征;其四,人情社會存在著容易被腐化、操控的天然劣根性,這就決定了引入法律、道德等具有規范效力的上層建筑對其制約的必然性。
1.2 網格化管理理論的界定
在我國21世紀之初,網格化管理的實踐就在我國行業協會領域有所應用,2003年,北京市工商學會就網格化管理應用在工商區域管理上帶來的變化進行討論,但那時并未形成系統的網格化管理理論體系,并在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僅僅停留在碎片式的具體操作上,網格化管理實踐并沒有在行業協會中得到廣泛施展。2004年,北京東城區將網格化管理運用于社會治理領域,才引起了社會學學者對于網格化管理的關注。2005年,鄭士源對網格化管理進行了界定,他認為網格化管理是借助互聯網信息技術平臺,將管理對象按照一定的分類標準進行網格樣式的劃分,通過互聯網平臺將信息資源集合起來,實現資源的共享,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進而實現一種高效率的管理方式。2007年,陳云從資源共享視角出發,將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內涵界定為各種資源的有效配置;宛天巍等提出網格化管理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一種“透在”服務。當前一般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是一種將管理對象進行單位劃分,并以此作為責任單位工作載體和平臺,實施扁平化、精細化、多元化和長效化服務管理的一種社會治理方式。
2.法治鄉村建設存在的問題
2.1 破壞選舉法
隨著憲法相關法的不斷健全和完善,選舉制度和程序日益規范化、系統化。但是基層鄉村地區的選舉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人”往往名不副實,相反,名不副實的身份卻為其帶來不法利益。
基層鄉村地區選舉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普通百姓不了解選舉制度的程序規定等內容,導致人們對選舉的關心程度和重視程度較低,村民們無法為保障程序公正貢獻自己的力量,只能把重點放在最后直觀的選舉結果上,但實際上,村民們也不清楚當選條件,重視當選結果也只是出于好奇心理,并非真正源自“主人翁”意識 ;(2)大部分年齡較大的村民限于受教育水平,難以領悟選舉對我國行政管理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意義,所以趨利的傾向比起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而言更為明顯,因此,較少金額的賄賂或其他好處都可能會使他們投出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選票;(3)在我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大量的政策優惠、建設資金和發展機遇噴涌而出,很多鄉村中原有的“大戶人家”瞄準發展的紅利,借助自身的人脈優勢和財力優勢在選舉中脫穎而出,然后通過身份牟取舊村改造、廁所改革等鄉村振興的資金撥款等,此種行為不僅嚴重地破壞了我國的選舉制度,還使惠及于民的行政撥款進入個人的口袋中,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社會矛盾進一步凸顯。
2.2 資源不均衡
在法治鄉村建設的過程中,資源分配不均衡始終是痼疾,我國的行政村落數量大、分布零散,想要達到資源豐富而均衡的情形還需要一定時間的經濟發展為支撐,但是我國基層鄉村法治建設也急需推進,因此在可承受的范圍內,盡量使資源利用更加合理化、高效化是我們解決這一痼疾的突破口。
想要真正打開這一突破口,還需要從以下問題循序漸進地著手:(1)每個行政村落與其臨近的村落之間資源共享的壁壘較高,每個村落雖然在現實中有路可通,但在實際上就是一座座“孤島”,村委會與村委會之間不懂得亦不愿意將有限的資源與其他集體分享,進而難以形成輻射狀的資源網絡,閉塞致使資源更加有限,本就不發達的村落更加落后,相對發達的村落也會逐漸消耗殆盡、走向沒落;(2)鄉村的基層決策者不懂治理之道,缺乏水滴石穿的治理“硬功夫”,因而村集體自己的資金往往被反復用于短時間內可以看出治理成效的項目,例如硬化一些不必要的村路,在路燈款式上標新立異,購入一些華而不實、不具全民性的健身器材并將其閑置在倉庫,又或是打著美化鄉村的旗號反復在鄉村的墻壁作畫等,上述舉措本身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反復地進行,超過了必要的“度”,那便是對資源的一種浪費;(3)村集體不能主動地尋求司法資源下沉的途徑,僅僅等待司法部門主動“送服務上門”,缺乏對外界環境的感知力和能動性,而且司法部門的設置和運行也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其自身彈性就比鄉村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要弱,故而它不可能去主動契合每一個村落的資源需求,這就更需要村集體“主動出擊”去搭建司法資源下沉的平臺。
3.從道義性的角度對法治鄉村建設問題分析的必要性
人情社會的道義性往往深埋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其天然地具有抽象性的特征,但同時也是激發每個社會主體內源性動力的抓手。法治建設的終極性目標之一就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主體都能發自內心地尊崇和信仰憲法和法律,這就需要激活每個社會主體的內源性動力,所以,作為激發每個主體內源性動力抓手的道義性,自然也是法治鄉村建設的抓手。
如果要從道義性的角度具體分析上述問題,我們就需要將抽象的道義性給具象化,而具象化的最常用方式便是尋找一個參照物或近似等同物。在鄉村這一大環境中,能夠代表道義性這一要素的典型,或者說能夠與道義性畫約等號的往往是德隆望尊的老者、退伍返鄉的軍人、回鄉發展的高知群體等這些道德修養佳、知識素養高、人民群眾信任度高的先進人士。這些先進人士本身就是潛力巨大的人力資源寶庫,他們具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經驗經歷,來自不同的行業,從事不同的工作,所以能夠應付寬領域、多層次的難題,因此,如果能夠充分發掘上述人士的自身價值,便可以為解答基層鄉村法治建設所存在的問題提供不一樣的思路。
4.法治鄉村建設問題的解決途徑:融道義群體于網格的管理模式
建構融道義群體于網格的管理模式,關鍵在于甄選出道義群體的組成人員,組成人員應當兼備年齡結構的合理性、職業種類的多樣性、工作剛柔的調和性等。除了甄選人員以外,還需要將村落劃分為若干個網格,網格不宜過大,過大則不容易管理,捉襟見肘降低管理效能;網格也不宜過小,過小則管理幅度過寬,道義個體之間協商一致的難度升高。同時,劃分網格可以不按人數或地域面積平均劃分,而按照道義主體實際的管理能力來劃分,避免出現年齡較大、精力欠佳的先進人士難以應付繁雜的事務、身心俱疲的情況,也給予了身體康健、精力旺盛的人員更多施展空間。甄選人員、劃分網格完成之后,還有一步不容忽視——公示。在所管理的范圍內進行公示相當于賦予這個管理群體正當和合理的地位,有利于理順道義群體和被管理者的關系。在完成以上準備工作后,便可以從以下角度切入,解決上述提到的問題。
4.1 組織普法小組,一對一幫扶普法
組織普法小組并非是件新鮮事,但是如何發揮普法小組的功能仍有討論的價值。第一,道義群體需要在自己所管理的片區范圍內組織起普法隊伍。普法隊伍的成員需要及時關注我國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部門的平臺上所發布的實時信息,但不能不加篩選、一網打盡,而是選擇需要人民群眾了解的內容,因為如果信息太多、過于專業,本身就是對道義群體的考驗,也會觸發群眾的抵觸心理,使得普法活動被扼殺在搖籃里。普法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讓人們普遍信仰法律的實踐精神和價值內核,不在于讓人民群眾掌握多少法律定罪量刑和糾紛處理的知識,因此信息篩選也是普法宣傳的重要一環。第二,除了有關法律的實時訊息需要普及,更要有側重地圍繞所管理人們的違法行為進行普法,收到的效果才會更加顯著。人們對于與自己有切身利益關系的法律內容總是愿意傾注更多的注意力,而且鄉村鄰里之間基于人情關系的緣故往往相互關心,這就使得一家遇到的法律問題會給周邊數個家庭起到警醒作用,因而針對一家的普法會產生輻射帶動的效果。第三,發揮法律規范的預測作用,通過使人們養成事先進行法律咨詢、預測自己行為后果的習慣,讓法律真正融于人們的生活,與百姓的一言一行密不可分。事前的法律咨詢需要較為專業的知識儲備和職業素養,因此可以尋找管理區域內從事相關法律工作的人員承擔該任務,或者是以村集體的名義購買市面上律師事務所的服務。
4.2 建立監督檔案,作為選舉的參考
建立監督檔案是強化基層鄉村法治建設強制性的重要手段。其一,道義群體對所管理區域內的個人進行監督登記,可以從外部加強對個體行為的約束,同時也可以加強對家族行為的約束。白紙黑字的記錄往往能給個體帶來更大的行為強制力和精神壓力,人們為了自身權利在未來不受限制或約束,會十分重視檔案記錄,進而自覺地與違法犯罪行為劃清界限。同時通過記錄,可以更加全面系統地去評價個人,為今后基層鄉村建設的其他工作遴選人才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無論是從法治建設角度,還是鄉村振興的其他工作角度,監督檔案的建立具有多角度的價值和意義。其二,當監督檔案制度具體落實在選舉上時,如果有參加選舉意愿的人在選舉前的時間里“奔走相告”,或者進行了賄選等行為,經他人舉報后,由道義群體負責記入檔案,這一舉動將會影響他人對其的認可與評價,進而影響其當選的概率,保障了選舉的公平性和人民性。其三,監督檔案制度的適用對象并非局限于道義群體以外的人,道義群體自身也必須納入這一評價監督體系之中,且要求更加嚴格,并對所管理范圍內的村民定期公開,如果犯了錯誤未記錄在檔案之中,其他村民有權利要求道義群體的總負責人更換本區域的管理者,并將更換事實記入其檔案之中,從而有效地監督制約道義群體,使其更好地發揮模范帶頭作用,打造循環監督的管理環境。
4.3 加強司法溝通,實現資源的共振
在鄉村司法資源總體不豐富、單位與單位之間不均衡的宏觀背景下,將有限的資源鏈接起來,形成資源網絡系統,進而實現系統共振是彌補資源不足這一劣勢的重要方式。首先,鄉村各村落之間的村委會應該通力合作,打通村與村之間的司法資源共享壁壘,集約法治建設的專項資金撥款,向專業機構購買服務來對道義群體進行適當的法律培訓,用專業素養來武裝鄉村法治建設的先鋒隊;還可以集中調配村落中接受過高等法學教育的大學生等人才,發揮他們的知識價值,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次,村委會在規劃本村的發展計劃時,在法治建設問題上要與道義群體達成共識,共同制定一個循序漸進、長效持久、滲透力強的法治教育方案。融入人類發展史的意識形態需要花費數代人的努力,而法治觀念屬于意識形態的重要方面,只有制定長遠的培養教育方案才能使人心扎出法治之根。最后,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可以與司法部門合作,共商共建法治建設實踐基地。在鄉村建設法治基地是實現司法資源下沉的有效決策,人們通過實踐基地管理、實踐理論檢驗、實踐項目孵化等多種方式引入、吸納、攝取、同化外部的司法資源,使得內外部資源同頻共振,為法治鄉村建設做了有力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