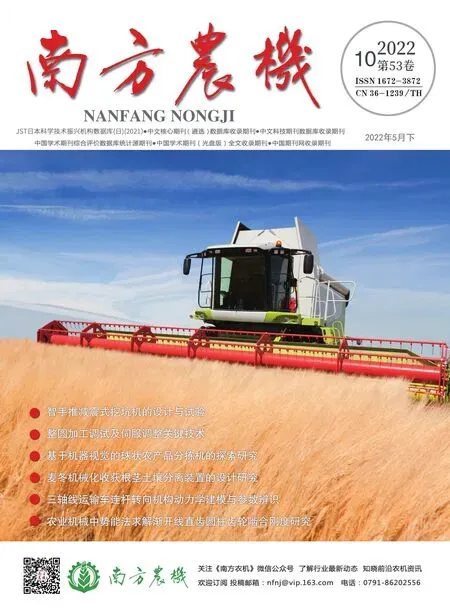數字鄉村背景下鄉村文化的多維共振
吳 婕
(貴州財經大學,貴州 貴陽 550025)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之所以“鑄魂”,就是要依托優秀文化革新人類的思想觀念、精神氣質、生活形式,間接影響人類的認知方式、思維形式、實踐活動,最終優化生活質量、豐富精神世界、提升人文素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鄉村振興既要“塑形鑄魂”,也要“疏通筋脈”,數字化作為鄉村文化發展的著力點是打通文化振興這一“任督二脈”的必然要求。將數字技術應用于鄉村文化振興的內容生產、媒介融合、人才培養各個環節,是喚醒鄉村文化獨特魅力,完善鄉村文明基礎建設,實現鄉村文化價值需求的必然路徑。數字鄉村文化振興應以政策為邏輯出發點,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主心骨”與“脊梁柱”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方向指導和經驗借鑒。在國家政策的持續引領下,鄉村振興最終會從宏觀戰略落地到微觀政策,要持續提升地方的政策解讀能力和執行能力,逐步明確發展路徑,走高效率、有特色、可持續的數字文化振興之路。
1 數字鄉村背景下鄉村文化的多重困境
隨著國家“數字鄉村戰略”的實施,將數字技術運用于鄉村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過程中是文化振興的內在要求,鄉村文化發展有了新的契機和方向。但是長期以來,鄉土文化自信消解、文化產業效益低迷、城鄉數字鴻溝等諸多因素制約了我國鄉村發展。因此,筆者以當前鄉村文化振興面臨的多重困境及成因分析為邏輯出發點,探索數字媒介對于鄉村文化建設以及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意義。
1.1 鄉村文化自信的逐漸消解
“鄉土文化所面臨的多重危機,在載體、內容和形式上消解了鄉土文化自信。”[1]鄉土文化當今所面臨的境況日益嚴峻,鄉村文化的傳播主體、實踐形式以及物質載體均面臨不同層面的危機,各領域的相互碰撞導致鄉土文化自信開始迷失與消解。在精神層面,現代城市文明深刻改變了鄉村社會的生存環境,并隨之影響村落個體的文化情感。毫無疑問,都市社會所呈現的繁榮魅力對絕大多數的村落個體而言是巨大的。“城市是水泥的、理性的……交換價值的。鄉土社會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產的、熟悉的、整體的、血緣的、實用價值的。”感官性危機隨之出現,即村落文化的離散性、多樣性和斷裂性給村民造成了精神寄托的“迷失”感,情感依賴的“疏離”感,價值歸屬的“游離”感[2]。在文化傳承層面,出現文化存續危機[3]。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出現明顯的“空心化”現象,作為“文化精英”的民間工匠和傳統技藝人背井離鄉,具有地域特色的傳統文化遺產面臨失傳。民間花會、曲藝雜技、地方戲曲等傳統文化市場微弱,各種民俗儀式已失去傳統文化功能。在物質層面,出現文化環境危機。受文化資本的影響,鄉村居民對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認知被重構,逐漸以經濟效益作為推動鄉村文化建設的目標,很多具有重要意義的傳統文化在此過程中日漸凋敝。
1.2 鄉村文化產業的多重制約
我國現有鄉村文化產業正在經歷從無到有的快速發展時期,然而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過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制約各地實際的文化產業發展并不充分。首先,對鄉村文化資源所蘊含的精神價值縱向挖掘程度不深。當前一些地方招商引資部門促進當地文化產業發展時,資源多重效益發揮不夠,文化建設存在“做虛功”現象,對于鄉村文化信息的數字轉化僅局限于表面。沒有對鄉村文化資源的起源發展過程以及更深層次的人文精神價值內涵進行深入探析,使得文化建設與地方產業發展相結合。其次,長期以來我們以簡單的個體單向性生產為主,結合互聯網完善新型鄉村文化產業模式的程度不深,導致產業結構無法升級,難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最后,多元協調聯動機制不明。目前政府、社會、市場和農民群眾的協調聯動機制還沒有形成,市場未充分發揮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調節作用,農村文化市場規模小,文化市場體系以及后續監管體系不完善,鄉村文化發展的“市場導向”意識還不夠。
1.3 鄉村文化服務的供給失衡
客觀歷史原因造成的城鄉二元體制不僅導致城鄉文化之間的差距,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以及區域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配置也存在不均衡的現象。一方面,城市文明以現代文明的形式走進鄉村,目前公共文化供給在服務設施、項目體驗、活動組織方面均集中于縣域,鄉村的文化服務建設不完善。面對“空心化”鄉村的社會現實,留守兒童作為鄉村文化建設的后勁力量,在獲取新知識時受到一定限制,留守在鄉村的空巢老人接受和傳播文化的能力微弱,符合老年人群體需求的娛樂文化活動很少。另一方面,東西部地區的“數字鴻溝”依舊很大。雖然全國已基本建成鄉村數字文化平臺,并逐漸覆蓋中央、省、鄉鎮、村落四級。相較于GDP、失業率等具有經濟屬性的政績指標,鄉村文化建設具有一定的行政-社會屬性,該類政績指標不易測量。江浙滬等發達省份有更多的財政資源以及政策偏好進行鄉村文化服務建設,但經濟欠發達的偏遠地區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部分山區未建設或不能及時更新數字農家書屋、電子圖書館、數字閱覽室等公共文化平臺信息。農村地區的文化生態復雜,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個性化低、重復性高,數字文化服務的供給內容與形式沒有充分滿足農民的多樣需求。
1.4 鄉村文化互動的程度淺顯
如今居住于城市的大部分居民或其祖輩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通過對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概念的深刻辨析,可以看到從鄉土社會中孕育出來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底色[4]。僅僅依靠鄉村內部的留守群體再生產鄉村社會中的文化價值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重視走出鄉村又再度返鄉的村民,這些“精英”(例如“網紅”李子柒、城市工作的退休職工、創業大學生等群體)返鄉后會重構鄉村社會內部規則,強化鄉村社會內部力量,革新鄉村社會文明風貌。但這種更有助于傳統鄉土文化實現現代性轉換的轉化過程似乎過于緩慢,中國鄉村的數字文化數字信息傳播基本上都是單向以及扁平模式,鄉村文化傳播感染力不足,群眾無法獲得更強烈的文化共鳴,因此缺乏積極性與渠道參與鄉村文化建設。
2 數字鄉村背景下鄉村文化的多維共振
文化空間是人們發生情感、表達情緒、寄予心靈盼望的場所,在這個領域可以感受豐富的文化生活和文化體驗,具有動態性、不可逆性、意識形態性等特性。文化空間表征著人文內涵、物理場景、虛擬生活等邏輯層次,不同維度的文化空間重合在一起能夠充分度量一個地區的整體文化風貌。現代化社會文化價值觀念介入鄉村后并不意味著鄉村文化的消失,只要在“現代”與“傳統”的天平之間找到平衡點,建立“數字”“文化”與“空間”的聯系,鄉村文化必將重構生存空間并成功實現振興,不斷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2.1 數字媒介重振人文空間
人文空間是鄉村文化的重要場景,既包括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族譜家訓、價值觀念、道德傳統等精神文化,也包括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習俗禮儀等行為文化,以及有益于維護村社穩定、成員利益、村莊發展的制度文化。民間音樂、農耕習俗、曲藝雜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人文文化的硬核內容,需要通過數字存儲和傳播技術搭建平臺,將具有文化本真之美的人文景觀傳承并傳播出去。一方面,以技術為驅動力加速傳播媒介融合。要打破以往分裂的鄉村文化傳播格局,就要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5G 等現代信息技術革命成果,引導鄉村自媒體生態良性發展,在相關政策的引導下推動鄉村媒體向現代化轉型,影響文化傳播的廣度、深度、力度。另一方面,以技術為支撐力凸顯文化魅力。近年來,人工智能、VR/VA 技術、可視化技術、多媒體交互技術等先進數字手段將特色鄉村文化以更為立體、生動、逼真的方式展示給群眾,同時掌握數字技術的村民還積極挖掘鄉村特色文化,延伸鄉村文化的內涵,打造具有辨識度的鄉村文化品牌,有效破除“千村一面”的困境,實現鄉村文化價值認同[5-7]。
2.2 數字文化重構生產性空間
鄉村文化產業是振興鄉村經濟的重要途徑,也是鄉村文化主體挖掘鄉村文化潛在經濟利益的內在動力。傳統農業、旅游業、餐飲業構成農村生產性空間的主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的注入為生產性空間帶來新的活力,數字文化產業以數字技術為載體,以文化內容為核心,為鄉村文化與鄉村經濟的融合發展提供了新思路,這一新型產業形態的出現重新構建了鄉村生產性空間的現代意象。首先,數字技術賦能高質量數字文化產品的生產與供給。以鄉村優秀文化為核心內容,創作和生產數字文化產品和數字文化服務,例如將優秀的鄉村文化以及特色民族文化基因注入動漫、游戲、網絡等數字文化產業中,可有效提高鄉村文化發展的質量,同時也推動著農村經濟逐漸轉型現代化。其次,數字文化產業的高度融合性優化了鄉村文化產業形態。在數字文化產業沒有發展起來之前,文化產業往往與傳統農業的養殖業、種植業和工業的制造業等相結合,為人們供給蔬菜、糧食、肉蛋奶等產品。但現在,農業可以與休閑娛樂、鄉村旅游、餐飲業、物流運輸業有機融合,工業也可以與節慶會展業、智慧鄉村建設、農村電商、特色小鎮等有效融合。不僅推動了鄉村文化的復蘇,也迭代升級了符合時代背景的鄉村文化產業發展體系[8-10]。
2.3 精準供給重塑物態空間
物態空間的文化場景表現為可感知的物化形態,自然風光、農村建筑、地貌形態、文化遺址等構成了古色古香的鄉村社會風貌。物態空間是地方政府推進鄉村發展的重點,農家書屋、文化廣場、文化驛站等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一方面,要精準捕捉物態空間的文化內涵。現代文明的快速推進使得一些古村落和古城鎮得到不同程度的開發,把“物”的建設和“文化”的傳承相結合,增強村落居住群眾的文化歸屬感、體驗感和認同感。另一方面,要精準捕捉村落群眾的服務需求。在數字化時代,人們接受文化信息的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要通過數字化的信息技術精準識別需求,完善需求采集機制,優化信息整合和分析、供給決策以及反饋評價的“一條龍”服務能力,充分運用數字資源對接公眾需求,彌補城鄉以及區域存在的“數字鴻溝”,實現高質量和高效益的服務供給。
2.4 數字教育重建網絡空間
鄉村社會中網絡空間的文化場景由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構成,表現為現實生活中各個村民之間構成的關系網絡空間,以及數字信息時代背景下智能網絡技術構成的虛擬網絡空間[11]。一是強化鄉村技術人才體系。技術人才是數字鄉村建設的基礎,既要關注數字鄉村人才的內部培養,發揮鄉村文化名人的帶動作用,也要重視外部引進,提高鄉村文化能人在鄉村社會的影響力。同時也要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完善招賢納士機制,吸引人才在農村扎根,從而為數字鄉村文化建設提供技術支撐。二是加強數字鄉村信息化力度。數字課堂、遠程教育等教學方式使得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流入農村,應完善鄉村中小學的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高鄉村教師的數字化教學水平,從而使得鄉村不同身份的主體都能充分享受數字文化教育。
3 結語
在數字鄉村和鄉村振興的雙重戰略背景下,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應靈活轉變視角,數字鄉村文化既能盤活其文化“存量”,也能帶來文化“增量”[12]。賦予鄉村文化以空間意義,以傳播媒介、產業發展、服務供給和信息教育的視角為出發點,實現鄉村文化人文空間、生產性空間、物態空間以及網絡空間的共同振興。將更全面更立體地探討數字鄉村文化的發展方向,把現代鄉村社會村民消極的感官危機轉化為積極的感官沖擊,提升鄉村社會整體經濟實力以及物質文明程度,實現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