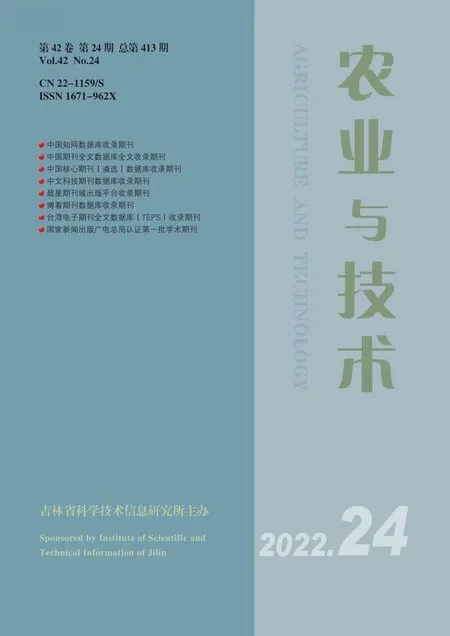基于土地利用變化的陜北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分析
周浩浩 徐清昊
(長安大學土地工程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土地利用是反映人類生活和生態系統之間耦合關系最根本的表現[1]。土地利用的變化會改變生態系統服務體系,進而改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首次由Costanza[2]提出,謝高地等[3]在此基礎上改進了ESV系數,估算了我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建立了一套可廣泛應用于評估我國生態系統服務的ESV系數;當量因子法由于具有操作簡單、綜合評價、適應性強的優點而被普遍采用[4]。
1 研究區概況
陜北地區位于黃土高原的核心地區,在行政區劃上包含陜西省的延安和榆林兩市,北與內蒙古的毛烏素沙地接壤,東部緊鄰山西省,西部接寧夏回族自治區和甘肅省。總面積92521.4km2,基本地貌類型是黃土塬、梁、峁、溝、塬,氣候干旱少雨,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多樣的地貌、流水侵蝕和各種程度的人類活動作用下,生態系統比較脆弱,易受破壞。
2 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的土地利用數據為自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獲取的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5期的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社會經濟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官網的《陜西省統計年鑒》和《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等。
2.2 研究方法
2.2.1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也稱馬爾科夫矩陣,可全面反映區域內各用地類型的轉移方向與轉移數量,被普遍應用于土地利用變化研究,能很好地展示土地利用格局的時空演變過程[5],計算公式:

式中,Sij代表n×n矩陣;S代表面積;n代表土地類型數;i和j分別代表研究期初始和末尾的土地類型。
2.2.2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可以直觀地反映某種土地類型的變化趨勢以及變化速度,計算公式:

式中,K表示某一類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Ua和Ub表示研究期初始和末尾某地類的面積;T表示研究時長,當T的時段設定為年時;K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的年變化率。
2.2.3 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
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反映某種土地類型轉變為其他土地類型的變化速率,計算公式:

式中,LC為研究期內某區域的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LUi為研究初期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ΔLUi-j為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轉為非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絕對值;T為研究時長。
2.2.4 生態服務價值計算
謝高地等學者的當量因子法首次測算了全國的生態服務價值,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并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被廣泛采用。劉浩等[6]指出,傳統當量因子法計算出的結果存在誤差。本文結合研究區的實際情況,選取小麥和玉米2種主要糧食產物為代表[7],根據農產品的單位面積的產值進行修正,根據修正結果,1個標準生態系統服務經濟價值等效系數為1039.25元·hm-2,進一步計算陜北地區的生態服務價值總量。計算公式:

式中,ESV是研究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VCi是第i種地類的單位面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Ai為第i種地類的面積;i為土地利用類型;ESVf是第f項生態系統服務價值;VCfi是第i種地類的單位面積的第f項生態系統服務價值;f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項數。

表1 陜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
3 結果與分析
3.1 土地利用時空變化
近20a內,陜北地區的土地利用類型在空間的分布上,主要以林地、耕地和草地為主,三者之和達研究區面積的93%左右,林地主要分布于研究區的南部地區,且集中分布于黃龍山和洛河河網地區,耕地和草地在研究區廣泛分散分布,且在研究區的東北部地區有集中趨勢,未利用地主要為與毛烏素沙地連接的沙漠化土地,集中分布于榆林北部地區,建設用地呈中心發散狀,集中分布于延安和榆林市的中心城鎮地區。分布位置見圖1。

圖1 陜北土地利用類型
陜北地區土地利用在時間上發生的變化,從總體上來看,近20a間的變化主要在林草地與耕地之間發生,表現為耕地的集聚減少與林草地的快速增加同步進行。從具體地類上來看,耕地面積從2000年的28453.44km2減少至2020年的25189.90km2,共計減少了3263.54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4%;與之相對應的是林地,由最初的11052.39km2增加至12289.15 km2,凈增加1236.76km2,增幅約10%;草地由2000年的34753.43km2增 加 至36083.63km2,凈 增 加1330.20km2,增加面積占總面積的2%;建設用地呈現急劇擴張態勢,由初始的297.90km2增加至1375.49km2,增幅達450%;以沙地為代表的未利用地,減少了約378km2,水域面積基本上保持不變。具體變化見表2。

表2 陜北土地利用類型面積
3.2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
20a來,除去水域面積波動不大外,其他5種地類均有明顯的地類轉移變化。2000—2020年,耕地呈大幅減少態勢,主要流出為林地、草地和建設用地,對其進行補充的地類主要為草地、未利用地和林地;林地轉出面積較小,主要為耕地和草地對其流入;草地轉出方向主要是耕地、林地和建設用地,轉入的主要是耕地;水域面積有小幅度波動,基本保持不變;建設用地呈現快速增加,各個地類均有轉入;未利用地流出方向主要為耕地、草地和建設用地,轉入的主要地類為草地。究其原因,各個地類之間的轉變主要受政策影響較大,耕地的大幅度轉出,與黃土高原的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緊密相關,建設用地轉入也有充分利用沙漠化荒漠化的劣地。具體的結構變化見表3。
3.3 土地利用動態度
從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方面來講,2000—2020年,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單一動態度為負值,建設用地、林地和草地的動態度為正值,且建設用地的動態度最大為18.09%,說明耕地、未利用地和水域呈現減少趨勢,建設用地、草地和林地呈增加趨勢,且建設用地擴張最為迅速。分時段來看,2000—2010年,此前10a耕地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為較小的負值,表明前10a耕地急劇減少;與之相對應的是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林地和草地的動態度為各自的峰值,說明在這2個時段分別為退耕還林和退耕還草最為迅速的時段;水域在整體上呈現波動姿態,在2005—2010年急劇減少,在2010—2015年快速增加;建設用地在2000—2005年為較小動態度,從2005年開始均以較大動態變化,說明陜北地區建設用地急速擴張是從2005年左右開始;未利用地一直以負值變化,說明陜北地區治沙行動從未停止,且在2005—2010年5a間成效最為顯著。從綜合土地利用總態度方面分析,2000—2010年10a間,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較大,且之后緩慢減少,顯而易見,陜北地區在這段時間的地類轉移變化最為頻繁。具體動態度數據見表4。

表4 陜北土地利用動態度
3.4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分析
陜北地區生態服務價值在這近20a間呈先增加后趨于穩定的趨勢,從2000年的888.53億元增加至2020年的914.86億元,在整體上凈增加了26.33億元,說明陜北地區整體的生態得到了改善。
從不同地類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來言,林草地為生態服務價值貢獻的主體,兩者之和占總體服務價值的65%以上,且林草的生態服務價值的變化趨勢與陜北地區整體的生態服務價值變化趨勢保持一致。耕地的服務價值呈現連續下降趨勢,未利用地和水域的生態服務價值在較小幅度保持減少,變化不大,未利用地的生態服務占比最少。具體各地類的生態服務價值如表5所示。

表5 陜北各地類生態服務價值
就不同的生態服務功能方面來看,一級服務功能中調節服務占比最大,達總量的50%以上,接下來為支持、供給和文化服務。除供給服務價值呈現降低趨勢外,其他3種均呈現緩慢增加趨勢;在二級服務功能中氣候調節和水文調節服務功能對生態系統總體的服務功能貢獻較大,分別為217.23億元和204.25億元,并且在變化量上,氣候調節生態服務價值的變化量最大,為11.58億元,且變化率最高,說明在整體的生態服務價值變化中,二級服務價值氣候調節功能的改善做出巨大的貢獻。在所有的二級服務功能變化中,食物生產為唯一負值,這與耕地的減少密不可分,其他生態服務價值均有增加,說明退耕在陜北地區對絕大部分的生態服務功能都有積極影響。具體生態服務價值變化見表6。

表6 陜北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變化
4 結論
土地利用變化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轉變的重要驅動因素[8],會改變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根據土地利用進行生態服務價值的研究切實可行的。通過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近20a內土地利用變化主要在耕地、林草地和建設用地之間發生較為劇烈的變化,具體表現為耕地的減少,林草的增加和建設用地以城市中心為基點的呈發散狀向外部急劇擴張,并且在北部的城市擴張同時利用了沙地,有較高程度的節約集約利用土地。在土地利用結構轉變方面,耕地減少,并且主要轉變為草地、林地和未利用地,較少量流向建設用地,林地增加,絕大部分是耕地、草地轉變為林地,草地也增加,來源主要為耕地和未利用地,建設用地劇烈增加,來源主要是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中的沙地。在變化速率方面,只有建設用地最為突出,且從2005年后增幅巨大。深入探究原因可知,陜北地區的退耕還林還草政策,是耕地以及未利用地變化的主要原因,建設用地的變化與陜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并且未利用地的范圍線有明顯的后退,且在原來其所屬范圍內,有建設用地的明顯擴張,呈現人進沙退的風貌。綜合來看陜北地區的風沙治理,生態改善政策成效顯著,且經濟活動比較過熱,有較高的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的意識。
近20a來,根據量表測算的結果顯示,陜北地區的生態服務價值有較大的增加,由最初的888.53億元增加至914.86億元,凈增約26億元生態服務價值。從地類來看,林地和草地這2種地類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貢獻率最高,變化趨勢控制了整體服務價值的走勢,且在前10a增幅明顯,后10a內趨于穩定。從生態服務功能方面來看,調節服務功能占比最大,并且逐年增加,在二級服務功能中氣候調節和水文調節占比較大,食物生產服務功能是所有二級服務功能中唯一減小的,其他功能均有所增加,追根溯源,與耕地的大幅減少和林草的增加密不可分。總而言之,陜北地區在整體上生態環境改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有所增加,除食物生產功能有所下降外,其他生態服務功能均得到改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