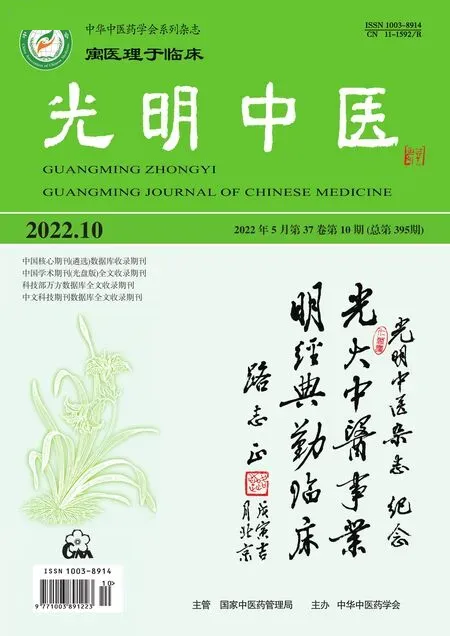從通腑氣角度探討張錫純運用建瓴湯治療腦充血
于汶仟 盧 健
“腦充血”這一病名由清末民國的醫學家張錫純首次提出,其癥狀與現代西醫的高血壓病、腦出血相符合,甚至包括腦出血之前的一系列癥狀。眾所周知,腦充血以其高發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殘率的特點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質量及生命安全。隨著醫學不斷發展,通腑法已成為腦充血的治療大法之一,無論是化痰通腑法[1],還是瀉熱通腑法[2]都已被證明具有很好的治療效果,而筆者在研究張錫純首創治療腦充血疾病的建瓴湯時發現張氏擬方中大黃、赭石、柏子仁和桃仁就有通腑氣之效,而張氏并未在書中指出,遂筆者從通腑氣角度探討張氏運用此方治療腦充血疾病。
1 立足中醫理論闡釋以通腑氣治療腦充血的合理性
1.1 上逆之氣為病機關鍵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明確指出西醫之“腦出血”在中醫古籍中早有記載,只是此前人們將其歸類于具有共同臨床表現的“中風”之中,并未準確規范具體病名,而后張氏衷中參西提出“腦充血”即“出血性中風”,才逐漸被大家接受[3]。《黃帝內經》中有:“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反則生,不反則死”,張氏云:此即西人所謂腦充血之證。從中醫理論講,氣為血之帥,氣行則血行,若其氣上行不返,升而愈升,血亦隨之充而愈充,腦中血管可致破裂,西人未深究病源,但名為充血,不曉上行之氣乃病機之根本,“血之與氣并走于上”為腦充血根本病機,欲使上行之血返回,必先降其上逆之氣。
1.2 腑氣通暢與否對腦充血疾病轉歸有重要影響腑氣不通是腦充血最常見的現象,最近研究發現,腦充血后便秘發生率高達 66%[4],而胃腸功能紊亂等胃腸道疾病也可以導致相關系統發生障礙,反過來導致腦血管病的發生或加重腦充血病情[5]。國醫大師周仲瑛認為腑氣不通之證會夾雜瘀熱之毒,使得燥屎壅結于腸道,濁氣不降,邪無出路,加之胃腸積熱,更加劇火盛陽亢之勢,病必加重。也有學者[6]通過整理病例發現在中風急性期伴有意識障礙者應用化痰通腑法治療后,患者意識障礙持續時間明顯縮短,筆者認為此是瘀熱之毒借陽明為出路從下而解,說明此法有助于意識恢復,從臨床角度證明了腑氣通暢對腦充血疾病的轉歸有重要意義。
現代研究也證實腑氣是否通暢對腦充血疾病轉歸具有重要意義,胃腸道受自主神經支配,而腦充血會損傷中樞自主神經網絡,導致腦充血患者存在交感、副交感神經系統功能紊亂[7],其常見問題中就包括腸道功能紊亂引起的便秘。由于膽囊收縮素-8(CCK-8)參與了急性腦血管病腦細胞損傷的病理過程[8],并且能夠保護神經細胞[9],而具有瀉熱通腑作用的涼血通瘀方可以增加腦充血患者腸組織及腦組織中膽囊收縮素-8的表達及含量[10],對腦組織疾病具有很好的恢復作用,說明從分子學角度也可以證明通調腑氣是否及時、得當對病情的轉歸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
1.3 通腑氣有助于降上逆之氣張氏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提出腦充血征兆之一“胃中時覺有氣上沖,阻塞飲食不能下行;或有氣起自下焦,上行作呃逆”,提示中焦氣機逆亂在疾病中有重要體現。近代醫家張伯龍、張山雷總結前人經驗,提出腦充血的發生主要在于肝陽化風,氣血并逆,上犯沖腦,且張伯龍對該病病因病機等方面的認識對張氏有很大影響[11]。而腦充血還有一征兆,即“其脈必弦硬而長”,弦脈為肝病之脈,《素問·生氣通天論》中有:“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肝為將軍之官,中寄相火,若人情志易怒,肝火過升,張錫純認為會引動膽氣、沖氣、胃氣相并上升[12],而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六腑以通為用,以降為和”,而胃氣上逆必然會加重氣血上行之勢,因此通降腑氣使得燥結有所出路,亦予上逆之氣以下行之通路,借通降陽明之氣既可平降上亢之肝陽,又可引上行之血下行,可謂一舉兩得。
2 建瓴湯通腑氣之體現
建瓴湯為張錫純所創,由赭石、生懷山藥、懷牛膝、生龍骨、生牡蠣、生地黃、生杭芍、柏子仁組成,具有平肝潛陽、引血下行的功用,張氏用以治療具有腦充血征兆者,后其友人朱缽文告其加大黃、桃仁治療腦充血效果更佳,“初服建瓴湯一兩劑時,可酌加大黃數錢,其身形脈象不甚壯實者,若桃仁、丹參諸藥,亦可酌加于建瓴湯中”。
2.1 方中大黃乃通腑氣之要藥建瓴湯從《金匱要略》風引湯化裁而來,原用以除似腦充血之熱癱癇證,《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瘛疭,日數十發,醫所不能治者,此湯主之”。方中大量寒涼石藥佐以性尤下降的大黃治療此證,張氏認為風引湯中大黃之用為“引逆上之血使之下行”,而筆者認為這更有通腑瀉下以除熱之功,為張氏運用通腑法治療腦充血之淵源。《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曾言大黃味苦,氣香,性涼。性雖趨下而又善清在上之熱,以其氣香,故少用之亦能調氣,且降腸胃熱實以通燥結。自古作為下法所常用的大黃有蕩滌胃腸之力,《神農本草經疏》言:“大黃能泄肺中之閉,又泄大腸,走而不守,能泄血閉腸胃渣穢之物,一泄氣閉利小便,一泄血閉利大便”。身體素來強壯或便秘嚴重者可稍加大黃蕩滌腸胃,中焦氣機得通,自然有助于上逆之血下行,而虛弱者可稍加其他具有輕微通腑氣作用的藥物以調暢氣機也未嘗不可。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研究大黃的活性物質對腦組織抗炎和抗氧化作用,現代多篇文獻表明大黃對腦充血進行干預可改善患者胃腸狀況,有助于患者病情好轉[13-15],這說明從現代藥理角度能夠證明使用大黃不僅能通腑氣助血下行,還能恢復腦組織病變。
2.2 尚有赭石 柏子仁 桃仁助大黃通腑氣《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記載赭石色赤,性微涼,其質重墜,善鎮逆氣,通燥結,用之得當能見奇效。袁震土[16]曾總結張錫純發現赭石降胃氣有六大特長,其重墜之力不僅能引胃氣下降直達腸中以通大便,還兼有安沖氣使其氣不上沖、制肝木使其氣不上干的作用,解決了大部分的氣機上逆問題,其性非寒涼開破,降胃通便引相火下行,使頭目眩暈自除又不傷分毫正氣,實有通腑氣之奇效。張錫純在周良坡夫人醫案中記載:患者有妊,連連嘔吐,諸藥食不進,大便亦不通行,自覺下脘之處疼而且結,張氏單用赭石四兩,又重羅出細末兩許,將余三兩煎湯,調細末服下,其結遂開,大便亦通,安然無恙,至期方產。充分體現赭石開結通腑而不傷正氣之奇效。
而建瓴湯方中配伍柏子仁不僅有理肝氣、滋腎水之功,更以其油質甚多而性不濕膩的特質具有通腑氣之效[17]。《本草綱目》記載:“大便虛秘,松子仁,柏子仁,麻子仁等分,研泥溶白蠟和丸梧子仁大,每服五十丸”。《醫法青篇》言:“年高不焦陰虛,六腑不利,多痛便難,乃幽門之病,宜五仁潤燥以代通幽,是王道之治。火麻仁,郁李仁,柏子仁,桃仁,松仁,當歸,白芍,牛膝,人中黃,脈小弱,形瘦腸,風已久,食少便難,噯噫泄氣,自寬爽釋,乃腑病,通即為補,仿東垣通幽意”。現代化學成分研究發現柏子仁中的油脂占總重的 57.40%[18],還有研究證明[19]柏子仁具有腸推進作用,且含油量增加可提高小腸推進率,含油量在30%時小腸推進作用最為明顯。臨床報告[20]證明柏子仁研碎煎煮后加入蜂蜜可以有效治療老年人便秘,可見柏子仁具有潤腸通便以及通腑氣的作用。
桃仁也同樣因其富含油質而有潤腸通便之效,且能破除腦中瘀血,《神農本草經指歸·卷四》言:“其仁充滿多脂,可入藥用……桃仁之脂,脂陰氣也,血亦陰氣也,取其脂,與血之陰,同類相從,得陽氣內藏合。桃仁之脂潤其瘀滯之血,開其血道之閉,血之滯得陽行之,血之閉得陽開之,而內結之癥瘕可解”。
3 小結
建瓴湯全方補瀉兼施,寓通于降,龍骨、牡蠣平肝潛陽以制陽亢;牛膝引上逆之血下行;懷山藥益腎氣、滋腎陰;生杭芍平肝斂陰潛陽;柏子仁潤腸通便;桃仁還可活血化瘀;生地黃制陽亢、滋真陰;赭石重鎮降逆,安沖氣又能通腑氣;生大黃瀉下通腑,予瘀毒以出路,并調暢一身氣機,但其藥性猛烈,易傷人體正氣,遂佐以山藥、芍藥、生地黃以滋陰緩急,使得祛邪不傷正,如此配伍,選藥考究,用以治療腦充血可見用心良苦。
張錫純用建瓴湯治療腦充血疾病具有良好的療效,其離不開通腑氣法的運用,雖然當時張氏并未指出通腑氣法對腦充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但通過中醫理論、現代藥理及臨床研究,都可證明這一學術思想的正確性,拓展了大黃、赭石、柏子仁及桃仁的使用范圍,并為研究張錫純治療中風學術思想提供新的方向,為建瓴湯治療腦充血提供了另一種治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