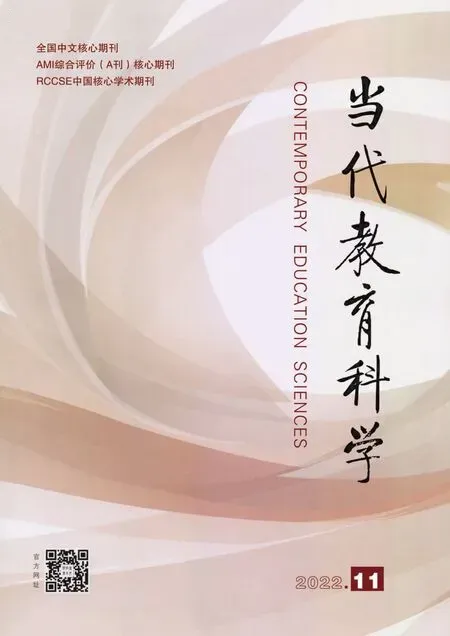“變”與“不變”:智能時代學校教育變革的圖景掃描與價值堅守
● 鹿星南
當前,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圍內呈井噴發(fā)展態(tài)勢,深刻變革著人類既有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和認知圖式,也正在吹響新一輪教育變革的號角。世界各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對教育的革命性影響,紛紛布局人工智能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和應用政策,以期推動人工智能與教育的深度融合。學校是貫徹教育思想和承載教育活動的重要場所,其形態(tài)、結構、運行機制等也因應技術革新不斷發(fā)生改變。人工智能引發(fā)的新一輪教育浪潮如一場“哥白尼式革命”,正在為學校變革賦能,涌現(xiàn)出“智慧校園”“未來學校”“無邊界學校”“智能教學系統(tǒng)與學習平臺”等實踐創(chuàng)新新樣態(tài)。2021 年11 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發(fā)布的《一起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為教育打造新的社會契約》報告中呼吁:“學校也應該被重新構想,以便更好地推動世界向一個更加公正、公平和可持續(xù)的未來轉變。”[1]毋庸諱言,人工智能與學校教育相互賦能的趨勢日益明顯,為打造智能化、個性化、開放化、終身化的學校教育體系發(fā)揮了鮮明的“頭雁效應”。然而,當社會各界對人工智能加速學校教育變革歡呼雀躍之時,對其所引發(fā)的不確定性也憂心忡忡。因為人工智能的學校教育應用依然存在諸多“不可為”,“幾乎每一次教育技術運動都留下‘新瓶裝舊酒的尷尬結局’”。[2]基于此,本文意在探討人工智能對學校教育變革的積極影響,明晰人工智能之于學校教育變革的邊界與限度,把握智能時代學校教育變革的價值堅守,力圖尋求智能時代學校教育變革的本真。
一、人工智能與學校發(fā)展:內涵與演進
(一)人工智能的由來及其內涵
人工智能肇源于人類試圖用機器模擬人的智能以期解放勞動的想象和憧憬。但囿于彼時的技術水平,人工智能的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1950 年,人工智能先驅艾倫·圖靈(Alan Turing)在《計算機與智能》[3]一文中以“機器能夠思維嗎”這一問題以及評估機器智能水平的“圖靈測試”,為人工智能的研究貢獻了理論可能。1956 年,在美國達特茅斯會議(Dartmouth Conference)上,以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為首的科學家共同探討“如何制造機制模擬人類的學習及其智能”[4],正式提出人工智能這一學術性概念。歷經60 多年的沉浮,當前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革命的核心驅動力,正成為全球各個領域的新寵兒。然而,關于人工智能是什么的問題,可謂眾說紛紜,仍存在諸多爭議。面對歧路紛出的人工智能概念迷宮,我們主要從如下幾方面進行闡釋。從技術論層面講,人工智能是會聚了互聯(lián)網、云計算、大數據、機器學習、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人機交互、自然語言處理、機器人等技術和工具的集合體,是模擬人類智能的技術創(chuàng)造物。從本體論層面講,人工智能是依托“計算”或“算法”實現(xiàn)人造的、模擬的、拓展的智能,但其對人類智能只是“局部上超過和整體上不及”[5],根柢在于服務人類及社會發(fā)展需要。從認識論層面講,智能機器和人—機系統(tǒng)作為一種基于算法和數據挖掘的知識發(fā)現(xiàn)新模式,擴充了認識主體、認識客體、認識工具等認識活動要素的內涵和范圍,孕育了人工智能認識論。從方法論層面講,人工智能是研究和模擬人類智能運行機理的方法、手段、范例等的綜合,逐漸從單一性的機械還原方法論轉向整體性的“信息生態(tài)方法論”[6]。從知識論層面講,人工智能是交融了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物理學、生物學、數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等多學科知識的一門綜合性交叉學科。由上觀之,人工智能作為憑依算法、大數據分析和計算機芯片等為載體的智能機器和人機系統(tǒng),是研究人類智能行為的運行機理和規(guī)律,以期投射、模仿、延伸甚或超越人類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工具)、學科。
(二)學校發(fā)展的歷史演進
學校作為開展教育教學活動的主要場所和專門機構,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因應社會變遷、技術革新與教育發(fā)展而趨向改進與完善。學校肇源于農耕時代的奴隸社會,主要是生產力發(fā)展、腦體分離、文字誕生以及階級分化的產物。據考證,“學校最早出現(xiàn)在古代東方各國”[7],如埃及的宮廷學校、夏朝的“庠”“序”“校”、印度的古儒學校等。農耕時代的學校告別了原始社會“非進取性的自適應的教育”[8]活動,依循等級性邏輯不斷發(fā)展,帶有鮮明的宗教或家族色彩。具體來講,在教育目的方面,旨在為統(tǒng)治階級培養(yǎng)治術人才和教化勞動人民,我國西周時期的“學術官守”就是最有力的注解。教育內容趨于知識化和抽象化,形成了以傳授政治、宗教、倫理道德等古典人文知識為主的“六藝”和“七藝”。教學組織形式注重個別施教,出現(xiàn)了官學和私學并存的教育體制。
18 世紀中葉以降,蒸汽機、電力的相繼問世和應用,開啟了世界工業(yè)化的歷史進程,社會形態(tài)由農耕社會躍遷至工業(yè)社會,發(fā)生了以機器大工業(yè)代替工廠手工業(yè)的重大生產方式變革。在工業(yè)時代,大規(guī)模標準化生產方式急需大量具備一定生產知識的產業(yè)人才,加之對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渴求,以班級授課制為基礎的現(xiàn)代學校應運而生。因應工業(yè)化浪潮的持續(xù)演進,學校發(fā)展的規(guī)模和速度達到了一個空前高度,極大地提高了教學效率,學校教育逐漸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現(xiàn)代學校承襲了工業(yè)文明所標榜的集中化、標準化、同步化邏輯,呈現(xiàn)出此種發(fā)展景象:“管理嚴格,學生缺乏個性,對座位、班級、評分等嚴格地規(guī)定,老師擁有權威性角色。”[9]
進入20 世紀中后期,電子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崛起與發(fā)展掀開了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篇章,人類文明開始向信息時代邁進。隨著信息化進程的全球式輻射,信息技術以網絡化、數字化、定制化的工作形態(tài)開始解構與顛覆機器大規(guī)模制造模式,塑造和“再結構”著人類社會的各行各業(yè)。面對工廠式學校模式日益顯現(xiàn)的弊端,世界各國紛紛將信息技術應用到學校教育中,涌現(xiàn)了計算機輔助教學、網絡學習、多媒體教學、數字校園等學校信息化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知識來源、豐富了學習環(huán)境、改善了教學手段,切實催化學校教育產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但是,信息時代的學校變革更多是在基礎設施、資源建設等方面發(fā)力,出現(xiàn)了盲目亂用、重復建設、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等問題,一直受到“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和“喬布斯之問”的糾纏與拷問。究其原因,技術至上主義和工具理性思潮的泛濫,使得信息時代的學校變革實踐“僅僅關注設備如何能被使用,卻不思考這些技術應該如何被使用”[10]而忽視了學校教育教學質量的提升。
進入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因應移動互聯(lián)網、大數據、物聯(lián)網、虛擬現(xiàn)實等智能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和廣泛應用,人類正在加速步入智能時代。然而,當前的學校教育仍表現(xiàn)出工廠式的運行模式和流程,規(guī)模化和個性化的教育發(fā)展取向已難以從傳統(tǒng)學校形態(tài)中獲得更多支持。智能時代的撲面而來,促使人工智能賦能學校變革的探索與實踐不斷演進,學校的教、學、評、測、管等都將發(fā)生一系列變革。
二、非變不可:智能時代學校教育變革的圖景掃描
基于社會轉型對高質量人才的期許,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時代命題,以及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學校變革的規(guī)模化實踐,學校的內涵和外延得以不斷延展,必將推動智能時代學校教育呈現(xiàn)出新的發(fā)展圖景。
(一)學習空間重構:智能感知、聯(lián)通融合、具身體驗
學習空間是承載學校教育教學活動的重要實踐場域。2015 年開始,美國新媒體聯(lián)盟發(fā)布的《地平線報告》頻繁將“學習空間的設計與重構”作為影響學校變革的關鍵趨勢。進入智能時代,智能技術的深度嵌入和現(xiàn)代學習理論的不斷革新,賦能學校的學習空間表征出新的發(fā)展樣態(tài)。其一,智能感知。依托多種新興智能技術和智能設備實現(xiàn)實時感知學校的物理環(huán)境、學習者的個性特征和學習情景,追蹤與分析學習行為全數據,幫助師生開展學習路徑自動規(guī)劃、學習材料個性推薦、學習評價精準實施等,從而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適需學習服務。其二,聯(lián)通融合。一方面,技術賦能推動學習不再局限于物化的教室空間,而是與虛擬空間、社會空間和個人空間等無縫聯(lián)通與無感知切換,構建學習發(fā)生的空間連續(xù)體,促成泛在學習和個性化學習的有效發(fā)生。另一方面,采用可移動、可組合的桌椅構建多種教室空間布局及座位排列,設計集成教學、創(chuàng)造、研討、協(xié)作、休息等多種功能的學習空間,支持師生開展多場景教學交互活動。其三,具身體驗。智能時代“在場空間”和“缺場空間”的多維交互融合,通過智能技術的深入應用,構建適應學習者需求的可“自由伸縮延展、動態(tài)演變、情境化”[11]的具身學習空間,更加關注身體的實時“在場”及其與空間各要素的沉浸式交互,加深學習者對知識的知覺、建構與應用。
(二)學習范式轉型:方式拓展、流程再造、路徑重構
當前,教育的重心正“從教學轉移到學習,從說教轉向創(chuàng)造性探究”。[12]人工智能對傳統(tǒng)學校教學的顛覆以及學習空間的智能升級驅動著學習范式的轉型,推動學校教育從單向度、程序式、預設性的教學范式向多樣化、動態(tài)性、生成式的學習范式轉換。首先,學習方式的拓展。智能時代的學校教育將突破或融合傳統(tǒng)學習方式,趨向泛在學習、混合學習、社群學習、人機協(xié)同學習、情境學習、具身學習、無邊界學習等多重樣態(tài)的未來學習方式,不斷拓寬學習深度、賦能學習體驗、提高學習效果,讓學生的學習真正躍升為“建構客觀世界意義、探索與塑造自我、編織同他人關系”[13]的活動。其次,學習流程再造。借助技術支持的認知工具和智慧學習平臺,學生自主選擇或接受平臺推薦學習資源,按照自身需求與特性開展學習,不斷突破“先教后學”的傳統(tǒng)學習流程,基于技術的探究活動、創(chuàng)造活動、交互合作活動將成為未來學習的主要流程。最后,學習路徑重構。借助智能感知技術精準測評與分析學習者學習特征、狀態(tài)和優(yōu)勢,并根據算法推薦模型促成學習需求與學習服務的雙向匹配,進而為每個學生規(guī)劃和提供量身定制的學習指導和學習路徑。
(三)課程體系創(chuàng)新:形態(tài)多元、內容定制、結構靈活
人工智能技術的持續(xù)革新及其所引發(fā)的知識形態(tài)、知識表征、知識傳播、知識價值等知識觀和現(xiàn)代人才培養(yǎng)需求的深層變革,指引著學校課程體系變革的未來動向,進一步促成課程形態(tài)、課程結構、課程內容等朝著更為靈活、彈性的方向發(fā)展。一是課程形態(tài)的多元與豐富。技術的智能化演進和學習空間的聯(lián)通融合,推動“紙本獨尊”的傳統(tǒng)課程階段轉向線上線下混合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fā)展階段。當前,學校領域中興起的微課、慕課、私播課等課程實踐已然表征出課程表現(xiàn)形態(tài)異常豐富和呈現(xiàn)方式多樣化的端倪。二是課程內容的定制與生成。5G 通信技術、移動互聯(lián)網打造了個性化、社會化的教育資源供給模式,推動學校資源供給“從‘電影院形態(tài)’走向‘超市形態(tài)’”[14],并借助大數據分析、自適應學習技術適時為學生匹配與推送個性化學習資源。同時,這些資源所集聚的課程內容也將從統(tǒng)一、預設、單一趨向定制、生成與多樣。三是課程結構的靈活與開放。以跨界融合、互聯(lián)互通為旨趣的人工智能將超越知識本位的分科教學課程體系,通過面向真實問題的項目驅動、多學科的交叉融通,增強各學科知識的貫通及其與自然世界、學生現(xiàn)實生活的聯(lián)結和際遇,從而打造縱向貫通、橫向銜接的高度靈活開放的課程結構,不斷指向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發(fā)展。近年來,美國的HTH 學校、THINK Global School 等一線學校通過跨學科、項目式學習和高水平的學業(yè)標準結合等實踐探索,克服學科知識與生活經驗的割裂困境,進而引領未來學校的變革。[15]
(四)組織管理變革:學制彈性、組織扁平、管理高效
人工智能與學校教育的深度融合趨勢,將解構傳統(tǒng)學校金字塔式的組織管理藩籬,轉向更加彈性、靈活、高效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其一,學制的彈性靈活。智能時代學校將基于學生的特長、興趣等合理安排教學時長、修業(yè)年限、課程設置,或學生結合個人需求自定學習節(jié)奏、自主選擇班級和學習資源,增強不同教育類型和學段的互通與互動。目前,基礎教育階段積極探索的走班教學、選課教學以及新冠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的在線教育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智能時代學制的彈性特征。其二,組織方式的扁平化、分權化。智能時代信息的高速流轉和學校環(huán)境的實時互通特征,能夠拓寬學校不同部門的信息傳播渠道、壓縮縱向管理層級、增加橫向管理部門,將淡化“命令—控制”型的學校組織方式,推動學校變革呈現(xiàn)組織結構扁平化和分權化、組織形態(tài)虛擬化、組織邊界模糊化等趨勢。其三,管理模式的精準高效。完備的學校智能設備和數據采集系統(tǒng)通過對數據感知、信息搜集和決策制定等環(huán)節(jié)的技術賦能,實現(xiàn)校園安全、教與學活動、教育質量、學生體質、學校輿情等學校核心業(yè)務運行狀況的可視化呈現(xiàn)、實時監(jiān)測與精準調控,使學校管理工作更加科學、高效與有針對性。例如,早期學習預警系統(tǒng)通過大數據和學習分析技術來預測導致學生輟學的可能因素或指標,并設計相關教育干預措施幫助有可能輟學的高中生順利畢業(yè)來減少教育不公平。[16]同時,伴隨學校與社會的開放互聯(lián)以及管理權的重心下移,智能時代的學校將從一元管理走向“學校與社會、教育管理部門、社區(qū)、家長等開展持續(xù)性交互”[17]的多元治理格局。
(五)評價模式革新:數據驅動的多元化評價
數據作為智能時代學校教育的重要資產,將成為撬動學校教育評價變革的關鍵要素,促進教育評價模式從基于假設的“小數據”評價或依賴教師主觀推斷的經驗式評價轉向數據驅動的多元化、精準化評價。首先,評價內容的多元化。依托物聯(lián)網、可穿戴設備、視頻監(jiān)控、虛擬仿真等智能技術實現(xiàn)評價數據采集的全樣本、全過程、多模態(tài),支持開展評價對象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的綜合測評,不斷指向個體的整全發(fā)展。其次,評價主體的多元化。人工智能為不同主體參與評價提供了豐富的評價空間和智能教育平臺,既實現(xiàn)了多元評價主體的實時在場與協(xié)商互動,又能多維度、多角度地呈現(xiàn)評價對象的真實情況。最后,評價方式的多元化。一方面,基于智能技術的作文批改、英語口語測試、心理健康監(jiān)測、教育質量監(jiān)測、實際問題解決能力測評等智能評價系統(tǒng)的開發(fā)與運用,實現(xiàn)了評價手段從紙筆測驗、抽樣調查朝著多元化、智能化的方向發(fā)展。另一方面,評價手段的智能化轉變,使得“采集的數據不僅包括學習結果,還包括學習行為、認知過程和心理變化等大量過程性數據,實現(xiàn)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18],進而扭轉評價方法“各行其是”或“一家獨大”的局面。此外,人工智能通過對多模態(tài)數據的全面采集與深度挖掘,動態(tài)把握評價對象的優(yōu)勢與短板,并借助可視化輸出與智能化推送技術使評價對象獲得自適應的評價反饋、精準的教育預測和個性化的教育干預。
三、不可替代性:智能時代學校教育變革的價值堅守
置身于智能時代,“如何最大程度地發(fā)揮人工智能應有的教育價值,正確認識人工智能技術在學校教育中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和限制是教育工作者首要考慮的問題”。[19]據此,智能時代的學校變革應厘清學校人工智能運用的邊界與限度,審視未來學校教育的技術異化,堅守其應然價值立場與內在規(guī)律,超越“去學校化”思潮的悖謬,以價值邏輯引領技術與學校教育的互涉共生。
(一)聚焦生命發(fā)展:堅守學校教育的育人邏輯
不可否認,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賦能使得學校教育在提升知識傳遞和技能訓練效率、改善學習認知方式、優(yōu)化教育資源配置等層面的優(yōu)勢明顯。相對而言,被人工智能浪潮裹挾的學校教育越發(fā)地熱衷通過技術產品或設備的先進性來確保學校的合法性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導致學校教育幽禁在人工智能技術所打造的“技術叢林”之中,人的生命意義與精神存在也因對技術的追逐而日趨退卻。事實上,學校教育實踐的技術化傾向與績效崇拜,合力造就了“教育過程、學習行為標準化,教育價值與意義認知簡單化”[20],學校教育的育人本質則被純粹的知識邏輯壓制甚或替換。
在雅斯貝爾斯(Jaspers)看來,“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21]——生命與生命間的喚醒與潤澤,同時申明“創(chuàng)建學校的目的,是將歷史上人類的精神內涵轉化為當下生氣勃勃的精神”[22]。學校教育作為屬人的、為人的事業(yè),其本真便是“維護著人的生命存在與成長……有目的地優(yōu)化人的生命、提升人的生命質量”[23]。此外,人工智能作為人的創(chuàng)造物,實質上是人類智能的物化形態(tài),“不具有生命形式和生命運動,沒有獨立的像人一樣的各種需要”。[24]不論人工智能如何演進,教育的尺度終究是帶有鮮活生命的人,人工智能與學校教育融合的根本限度在于人的生命特質是難以取代的。基于此,智能時代的學校變革不是單純的人工智能教育應用,而應回歸其育人本質,錨定教育的生命立場,讓學校真正成為關注生命境遇、尊重生命差異、喚醒生命意識、提升生命價值的樂園。
(二)聚焦人文關懷:堅守學校教育的主體邏輯
學校教育的智能化轉向催生了虛實融合的學習時空、個性化自適應學習、人機協(xié)同的教學模式、智能教育測評等典型應用場景,通過實時搜集學習行為數據、動態(tài)監(jiān)測與評估學生學業(yè)質量、精準推送個性化學習資源和學習路線、自動調整學校教育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學校教育教學的高效化、專業(yè)化、科學化。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質是以數據和算法為核心邏輯對教育進行程序化、確定性的認識與操控,并演化成一種數字規(guī)訓權利,使得看似智能化和個性化的學校教育異化為“重物輕人”的規(guī)訓機構,同時“宣示著人文主義教育理念的沒落”[25]。例如,當前學校中備受“器重”的人臉識別系統(tǒng)、智能教學系統(tǒng)、可穿戴設備等技術應用已然成為學生學習生活中的一部分,卻試圖將學生圈養(yǎng)在“數據和算法”的估算和管制之中,“一是把學生降格為一個可隨時對其加以‘監(jiān)控’和‘分析’的客體,二是使得作為客體的‘技術人造物’升格成了‘教育主體’”。[26]長此以往,教育主體在失身于對智能技術的依賴和盲從中,也在“自覺或不自覺中交出了自身‘內在的自由’和獨立思考、選擇、決定與行動的權利”[27],作為教育主體應然的主體性和人文向度面臨著被放逐或消解的風險。
人是一種主體性的存在,拉普(Lapp)指出:“把技術說成是自主的主體,實際上描繪了一幅根本錯誤的圖景。”[28]盡管當下的學校變革熱衷于各種智能技術,但人工智能終究是屬人的,不可能具備與人一樣的主體性,更不會改變人在學校教育中的主體身份。與此同時,學校教育作為“一個以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為指導所進行的人文關懷過程”[29],是一種“人在其中”的活動,其本體堅守在于確證人的主體地位、喚醒人的主體意識、高揚人的主體性價值。事實上,人的主體性及其實現(xiàn)才是智能技術融入學校教育的邏輯起點和行動指向。故此,智能時代的學校變革,應保持人的主體性在場和人文價值卷入,規(guī)避人工智能對人的主體性的戕害與反動。
(三)聚焦真實體驗:堅守學校教育的實場邏輯
人工智能技術所打造的智能學習空間實現(xiàn)了實體教學空間、虛擬學習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時空聯(lián)通與虛實融合,其所具備的智能感知、具身體驗等特征有效拓展了師生的交互場域和路徑,提升了學生的學習體驗和學習效果。但隨著智能學習空間的無限擴張,師生的交互與體驗則被擱置在“身體離場”的數字化場景之中。在此境遇下,師生更傾向于借助智能設備和搜索引擎投喂和獲取“知識快餐”,始終以離身的虛擬身份出現(xiàn)在云端,而疏于與同伴進行面對面、有情感、有溫度的感知、交流與碰撞,其精神體驗與情感表達則在虛擬交往空間中悄然離場。如若學習者長期寄居于智能學習空間所形塑的高效率、高精準的技術邏輯,學校教育原本基于真實場域的生動、豐富人際交往和身體體驗則“被降格為物與物之間的機械組建,機械物的冰冷運轉取代了人的心靈融通與情感共振”[30]。
有研究者認為人工智能營造的“‘具身’并非有血有肉有靈魂的‘真身’,而是數字化了的‘分身’”[31],意味著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是離身的。而真正的教育始終是身體在場的教育,讓學生以身體為認識基點與周遭的事物、他人、世界相遇時收獲真實的體驗與感受。學校教育無法脫離物理空間而獨立運轉,只有作為具身式體驗場的實體教育場域才能幫助學生通過親身探究、主動經驗等真實體驗過程達成情感的互動、精神的解放與意義的建構和生成。因為“在未來的學校里,學生們可能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的課堂,但他們依然要與同學們保持互動,分享學習帶來的歡笑和淚水”。[32]所以,智能時代的學校變革還應關注真實情境中的具身體驗,讓學校教育復歸“孔子杏壇的師生質疑問難、蘇格拉底的問道中途、亞里士多德的學林漫步”[33]等原初形態(tài)。
(四)聚焦學習復雜性:堅守學校教育的生態(tài)邏輯
學校系統(tǒng)通過整合教育大數據、學習分析、深度學習等智能技術,幫助學生精準刻畫學習行為、適時推送定制化學習資源和學習策略,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工廠式學校的標準化邏輯,極大地滿足了學生個性化學習需求和發(fā)展需要。但人工智能賦能學校教育的技術路線建基在數據、算法和計算之上,依循形式化、簡約化邏輯規(guī)則將復雜多樣的教育情境和教育過程還原成可計算、可操作的數字指標,并將教與學的過程、內容、方法等預設為某些線性、程式化的操作路徑。而且,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甚至可能加劇當前標準化教育的泛濫”,使得學校“異化為標準化知識傳輸的工廠”[34],打破了學校教育的生態(tài)平衡。譬如,算法的大規(guī)模學校應用,實質上是借助數據計算來匹配和推送學生喜歡或感興趣的內容,甚至自動過濾或剔除學生的好奇心、創(chuàng)造力、探究欲、情感等復雜因素,驅使師生圈囿于“信息繭房”或“過濾汽泡”之中,個體發(fā)展的復雜性、多樣性則讓渡給算法的同質化、形式化。
事實上,學校教育的技術入場一度陷入“計算得清楚的東西未必都重要,重要的東西也未必都計算得清楚”[35]的認識論誤區(qū)。教育數據獲取的局部和算法應用的有限使得生成的數據計算結果,“只是教育共性基礎上的有限分析,并不是量身定制的教育個性化分析”。[36]況且,學校作為一個復雜生態(tài)系統(tǒng),具有非線性、生成性、模糊性等特征,必須珍視學校教育的復雜性取向。就學生學習來講,學習過程中的靈感閃現(xiàn)、頓悟創(chuàng)造或“醍醐灌頂”式的認知建構等復雜性、涌現(xiàn)性范疇是人工智能技術無法表征或預測的。真正的學習不等同于定制化的知識推薦、教學指導和學習策略制定,而是學生知、情、意、行等多種綜合因素共同互動的結果。此外,當下學校教育的發(fā)展趨勢是“從傳統(tǒng)教育機構,轉向混合、多樣化和復雜的學習格局”[37]。由此,技術賦能的學校變革應保持對教育不確定性和學習復雜性的敬畏,警惕技術理性肆虐對學校教育生態(tài)平衡的規(guī)訓與控制,探尋技術與學校教育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發(fā)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