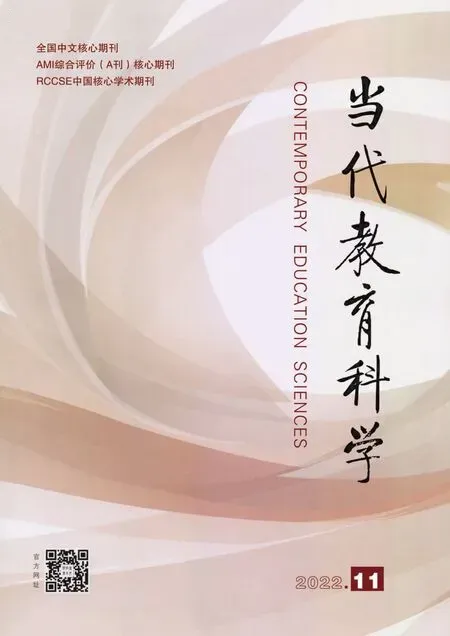論教學關系中的身體參演
● 朱麗楨
教學源于關系,也必須存于關系之中。作為人類有目的、有組織的實踐活動,教學由不同層次的實體構成,并誕生于實體要素間關系的建立。可以說,教學是一種關系性存在,關系相對于實體在教學中具有邏輯先在性,教學存在是關系與實體的辯證統一。[1]教學既體現為一種實體系統、活動范疇,更表現為一種關系過程,“關系性”是教學的本質屬性。[2]“教學關系”的引入便是對教學“關系屬性”的強調和表征。在實體層面,教學關系指稱以師與生為代表的主體之間的交往關系;在活動層面,教學關系指稱人與文化的雙重建構關系;在微觀層面,教學關系是人與自我的意義生成關系。可見,教學關系總是以人為核心,并通過人與人、與文化(知識)、與自我的交往關系實現人之“整體性”發展。“身體”作為人之存在的顯現與展露,是我們通往教學世界的媒介。“身體”不僅界定了人之存在的邊界,制約了人對世界的經驗,更承載著人的生命過程并呈現著人的完成狀態。在教學關系中,身體成為一切關系建構的前提,也成為關系持續的保障。但對“身體”的誤解和偏見卻導致教學關系陷入“無身”之局面,重審教學關系中的身體,促進教學關系中的身體回歸,成為培養“整體人”和“身體人”的關鍵。
一、身體之于教學關系的重要價值
人不只擁有身體,更是身體本身。身體不僅是生物屬性的,更具有社會性和精神性。梅洛·龐蒂更是直接指出人是“身體——主體”之存在,實現了人的意識身體和物質身體的統一。在教學活動中,教學關系的建立不僅以身體為先在,更是將身體完善視為目的,并在教學關系中實現自然身體向社會身體的轉變。身體在教學關系中具有重要價值,主體交往必須依賴身體進行互動,知識交往必須通過身體參與進行學習,自我交往更是需要借由身體進行反思,從而完善自我,建構人的意義世界。
(一)借由身體的互動:教學關系中的主體交往
生物特性的軀體和社會特性的符號,讓身體充滿了神秘性和能動性,身體成為人際溝通和自我表達的依據。一方面,身體的實在性讓身體得以成為互動之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特性和歷史屬性又讓身體超越其局限,擁有盡可能多的意義和象征,促成了互動的復雜性和目的性。在身體形構的教學關系中,身體更是成為維持教學主體之間日常互動、身份角色、交往關系及自我認同的重要基礎,從而實現對教學主體的身體塑造。首先,身體形構著教學主體間的教學交往。對“身體”的觀照讓教學主體間的互動擺脫了集體或群體無意識,交往成了個體事件,身體的唯一性使教學主體均擁有了自己的“姓名”,雖在集體,但交往是“一對一”的。身體的參與也讓個體獲得了極具個性化的體驗,教和學充滿了私人性,實現交往主體對每個交往對象之關注,教師和學生被形塑成為獨特個體;而身體的參與程度也導致了不同的教學交往成效,影響教學關系的深度、廣度和活力。其次,身體形構著教學主體間的心理交往。身體是交往的媒介,不僅意味著身體承載著交往的意義和符號,更表明只有我們借由身體才能在教學活動中表達自我、展示自我甚至隱藏自我,主體通過身體言說內心,交往對象經由身體語言、動作、表情等,解讀對方,使交往不再滯留于表面,而是深入人心。再次,身體形構著教學主體間的倫理交往。教學主體的交往并非隨意,需限制于一定的倫理框架之內,使交往表現出一定的倫理規范,而這種規范性首先體現于交往主體的身體規范。身體規范是身體秩序建立之前提,經過對身體的規訓和形塑,實現“內具和諧而外具秩序”的人的培養,使人從自然的野蠻狀態走向社會的理性狀態。
(二)通過身體的學習:教學關系中的知識交往
知識是涉身的,教學中的知識交往也必須身體出席。知識交往對身體的依賴不僅表現在知識的生成要求教學主體身體感官、神經、肢體等生物性支持,更表現在身體體驗、情感、經歷等經驗的嵌入。身體的納入,讓知識不再是客觀或科學的化身,知識交往不再追求知識的確定性,知識建構不再囿于科學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知識的情境化、體驗化、差異化和多樣化,知識交往回到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中,實現對“身體的人”的關照。教學中的知識交往便旨在通過對“身體的人”的關照實現對人與文化的雙重建構。首先,知識建構著“身體的人”。教學關系中的知識交往以人的未完成性為基礎,追求人的自由且完滿。[3]人的“未完成性”就是身體的“未完成性”,表現在知、情、意、行等諸多方面,并以身體的“幼態”和“生澀”作為表征。經由知識交往,教學主體走向自我完善,教師教學智慧的提升,學生“五育并舉”的發展,都需以身體學習為前提,以身體內化為條件,最終以身體暴露為體現,身體成為檢驗教學主體各自身份與角色的外在標準。同時,知識的學習、投資和積累也將形成文化資本,附著于人之身體,賦予教學主體以價值和意義;而經由身體之互動,文化資本更是為個體帶來符號資本,體現在人的身體上,便形成“身體資本”。其次,教學主體經由身體實現對知識的再生產。教學中,知識交往之目的不只是知識掌握,更是指向知識創造。身體是人類知識的根源,知識在認知主體與認識對象的互動中產生,并形成極具個人化的知識,諸如波蘭尼所講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日用而不知”的默會知識等,[4]均是一種“身體知識”,并以身體的姿勢得以彰顯,包括教學主體的身體技能、作業、作品等多個方面。可以說,身體的納入讓一切知識都演變成“個人知識”,經由身體,教學主體實現知識的再生產。
(三)依賴身體的反思:教學關系中的自我交往
作為主我和客我的相互作用,自我交往在教學關系中具有隱秘性,并貫通主體交往與知識交往的始終。而自我首先必須是身體,是感受對身體輪廓和特征的覺知,也是對世界的創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5]更是個體反思的投射,沒有自我的反思意識和反思行為,自我便蕩然無存,人也將失去意義和價值;沒有身體參與的反思,自我也將失去發展。可見,教學關系中的自我交往是依賴身體的反思實現的,在身體這個“行動系統”的支持下,教學主體實現對自我存在的確證、自我價值的實現和意義的生成。首先,依賴身體的反思,教學主體得以確證我之存在。反思不僅需要對象,更需要參照和標準,身體作為鏡像中的自我構成了我的反思對象,他人之身體便成為反思的參照和標準,通過“我”與“他”的對照,教學主體了解自我、定位自我,從而使教學主體在教學關系中找到我之存在的證據,掌握存在現狀,形構我之形象。其次,依賴身體的反思,教學主體得以實現自我調控。在“我”與“他”的身體對照中,教學主體不僅確證了自我,更是誕生了驕傲、滿足、落差、失望等諸多情緒。對學生而言,這些情緒或將導致新的學習行為的發生,或將成為擊潰學生個體的誘因;對于教師,亦是如此。而這些情緒以及情緒所導致的后續行為都是經由自我反思實現的,根據反思之結果,主體進行自我調控,并將調控結果身體化。同時,在這種依賴身體的反思所獲得的身體體驗成為教學主體意義世界建構的最具體形式,并在與主體交往和知識交往的過程中,使意義更加具體和豐富。
顯然,身體在教學關系中具有重要價值和作用,是身體形構了“我”,并作為教學主體與他人交往、與知識交往、與自我交往的媒介和根源;教學活動的發生和教學關系的建構更是以塑造“身體的人”的完善和全面為準則。可見,“身體”已全面介入教學關系之中。
二、教學關系中的身體處境變遷
人的實踐就是身體的實踐。人便是身體,身體與人始終統一,構成“身體的人”或“人之身體”。隨著社會發展,人類認識不斷將身體從“人”的存在狀態中驅逐出去,身體遭受誤解、褻瀆、物化,甚至出走。在以人為主體和中心構建的教學關系中,身體更是在科學和理性的催化下,被視為人的心靈、思想、理性的物質載體,學生發展陷入“抑身揚心”的處境,師生交往成為教師對學生身體的規訓和操練,知識交往通過身體壓抑實現理性增長,自我交往走向對身體的放逐。可見,在教學關系中,“人”從“身體”中抽離出來,成為縹緲之物;“身體”從“人”中被剝離,成為物化工具,“整體的人”的培養陷入窘境。
(一)身體媒介時期:教學關系中的身心一體
人類早期雖未確立嚴格規范的教育教學制度,但寬泛意義上的教育教學活動卻是真實發生的。此時的教育教學交叉并滲透于人類日常生產實踐中,教學活動零散而豐富,旨在傳授人類生活常識和生產經驗,教學活動不受時空限制,發生在人類實踐的各個角落。教的行為和學的行為也未分化,統一于人類日常實踐中。可以說,教育教學的原初形態就是年長者與年幼兒童之間的言傳身教。在這種言傳身教的過程中,長者通過自己的身體與自然對抗獲得經驗和技能,并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以身體的形式呈現出來,實現人類經驗的傳遞;年幼者等他人通過親身感受、身體模仿、身體內化最終習得經驗,并以身體經驗的豐富作為成人的標志。可見,早期的教育教學是以身體為核心的生產勞動教育,教學活動中無論是教者和學者的交往,或是以經驗為核心的知識交往,還是身體式的自我交往,教學關系總是以身體為基礎展開,并以身體互動為過程,最終以身體經驗的獲得結束。這一時期可稱之為“身體媒介”時期,誕生于這一時期的教學便可稱之為“通過身體的教學”。在這種以身體為核心的教學關系中,人作為身體的人,是身心一體的存在狀態。雖然,此時的教學關系是一種較為原始且低級狀態,其旨趣也只是周旋于人的基本生存,沒有涉及人的理性和完滿,但作為人類教學活動的最原始和最根本狀態,卻奠定了身體在教學中的根本地位。
(二)印刷媒介時期:教學關系中的身體操練
文字的出現讓知識的記錄和傳播擺脫了對身體的依賴,成為知識的載體,尤其在印刷技術的支持下,知識生產更加迅速。知識的不斷豐富使人意識到自我的貧瘠,并投身于知識追求。也正是在知識追求過程中,人類摒棄了身體,將身體視為理性之載體,身體被異化為工具。一方面,身心二元論將身體與心靈割裂開來,身體被視為心靈的載體,甚至人類墮落的原罪;另一方面,社會分工分離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伴隨著對腦力勞動的歌頌,身體被視為是下等人的謀生之道,遭受恥辱和唾棄。如此,學校教育便陷入對人的精神和理性的褒揚之中,教學活動圍繞科學知識展開,知識凌駕于身體之上,成為身體的主宰,教學關系呈現出人與身體的絕對對立。首先,教學關系中的身體邊緣化。在教學活動中,身體被視為欲望、沖動、邪惡的化身,這導致教學關系中的主體交往、知識交往、自我交往忽視了身體的教育價值及對身體的保護和培養,身體可以被隨意“損害”,成為可有可無之物,甚至人類進步的阻礙。其次,教學關系中的身體片面化。教學主體對身體的認識局限于生理學層面,身體被視為精神、思維之載體,生命的物質基礎或遺傳性因素,作為人的存在前提并不參與教學關系中的各種交往活動。再次,教學關系中的身體工具化。對身體的狹隘理解和對身體的誤解,讓人們萌生了對身體的操縱和規訓,這在教學活動中極為明顯和常見。教學活動中,師生交往的言談舉止、兒童端坐、校服、課程表、行為準則等均在于身體之規訓;知識交往的目的也旨在擺脫身體之欲,成為德行規范且高尚之人;而自我交往中教學主體對身體的過度裝扮也是不被允許的。經過人類努力,正如所愿,人終于擺脫了身體,成為“理性之人”和“抽象之人”。
(三)網絡媒介時期:教學關系中的身體缺失
互聯網的誕生讓人類交往從現實轉向了虛擬,“在線”形式的網絡交往成為與“在世”并列的人類生存方式。網絡交往通過信息的數字化編碼和解碼,并在電腦支持下實現人與人之間的非面對面溝通,[6]遵循的根本邏輯就是不斷突破時空對于“身體的人”的限制,以實現人類交往的高效、便捷、快速。這為教育教學活動帶來了福音。教學活動更加開放,資源實時共享,甚至成為促進教育公平的支點,并試圖通過虛擬現實等網絡技術尋求教學活動中主體交往的真實性和切身性。可見,網絡媒介誕生于對人身體的突破,但又在發展中不斷追求人的身體直觀。但人始終是“身體的人”,身體自始至終地嵌入在網絡交往過程中,正是這個嵌入的身體保證了網絡交往者的屬人的現實主體性。[7]然而,網絡的虛擬屬性及對網絡交往的誤解,導致網絡媒介在建構人類交往新世界的同時也解構著網絡形式的教學實踐。首先,網絡媒介解構了教學主體的身心一體狀態。網絡交往的符號化、標簽化讓在線教學中的“在線”之“在”窄化為人的心理、思維之在,甚至教學交往脫離身體和心靈,使教學關系中的主體交往淪為“符號”交往,知識交往也在身心解構中浮于表面。其次,網絡媒介隱匿了人之身體。循著這種“在線”之在是心靈、符號在而身體不在的思路,網絡交往又演繹出“虛擬”“匿名”“標簽”等現象,“在線”之人通過藏匿自己的身體,實現對現實身體束縛和身份約束的擺脫,從而在達成交往目的的同時又避免了道德倫理、公序良俗的懲罰。在線教學中;隨著教學主體的身體隱匿,教師的身體權威被削弱,沒有教師權威的規訓,學生的學習行為也更加隨意和不規范,教學關系陷入混沌和無序。
三、教學關系中的身體重審與回歸
教學活動中,身體總是與人共處,真正的身心分離并不存在。然而,對身體的誤解和偏見使人迫切地想要和身體分離,人在理性的操控下產生了對身體的刻意忽視、壓抑和懲罰,教學關系便也圍繞著理性展開,通過對感性、情緒、體驗等身體經驗的貶斥,實現對“理性人”的培養。因此,若要重新確立身體在教學關系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應正視人與身體、理性與身體的關系,允許感性、體驗等身體經驗在教學關系中的參與,讓人“顯身”,實現身心一體的教學關系的建構。其次,正視身體的價值,允許教學關系的身體表演,通過身體表演,呈現人的學習狀態和學習結果。最后,在對身體的關照和重審中,解放身體,引導身體走向自由,并在身體秩序的規訓下,實現自由完滿的人的培養。
(一)顯身:教學關系中的身體參與
人類對身體和自我的認識是逐步統一的。尼采最先將身體擺在與理性同等的位置,提出“一切從身體出發”,并指出“我完完全全是身體,此外無有,靈魂不過是身體上的某物的稱呼”。[8]胡塞爾指出身體是對空間對象的知覺以及與其作用的可能性條件。[9]海德格爾認為身體比靈魂更可靠,身體世界比精神世界更具本源性和本真性。[10]之后,福柯以新的視角解讀權力、話語、歷史與身體之間的關系,身體雖在,但成為控制人類的手段。梅洛·龐蒂認為心靈居于身體之中,身體是人與世界聯系的手段,確認了身體的優先性;[11]并通過強調“心靈的肉身化”和“身體的靈性化”打破了身心二分,消除了肉體與心靈的對立,將身體還原為靈肉交融的統一體,身體與人實現統一。自此,人們認識到身體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身體不再是軀體,轉而成為人本身,并與人的情感、意志、經驗、行為等密不可分,身體作為存在之根本具有精神性、主體性、歷史性、倫理性、整體性等內在固有屬性。人作為教學活動的主體和目的,人之身體更應該擁有自己的姓名和地位,并作為“身體—主體”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使身體在教學活動中“顯身”,解決教學對身體的偏見。首先,建構“身體—主體”式的主體交往。師生交往不再只是理性和規訓的,師生的身體經驗和體驗、肢體語言、需求均被放置在教學交往中,走向對“身體的人”的理解和關懷。其次,促成“身體—主體”式的知識交往。身體的正名,讓理性與感性得以統一,知識交往在對身體的重視中,開始關注身體的感性層面,逐漸擺脫知識中心,走向意義生成和建構。最后,完善“身體—主體”式的自我交往。自我交往也應走出人之精神世界的反思與重構,在對身體的關照中實現對“身體的人”的整體性塑造。
(二)表演:教學關系中的身體呈現
人通過身體表演實現表達自我。表演是一種交流方式、一種言說方式。[12]人總是處在表演中,表演具有身體性,可以說任何表演都是身體表演。當人主動表演時,他便支配著自己的身體,享有身體具有的主體性。[13]但教學對表現性評價、外向型人格、直觀教學效果的熱衷,使教學淪為“表演”,陷入熱鬧、活躍的劇場;人們開始質疑教學“表演”,認為表演讓教學充滿刻意、預設、功利,失去了對自我的真實表達和呈現。可見,“表演”不是原罪,而是教學活動中的虛假、造作、功利和身不由己,更是理性將身體工具化的表現。因此,應正視教學活動中的身體表演,使教學主體在身體表演過程中,實現對自我的真實表達和呈現,構建真實、向善、向美的教學關系。首先,促進教學關系中身體呈現之真。教學主體敞開自我,調動身體感官和心智參與到教學中,并通過身體姿態、運動、言語等表現自我、傳遞意義,實現對各自角色的詮釋,并履行各自責任和義務,使教學主體的行為不再虛假、扭捏,彼此坦誠,實現理解。其次,促進教學關系中身體呈現之善。有表演就會有觀眾。教學主體的身體呈現不是隨意的自我信息的輸出,因為他者,甚至權威主體的在場和“觀看”,導致主體交往及其知識交往均處在自我或他人的規約之下,在這個“表演與觀看”的互動過程中,主體內化道德倫理要求,實現向善。最后,促進教學關系中身體呈現之美。美是人之完滿自由的表征,教學以人之美為追求。美并不抽象,它以身體為媒介得以呈現和外化。在教學中,人在觀看他人的身體表演中發現美、模仿美,創造“理想自我”的形象,并通過不斷地改進和調整,以身體姿態呈現美的自我。
(三)自由:教學關系中的身體解放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4]自由是人的本質,實現自由是人的終極目的。人的自由程度也成為人的主體地位彰顯的重要表現。教學作為育人、成人的活動,通過解放人之身體和人之精神,促進著人的自由完滿的實現。要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就必須先將“身體人”從“抽象人”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擺脫對人的身體的偏見、誤解、褻瀆和利用,使人的身體歸位,發揮“身體人”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實現人之自由。因為,人的自由完滿和全面發展以身體解放為前提,以身體自由表達為基礎,最終以身體自由發展為旨歸。同時,教學關系中的身體自由不是精神之自由、也并非人的內在自由,更不是無所限制的自由,而是“整體人”“身體人”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合道德合倫理且被秩序規范的自由。首先,在身體自由中促進人的自由發展。人的身體自由不僅表示其行動處于理性的選擇,更是在于他的行動不受他人的鉗制和壓迫。以此為目標,教學關系中的主體交往應走出對師生身體的限制,賦予教師更多的教學自主,發揮教師身體的教學價值,在“言傳身教”和“身體榜樣”中,促進學生身體規范和自由發展;學生更應在教學交往中解放身體,回到生活世界,回歸其自然天性,使教學生活煥發出生命的活力。教學關系中的知識交往也要擺脫對理性的貪戀,在感性中追尋人的意義。其次,在身體秩序中促進人的自由的實現。教學關系中的身體自由不是絕對的,受到相應秩序的規訓。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教學關系中一切關于秩序的設置都是為了滿足師生追求自由的主體需求,包括人的身體行為需要符合道德、倫理要求,以及對失范行為的懲戒等,均是通過對身體秩序的養成,為教學關系中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保障;同時,自由發展的人也必定是身體合秩序、合規范、和諧之人,只有在秩序中,人才能超越自然身體,走向社會身體,實現人的自由完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