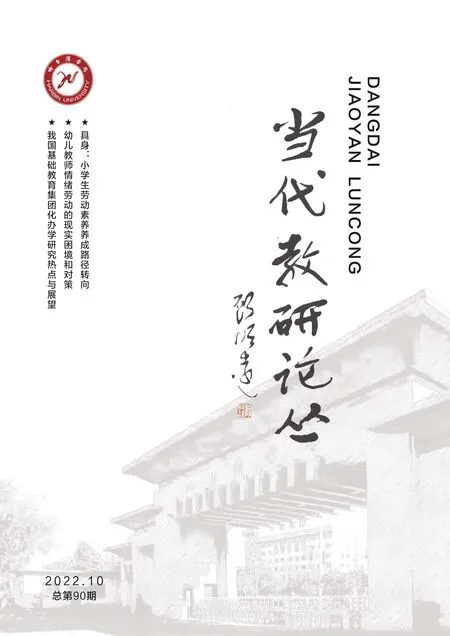跨學科式文學研究的理論問題簡述
潘東偉,司 維
(1.黑龍江省婦女研究所,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職業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文學定義的開放性注定了文學研究會包羅萬千。任何一種文學,無論是文學理論,還是文學作品,從未單純只表現獨屬于文學的內容。并且從現實層面出發,人類認識領域是否存在僅屬于文學的內容尚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在一部文學作品中,可能有歷史的指涉,有政治的指涉,有經濟的指涉,有社會生活的指涉。因此,文學研究必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問題在于如何從理論話語的層面論證文學研究跨學科的可行性、必然性,如何為跨學科式的文學研究整理出一條標準的理論路徑,讓文學研究跨學科而又不偏離專業本位,讓跨學科成為拓展文學研究的有效方法。
一、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宗旨:跨學科的理論定位
什么是跨學科,怎樣才算跨學科,這是從理論高度進行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基本問題。人文學科的各個對象彼此聯系,相互滲透,不僅跨越國界、跨越時代,也貫穿了不同的學科,所以“跨學科”被視作突破學科研究瓶頸的一種有效途徑,學界對跨學科研究方式的期待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對“跨學科”概念本身做細致并深入的研究,縱觀其歷史發展過程、探討其發展的理論緣由、確定其研究方式,并在此基礎上,歸納總結跨學科的優勢以及存在的問題,以此不斷豐富跨學科研究方式的內涵,糾正其存在的問題,擴大跨學科研究對于文學的啟示作用。文學從某種意義上即是人學,一切由人所創造的學問,都與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而,研究文學勢必要跨越學科。本文以美國的文學研究為例,探討跨學科的理論定位。
根據美國文學史著名學者斯皮勒的研究,直到1918年,美國文學并沒有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出現在大學課程中,此后的很長時間里仍然沒有得到特別的關注,盡管美國文學在美國大學中的教學可以追溯到19世紀90年代,甚至更前。有關美國文學的闡釋,從一開始就被放置于美國思想發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在這個方面,1927年出版的《美國思想主流》可以看作是一個范例。作者帕靈頓在導言里這樣說明其研究方式:“(本書)選擇了一條寬闊的道路,融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于一體,而不是狹窄的基于‘美文’的純文學作品(belletristic),主要研究內容放置于構成文學流派和運動發展的各種勢力之中,它們形成了思想的體系,而文學的潮流最終是從中發展出來的。”在帕靈頓的這個思想體系中,被并列在一起加以討論的有文學作者庫珀、愛默生、梭羅、富勒、艾倫·坡等,以及思想者愛德華茲、富蘭克林、杰弗遜、林肯等。顯然,帕靈頓的做法打破了以往的聚焦于“美文”的文學研究方式,把文學視為思想表述的渠道之一,意在從文學中辨析美國思想發展的痕跡,正如美國研究學者懷思所稱,帕靈頓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探索所謂“美國心靈”(American mind)。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帕靈頓所運用的方法,實際已經涉及跨學科方式,盡管在那個時候甚至連一些學科的分野并不那么清晰。
帕靈頓著重于歷史背景的綜合式文學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后時常出現在美國文學研究的著述中。簡括來說,帕靈頓研究方法的精髓是深入歷史語境,歸納其中的核心思想,于縱橫交錯中勾勒出美國思想的發展脈絡,具體做法則是對各種不同文本進行細讀,將文學文本與其他非文學文本放置在一起,爬梳歸類,從中探尋主流思想的發展軌跡。這種對不同類型的文本進行研究的方式,其實已經顯現了跨學科傾向。1941年哈佛大學教授馬西森出版的《美國的文藝復興:愛默生和惠特曼時代的藝術與表達》一書,被譽為美國文學研究的奠基之作,確立了“美國的文學身份”。馬西森延續了帕靈頓開創的背景研究方式,強調對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進行闡釋。但他同時也批評帕靈頓把文學僅僅當成思想表達的工具,忽視了文學本身存在的重要性。在馬西森看來,“文學反映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照亮了這個時代”,而所謂“照亮”是指文學本身的作用,文學不僅僅反映歷史大潮流,它也有“自己的生命”。[1]由此,他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文學研究模式,即以對文學發展過程的研究為目標,以對主要作家的闡釋為手段,梳理美國文學表現的特征。這種對文學本身的重視,之后也成為美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需要指出的是,帕靈頓和馬西森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一種截然相對的關系,而是彼此間可以互相借鑒;歷史背景與文學闡釋無論在哪種方式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兩者的融合與后來出現的“美國研究”關系密切。現在看來,這種融歷史背景與文學本體于一身的研究方式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就跨學科方式而言,一是要把文學研究放置于思想研究的大背景中進行,二是要始終確定文學研究為本體的宗旨,以一種“我注六經”的手段拓寬文學研究的領域,以“六經注我”的方式深化對文學文本的多元化認識。[2]
如此來看,跨學科僅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的應用無損于文學研究的獨立性。事實上,強調跨學科的意義正在于凸顯文學研究的獨立性,因為文學研究綜合了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這種綜合性恰好是其他人文學科所不具備的。而文學的綜合性未嘗不是因為文學所研究的中心對象是人類的表達能力和表達習慣,是建構起人類思維整個羅格斯體系的語言。而在二十世紀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強調共時研究之后,文學學科的語言學基礎逐步明確,而語言又成為了將文學聯系到其他諸多學科的紐帶。因而跨學科之于文學研究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必須選擇的方法。
二、跨學科的理論價值:一種新的文學觀的凸顯
自韋勒克對文學做出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分以來,人們的文學本質觀日日更新。事實上,這表明了文學觀是一個問題區間,且這個區間具有張力性。而多學科融入文學研究就是釋放這種張力,讓文學觀處在一種自然流動的進步狀態。文學觀的進步也不意味著文學問題有了逐漸明確的答案,[3]突出的不是文學問題的邏輯性,而是文學問題的邏輯性和開放性。這里以中國兒童文學為例加以論述。
關于兒童文學有許多定義,這些定義基本上都是在描述“成人為兒童創作”這一單向關系。為了避免這一缺陷,對兒童文學構成的內部機制,我設立了“兒童文學=兒童×成人×文學”這一公式進行描述。我用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顯示兒童與成人在文學這一平臺上形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交互關系。如果成人文學也有一個公式的話,我認為它不會有兒童文學這么復雜。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絕不會復雜過兒童與成人之間的關系。我們說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有其特有的難度,就是因為要處理、解決好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復雜關系。處理、解決好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復雜關系的前提是對兒童這一生命存在獲得真正的理解和認知。兒童研究是難的。
兒童研究不僅是一門大學問,而且更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兒童文學的兒童研究,主要涉及的學科有哪些呢?如果我們將兒童文學視為關注、關懷兒童成長的文學,那么,涉及兒童成長問題的就有兒童心理學、兒童教育學以及哲學(主要是探究“自我”建構的問題)。由于年幼兒童的圖像認知這一思維方式,具有實指性定義功能的繪畫(美術)大規模進入兒童文學,構成了圖畫書(又稱繪本)這一重要文類,于是,繪畫(美術學)研究成了兒童文學研究的題中之義。不是有生物意義上的兒童存在,就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兒童文學是歷史的概念,是在人類社會對兒童的認識發展到更高水平的階段才會出現的一種新文學,所以,童年歷史學也是兒童文學史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要寫出適合兒童理解并被他們喜愛的兒童文學,就要了解兒童閱讀的機制,于是,認知科學和腦科學的知識及其方法,自然也就進入了兒童文學研究領域,比如,尼古拉耶娃等人就在從事具有前沿性的兒童文學認知研究。
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力量的分布也表現出鮮明的跨學科性。就中國來看,呈現出的分布圖是:在文學系統里,分布于文藝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英語等不同語種的文學、翻譯學等學科;在教育系統里,分布于小學語文教育、學前教育等學科;在心理學系統里,分布于兒童閱讀與學習領域;在美術系統,分布于美術設計、插畫等專業領域。可以說,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學科不同,兒童文學學科是由眾多學科的學術力量所組成的“學術共同體”。
而文學學術也可以看做這種“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的存在揭示了各個人文學科先驗存在的聯系。同時,我們可以從中發現文學處于其中哪一個環節,這個環節可能不是固定的,故而文學觀也是時常更新的。
三、理論的外延:文學研究跨學科的更多可能性
長期以來,文學研究被認為是意識形態領域理性思辨的主觀研究,科技人文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當前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的前提下,科技人文研究由于計算機技術的引領,也被稱為數字人文。1837年,美國人莫爾斯研制的世界上第一臺有線電報機,最早利用科學技術解決了語言文字遠距離傳輸的問題。摩爾斯電碼是一種早期的數字化通信形式,是當代數字通訊的源頭。1898年,丹麥的波爾森發明了鋼絲錄音機,解決了人類保存語言的問題。1981年,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購買了MS-DOS(Microsoft Disk Operating System),為IBM PC機定制了微軟磁盤操作系統,從此拉開了科技人文數字化信息化的帷幕,文學開始進入科學化的時代。科技人文研究國外早已開始,如牛津大學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數字人文研究。21世紀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在文學、語言、歷史等人文研究領域,傳統觀念和研究方法要么科學化,要么被拋棄,古籍文本數據庫的建設就是傳統學科研究科學化的實例。
我國有關科技人文的研究在近幾年發展迅速,已經形成趨勢,國內一些高校如清華大學和中華書局聯合主辦了中國大陸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數字人文學術期刊《數字人文》(2020),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已經開始實施科技人文研究的規劃。就中國高校的雙一流建設而言,文學研究要實現雙一流建設的目標,趕超世界一流大學,科技人文跨學科研究是發展的必然之路,可以說是不二選擇。科技人文跨學科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文研究觀念的科學更新,二是科學方法在人文研究中的運用。
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的進步與繁榮,是在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推動下實現的。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同傳統的人文科學研究相比,科技同人文研究的融合改變了人文研究的性質,即將傳統上以意識形態為特征的主觀研究轉變為以科學原理探討和技術分析為特征的科學研究。認知神經科學、人工智能、生物芯片、人機接口等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它們在人文科學中的普遍運用,已經呈現出主導人文科學研究的總體趨勢。由于科學技術不斷介入人文科學的研究,傳統上與科學技術相對的人文研究正在迅速地同科學技術融合在一起,如數據統計分析、數據庫資源的運用及信息搜索,人機對話與交流,人工智能等,正在或將會主導人文科學的研究。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語言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智能翻譯、專家系統等在人文學科領域得到廣泛運用,人工智能甚至已經可以取代作家、讀者和研究人員的部分工作。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開展人文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對于當今人文科學研究而言,科學技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顯得重要,千百年來人文學科一直依賴傳統意義上的圖書館,正在被數字資源庫迅速取代,紙質人文正在快速轉變成數字人文。文學同語言學、歷史、哲學、倫理學、生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相互交叉、滲透、融合,形成了數字文學及數字文學研究。
當代科技介入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并逐漸形成對人類生活的主導,已經不是我們出于倫理的思考選擇接受與選擇拒絕的問題,而是接受即生存、拒絕則淘汰的問題。
人文研究借助科學技術的優勢和資源推動文學、語言學、哲學、歷史等學科對基礎理論及具體問題的研究,在整個科技人文交叉發展的宏觀背景下有效地推動了人文學科的整體發展。另外,國內外人文學科建設都是由語言、文學、哲學、歷史等具體學科的建設體現的,對人文學科建設的目標評估也是以上述學科為對象,因此科技人文跨學科研究的目標不是淡化具體學科,而是在國內外人文學科尤其是國際一流人文跨學科發展的前提條件下,用新的觀念和方法既推動一流人文學科的整體建設,又突出各個學科的特色,如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四、結語
在理論研究的范圍內,跨學科式的文學研究已然成為一種常態,而從理論走向實踐,從研究文學的現狀到預期文學的未來,這種常態等于是在給未來的文學劃定路線。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與時代發展,與社會現實,與人們所需相契合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強調跨學科即是強調學術體系的內在親緣關系,這種親緣關系喻指著人類的普遍理性,喻指著一種理想的人類學術的建構。在這條路上,每一個正在思考的人都是榮辱與共、親密無間的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