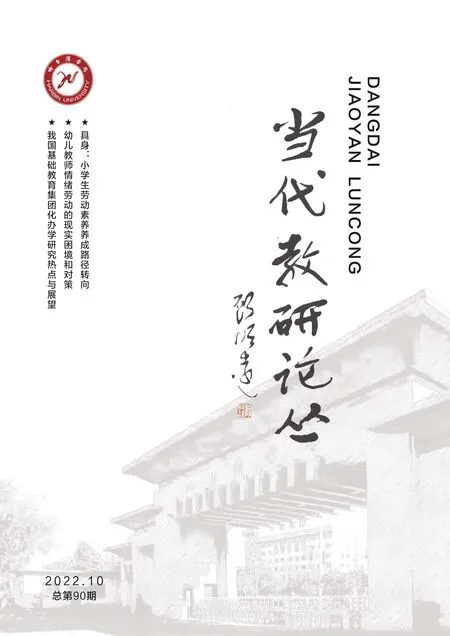“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資源利用研究
——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例
由俊勇
(山東華宇工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德州 253034)
一、蔣廷黻其人其書:被遮蔽與再審視
蔣廷黻生命歷程是復調結構:前半生學者論政,后半生從政學者。近代史學家馬勇評價他“在20世紀晚期,還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失蹤者’”,[1]相關研究被遮蔽(Obscured)掩蓋,千禧年過后才回歸歷史學者的視野。許紀霖形容蔣廷黻政術及學問的人生像一頭“猛牛”,在“瓷器店”里橫沖直撞,在“精細”與“笨拙”之間完成既定目標。[2]近現代中國兼具“政統”與“學統”的“通才”不乏其數,如文化雙重人張謇;[3]而《中國近代史》著者蔣廷黻史學思想注重整體把握和綜合分析以及全面闡述己懷的近代化歷史觀、國家觀與民族觀,被稱作“近代外交史拓荒者”。
近年來,學術界對蔣廷黻先生“內涵”與“外延”已有涉獵,“內涵”指的是歷史學方面,體現在史學思想淵源與流變形成實踐、史學因緣與學人交流、史學流派構建與貢獻等;“外延”是指圍繞蔣廷黻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經濟現代化思想、善后救濟思想、大學教育思想等;“內涵”與“外延”方面研究較為深入,此文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蔣廷黻個人歷程及所著《中國近代史》對于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應該有所挖掘。
二、蔣廷黻“近代化”史觀形成的教育因素
蔣廷黻“近代化”史觀的形成離不開生命成長歷程中的教育因素。可以說,蔣廷黻的童年記憶、啟蒙時期的教育及其留學經歷,對于其史觀的塑造至關重要。
(一)童年記憶
蔣廷黻生于1895年12月7日,即光緒21年10月21日,家住湖南寶慶府邵陽以北30里。蔣廷黻童年記憶中對祖母印象深刻,他對太平天國運動的立足點基于“長時間”史學理論,這其中包含著“大亂大治”循環論與“朝代更替”觀,他稱贊太平天國運動是有為的“宗教革命”和“種族革命”。他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也很高,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與其童年記憶相關,兒時的他對“賀某事跡”記憶猶新,并將賀當作大英雄。童年記憶對于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史學觀念形成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二)啟蒙教育
1901年蔣廷黻入私塾讀書,1905年因清政府廢除科舉而進入新式學堂,僅接受了四年的儒學正規教育,接受時間過短,同時也意味著其對儒學的被動放棄。蔣廷黻隨之成為科舉時代最后的童生,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但卻接受了傳統的教育,這對于他的事業至關重要。可以說蔣廷黻是新舊交替時代的受益者,他熟悉四書五經以及歷代重要經典,是新時代新知識人中最具有古典主義情懷的一批人。
在時代大背景下,科舉廢除與儒學的衰落更像是蔣廷黻個人的機遇,便于他接受西方化的學習。格外重視子侄輩教育的二伯父,原本期望他在科舉路上有所收獲,但朝廷廢除科舉考試,再上私塾和舊時學堂就毫無意義可言。相對于傳統教育模式學習《三字經》和練習毛筆字而言,明德學校的科目教育更趨于多樣化——以自然學科為主(國文、數學、修身、圖畫與自然)。在蔣廷黻認知歷程中,明德學校是一所充滿近代化氣息的學校,與傳統學堂不同,有如“老虎與貓”。[4]1906年秋,二伯讓蔣廷黻兄弟轉學湘潭長老教會學校即益智中學,從此奠定蔣廷黻信仰基督教的教育基礎。在益智中學,蔣廷黻所學知識更加豐富,其思想也逐漸向西方化轉變。在學習歷史過程中,所知的只是星星點點,不能窺其全豹,所以蔣廷黻研究整個西方世界的進步情形。儒學的揚棄與西學的接受對蔣廷黻都有一定影響。
(三)留學經歷
1919年蔣廷黻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海斯教授。[4]海斯教授是美國“新史學”的代表人物,新史學派以實證主義為基礎,強調史學的實用價值和社會功用,受其影響,蔣廷黻日后的史學研究中隨處可見“新史學”的影子,《中國近代史》就充分彰顯了史學的社會功用。蔣廷黻受海斯“族國主義”的影響更甚,從1923年他對英國對外政策研究的博士論文開始,一直到1938年他研究《中國近代史》為止,他都堅持這一思路。蔣廷黻認為帝國主義并非是資本主義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卻是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蔣廷黻將其命名為“擴張性的民族主義”。他對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認知出自對西學的學習與認知,這與錢穆的思想有著極大的不同。
三、《中國近代史》敘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
改革開放之后,面對“史學危機”,中國史學界開始警醒。與其說史學危機是對傳統史學研究范式的質疑和顛覆,不如說它是史學自身發展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從而史學研究向社會學轉軌。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兼備革命、外交及近代化三重敘事結構,體現挫折疏導教育、民族振興情懷和個人理性啟蒙,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一)革命敘事與挫折教育啟示
近代史的苦難革命敘事基于中國總體性危機背景,[5]正可謂“多難興邦”,讓學生理解歷史進程中的曲折,感受線性脈絡中的屈辱,能夠提升當代青年大學生群體的抗挫能力,激發其對人生價值的思考。歷史進程是螺旋式的上升,具有前進的曲折性,革命不是一帆風順,歷史進程啟示當代大學生要正視生命歷程中的挫折,對大學生群體進行挫折教育具有實用性與現實性意義。
(二)現代化敘事與民族振興教育
蔣廷黻對史學懷揣“貫通”的思想,認為史學工作者不“只能成為某一特殊時代或某一本書的專家”;以至于對比西方史學思潮,希冀“可以有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由此萌生著作“通史”的想法,《中國近代史》的著寫就體現“通史”觀念。蔣廷黻在該書總論中闡述近代化史學觀念和問題關懷,大聲吶喊能否科學現代化、機械現代化、民族現代化,汲取近代中國歷史教訓,總結經驗。在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章節中,對于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和落伍的原因歸納為近代化進程未能及時啟動。蔣氏還認為自強及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在于未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這表現出改革“不徹底性”;除此之外,士大夫“舊的精神”與民眾的迷信也是近代民族“不徹底性”的關鍵因素。蔣廷黻注重批評士大夫群體沽名釣譽和空談誤國的本領,認為這是阻礙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民眾迷信尚可通過教育和改造加以修正,但高級知識分子群體認為名譽比國事重要,近代化路程可能尚待時日。所以,蔣廷黻呼吁人們珍惜歷史時間,加快民族振興,擯棄舊制度和舊精神,投身到近代化歷程中去。
我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及在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蔣廷黻所著《中國近代史》啟示大學生群體實現個人現代化,而個人現代化是語言現代化、身體現代化、思維現代化、能力現代化的集中體現。大學生群體只有完成個人現代化即現代性的塑造,才能夯實民族基礎,實現民族振興。
(三)外交史敘事與理性教育
蔣廷黻注重近代中國外交事務,在《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和《琦善與鴉片戰爭》章節中總結外交的歷史經驗,他認為外交的元素“理”和“勢”非常重要,[6]“理”的內涵在于有理有據,“勢”的內涵在于審時度勢、知己知彼,達到權衡利害輕重效用。蔣廷黻始終是功能主義者,認為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非理性的情感主義不利于外交工作的展開。在馬戈爾尼使團訪華以及侵略戰爭的外交努力中,他認為中華民族妄自尊大的國家情感要不得,他在一定程度上企圖用理性思維手段來描述近代中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所以,近代中國早期外交談判被他認定為大部分是“錯誤的鬧劇”,表現后果為協定關稅與治外法權的喪失,其中緣由之一是近代化視域下法制建設不完善。“鬧劇”發生在于中國使用民族自豪感的情感思維與西方國家使用利益至上的理性手段導致“風牛馬不相及”的歷史錯位。
對于理工科背景的大學生,使其深入了解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的外交史,運用科學邏輯思維和理性認知觀念探究“實事求是”的思想內核;而對于文科背景的大學生,重塑其理性、辯證、法治的分析思想,使其能全面思考歷史問題。
四、結語
蔣廷黻史學思想擅于總結歷史經驗,從歷史問題中反思前人留下的教訓。蔣廷黻的近代化思想是其史學思想的內核,是在歷史經驗和教訓中總結出來的;他的外交理念是史學思想的外核,注重解決現實性和迫切性需求。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蔣廷黻史學思想兼具革命、外交及近代化三重敘事結構體現挫折疏導教育、民族振興情懷和個人理性啟蒙,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蔣廷黻線性脈絡里苦難書寫可以提升學生振作能力,引導學生心理健康進一步發展;蔣書理路中近代化問題意識、民族問題具體化回歸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母題,“育心”與“育德”協同進行,其重視的外交理性更加有助于培育學生政治規矩。當然,我們對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內容必須有所“揚棄”,需以辯證全面的視角觀察問題。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挖掘書中合理有效的部分,加強學生的歷史意識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