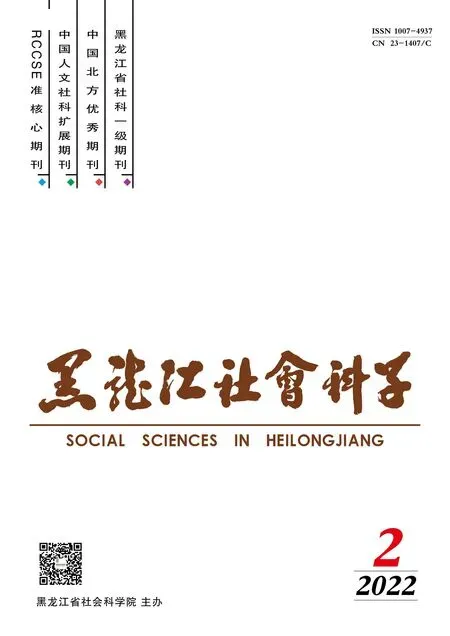馮內古特短篇小說的戰爭書寫
潘 慧 影
(1.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80;2.齊齊哈爾大學 文學與歷史文化學院,黑龍江 齊齊哈爾 161006)
作為親歷二戰的老兵,馮內古特以曾經的軍人身份為榮。他曾在采訪中表示希望死的時候最好有軍禮厚葬,號手奏樂,國旗蓋棺,鳴響禮炮,抬入圣地。這是他一直都很向往的事,因為這些代表了同胞對他的絕對認可[1]。作為現代小說大師,馮內古特寫作不拘一格,體裁多樣,題材廣泛,其中戰爭是他最擅長的創作主題。他的代表作《五號屠場》的主題就是戰爭和死亡。馮內古特不僅擅長用長篇小說反映戰爭,同時也鐘情于用更“經濟”的形式來進行書寫,那就是短篇小說。對于短篇小說的寫作,最初在馮內古特看來是一樁“特別誘人的生意”,因為在雜志行業蓬勃發展的時期,《科利爾雜志》和《星期六晚郵報》每星期都分別需要五篇短篇小說,而他恰恰不缺少寫作小說的天分,因而依靠寫作短篇小說,馮內古特很快可以辭去通用電氣的工作,實現了財富自由。
馮內古特的戰爭小說不拘于記錄戰爭事件,描繪戰場情景。“雖然親眼目睹了發生在德累斯頓的這場戰爭浩劫,馮內古特卻沒有直接描寫戰爭的慘烈場景,而是從一個側面,即戰爭給人在戰后帶來的無法抹掉的陰影和噩夢來表現戰爭。《五號屠場》《黑夜母親》《貓的搖籃》和《上帝保佑你,羅斯瓦特先生》這四部作品表現了二戰的殘酷和給人帶來的精神創傷。”[2]在他的十幾部戰爭短篇小說中,除了揭示戰爭造成的創傷之外,還暴露了戰爭與人性的激烈沖突,詮釋戰爭的悲劇性,展現平民的遭際命運及其反抗、他們對和平的強烈向往和憧憬,表達了作家對平民、兒童和普通士兵等邊緣群體的深切同情。文學或許不具備直接改變社會、消滅戰爭的功能,但用文學書寫戰爭,以戰爭為鏡,反思歷史,拷問人性,將推動人類思考遭遇苦痛災難的根源,從而探索世界走向和平的路徑。
一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戰爭一直形影相隨,而且與政治密不可分。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在《戰爭論》(TheTheoryOnWar, 1832)中提出:“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3]在戰爭中,政客們編織謊言,混淆視聽,給戰爭披上了合理化甚至是神圣化的外衣,蒙蔽剝奪民眾理性思考的能力,掩蓋了戰爭的本質。
馮內古特的戰爭短篇小說《載人導彈》以兩位宇航員父親的通信構思情節,兩位本不相識的父親因為他們的兒子都是航天員而產生了聯系。其中,米哈伊爾的兒子斯捷潘·伊萬科夫少校是第一個太空人,查爾斯的兒子布萊恩特·阿什蘭德上尉是第二個太空人。阿什蘭德在拍攝伊萬科夫過程中因為距離太近,發生碰撞而導致事故,盡管二人彼此搭救,但最終都死于太空。無論是伊萬科夫還是阿什蘭德,他們都堅信自己從事的科學工作是為了和平,而非戰爭。查爾斯在回信中對米哈伊爾傾訴對所謂專家、傳媒機構的不滿:“我告訴您,伊萬科夫先生,我已經受夠了專家。要我說,我們倆的孩子是被專家搞死的。你們的專家搞了個什么東西,我們的專家就用一個幾億美元的神氣漂亮貨回應你們,然后你們的專家再用更神氣的東西回應我們,最后就發生了最后發生的事。他們就像一群拿著幾十億美元或幾十億盧布或者其他玩意兒的孩子。”[4]59-60因為戰爭的需要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兩個天真、熱情,執著于太空探索的年輕人被統治集團利用欺騙,成為戰爭游戲的犧牲品,留下的是兩個傷心絕望的老父親黯然神傷、互訴衷腸。
當權者的欺騙和蒙蔽在小說Thanasphere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戒備森嚴的空軍實驗站發生了爆炸,而真相卻被空軍涉外情報局和北美觀測站的天文學家隱瞞了。他們要掩蓋美國有飛船在天上秘密檢測導彈的事實,這個秘密的埋葬以犧牲航天員賴斯為代價,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家格羅辛格意識到“科學給了人類足以毀滅地球的力量,政治則給了人類一個公平的保證,就是武力必將被使用”[4]78。從而點明了戰爭的本質,即任何戰爭都是政治的產物,都是為政治服務的,都是在政治領導下進行的。戰爭是手段,政治才是戰爭的真正目的。為了實現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統治集團不擇手段,致民眾生命利益于不顧,不達目的不罷休。
《石化了的螞蟻》中的領導者波格洛夫利用螞蟻學家彼特和哥哥約瑟夫研究螞蟻化石來尋找制造武器的鈾和銅礦。而兄弟倆則在研究螞蟻的進化過程中意識到螞蟻曾有過和人類一樣豐富燦爛的文化,但如今“發生在那些螞蟻身上的事正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注定要成群結隊地忙碌和爭斗,僅靠本能生活,使一座又黑又濕的蟻丘揚名于世,甚至都沒有智力想為什么!”[4]264人類與螞蟻一樣曾經和諧共處,但統治集團為了爭奪不斷挑起戰爭,在爭斗中葬送了曾經燦爛輝煌的文明。波格洛夫在利用完兄弟倆完成研究報告后,把化石扔回深不可測的洞里,并把約瑟夫和彼特遣送到了西伯利亞,悄無聲息地埋葬了這個政治秘密。
馮內古特通過這些戰爭短篇小說揭發統治集團的種種陰謀,戳穿戰爭背后的黑暗內幕,暴露統治集團大量聳人聽聞的罪行。他們為了實現政治利益最大化彼此勾連,沆瀣一氣,操縱控制戰爭,欺騙利用民眾,葬送無數平民的生活和生命,共同制造人類歷史上一幕幕慘劇,從而使人們認識到戰爭欺騙、暴力、控制的真相,戰爭的本質就是一種罪惡的“陰謀”。
二
戰爭是人類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與人性、道德、倫理等概念密切相關。脫離了對人性思考的戰爭文學是沒有生命的作品。戰爭是冰冷的,是對人類最殘酷、無情的踐踏和蹂躪。戰爭屠戮之下,人性中的善良、美好不可遏制地遭到壓抑、扭曲,而向善的天性又促使人類不斷努力復歸、修整被異化的人性。于是人性的善惡兩極相互牽引、撕扯,周而復始,自始至終。馮內古特在戰爭短篇小說中聚焦戰爭環境下純潔美好人性的麻木和異化,由此展示戰爭的荒誕和破壞性。
《國王的人馬》構思了一個以生命為賭注的國際象棋游戲,這場對弈就是人性的比拼。美國的凱里上校一行人員因飛機失事落到游擊隊長皮英的地盤上。為了娛樂和證明自己,皮英與凱里約定下一盤棋,賭注是凱里一行16個俘虜的性命。此番博弈,皮英執木頭棋子,而凱里一方的棋子卻是活生生的人,其中包括他摯愛的妻子和孿生兒子。凱里想保全每個人,但根本無法實現,起初他倉皇失措,喉頭發緊,后來逐漸冷靜下來,此時的凱里已經不再是丈夫、父親、長官,而異化成為一個冷酷無情的戰爭機器。他采取犧牲兒子的策略,迷惑了皮英,在皮英和東方姑娘死了之后,巴爾佐夫接替皮英繼續棋局,但他也沒抵擋住這種情緒的誘惑,凱里始終保持冷靜,不敢暴露自己的計劃和情緒,經過多番博弈,最終取得了勝利。此時,“凱里發覺,自己眼看家人面對死亡竟沒什么感覺,不禁感到困惑。等在黑暗監牢里時的那種恐懼已經消失了。現在,他認出了這種怪異的平靜——戰爭的老朋友。這種平靜之下,唯有才智和官能的冰冷機械還在運作。這是將領的麻醉劑。這是戰爭的本質。”[4]2對于皮英來說,16條美國人命賤如草芥,而凱里為了最終的勝利,只能選擇做一個冷漠的戰爭機器。此時對弈比較的已經不是棋藝,而是人性。誰能做到更加冷血,更加狠心,誰能棄絕人性,才有可能茍活。小說由此揭示出戰爭對生命價值的踐踏以及對人性的扭曲。
短篇小說《就咱倆,山姆》開篇即讓人感到驚悚:“這是一個關于士兵的故事,但不完全是戰爭故事。所有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因此我覺得這就成了一個謀殺故事。沒有懸念,就是謀殺。”[4]195受眾人冷落,善用手腕的納粹分子喬治為了占有杰里的手表出賣了他,接著不斷用“咱們倆,山姆,我們兩人同甘共苦”,“你和我兩個”“兩個人正好”“我喜歡跟你作伴”“咱們兩個,山姆”“紅頭發的人就應該同舟共濟”來迷惑“我”,企圖換取“我”的身份借以逃脫戰后對納粹分子的審判。《紀念品》中金發為了逃避美軍的逮捕,企圖用希特勒贈送的名貴金表交換埃迪和巴澤的身份。喬治和金發都將金錢凌駕于他人生命之上,將自我的生命凌駕于他人生命之上,人性的扭曲讓人觸目驚心。
在《海盜旗的巡游》中,內森·杜蘭特被戰爭規訓成了工具人、空心人。17年的軍隊生活使杜蘭特“想到打底就是地形,想到山和谷就是縱射和遮障,想到地平線就是一個人絕不可以讓自己的身形呈現出來的地方,想到房屋及樹林跟灌木叢就是掩體。這樣的生活很好,想厭了戰爭的時候,他就給自己找一個姑娘和一個酒瓶,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準備好再多想想戰爭了”[4]95。杜蘭特后來躲過炮彈轟炸,僥幸逃生,但退役后的和平歲月于他來說仍然是陌生而可怖的。遠離戰爭的生活讓他無法適應,周遭的人們也與他格格不入,他深深感到“他誰都不是,什么也不是。火花熄滅了”。本來對新生活抱有期待的杜蘭特回到海盜旗上覺得“無論哪兒都沒有任何東西在等我”[4]103,“我對任何人都一文不值”[4]103。“戰爭是恐怖和深刻的悲劇,但其罪惡和悲劇不只是在生理方面進行肉體的強暴和戕害……在更深的層次上,存在著精神的暴力和精神的殺戮。”[5]在馮內古特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戰爭不僅傷害了人們身體健康,更摧毀了人類的精神意志,給人類造成了無法彌合的雙重創傷。軍隊的生活將杜蘭特與世事隔絕,離開軍隊,讓他找不到歸屬,他已經被戰爭、被軍隊生活規訓成了工具人,他的個人身份和個體價值已經被戰爭所吞噬。同時,人們對于戰爭及為戰爭付出生命的軍人的忘卻,讓他感到生活全無價值和意義,變成了空心人。
人類歷史上的戰爭總是以生命的逝去、財物的掠奪、文明的毀滅、人性的淪落與滅失為代價,在人們心中留下難以言說的痛苦記憶。二戰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噩夢,更是人類難以治愈的歷史創傷。關于這段歷史,馮內古特的創作不同于傳統戰爭小說的宏大書寫,而是通過挖掘戰爭背景下人性的善與惡、正與邪、是與非之間的沖突及其轉化,流露出對個體生命的憐憫與關懷,從而展現戰爭的悲劇性,揭露戰爭的罪惡。無論是《國王的人馬》中的凱里面對親人、戰友被迫的機械冷漠,皮英游戲他人生命,還是《紀念品》中金發和古德里將軍將自己的生命凌駕于他人生命之上,抑或杜蘭特被戰爭異化成了空心人,陷入絕望和恐懼的深淵,《戰利品》中戰勝國對戰敗國百姓燒殺搶掠,無不讓人深切體會到戰爭之下人性的殘酷無情。馮氏的戰爭書寫盡管很少敵我之間面對面地血腥對決、互相殘殺,但人與人之間最和諧美好的親情、友情、愛情,純真美好的天性都被戰爭踐踏得體無完膚,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巨大悲哀。
三
在很多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作家關注更多的是大歷史,包括塑造叱咤風云、英勇無畏的將領、戰爭勇士,書寫描繪慘烈壯闊的戰爭場面。而在馮內古特關于戰爭的短篇小說里,幾乎看不到傳統戰爭小說中宏大敘事建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戰爭場景。他以黑色幽默抑或荒誕的內容形式將宏大的戰爭命題輕松駕馭于股掌之間,將戰爭中的“小歷史”機智地表現出來。雖然采取的是間接處理戰爭的方式,讀者卻能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戰爭給人們尤其是平民帶來的災難性傷害。在這些戰爭短篇小說中,馮內古特不著意于打造英雄形象,他關注更多的是小人物,將目光投射到被迫卷入戰爭的兒童、俘虜、普通士兵、婦女、貧民的身上,并用戲劇化的手法將其苦痛遭遇放大,反映平民普遍受難的不幸命運,讓人們深切感受到被迫卷入戰爭的人們是如何在水深火熱中奮力掙扎,從而揭示戰爭帶來的巨大創傷,表達對和平的強烈渴望,效果振聾發聵。
《流離失所的人》中有81個戰爭孤兒,其中喬強烈渴望親情。盡管彼得已經告訴他,爸爸是美國兵,戰爭結束后走掉了,喬的媽媽是德國人,把喬給了修女也走掉了。但喬聽了木匠的玩笑話,堅信爸爸就在鎮里。喬跑出孤兒院后遇到一群正在挖工事的士兵,認定其中的中士就是爸爸,堅持要和中士在一起。雖然中士一再解釋,眾人給了喬夠吃20年的巧克力,甚至將昂貴的手表、小刀也送給了喬,勸導喬松開中士,返回修道院,但是喬眼淚汪汪地說:“我不想回去。我要和爸爸在一起。”[4]50眾人表示:“如果可以我們會回來的,喬。士兵永遠不知道第二天要去哪兒。”喬是戰爭棄兒,因為戰爭,他的爸爸來到這里,認識了他的媽媽,一段露水情緣生下了喬。隊伍開拔,喬父親的死活尚不得而知,媽媽也棄他而去。兒童時期是最需要父母呵護關愛的,但是戰爭奪去了這一切。盡管修道院里有細心呵護他的修女,有朝夕陪伴的80個小伙伴,但這些都無法彌補喬對爸爸的思念,對親情的追尋。感謝那隊挖工事的士兵,盡管他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明天,卻用善意的謊言給予喬一份安慰和希望。
《戰利品》中的小男孩在劫掠者離開后,返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以拐杖能夠行走的最快速度走向倉房。他消失在倉房里,在里面待的時間長得令人難以忍受。保羅聽到他微弱的驚呼聲,看到他走到門口,手里拿著柔軟的白色毛皮。他把毛皮貼在臉頰上,然后在門檻上坐下,把臉埋在毛皮中不斷傷心地抽泣”[4]194-195。小男孩雙腿殘疾,出行不便,父母照顧他已經負擔沉重,自然無法帶著他的伙伴小白兔一起逃走。戰后村莊被洗劫一空,可愛的小兔子也成了美軍的盤中之物。戰爭環境下,人們四處奔逃保命,兔子是小男孩兒唯一的朋友,帶給他無限的心靈慰藉,但僅有的快樂和陪伴如今也被無情地剝奪了。覆巢之下,無有完卵,平民是戰爭最直接也是最深重的受害者。人類文明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側面是與其他生命的關系。能否尊重生命,能否對他人和生命都懷有一定的惻隱之心,被視作現代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盡管保羅對自己的掠奪行為十分愧疚,從此再未搶劫,但戰爭中還是出現了太多屠戮無辜生命的慘劇。
普通士兵也是馮氏戰爭短篇小說中重要的觀照對象。《殘暴的故事》中的“我們”是最后一批在位于勒阿弗爾附近的“好彩軍營”中轉的被解救的美國戰俘。“我們”當中的一個士兵斯蒂夫因為從地窖出來帶了半瓶子刀豆,以劫掠罪被處死。因為沒有律師,也不會一句德語,斯蒂夫很難說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小說結尾的一句話反映出殘暴的現實:“是啊……他們會為這事把那靶場周圍方圓五十英里之內的所有人都吊起來殺了。”[4]272在戰爭中,生命被棄之如敝履,隨意加以處置,斯蒂夫之流根本沒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保護自己的生命,只能是案板上的刀俎,任人宰割。
《大日子》中的主人公“俺”是時間屏部隊一員,頂頭上司波利茲基對“俺”的稱呼就是“當兵的”。他委派“俺”當第一排第一班第一個沖鋒的。對于長官的所有要求,“俺”惟命是從:“不管當官的跟你說啥,你都必須信,再荒唐也得信。當官的呢,他們必須信科學家說的。”[4]135“當兵的都在小小的淺溝里,頭上沒遮沒蓋的。命令一下,他們就得從壕溝往外跑。這樣的命令下起個沒完。”[4]131在戰爭中,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如果上級的意志違背了良知,將為了個人理想或國家利益而戰的普通士兵的生命視為草芥,無情剝奪士兵作為獨立個體的生命價值和人生訴求,那么被迫卷入戰爭的普通士兵就將被歷史吞沒,淪為戰爭的犧牲品。
在馮內古特的戰爭短篇小說中,可憐的戰爭棄兒、失去伙伴兒的殘疾兒童、被隨意處置的戰俘及戰場上面對死亡絕對服從的士兵是千百萬受害平民的代表和縮影。他們在炮火紛飛中失去父母、親人、朋友,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在戰爭的鐵蹄下,普通人根本無法把控自身的無常命運,他們的尊嚴被踐踏,生命被剝奪,希望被摧毀,徹底淪為戰爭的殉難者。馮內古特的戰爭短篇小說正是通過對戰爭中平民遭際命運的關注,表達了對戰爭背景下平民不幸命運的深切同情,將馮氏的人道主義精神展露無遺。
除此之外,馮內古特在戰爭短篇小說中還塑造了另一系列卑微渺小的人物形象,例如《獨角獸陷阱》中的樵夫艾爾默,《司令的辦公桌》中的木工廠主,他們是一群戰爭背景下茍活于社會底層,對黑暗現實極度不滿,個人能力十分有限而難以逃脫命運操控的普通人。但他們在戰火的洗禮中不斷成長,逐漸克服身上的懦弱,意識到反抗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并在行動上以自己的方式對暴力和強權進行抗爭,成長為戰爭中的覺醒者。
《獨角獸陷阱》開頭就是一幅恐怖的畫面:“公元1067年,在英格蘭的丘陵緣,十八個死人懸掛在村子絞刑架的十八個拱門上左擺右旋。他們是被征服者威廉的朋友恐怖羅伯特處死的。他們的眼睛怪模怪樣,打著圈子回到原處:向北,向東,向南,再向北。好人、窮人和心善人都感到沒有一點希望。”[4]173恐怖羅伯特就是強權的代表。樵夫艾爾默一向安于現狀、與世無爭,卻被迫要成為恐怖羅伯特貪欲的代表人,否則就要被殘忍地處死。面對恐怖羅伯特的殘暴,艾爾默極度不滿但又不敢反抗,怯懦讓他感到羞愧難當。艾爾默最終決定不當收稅人,即使被絞死也在所不惜。在臨死前的最后一夜,艾爾默去找尋檢查陷阱的兒子。出乎意料的是,艾爾默的兒子竟然用簡單的陷阱捕到一頭鹿,這喚起了艾爾默對生活的希望和反抗的斗志。艾爾默和兒子的夢想就是逮住一頭獨角獸,過上幸福的生活。他說,“如果上帝連一個小樵夫和他兒子的祈禱也都能聽到”,“世界怎么會沒有希望?”[4]186接下來,艾爾默殺掉了恐怖羅伯特,全家飽餐了一頓鹿肉。繼而清除了恐怖羅伯特和鹿的痕跡,隨著諾曼斗士在他們家門前呼嘯而過,恐怖的生活暫時消失了。
《司令的辦公桌》中的“我”是一個小家具工廠主,在戰爭背景下,妻子死于難得的正常死亡。1916年,“我”在奧地利參軍時失去了左腿,帶了一只精致的橡木假肢。女婿戰死后,女兒瑪塔與我相依為命。德軍失敗撤退后,美軍軍官想用工廠里的家具,伊文斯少校看中了“我”給蘇聯司令特制的辦公桌,但需要把桌子上的徽標改動為美國之鷹。刻好了徽標的辦公桌被抬走后,“我”寫信告知少校辦公桌的秘密,原來我之前把炸彈置于辦公桌中,設置了機關,蘇聯司令一旦啟用這張辦公桌就會被炸死。盡管我只是勢單力薄的一介平民,卻一直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戰斗。面對強大的侵略者“我”也曾感到失落、壓抑、孤獨和無助,期盼美國人的拯救,但我從沒有置身事外、獨善其身、怯懦脆弱,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方式進行斗爭,表現出了平民孤膽英雄強大的反抗力量:“我想告訴他我如何抵抗哈布斯堡王朝和納粹,然后是捷克共產黨,然后是蘇聯人——用我自己個人的方式同他們斗爭。我從來沒有一次站在獨裁者一邊,我也永遠不會站在他們一邊。”[4]229
如果戰爭文學作品不關注戰爭中普通人所遭受的巨大傷害,就無法真正揭示戰爭的悲劇性;如果戰爭文學不關注戰爭中普通人的反抗,那么就無法真正感受戰爭中人性的尊嚴和力量[6]。馮內古特在一系列戰爭短篇小說中不著意書寫塑造英雄人物,而是以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觀照身陷戰爭泥沼的“非英雄”人物,關注他們在戰爭中的苦難遭遇,透視他們不甘屈服的內心世界,展現他們的智慧與反抗。盡管這群人地位卑微,力量弱小,是名副其實的“無名之輩”,但是在大的戰爭背景之下,他們對于生命的敬畏,對于強權的反抗,使他們的形象放射出耀眼的光輝,展露出人性的力量,也讓人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和曙光。
戰爭,非人類所愿;和平,才是永恒主題。戰爭的毀滅性打擊,人們戰后漂泊離亂的生活及精神的崩潰扭曲,促使馮內古特在批判揭露的同時,不露聲色地書寫出對和平生活的期冀和向往,這一主題貫穿于《生日快樂,1951》《載人導彈》等作品中。《生日快樂,1951》塑造了一位充滿愛心、愛好和平的老人,還有一個不知戰爭為何物,對戰爭充滿好奇的孩子。老人和男孩相依為命,因為生活困窘,孩子六歲了沒有慶祝過生日,今年老人決定給孩子過個生日。老人準備的生日禮物既不是孩子期盼的蛋糕,也不是老人想過的手推車,而是“明天我要帶著你離開戰爭”[4]160。于是老人帶著孩子到了密林深處,坐在一塊巖石臺上共享生日午餐。孩子對這樣安靜的環境卻不適應,感覺“這里太安靜了”,“我更喜歡城里,有士兵還有——”老人卻說“本該這樣才好”,“那才叫美。”[4]163老人在小憩醒來后找不見男孩,卻看到男孩惡作劇般從坦克的塔臺上探出頭來,一副勝利的姿態[4]164。從一老一小的對話中不難看出,在孩子的眼里,戰爭就像游戲一般,你打我一拳,我回擊你一下,他根本不清楚戰爭的恐怖,而老人對此卻是知之甚深,和平才是最珍貴美好的禮物。
結 語
戰爭是“對峙雙方為了一定的政治、經濟需要而采取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行為”[7]。只要是戰爭,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采取什么樣的方式,都要不同程度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戰爭就是相互謀殺,是對人性的極端考驗。馮內古特曾經親歷二戰,在戰爭中目睹德累斯頓大轟炸的慘況。對于馮內古特來說,戰爭是最野蠻兇惡、反自然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一切人性丑惡與政治陰暗潛滋暗長的基床。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揭示戰爭的本質,表現混亂悖謬的現實,引發歷史性的反思是馮內古特應對這個瘋狂世界的獨特書寫方式。
縱觀馮內古特的戰爭短篇小說,幾乎不涉及戰爭本身,對于戰爭的緣起、過程及后果也不做詳細完整的敘述,而是將視角投注于戰爭“大歷史”背景下普通人的命運和遭際,即“小歷史”。從多維視角反映暴力戰爭帶給人類的沉重苦難,表達對平民、兒童和普通士兵等邊緣群體的深切同情,詮釋戰爭的悲劇性,以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懷抒發對戰爭的厭惡、對生命的憐憫、對人性的思考以及對世界和平的憧憬。馮內古特在《大日子》中曾描述了他理想中的新世界的模樣:沒有戰爭,人們參軍不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和平,全世界只剩下了一個軍隊就是世界軍,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能和諧相處。戴夫·艾格斯在《2081:馮內古特短篇小說全集》前言中提到馮內古特曾拓下石碑上的墓志銘“該死,你得善良”送給他,使得艾格斯意識到“人得善良。別傷害。關心你的家庭。別發動戰爭”[4]3。理想世界的愿景加上這短短四句話,道出了幾乎接近了真理的馮內古特哲學:要和平,不要戰爭!而這恰是馮氏在戰爭短篇小說中一以貫之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