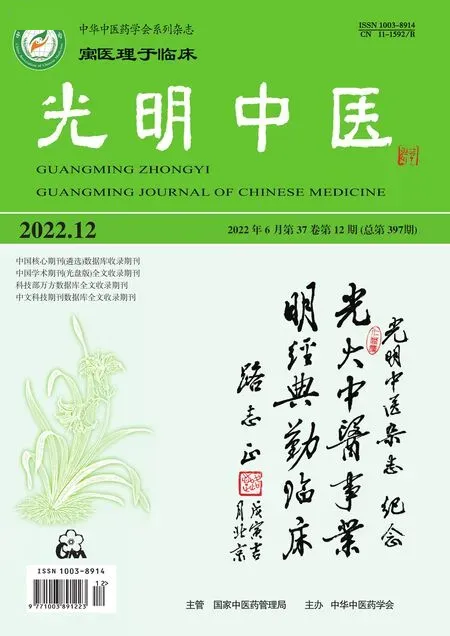經方論治咳嗽思維探析
楊偉偉 馬家駒
咳嗽是常見的臨床癥狀,各個年齡段均可發生。咳嗽根據發病時間分為3周以內、3~8周、8周以上。其中,3周以內的常稱為急性咳嗽;3~8周考慮為亞急性咳嗽;超過8周稱為慢性咳嗽,也稱頑固性咳嗽。慢性咳嗽病因常見的有變態反應性、胃食管反流病、慢性咽炎、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鼻后滴流綜合征等等,西醫對癥治療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癥狀,并不能完全治愈,反復發作,給工作生活帶來不便。
1 咳嗽中醫含義
有聲無痰為咳,有痰無聲為嗽,當代醫家認為病變臟腑為肺,涉及肝、脾、腎三臟。病因常有外感六淫,兼挾為病;臟腑不調,七情內傷;稟賦異常,內外合邪等,導致肺失宣肅,肺氣上逆作咳[1]。
2 咳嗽辨證
經方治療咳嗽,采用六經辨證有較好的療效,《傷寒雜病論》是以六經辨證思想為指導,采用經方治療咳嗽,取得了一定的療效,本文試從六經方證辨證角度探討經方治療咳嗽的思路。
2.1 咳嗽可見于太陽表證在《傷寒雜病論》中,張仲景對咳嗽一癥論述精詳。如《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并治第七》:“風舍于肺,其人則咳及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提出以風邪概括外感六淫之邪,客于肺則咳嗽,治法為發汗。發汗為八法之一,針對的則是太陽表證。可知咳嗽一癥可見于太陽表證。按照《傷寒雜病論》六經辨證,除咳嗽,若伴有身熱,汗出,惡風,脈緩者,為太陽中風,方用桂枝湯,伴有惡寒,體痛,脈陰陽俱緊者,為太陽傷寒,方用麻黃湯。若脈沉脈弱,屬少陰病,方應合四逆輩。即根據六經辨證為表證,再根據舌脈辨為太陽病、少陰病,再具體到方藥。
2.2 咳嗽臨床上多見于表里同病《黃帝內經》曰:“有諸內,必形諸外”,咳嗽只是臨床中一個癥狀,病位不一定在表,在《傷寒雜病論》中:“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干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黃元御在《黃元御傷寒解》中提到小青龍湯用于表有寒而里有水也,傷寒之人,或表邪外郁而宿水里發,或渴飲涼水而停留不消,是以多有水氣之證。以其熱渴,雙解表里之寒,小青龍乃不易之法也。小青龍湯是里陽之虛,內有水氣。陰陽一偏,逢郁即發,大小青龍,外解風寒而內瀉水火,感證之必不可少者也[2],提出小青龍湯為表里雙解方劑,用于表有寒,內有水飲證型。曹穎甫《經方試驗錄》曰:“余屢用本方治咳,皆有奇效。顧必審其咳而屬于水氣者,然后用之,非以之盡治諸咳也。水氣者何?言邪氣之屬于水者也”。又在文中如何得水氣,一則習游泳而得水氣,二則多進果品冷飲而得水氣,又如遠行冒雨露,因得水氣,其三也,四則夙患痰飲,為風寒所激,凡此種水氣之咳,本湯皆能優治之[3]。也證實小青龍湯用于外有表寒,內有水飲之證型,并對內有水飲4種情況進行了詳細闡述。對于藥量輕重,曹穎甫也有自己的觀點:顧藥量又有輕重之分,其身熱重,頭痛惡寒甚者,當重用麻桂。其身微熱,微惡寒者,當減輕麻桂,甚可以豆豉代麻黃,蘇葉代桂枝。其痰飲水氣甚者,當重用姜辛半味,因此四者協力合作,猶一藥然,用五味嘗多至三錢,切勿畏其酸收。其咳久致腹皮攣急而痛者,當重用芍草以安之[3]。并對小青龍湯主治進行了闡述:小青龍證,在里為水氣,在表為咳(咳之前喉皆常作癢),其表證之重輕,初可勿拘,其舌苔亦不必限于白膩。遑論其他或喘、或渴、或利、或噎此皆經驗之談,不必泥于書本[3]。只要辨證為外有表,內有水氣,無論癥狀如何,皆可以用小青龍湯。《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中曰:“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歷代醫家多認同此觀點,代表方有大青龍湯、小青龍湯等,但事實上,咳嗽亦可見里證、半表半里證。
案1 楊某某,女,34歲。2019年12月5日就診。主訴:咳嗽1年,1年前患者感冒后遺留咳嗽,干咳,咽癢,經常鼻塞,汗出少,無口苦,夢多,脾氣急,怕涼,手足不溫,口干渴喜熱飲,大便2~3次/d,質溏稀,月經提前5~7 d,量偏少,色暗。舌暗胖大,齒痕,苔白厚,脈沉略弦。辨證分析:鼻塞、汗少,辨為表證;便溏、脈沉、飲熱水,四逆為里寒陰證之太陰病。結合舌脈,辨六經為少陰太陰合病,辨方證為小青龍湯合附片合五苓散加減。處方:麻黃10 g,白芍10 g,細辛6 g,干姜6 g,炙甘草10 g,桂枝10 g,五味子6 g,豬苓10 g,澤瀉15 g,炒白術15 g,茯苓15 g,姜半夏15 g,黑順片(先煎)10 g,生石膏(先煎)30 g。7劑,水煎服,每日2次。溫服,服藥后微發汗1次。2019年12月19日二診。服藥后咳嗽緩解80%,表證不明顯,未再服藥。1年后隨訪未再咳嗽。
按語:經方治病,重在辨證。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明確提出辨各經病脈證并治,六經是以表、里、半表半里為經,寒熱、虛實為緯,將百病劃分為六經病。分為表實熱證的太陽病,表虛寒證的少陰病,里實熱的陽明病,里虛寒的太陰病,半表半里偏于陽熱證的少陽病,半表半里偏于虛寒證的厥陰病,這樣六經與八綱一一相應。辨六經的過程,其實就是辨別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的過程。醫案1為青年女性,慢性咳嗽,以咳嗽為主訴。患者鼻塞、汗少,辨為表證;便溏、脈沉、飲熱水,手足不溫為里寒陰證之太陰病。整體病性屬虛、屬寒,屬于陰證。此病為少陰太陰合病,咳嗽,給予小青龍湯合附片合五苓散加減,服用7劑咳嗽癥狀緩解明顯。五苓散出自《傷寒雜病論》多條條文,成無幾曾釋五苓散方為和表里,散停飲,生津液[4]。黃元御曰:陰盛之人,陽亡土濕,則入太陰,而成五苓散證。若汗后脈浮,小便不利,熱微消渴,則太陰之象已見端倪,宜以五苓燥土而行水。此之消渴,消少水而頻飲,不能大消,以其濕盛而熱微也[2]。五苓散,桂枝行經而發表,白術燥土而生津,豬苓、茯苓、澤瀉行水而瀉濕也。多服暖水,蒸泄皮毛,使宿水亦從汗散,表里皆愈矣[2]。方中加附片,合炙甘草、干姜組成四逆湯,癥狀有下利、脈沉、四逆,四逆湯可用于太陰病、少陰病,在馬家駒六經入門講記中提出,四逆湯不僅可以治療危急重癥,還可用于太陰病里虛寒相對輕的情況,比如大便溏、脈沉弱,有時并不出現四逆,屬于四逆湯輕證,四逆湯可以小劑量應用,同樣也能夠起到溫中補虛的治療作用,陽虛嚴重的時候,四逆湯劑量可以加大。還提到一般溫陽的時候用炮附片即可,溫陽益氣的都是炙甘草,不是生甘草[5]。黃元御在《傷寒懸解》中提出少陰水臟,病見沉脈,仲景傷寒,少陰但有瀉水補火之法,而無瀉火補水之方[2]。
案2 楊某,女,32歲。2019年7月25日就診。主訴咳嗽3年,2016年患者感冒后遺留咳嗽,曾至中日醫院、北京協和醫院診斷為變異性哮喘(氣道高反應),應用信必可治療2年,效果不明顯,外出、遇冷、情緒激動時易咳,伴胸悶胸癢感,干咳,平素無明顯鼻部癥狀,惡寒,易汗出,口干不苦,月經量少,大便干,無手足怕冷。舌淡紅邊有齒痕,苔薄白,脈沉細。
辨證分析:患者外出、遇冷時易咳,惡寒,易汗出,辨為表證,脈沉,月經量少,舌淡邊有齒痕,為里寒陰證之太陰病,整體病性屬虛屬寒,屬于陰證。此病為少陰太陰合病,咳嗽,故給予桂枝加附子湯合當歸芍藥散加減。處方:桂枝10 g,白芍10 g,炙甘草10 g,生姜10 g,大棗10 g,炮附片10 g,干姜10 g,當歸15 g,川芎10 g,茯苓30 g,生白術30 g,澤瀉15 g,紅曲米12 g,紫蘇葉10 g,杏仁10 g。7劑,水煎服,日1劑。
二診。吹空調后咳,無咽癢,胸癢感減輕,大便干減輕,口中和,苔薄白,脈沉細。表證仍在,仍需繼續解表,上方加杏仁10 g加強止咳定喘作用,14劑,水煎服,日1劑。
三診。本次服藥后自覺改善明顯。舌淡紅,齒痕,苔薄,脈細弱。表證仍在,還需解表,處方:桂枝10 g,白芍10 g,炙甘草10 g,紫蘇葉10 g,大棗10 g,當歸15 g,川芎10 g,茯苓15 g,生白術30 g,澤瀉15 g,炮附片10 g,干姜6 g,杏仁10 g,枇杷葉10 g,紅曲米12 g。7劑,水煎服,日1劑。
四診。患者咳嗽已,1年后隨訪無復發。
按語:該案的六經病的判定,亦是根據表里寒熱虛實的八綱而定的,該案患者青年女性,變異性哮喘,此次就診以慢性咳嗽為主訴。患者外出、遇冷時易咳,惡寒,易汗出,辨為表證,脈沉,月經量少,舌淡邊有齒痕,為里寒陰證之太陰病,整體病性屬虛屬寒,屬于陰證。六經的判定是依據整體機體的反應,咳嗽機體反應為表里合病,不僅要解表還要表里并治,此病為少陰太陰合病,咳嗽,故給予桂枝加附子湯合當歸芍藥散加減。桂枝加附子湯出自《傷寒雜病論》:“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柯琴說:“是方以附子加入桂枝湯中,大補表陽也。表陽密,則漏汗自止,惡風自罷矣。汗止津回,則小便自利,四肢自柔矣”[5]。當歸芍藥散為太陰病血虛之方,婦人懷娠,腹中疞痛,當歸芍藥散主之,為補血利濕方。故二診時咳嗽已明顯好轉,后調理而愈。
2.3 咳嗽可表現為里證或半表半里證經方注重方證相應,它的魅力在于效如桴鼓的臨床療效。在《傷寒雜病論》文中提到:“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桂枝證、柴胡證、四逆輩等方劑在《傷寒雜病論》中被多次提到,它強調了在經方辨證中方證相應的重要性。在經方臨證中,當先辨六經,再辨方證,求得方證相應,從而治愈疾病。可以說經方臨床療效的有無,在于辨六經辨方證是否準確。《傷寒雜病論》條文:“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咳嗽不僅表現在表證,通過疏散表邪達到臨床上很好的療效,通過六經辨證,亦有里證、合病、并病的問題。
案3 郭某某,女,53歲。2019年7月18日就診。主訴:反復咳嗽6年,加重2個月余。刻下癥:咳嗽咳痰,白痰質稀,無鼻塞,有噴嚏,乏力,不惡寒,便秘,無手足怕冷。舌淡暗苔白,脈沉弱。
辨證分析:乏力,白稀痰,脈沉弱為里虛寒證,此處大便未行,當為虛寒導致脾胃功能低下所致,非陽明病的胃家實。六經當屬太陰病,方用半夏厚樸湯合六君子湯加減,處方如下:姜半夏15 g,紫蘇葉12 g,厚樸15 g,茯苓15 g,生姜(自備)10 g,黨參10 g,生白術15 g,炙甘草6 g,陳皮15 g,枇杷葉15 g。7劑,水煎服,日1劑。
二診咳嗽減輕,抄方。
8月15日三診。咳已,無咳痰,調理而愈,未再復發。
按語:六經辨證,辨的是3個病位(表、里、半表半里)上的陰陽。六經辨證以病位、病性及提綱條文來作為判斷依據,典型驗案可以直接依據提綱條文來判斷,不典型的時候則需要辨病位、辨病性。該患者無表證及半表半里證臨床癥狀,病位上可辨為里證,結合舌脈及乏力,白稀痰,病性屬虛屬寒,六經辨為太陰病,給予半夏厚樸湯合六君子湯加減,效果顯著。
案4 于某某,女,35歲。2019年6月13日初診。主訴:咳嗽1周,刻下癥:咳嗽,無鼻部癥狀,口苦,咽干,二便可。月經偏少,痛經,乏力,舌尖紅苔薄,脈弱。
辨證分析:口苦、咽干,屬半表半里熱,在傷寒少陽病提綱:少陽之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口、咽、目是清竅,半表半里熱上擾清竅,容易出現口苦、咽干、目眩,也反映了半表半里熱郁的狀態。該案雖然半表半里熱證明顯,但同時有月經量少,痛經,乏力,脈弱虛寒證,整體為上熱下寒,辨當屬半表半里寒熱錯雜的厥陰病,因女子以血為本,體質弱,血虛不足,則月經量少,乏力,治療當調和寒熱,養血益氣,扶正祛邪,給予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當歸芍藥散。處方:柴胡15 g,桂枝10 g,干姜6 g,天花粉15 g,黃芩10 g,炙甘草6 g,生龍骨15 g,生牡蠣15 g,當歸9 g,川芎9 g,白芍20 g,茯苓12 g,生白術12 g,澤瀉15 g,枇杷葉10 g。7劑,水煎服,日1劑。
2019年6月27日二診。咳嗽服藥后減輕,后因感冒出現鼻塞流涕噴嚏,不汗出,余癥狀同前,舌脈同前,鼻塞流涕噴嚏為太陽表實證,加用麻黃6 g,杏仁10 g,合桂枝、炙甘草合麻黃湯解表。7劑,水煎服,日1劑。
10月24日三診患者已不咳。
按語:經方治病,先辨六經明確治療大方向,然后細辨方證,以求方證相應獲良效。患者寒熱錯雜,單純清熱則易加重下寒,單純溫陽則易助上熱,治療時當根據方證選擇合適治療方案。
2.4 咳嗽以合并里陰證常見馬家駒老師[5]在多年臨床中發現,慢性咳嗽久治不愈往往會伴有里虛寒,太陰病的痰飲水濕,表現為舌胖大有齒痕、脈沉弱、便溏、乏力、惡寒等,在應用半夏厚樸湯的基礎上,需要加大溫運太陰的力度,可能會與四逆湯相合。如果虛證不明顯,只有乏力、氣短、便溏的癥狀,就與四君子湯相合。面對一些久治不愈、頑固性疑難雜癥的時候,要多關注太陰的問題。
案5 樊某某,女,50歲。2019年8月1日初診。主訴:咳嗽3個月余。刻下癥:咳嗽,平臥后明顯,痰少白黏,無鼻部癥狀,飲水多自覺飲停右脅肋,無胃脘部不適,乏力不惡寒,二便調,飲水多小便頻,口黏。既往3個月前行右肺癌胸腔鏡手術,左肺結節、乳腺結節病史。舌暗紅,苔薄膩,脈弱。
辨證分析:咳嗽痰少白黏,飲水多自覺飲停右脅肋,小便頻,口黏,屬太陰病,結合舌脈,辨六經為太陰病,辨方證為半夏厚樸湯合五苓散加減。處方:紫蘇梗15 g,厚樸12 g,茯苓15 g,生姜10 g,姜半夏15 g,豬苓10 g,澤瀉15 g,炒白術15 g,桂枝10 g,陳皮15 g,紅曲米12 g。14劑,水煎服,日1劑。
2019年8月15日二診。上方服第2劑藥咳已,今日感冒,喘,腹瀉,汗出不多,無鼻部癥狀,頭痛,胸悶,無口干苦,尿頻。舌暗紅,苔薄膩,脈弱。有表證,調整方藥為:紫蘇梗15 g,厚樸12 g,茯苓15 g,生姜10 g,姜半夏15 g,麻黃10 g,杏仁10 g,炙甘草10 g。服藥后覆被發1次汗,若感冒愈,去麻黃,接上方。
9月12日三診。咳嗽已,感冒癥狀已。
按語:經方治病,重在辨證。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明確提出辨各經脈證并治,六經是以表、里、半表半里為經,寒熱、虛實為緯,將百病劃分為六經病。分為表實熱證的太陽病,表虛寒證的少陰病,里實熱的陽明病,里虛寒的太陰病,半表半里偏于陽熱證的少陽病,半表半里偏于虛寒證的厥陰病,這樣六經與八綱一一相應。辨六經的過程,其實就是辨別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的過程。
該案中,患者中年女性,以咳嗽為主訴,無明顯表證,不屬于太陽、少陰證,飲水多則飲停右脅肋,小便頻,口黏,脈弱,為里寒證之太陰病。整體病性屬虛屬寒,屬于陰證。此病為太陰病,咳嗽,給予半夏厚樸湯合五苓散加減。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五苓散,黃元御在《傷寒懸解》中提到小便不利者方用茯苓,五苓散則兼用豬、茯苓、澤瀉瀉水以發汗。傷寒多傳太陰,病水者固眾。五苓散,桂枝行經而發表,白術燥土而生津,豬、茯苓、澤瀉行水而瀉濕[2]。二診中患者有表證:喘、頭痛、汗出不多,辨證為太陽病,加用麻黃湯。麻黃湯: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不汗出而喘者,麻黃湯主之,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囑服藥后覆被發一次汗,去麻黃,接上方。
3 討論
柯琴推崇六經辨治,在他的《傷寒來蘇集》中曰:“夫仲景之六經,為百病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制”。咳嗽的治療同樣需要遵循仲景六經辨證原則,即先辨六經再辨方證。經方強調辨六經,而辨六經的實質即是辨八綱,即辨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因此可以通過辨八綱來確定六經。辨方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經方愈病之理在于辨方證,方證相應方能效如桴鼓。臨床上當先辨病位(表、里、半表半里),再辨病性(大的方面是陰陽,具體為寒熱、虛實)。即表證的陽證為太陽病,表證的陰證為少陰病,少陰病是邪在表而呈虛寒一類證候者[5],里證的陽證為陽明病,里證的陰證為太陰病,半表半里證的陽證為少陽證,半表半里證的陰證為厥陰病。半表半里部位可用排除法確定,癥狀非里證非表證即為半表半里證,再辨別陰證陽證,病位確定了,方子也就確定了。臨床上深深體會,經方臨床療效的有無,在于六經辨證是否準確。
在《黃帝內經·咳論》提出:“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綜觀以上驗案,六經病皆可引起咳嗽。咳嗽病位不一定在表,可在里,或半表半里,或表里合病,在表則從表論治,在里則從里論治,表里合病則可表里雙解,或先表后里,或先里后表。因其可表現為多種經病,故臨床治療需以六經方證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