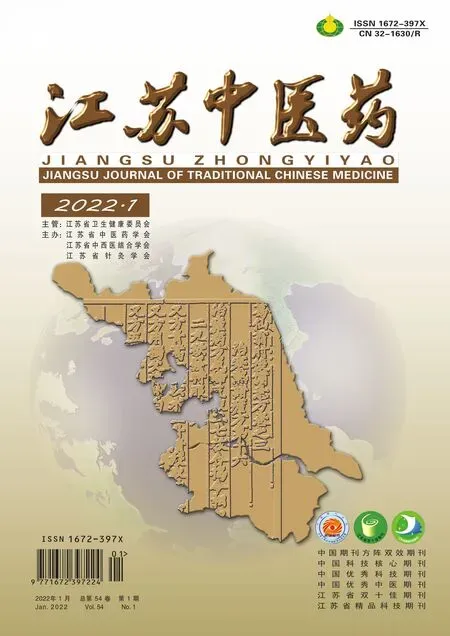基于藏象學說探討特應性皮炎發病機理及辨治規律
李丹陽 朱澤兵 徐 菁 段行武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北京 100007)
特應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又名異位性皮炎、遺傳過敏性皮炎,是一種具有遺傳傾向的慢性復發性、炎癥性皮膚病,主要表現為皮膚紅斑、丘疹、滲出、鱗屑,瘙癢劇烈,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1]。現代醫學認為遺傳、環境因素與本病密切相關[2],免疫系統異常、皮膚屏障功能受損及皮膚菌群紊亂等相互作用共同導致AD的發病[1]。AD可歸屬于中醫學“四彎風”“奶癬”“胎瘡”等范疇,古代醫家認為本病多由稟賦不耐,胎毒遺熱,熱伏于內,加之感受風、濕、熱邪而發病[3]。現代醫家在此基礎上達成了從心火脾虛立論,分期治療的共識[4]。除“心火過盛,脾虛失運”基本病機外,筆者認為肺、肝、腎三臟功能失調的病機亦不可忽視。本病嬰兒期皮損以滲出為主,多因胎毒遺熱、心火亢盛而致;兒童及青少年、成人期皮損多樣,反復發作,多與脾虛濕蘊、濕熱互結密切相關;病久或老年期患者皮損干燥、肥厚、鱗屑、苔癬樣變,則為肝腎虧虛、陰虛血燥、肌膚失養所致。而肺主皮毛、主通調水道的功能貫穿本病的全過程。藏象學說是研究五臟六腑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及其相互關系的學說,皮膚的生理、病理表現究其根本源于五臟的功能狀態,正如《外科啟玄》[5]曰:“言瘡雖生于肌膚之外,而其根本原集予臟腑之內。”本文以藏象學說為基礎,論述臟腑功能失調與AD發生發展的關系,并探討通過協調五臟、調理氣血精津等措施來治療本病。
1 心與特應性皮炎
1.1 病因病機——心火亢盛,心神失養《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痛癢瘡,皆屬于心”,高度概括了外在的瘡瘍與心的密切聯系。劉完素后將其改為“諸痛癢瘡,皆屬于心火”,明確將痛癥、瘙癢、瘡瘍諸癥之病機統歸于心火。兒童為AD好發人群,生理方面,小兒為純陽之體,“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心屬火,所謂壯火之氣,故心火易動;病理方面,小兒腎水不足,易于感受熱毒,導致“心火獨亢”。心主血脈,心氣推動和調節血液循行于脈中,周流全身,內養臟腑,外溢肌膚。若氣化太過,心火內熾,熱郁肌表,氣血阻滯,則見皮膚瘙癢、口舌生瘡甚至糜爛;或氣化不足,心氣無力推動血行,血虛生燥,肌膚失養,則見皮膚干燥粗糙、瘙癢無度。此外,心藏神,為五臟六腑之大主,若心神失養,可出現精神情志和感知方面的異常,如心煩、失眠,甚至瘙癢、疼痛等,西醫學也明確指出,精神神經因素是AD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6]。故心的功能失調在AD發病中具有重要意義,血脈失調是發病前提,心火亢盛是重要病機,心神失養是關鍵因素,這三者貫穿于AD整個發病過程。
1.2 從心論治——清瀉心火,調養心神基于前文論述,從心辨治AD當以清瀉心火、調養心神、濡養血脈為大法,治療時可選用清心解毒、養血止癢的藥物,如連翹心、梔子心、蓮子心、生地黃、玄參、車前子、燈心草、蟬蛻、茯苓等[4],共奏清心導濕、解毒止癢之功。此法常用于嬰兒期AD的治療,癥見紅斑、鱗屑,形如癬疥,或生丘疹、丘皰疹,黃水浸淫、糜爛、結痂,瘙癢無度,啼吵不安,煩躁不寧,溺黃短少。有學者認為心神失調是AD的主要病機,故采用鎮心安神法治療本病,方選龍牡湯,取得良好療效[7]。也有學者指出“心火”因素在兒童AD發病中貫穿始終,故可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加淡竹葉、燈心草等清心除煩之品[8]。心火得清,煩熱得除,則失眠、心煩、神志不寧等癥狀可解。
2 脾與特應性皮炎
2.1 病因病機——脾胃虛弱,納化失常一方面,濕邪是貫穿AD發病始終的關鍵致病因素,也是導致本病反復發作、纏綿難愈的根源所在,而濕邪的產生與脾密切相關,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濕腫滿,皆屬于脾。”另一方面,AD的發生與正氣虛弱有關,誠如《素問·評熱病論》所說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而正氣的強弱也與脾胃功能密不可分,所謂“胃氣一虛,耳、目、口、鼻聚之為病”。此外,《素問·經脈別論》提道:“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既虛,水液運化失司,風濕熱邪易與內濕相互搏結,浸淫肌膚,繼而出現水皰、斑丘疹、浸漬糜爛、瘙癢難耐;若久病,氣血生化進一步乏源,陰血不足,肌膚失養,可出現皮膚干燥、脫屑、肥厚等癥。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AD的發生與食物過敏、腸道黏膜屏障缺損及腸道滲透率的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有關[9],而這些均與中醫脾胃功能密切相關。因此,脾胃虛弱貫穿AD發生發展始終,只有脾胃納化相依,升降相因,燥濕相濟,運化功能正常,濕邪得除,則肌膚自安,疾病自愈。
2.2 從脾論治——健脾和胃,祛濕止癢脾虛為本病主要病機,因此固護脾胃、健脾除濕是本病治療關鍵。方藥可用參苓白術散或四君子湯加減,或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加蒼術、白術、茯苓、澤瀉、陳皮、山藥、薏苡仁等。小兒“脾常虛”,此法多用于嬰兒期和兒童反復發作的穩定期,癥見紅斑、丘疹、糜爛、滲液,常伴有口黏、納呆、倦怠乏力、大便稀溏,舌胖有齒痕、苔白膩。宋坪教授從臟腑風濕的角度討論了AD的辨證論治,運用小兒化濕湯加減取得一定療效[10]。此外,內濕多易與風濕熱邪相搏,若夾風邪,皮損多泛發,游行善變,瘙癢明顯;濕重于熱,則見皮膚輕度潮紅,皮損肥厚、色澤黯淡,抓后糜爛滲出較多;熱重于濕,則見皮損潮紅焮熱,輕度腫脹,繼而粟疹成片或水皰密集,滲液流滋。辨治時,熱重于濕者,以治標為主;濕重于熱者,以治脾為主;濕蘊日久不解者,酌加祛風止癢或養血潤膚之品。AD初期,應先治濕熱之標,再理脾助運以治其本。總之,無論處于哪個階段,脾胃功能的強弱均為本病轉歸的關鍵。
3 肺與特應性皮炎
3.1 病因病機——肺氣虛弱,宣降失司《靈樞·九針論》言:“肺者,五臟六腑之蓋也。”肺為臟之長,保護諸臟免受外邪侵襲;肺為“水之上源”,主通調水道,對體內水液的輸布、運行和排泄起著疏導調節作用。肺主皮毛,宣發衛氣,司腠理之開合,衛氣對皮膚有著溫養、濡潤、固衛的作用,“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致密矣”。若肺氣虛或宣發肅降功能失常,則可致腠理不固,玄府不開,氣血壅滯郁于肌膚而不行,正邪相搏而生斑疹、丘疹及致癢等,或衛外功能失常,腠理開闔失司,皮毛失其濡潤而致干燥、無汗,或水液失于輸布,飲邪內停而表現為皮膚水腫等。因此,皮膚的生理功能與肺密切相關。AD患者常合并其他特應性疾病,如哮喘、過敏性鼻炎等,現代醫學已經證實,AD與這類呼吸道變態反應性疾病在發生發展中的病因學、免疫機制及臨床表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11]。有報道指出,幾乎1/3的過敏性皮膚病患者伴隨哮喘、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肺部相關疾病[12],說明皮膚異常可為肺部病變以及肺功能異常的外在表現。此外,皮膚屏障功能障礙也是本病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3]。可見,肺失宣降是AD發生的重要病機。
3.2 從肺論治——益氣宣肺,祛風止癢從肺論治AD,除了運用治療肺部疾患常用的宣、補、潤、清等治肺四法外,從皮毛入手治療也是臨床上常用的方法。在AD治療中,清熱祛風與宣肺解表常同時使用,可選消風散與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加減,可酌情配忍冬藤、雞血藤等藤類藥,白鮮皮、地骨皮等皮類藥加強走表之力,疏風通絡,注重“運而不補、溫而不燥、滋而不膩”[14]。此法適用于AD急性期,或AD伴有外感表證時,除基本皮損外,還伴隨頭身疼痛、無汗、脈緊等表現,或伴有咳喘等肺部癥狀,此時外邪侵襲肌表并入里傷及于肺,用此法治療可表里同調,和解內外之邪。此外,臨床上以肺脾立論亦多見,從肺脾氣虛的基本病機出發,采用肺脾同治法,健脾與固肺并重,以達到運脾除濕、祛風宣肺的目的[13]。馬紹堯教授首創“運脾化濕清肺湯”應用于AD患者,運脾除濕為本,佐以清熱祛風宣肺為要[15]。艾儒棣教授以馬齒莧湯和四君子湯聯合運用,內服結合煎湯外洗,內外同治,肺脾同調,健運脾氣又有培土生金之意[16]。
4 肝與特應性皮炎
4.1 病因病機——肝失疏泄,肝血不充《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云:“四彎風,生于兩腿彎、腳彎,每月一發,形如風癬,屬風邪襲入腠理而成,其癢無度,搔破津水,形如濕癬。”風邪與本病發病有重要關系。《素問·至真要大論》言:“諸風掉眩,皆屬于肝。”由此可知,肝為內生風邪之源。肝主疏泄,調暢一身氣機,氣機升降正常,則氣血沖和,陰陽平衡,百病不生。若肝失疏泄,肝氣郁結,氣滯血阻,氣血不調,瘀阻肌膚,漸生斑疹,發為本病,日久可見瘙癢、皮膚干燥粗糙等臨床表現。氣郁濕滯,化火化熱,浸淫肌膚則見糜爛、滲出、流滋等癥。現代醫學認為,皮膚病的發生多與機體免疫功能失調有關,而肝主疏泄是人體免疫調控功能活動的核心[17]。此外,肝主藏血,若肝血不足,血不營膚,肌膚失養,可見皮膚干燥、脫屑、瘙癢等“血虛風燥”之候。《丹溪心法》言:“諸癢為虛,血不榮肌腠,所以癢也”,明確指出瘙癢與血虛不潤膚密切相關,進一步說明了肝藏血功能失職引發本病的病理機制。故肝失疏泄、肝血不充是AD的重要病機。
4.2 從肝論治——疏肝理氣,養血柔肝從肝論治本病,疏肝理氣、養血柔肝是基本大法,可選逍遙丸合當歸飲子加減。逍遙丸疏肝健脾養血,當歸飲子養血潤燥、祛風止癢,二者合用,則肝氣可疏,氣血調和,疾病自安。此法常對應本病的血虛風燥證,即青少年和成人反復發作的穩定期,癥見皮膚干燥、肥厚、抓痕、血痂、瘙癢無度,面色蒼白,形體偏瘦,食后腹脹,可伴情志不遂,舌質偏淡、苔白,脈弦細。陳漢章教授主張從肝論治皮膚病,認為肝氣的疏通調暢是皮膚抵御外邪之基礎;氣血充足,肝木得養是皮膚潤澤的關鍵;肝氣柔和,五臟得安是皮膚病良好預后的重要因素[18]。張小杰教授從肝論治皮膚病,采用疏肝、清肝、養肝三法,在此三法的基礎上辨證治療,酌情配合活血、祛濕、滋陰、祛風等法[19]。此外,“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故肝脾同調法在皮膚病臨床治療中亦很常見[20-21]。
5 腎與特應性皮炎
5.1 病因病機——先天不耐,久病及腎腎者,先天之本。腎對本病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精血與津液代謝兩方面。腎藏精,肝藏血,精血同源,相互滋生。腎精虧虛、肝血不足,可致血虛生風,皮膚干燥脫屑、瘙癢無度,發為本病。人體水液代謝以腎為本,“腎者主水”,腎的氣化作用貫穿于水液代謝始終,腎之功能失調,則氣化失司,開闔失度,導致水液代謝障礙。氣化失常,關門不利,闔多開少,津液乏源,則導致皮膚肥厚、干燥、脫屑;若開多闔少,津液停滯,外溢肌膚,又會出現水腫、滲液等。腎為臟腑之本,主一身之陰陽,五臟六腑之陰非腎陰不能滋助,五臟六腑之陽非腎陽不能溫養。腎虛則五臟皆虛,氣血陰陽失和,日久脈絡瘀滯,腠理肌膚失養,則見皮膚干燥、脫屑、瘙癢等癥;病程日久或年老體弱,五臟受損愈甚,久病則陰陽俱損,必擾先天腎之根本,最終久病及腎,導致腎之陰陽虛衰。慢性皮膚病,尤其是部分難治性、頑固性皮膚病,腎虛是其不可忽視的重要病機。AD的發病與先天稟賦不耐有關,根據中醫學“治病求本”“久病及腎”的理論,從補腎入手治療本病,可達到治療及減少復發的目的。
5.2 從腎論治——滋陰補腎,調和陰陽腎為五臟之本,補腎法在老年AD患者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腎論治本病,當以滋陰為主,兼顧潛陽,陰陽調和而疾病自愈。臨床常用六味地黃丸、二至丸等滋補肝腎、潤燥止癢。此法常對應本病的陰虛血燥證,癥見皮膚干燥,覆有少量鱗屑,反復搔抓,病久皮損表面粗糙肥厚,甚至皸裂,伴明顯干燥感,夜間瘙癢劇烈,口干,五心煩熱,舌質紅、苔少,脈沉細或弦細。禤國維教授運用滋陰補腎、涼血補腎、溫陽補腎、養血補腎等法治療難治性、頑固性皮膚病,取得良好療效,尤以滋陰補腎法為要,首選六味地黃湯[22]。腎虛是慢性皮膚病的重要病機,也是疾病遷延不愈的重要原因。治病必求于本,無論本病屬于何種證型,只要患者存在腎虛的癥狀,均可從腎入手,靈活輔以補腎之法,調和陰陽,注重腎精的填補和腎陰的滋養。
6 結語
特應性皮炎的病因病機復雜,但無外乎內外二因。外因與環境及遺傳因素相關,風濕熱三邪為標;內因責之五臟,主要病機是臟腑失調,與心、脾、肺、肝、腎五臟均相關。縱觀AD的發病特點和臨床癥狀,本病本虛標實,心肝有余,肺脾不足,腎常虛,治療亦常需標本兼顧,隨證治之。基于藏象學說從五臟對特應性皮炎進行辨治,也可為臨床提供一個更加系統、便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