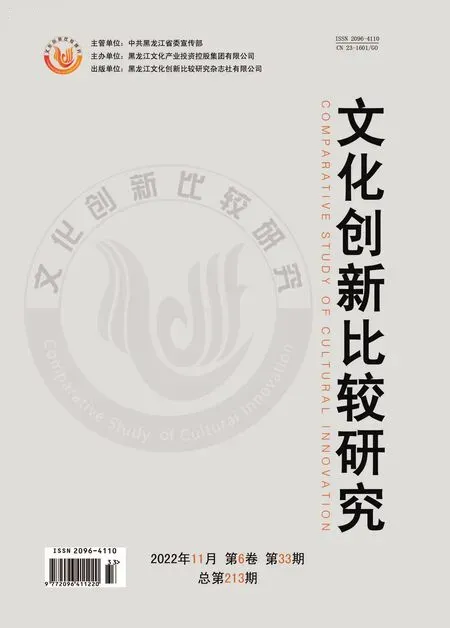東漢石刻所載四川地區外籍官員遷轉途徑考析
程訪然
(西華大學,四川成都 611700)
針對東漢時期遷轉到四川地區的官員,其任官方式、入川為官條件的探究,可從其來川仕官的地區和職位進行分別研究,因四川各地出土或傳世的記功碑中有對官員生平事跡的描述,因此東漢石刻的材料和文獻記載就成為考察入川官員遷轉的重要史料。但因四川地區各郡縣和各級別官員的遷任方式和州郡來源各不相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 蜀郡、犍為郡、廣漢郡太守
蜀郡、犍為郡、廣漢郡三郡在先秦時期屬古蜀國范圍,其主要居民為蜀人,地域范圍包括今成都、眉山、樂山、德陽、綿陽、廣漢、遂寧、宜賓、瀘州、自貢、簡陽、資陽、合江等漢族聚居區域。三郡也是當時經濟最發達、地位最重要、漢文化融合程度最高的區域[1]。郡太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長官,身份地位高,且常常遷升為中央高級官員,是各功德碑中常出現的立碑對象之一。文獻考證及石刻所記載的三郡太守共計22人,其中遷官記錄較為詳細的有16人。2011年經考古發現新出土的《裴君碑》中有關碑主裴君的遷官記錄資料最為可貴。
《裴君碑》(見圖1)的碑文[2]詳細記載了碑主裴君的出身及任官經歷。據趙超先生考證,碑文記載裴君:“累錫」苻(符)銀,四世遵統……祖自河東,先人造創。銀艾相承,選由孝廉。至君握惠,體含清妙。位歷臺署,博游遼(寮)俊。百工師師,」靡不則卬(仰)。超統定襄,外蠻侵暴。朱衣建鈰(旆),順天平亂。奮威討黠,鬼方震悼。師出旬時,猾夷降從。到(倒)載干戈,返文」行慶。利涉大川,黎元砥定。基(朞)月有成,美聲勃洞。運苻(符)四郡,所在流化。蜀承汶水,緝熙極敬。列備五都,眾致珍怪。”[3]裴君姓名雖并沒有在文獻有所體現,但根據碑文,仍然能清楚得知裴君為河東人士,舉孝廉出身,出任郡太守一級的長官。“位歷臺署”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后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的注引《漢官儀》中“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4]志第26《百官三》中注引:“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5]《百官二》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說明裴君舉孝廉拜為郎官后詣臺試成為尚書郎,然后由中央出任地方長官,“超統”破格出任邊患嚴重的并州定襄郡太守,在平定定襄郡當時所面臨的“外蠻侵暴”后,又遷轉四郡任太守,“運符四郡,所在流化”,前三個郡名已經無所得知,但最后一郡為蜀郡。裴君生活的年代為東漢中期漢順帝至桓帝時期,本初元年仍是蜀郡在任太守。根據碑文可知,裴君是河東望族裴氏子孫,祖上四世均為郡太守。裴君舉孝廉之后拜郎中進入中央,擔任尚書郎。嚴耕望先生認為:“自武帝從仲舒之議,使郡國歲貢孝廉拜郎中,集天下之賢才加一番訓練,再使出牧百姓,誠為良制。”后定襄郡有“外蠻侵暴”,裴君被破格提拔擔任定襄郡太守,后因平亂有功,此后一直輾轉各地任太守。裴君到蜀郡任太守之后,繼承先太守李膺來蜀郡任太守的主要任務,即興學教化,振興蜀地教育。可見裴君在出任四川地區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成都蜀郡太守時,是在遷轉了至少三郡太守積累一定從政經驗的結果。

圖1 《裴君碑》碑陽
比裴君時代稍早的蜀郡太守黃昌的事跡,可見于《后漢書·酷吏列傳》的記載。吳昌在任蜀郡太守約4年時間,后升為陳相,又升為河內、潁川任太守,永和五年(140年)征召任為將作大匠。如果將其在任陳相之前擔的任期都以三四年計算,其擔任蜀郡太守的時間可估為安帝中期。該人出身低微,因好學,熟讀文書法律,沒有經過舉孝廉,先為本郡(會稽郡)決曹,后被刺史辟為刺史從事,又遷轉為南陽郡任縣令,后以宛縣令升蜀郡太守。其在蜀郡的主要功績也不在施政教化,而在于明斷訟獄,使“宿惡大奸,皆奔走他境”。蓋與安帝時期宦官當道,社會矛盾尖銳有關。由此可見,東漢不同時期遷轉來川的官員,其遷轉途徑和來川主要施政方向,也與當時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裴君其人,任蜀郡太守數年后便“致仕而閭巷”,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從《后漢書》的文獻記載來看,部分遷任來川的官員,在離開四川之后便進入中央擔任高官,如在東漢前期順帝永平年間的第五倫“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因其知人善任治理蜀地得當,在蜀郡任太守達7年之久,而后擢升為三司之一的司空;章帝、和帝時期的陳寵“后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貪,誅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后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但這部分官員是少數,照比由中原地區郡太守入職中央的官員來說數量較少,更多的官員遷轉入蜀中三郡后,便一直輾轉各地,也有人在四川結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如黃昌任遷蜀郡太守后又遷任陳相、河內太守、潁川太守;趙瑤從扶風太守遷任蜀郡太守后又遷廣漢太守等。
2 巴郡太守、越嶲太守、廣漢屬國都尉和蜀郡屬國都尉
東漢巴郡所轄地區包括今重慶地區和四川渠縣、閬中、南充、達州等地[6]。《隸釋》中《巴郡太守張納碑》對張納的遷官經歷進行詳細敘述。張納其人,遷官經歷由舉孝廉開始、除郎中后擔任尚書侍郎,爾后擔任甘陵冤句縣令,因親人病故而去官,后為司空司徒征辟,但未就任。后又因舉高第征辟為太尉、拜侍御史,平嶺南賊寇后去山東某郡任太守,最后遷轉巴郡任太守。因為朐忍夷時常發生騷亂,而張納曾去嶺南地區平賊寇有功被封為都亭侯,可見其有平亂之能,故提升其任巴郡太守,其官吏生涯的最后一任就是巴郡太守。《華陽國志》中能記載與其有相似遷官經驗的巴郡太守傅寶、但望二人。傅寶本出身牂牁平夷,來自少數民族地區,其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桓帝時泰山郡人但望從并州刺史遷為巴郡太守,因并州為東漢時期的北方邊塞,其中雁門、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郡更是直面匈奴,所以,并州刺史一職也負有平定邊患的任務。張納、傅寶、但望三人,擔任巴郡太守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他們有平蠻夷之亂的經驗或有所功績,朝廷才遷轉他們來巴郡任太守,并且不再遷轉外地為官。所以,一定程度上可說明巴郡太守的升遷原因與蜀郡、廣漢郡、犍為郡太守的任職原因并不相同[7]。
古巴國和古蜀國自先秦時期就不屬同一文化傳統。《華陽國志》記載“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其失在于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其中賨人又名板楯蠻,勇武好戰,桓靈時期其因賦稅嚴苛而數次反叛。因此漢朝庭對待巴郡的治理態度和治理蜀、廣漢、犍為三郡有所不同,也可將其認為是導致派任巴郡的外籍太守的遷轉途徑和遷轉條件不同的原因。
越巂郡與廣漢屬國、蜀郡屬國的外籍長官遷任,也與巴郡太守有相似之處。越嶲郡與蜀郡屬國所轄漢嘉等地本就是西南夷聚居之地,《華陽國志》中“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種也”。《廣漢屬國侯李翊碑》中《隸釋》卷9中記載,李翊本就是牂牁郡人氏,“郡守嘉貪,禮請署督郵、五官功曹守長……延熹六年,大守東萊李君懿其高潔,順天報國,察舉孝廉,除郎中,特慕供養,常托疾在家。時益部擾穰,為三府所選,拜廣漢屬國侯。到官鷹揚威懷以文,得殊俗歡心,撥理之效。至建寧元年,遭從事君憂去官”[8];《曹全碑》中曹全的曾祖父曹述,敦煌人氏,“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9],從其籍貫和任官經歷來看,可見都是具備一定治理和熟悉邊地蠻夷經驗的官員,這與漢朝廷對待少數民族聚居地的政策吻合,即“置吏主之”[10]。
3 結語
來四川地區做官的外籍官員,其官員的背景也不盡相同。由于功德碑、墓碑等刻石形式要求書寫被立之人的生平事跡,所以,通常對官員的生平事跡描述得十分詳細。雖然記功碑中也有夸大事實的成分,但更多要看到石刻文字的寫實性,這些碑刻所反映出來的官員遷任途徑路徑,是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的問題。故任職秦蜀郡這三蜀地區的太守,往往要求官員擁有一定的郡守經驗。而在四川蠻夷居住人較多的郡縣,則往往要求官員具有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活經驗和擁有平叛對夷作戰的經歷,可見其當地官員即使遇到問題也有能力調和當地矛盾來維持社會穩定。而在四川任職各縣令、長的外籍官員則多由常規晉升途徑舉孝廉除郎中而來。可見,探究東漢石刻的內容和文獻,能夠為研究東漢時期官吏的選拔任用和遷轉制度提供重要史料,進一步彌補以往文獻對其記載的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