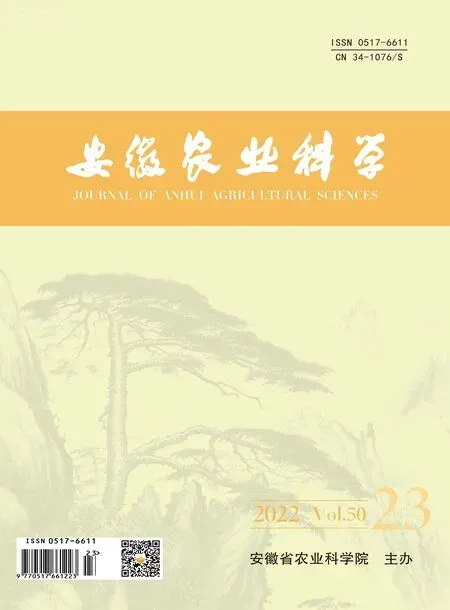青海祁連山片區人工林近自然森林經營關鍵技術研究與實踐
馬慧靜
(青海省林業技術推廣總站,青海西寧 810008)
2015年9月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青海時明確指出,今天的青海,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對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性尤其突出。青海省委省政府認真領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精神,提出堅持生態保護優先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的“一優兩高”戰略部署[1]。
青海祁連山地區水源涵養功能顯著、生物多樣性豐富、生態保護任務繁重、生態系統敏感而脆弱,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區、水源涵養區。由于過去傳統理念的制約、自然資源的粗放式利用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加快,導致區域景觀破碎、植被退化、水源涵養能力下降、各類生態服務功能降低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2008年3月,由青海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編制完成了《青海省祁連山水源涵養區生態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規劃》。2012年12月2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批復了《祁連山生態保護與建設綜合治理規劃(2012—2020年)》。因此,祁連山生態保護與建設綜合治理工程是在國家生態戰略層面上開展的,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也是青海省在落實生態優先戰略上的重大舉措和重點布局、積極推動的項目。在該背景下,開展科技示范與推廣項目,無疑對促進祁連山生態保護和治理,加大項目科技支撐具有重大意義。
1 研究的必要性
目前祁連山生態保護工程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對改善祁連山農牧區生產生活條件和促進農牧民增收以及生態環境保護與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成效顯著。
2017年6月26日,國家通過了《祁連山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同時青海省政府批復了《青海省祁連山區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修復試點項目實施方案》,青海省祁連山地區生態治理工作向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態要素方向發展,向努力增綠擴面補齊生態短板方面持續推進。為適應形勢發展對科技支撐的需求,在總體大方向不變的情況下,對形成較早的《青海省祁連山水源涵養區生態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規劃》進行適度調整十分必要。
在祁連山生態治理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的基礎上,為緊密配合祁連山生態保護與建設綜合治理工程的實施,提高工程項目的顯示度,進一步提升科技在工程項目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省科技廳、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省林業和草原局等多方協調,項目研究在加速祁連山地區林草植被協調發展和解決祁連山地區森林系統在水源涵養總量估算及水源涵養功能提升潛力余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森林生態系統具有重要的生態水文功能,其在保持水土、涵養水源、改善環境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水源涵養林作為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不但具有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且具有涵養保護水源、調洪削峰、防止土壤侵蝕、凈化水質和調節氣候等生態服務功能。森林生態系統功能的價值數倍于草原生態系統。
祁連山水源涵養區主體地貌以山地為主,兼有溝谷和盆地。發育著包括森林、灌叢、草原、草甸等多樣化植被類型,其中林地面積2 954.75 km2,森林覆蓋率4.63%,覆蓋率高于全省水平。對全省而言,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義[2]。近5年來青海省在人工林建設方面累計投資210億元,完成營造林85.05萬hm2,義務植樹7 500萬株。在提升森林覆蓋率,保護與恢復區域生態環境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也存在人工林建設樹種單一、用材林改公益林后林分調控措施缺乏,在林地保護與恢復方面的研究力量投入不足等問題,導致在水源涵養林建設的技術集成度不高,林地整體水源涵養功能不佳,物種多樣性匱乏。
綜上所述,通過水源涵養林高效空間配置和結構優化調整,形成混交、穩定、異齡復層、可自然更新的近自然森林系統,可大力提升和充分發揮森林系統在祁連山地區水源涵養能力。同時,建立可量化的森林生態系統水源涵養評價體系,可為祁連山地區生態工程水源涵養總量的核算與水資源增貯潛力的評測提供技術支撐。該研究將有助于進一步推進祁連山生態保護與建設綜合治理工程和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片區)體制試點實施的順利開展,為落實省委省政府關于“一優兩高”指示精神提供科技支持與保障。
2 近自然森林經營的概念
遵循森林的自然生長發育規律,以森林更新到穩定的森林群落為周期,設計和實施各項經營活動,充分利用影響森林的各種自然力,不斷優化森林經營過程,實現森林的樹種組成鄉土化、林分結構多層化、綜合功能最大化,從而使人工生態公益林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達到一種最佳結合的接近自然的森林經營模式[3]。
3 研究區概況
祁連山地區是我國西北荒漠區和青藏高原高寒區的過渡區,遠離海洋,具有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和高原氣候特征。該地區地勢高差大,地形條件復雜,水熱條件差異明顯,由東向西隨著干旱程度逐漸增強,植被由溫帶半干旱草原逐漸向溫帶半荒漠及荒漠過渡。
森林系統(包括常綠針葉林和落葉闊葉林),主要分布于祁連山東段的樂都區、互助縣、大通縣、門源縣、祁連縣。灌叢系統(主要包括河谷灌叢、溫性灌叢和高寒灌叢),主要分布于祁連山東段的高山與河谷地區,祁連山中部和西部也有少量分布。
據初步調查,祁連山地區森林系統(包括喬木和灌木)總面積85萬余hm2,其中,互助縣、大通縣、門源縣和祁連縣分布面積分別占總森林系統面積的18.76%、12.48%、27.36%和23.85%,研究區4個縣總體占森林分布面積的82.45%。同時涵蓋青海省分布的常綠針葉林、落葉闊葉林和灌叢三大森林系統。
總體上,從氣候和森林類型與分布特征等方面,針對研究地區高寒貧瘠、樹種單一的植被重建現狀和作為區域重要水源地的環境特點,結合水文和氣候等相關資料,以祁連山自然保護區試驗區及其外緣的水源涵養功能區作為項目實施區,統籌不同立地植被群落結構、植被格局與水源涵養功能關系等要素,在祁連縣、互助縣、門源縣和大通縣等地展開,建立10處單項技術試驗示范點和1處小流域綜合試驗示范點。建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示范區,形成可復制性、可推廣的技術支撐體系,同時對全省具有很好的示范意義[4]。
4 技術措施
該項目針對研究地區高寒貧瘠、樹種單一的植被重建現狀和作為區域重要水源地的環境特點,以祁連山自然保護區試驗區及其外緣的水源涵養功能區為項目實施區,通過不同立地植被群落結構、植被格局與水源涵養功能關系的量化分析,開展森林近自然經營水平診斷與綜合評價,并據此,集成研發滿足保水功能提升、林分穩定為核心的林草植被結構調整技術,集成研發近自然化理想林分結構的植被類型與結構改善的途徑及流域尺度的景觀格局優化配置技術,研發和集成現有植被結構調整的方法體系并開展試驗示范。
4.1 基于水源涵養功能保障的林草植被群落結構綜合評價體系構建
4.1.1探明林草植被區域背景,構建水源涵養功能評價體系。該項內容以祁連山自然保護區試驗區及其外緣的水源涵養功能區在不同階段建設的人工林群落/分布區作為主要研究工作區,兼顧其他植被恢復工程建設區,主要通過遙感影像及野外調查等探明林草植被區域背景,以立地環境-植被結構-空間格局與水源涵養功能的關系為研究主脈絡,采用各立地類型林分相應的水源涵養功能要素,基于PSR(壓力-狀態-響應)模型構建區域林草植被水源涵養功能評價體系。
森林生態系統多樣性調查方法:
(1)樣線、樣點布設。多樣性調查采用地面實地調查為主,喬木林包括針葉林和闊葉林,分別設置樣地5個,布設的樣線與樣點見圖1。分別在針葉林、闊葉林設置監測樣方,樣方設置包括喬木層、灌木層和草本層。喬木林樣方為28.28 m×28.28 m(圖2),同時采用5點取樣法設置灌木層和草本層樣方5個;灌木層樣方設置為4 m×4 m(圖3),樣方數量5個;草本層樣方設置為1 m×1 m,樣方數量5個。

圖1 森林生態系統多樣性調查樣線、樣點設置Fig.1 Sample line and sample point setting for forest ecosystem diversity survey

圖2 喬木林樣方設置Fig.2 Setting of tree forest quadrats

圖3 灌木林樣方設置Fig.3 Setting of shrub forest quadrats
灌木林:灌木林樣地共設置8個。灌木林樣方包括灌木層和草本層,確定灌木層樣方為4 m×4 m,草本層樣方設置為1 m×1 m,樣方數量5個[5]。
(2)調查項目。林分調查:調查主要樹種和林分組成、林木分布狀況、林齡、株間距、樹高、胸徑、郁閉度、植被覆蓋度、葉面積指數等,采用冠層分析儀測定不同林分的葉面積指數(LAI),以確定林分冠層結構。立地調查包括地貌類型、海拔、坡位、坡度、坡向、腐殖質層厚度。土壤理化性質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測定在室內進行,野外采樣為在每塊樣地內隨機15個點采集土樣并采用四分法混勻后帶回室內,按照常規試驗分析方法測定土壤理化性質(土壤質地、容重、孔隙度、土壤含水量、土壤肥力等),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采用高通量測序MiSeq平臺微生物多樣性分析方法測定。將調查結果填入樣地調查表(圖4)。

圖4 樣地調查表設計Fig.4 Design of sample plot survey
4.1.2判定可提升多種服務功能的林草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綜合評估現有林草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在基本滿足其主導服務功能條件下的林分穩定性及可持續性,評估其提升多種服務功能的空間適宜性和可提升余地,判定立地-坡面-小流域等不同尺度可調整與提升林草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提出調整或改造的等級。在現有林草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在基本滿足其主導服務功能條件的基礎上,評估影響林分穩定性及可持續性的林草植被類型及環境變量。林分的穩定值采用每公頃林木株數和蓄積量的乘積再除以1 000的值得出,利用多元回歸法及SPSS分析林草植被類型(林分多樣性、郁閉度、枯落物量等)和環境變量(坡度、坡向、坡位、海拔)與林分穩定性的關系,從而評估林分穩定性。林草植被資源消耗的增長率不超過林草植被資源的增長率是可持續利用的必要條件,利用Logistic曲線,根據林草植被資源增長變化趨勢與林草植被資源消耗的變化趨勢的匹配程度來判斷資源變化的宏觀趨勢,可得出4種模型來判斷這種關系,即可持續模型、不可持續模型、先期可持續而后期不可持續模型、先期不可持續而后期可持續模型,繼而評估林分的可持續性。綜合評估林分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得出影響林分穩定性及可持續性的林草植被類型及環境變量指標[6]。
主要觀測指標:在調查樣地確定后,按區域歸類開展相關林地小氣候(自動小氣候工作站)、林冠截留降水量、枯落物持水量、土壤滲透性及蒸發量等定位觀測,以獲取現場第一手水文效應數據;水文觀測主要集中在5—8月進行,按照地形因地制宜布設/構筑簡易測流堰,并配套自壓式水位計開展集水區徑流觀測和小流域徑流觀測。
樹冠截留量按前期積累數據建立的數學模型計算。
基于已有數據,采用專家信息法、回歸分析法等數學方法,應用EXCEL、SPSS統計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和歸一化處理,利用綜合評判模型進行計算并排序,對人工植被生態系統主要服務功能進行綜合評價,基于前述得出的影響林分穩定性及可持續性的林草植被類型及環境變量指標,評估其提升多種服務功能的空間適宜性,并利用專家信息法對其可提升余地進行評估[7]。
結合樹種或植物群落的優化調控措施,影響林分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的林草植被類型及環境變量指標,對林草植被類型和環境變量指標的現狀進行研究,最終提出調整或改造的等級。結合模型將研究區內典型林草植被功能劃分高、中、低3級或高、較高、中、較中、低、較低6級水平的類型,以期為低效林評價及功能提升提供科學依據。
4.1.3構建水源涵養功能提升的林分結構優化配置與調整試驗示范的綜合評價標準體系。從系統工程的角度出發,以基于InVEST模型評估的林草植被多種服務功能和基于PSR模型構建的林草植被群落健康評價體系為研究對象,應用層次分析法(AHP)構建水源涵養功能提升的林分結構優化配置與調整試驗示范的綜合評價標準體系[8]。
通過理論分析和專家咨詢,將該體系分為目標層、中間層和指標層3個層次,其中,目標層為綜合評價標準體系,中間層為多種服務功能提升和林分結構優化配置與調整試驗示范,并將其逐一分層細化,形成由13個評價指標組成的指標層(圖5),在評價過程中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或增加相應指標。

圖5 層次結構模型Fig.5 Hierarchy model
由于各指標的作用不同,最終綜合評價標準體系的影響程度也有一定差異,為了區分各指標間的差異性,采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值。將這些指標按照隸屬關系的不同分為2個層次,利用數學分析方法及專家咨詢,給出各層次各目標的相對權重值。最終構建多種服務功能提升的林分結構優化配置與調整試驗示范的綜合評價標準體系[9]。
4.2 基于水源涵養功能提升與穩定性維持的近自然林分結構調整試驗示范
4.2.1篩選確認符合項目區實踐的近自然化理想林草結構經營類型。
4.2.1.1不同立地試驗林分選擇。依據可提升多種服務功能的林草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判定以及歷史調查研究資料,根據遙感判讀、森林資源二類調查和水源涵養功能提升建議,通過現場踏查,選定典型代表林分類型進行林分穩定性及可持續性綜合評估,篩選出不同立地條件下(陰坡、陽坡和半陰半陽坡)的代表林分類型,主要涉及青海云杉純林、青海油松純林、祁連圓柏純林、華北落葉松純林、白樺華北落葉松混交林、華北落葉松青海云杉混交林、青海云杉白樺混交林、青海云杉白樺青楊混交林、青楊純林、沙棘、金露梅小檗灌叢和檸條灌叢等。
4.2.1.2近自然理想林分的篩選。根據近自然林應具有的林分異齡、復層和自然更新的結構特征,采用林下植被生物多樣性、林分空間結構、林分生產力、林分健康和土壤水分5類評價指標。
4.2.1.3評價指標測定方法。在前述的調查樣地確定后,在標準樣地開展林下植被生物多樣性(豐富度、多樣性Shannon diversity和均勻度Pielou’s evenness指數)、林分空間結構(樹齡分布、蓄積量、水平結構、垂直結構)和林分生產力(年樹干生長率)現場調查;采用葉綠素熒光儀和植物水勢儀分別測定葉綠素熒光動力參數和水勢,得出林分健康指標;利用便攜式土壤水分速測儀現場測定土壤水分。
4.2.2確定水源涵養功能提升的穩定林草植被人工定向調控目標。研究影響其自然更新、群落正向演替的環境因素與林分結構和森林可持續經營技術等調控因素的關系。通過對不同植被類型的對比,采用參評因素因子分值量化方法進行近自然化理想林草植被和其他類型林草植被如人工純林和低效林的功能差異分析,開展近自然林和人工純林功能差異分析[10]。
通過研究分析水源涵養功能和植被結構的關系以及不同樹種的生長對環境因子以及立地條件的響應,采用統計學方法,對限制因子進行排序并識別出對樹木生長和實現自然演替的一些關鍵環境和立地條件因子,從而為設計因地制宜的多樹種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配置提供支撐,為確定不同林草植被類型的調控目標和調控改造技術提供依據。最終,從生態服務、遺傳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游憩景觀等功能提升角度確定穩定林草植被人工定向調控綜合目標。
4.2.3形成祁連山水源涵養林區林草植被維穩、提升改造關鍵技術體系,開展試驗示范。探討近自然林草結構環境因素與經營管理調控之間的關系:依據調查和試驗結果,篩選可滿足近自然的林草植被結構穩定的林分樣地,推演其植被自然演替的關鍵因子和經營策略。集成祁連山地區近自然林分結構調整和經營調控項目成果:總結近自然林業理論進入我國近20年來在國內的實踐成果,分析近自然林分自然更替的樹種選擇與調控技術。該項目初步篩選的祁連山區主要造林樹種見表1。

表1 項目區主要造林林草篩選結果
綜合上述研究,集成綜合成果開展試驗示范,構建近自然林草植被維穩,提升改造關鍵技術體系,形成6種技術模式共10項技術,并開展試驗示范(表2)。表2中序號1~8為以水源涵養功能提升為導向的林草植被結構調整技術示范,序號9~10為以水源涵養功能為主的生態功能進一步提升技術示范。

表2 單項技術試驗示范林匯總

續表2
5 效益分析
5.1 社會經濟效益通過項目實施,在水源涵養林建設中建立近自然林改造的理念;引導農牧民在生產、生活及旅游中提高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識,減少對生物的破壞,改善生物環境;有利于樹立民眾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科學觀,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飲水水源林保護的良好氛圍,形成全社會共建生態文明的格局,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水源涵養林為導向的近自然林改造中,建立的景觀格局營建模式,可為當地旅游業的提質增效奠定基礎,為旅游業持續穩定的發展建立技術支撐。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需要聘用當地農牧民參加野外調查和植被補植建植工作,直接增加農牧民的可支配收入[11]。
5.2 生態效益該項目研究堅持以水源涵養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為核心的生態功能定位,所形成的優化組合構建的各類低效人工水源涵養林結構調控應用技術模式與運作方式,可為祁連山地區未來的水源涵養林近自然可持續經營提供可借鑒的參考依據和示范案例。通過項目實施,試驗示范區水源涵養功能得到明顯提高,植物資源種類和遺傳多樣性明顯提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