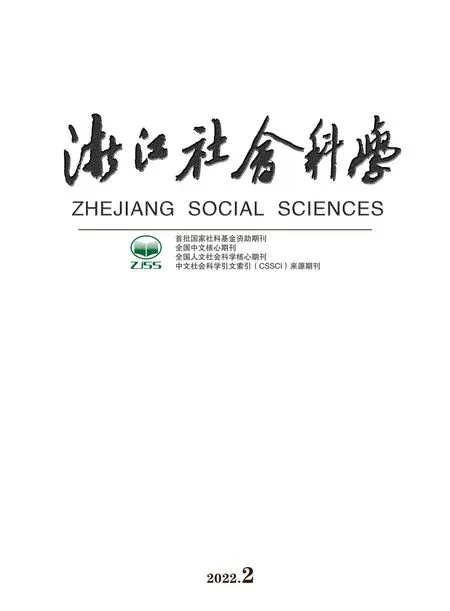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資本奴役關系透視*
□ 張一兵
內容提要 在馬克思的眼中,人類社會獨有的社會關系場境存在,正是物質存在的一種特殊方式,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觀念和范疇都必然與特定時間中的物質生產關系賦型相關聯。并且,他將這一物質關系進一步指向在經濟的社會形式中出現的經濟關系。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將資產階級的歷史時間中的生產關系偽飾成天然的、永恒不變的自然規律,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歷史性的一種本質遮蔽。
1846年到1849年,馬克思在第二次經濟學研究的進程中,確定了生產關系概念,在進一步深化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塑形的同時,也在科學社會主義的視角中較多關注了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問題。很顯然,這仍然是一個現象學和批判認識論話語缺席的時期,馬克思盡可能用“實證科學”的事實話語,來客觀描述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各種奴役現象。最終,馬克思科學地認識到資本是一種支配性的統治關系,從而為下一步透視以資本關系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質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一、市民社會話語IV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性
1846-1847年,馬克思在第二次經濟學研究的最后,寫下了《布魯塞爾筆記》C,其中最重要的是“居利希筆記”。這是他對古·居利希①的“關于現代主要商業國家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1830—1845年耶拿版第1-5 卷(G.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des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I-V,Jena,1830-1845)一書的摘要。②這一筆記中,馬克思進一步找到了深化歷史唯物主義和進入經濟學的入口。我們可以看到,在經濟學研究中,他第一次接受了勞動價值論,并站到了李嘉圖的立場上。
1846年6月,正當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和修改《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最后時刻,蒲魯東出版了《經濟矛盾的體系,貧困的哲學》(以下簡稱《貧困的哲學》)③一書。這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創立了科學方法論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之后,蒲魯東卻在他們正在進入的經濟學領域中,拋出了一個用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構式構序和塑形出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學話語通過貌似社會主義的形象來全面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這使得蒲魯東的理論一經提出立刻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的推論是,蒲魯東的這本書基本上是受馬克思1844年用哲學話語批判經濟學影響的結果。因為那時候,“他們兩人在巴黎常常終夜爭論經濟問題”(恩格斯語)④。可能發生的事情是,蒲魯東講自己批判資產階級財產關系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會講透視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黑格爾的否定辯證法,馬克思自己也承認,“在長時間的,往往是整夜的爭論中,我使他沾染了黑格爾主義,這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不懂得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⑤恐怕,這正是我們在分析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1844年手稿》)中看到的馬克思那種極其復雜的黑格爾現象學話語構式。這一定深深打動和吸引了蒲魯東,所以讓后者“沾染了黑格爾主義”。可是,當不懂黑格爾否定辯證法的蒲魯東去模仿馬克思的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時,馬克思已經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倒錯的學術悲劇。
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十分鄭重地致信給俄國自由派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作為他11月1日來信論及蒲魯東的經濟與哲學觀點的答復。⑥有趣的是,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一書出版前不久曾致信馬克思,說他“等待著您嚴格的批評”,馬克思的正式答復就是1847年出版的 《哲學的貧困》。也是在這兩個馬克思用法文寫作的文本中,我們看到了他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認識深化,其中,最重要的進展是對資產階級社會奴役本質的揭露,以及科學的生產關系概念的生成。
首先,在《致安年柯夫的信》(Marx an Pawel Wassiljewitsch Annenkow)中,我們先是看到了馬克思那個獨有的市民社會IV 的概念。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語,從作為政治交往共同體的市民社會話語I,下沉到勞動和需要體系的市場關系的市民社會話語II,再由黑格爾生成超越“第二自然”的批判性的市民社會話語III。關于這一觀點,我已經有過初步的討論⑦。我們需要注意,這個在資產階級社會之外的特殊的市民社會IV,幾乎貫穿馬克思關于社會歷史觀察的整個過程。他批評蒲魯東“沒有從現代社會制度(l'état social actuel)的聯結(engrènement)”中去了解今天的資產階級社會。⑧這是明確標識觀察社會的非物像場境特征,engrènement 是指突現在主體際關系中的社會場境關系賦型。因為,社會并不是蒲魯東所說的什么“人類無人身的理性”,“社會(la société)——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 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Le Produit de l'action réciproque des hommes)”。⑨馬克思的這個“交互作用的產物”,是在否定蒲魯東將社會看成一種先驗主體的看法,但它極為深刻地呈現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場境存在觀。這個以engrènement 為本質的社會定在,既不是舊唯物主義直觀中的對象物的堆砌,也不是沒有了人身主體的理性構境,它是在特定時期、由特定的人們以特定的方式建構起來的具有特定性質的、活動的、相互作用的共同生存關系場境。這是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認的,“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斷言,在更大社會空間中的延伸。依馬克思的看法,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un certain état)下,就會有一定的(telle)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telle société civile)。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正式表現的一定政治國家。⑩
在《回到馬克思》第一卷中?,我已經指認這八個“一定的”突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獨有歷史性時間特質,其實,這也會是科學的歷史認識論的重要基礎。從這一表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當馬克思從客體向度去描述社會定在的時候,他總是從社會生活的內在關系構序和構式本質出發的:一是生產力發展一定狀況,這是一個深埋在主體勞作工藝和客觀動能中的功能性水平表征; 二是生產力的歷史性的構序質性決定了一定的交換的消費方式,這是物質生產與再生產構序之上構式出來的特定商品交換和消費的經濟關系場境; 三是這種經濟關系所塑形的家庭關系、階級關系筑模起來的社會制度,即市民社會(IV);四是市民社會之上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這里的法文話語實踐中,出現了在德語中無法表達的有深刻含義的詞語細分:馬克思專門使用了法語中特有的société civile,以區別于他同時使用的société bourgeoise。馬克思在此信中五次使用société civile 這一術語。從馬克思這一表述的具體構境來看,這個société civile并不是特指資產階級社會,而是在德語中無法區分的市民社會IV,即在社會賦型結構中那個決定了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性基礎。然而,馬克思這個時候的觀點也由于歷史知識的缺乏帶有一定的局限。因為,這個“市民社會”只是建立在已經出現交換和消費的經濟關系和階級組織之上,它雖然會是一定政治國家(包括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的結構性基礎,但它并非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全程。應該指出,馬克思此處關于市民社會IV 的內核,主要還是基于一定生產力水平之上的交換和消費活動中的交往關系,還不是更深刻的生產關系概念。生產關系的概念是在不久之后的《哲學的貧困》一書中形成的。
第一,市民社會IV 的歷史性轉換。在馬克思的進一步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市民社會IV更清楚的賦型所指。馬克思說,蒲魯東“混淆了思想和事物(les idées et les choses)”,他不能透視第一層級的物象化迷霧,所以無法理解“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系(rapports matériels)形成他們的一切關系的基礎(base)。這種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也是在這里,我們遭遇“基礎”這個重要的表述。這個作為社會結構基礎的本質,是讓個體以一定的方式生存的“物質關系”。我以為,這同樣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場境存在論的重要體現,在馬克思這里,他談及人及其個體,觀察社會生活,從來都不是停留在人的肉身和對象物的感性直觀現象上,而是非物像地在關系存在論的特定歷史語境中描述其人對自然和人與人的物質活動構序和關系賦型上。可是在這里,馬克思是專門提醒我們,雖然人的社會關系賦型是非實體的場境存在,但同樣是客觀存在的rapports matériels。這說明,在馬克思的眼中,人類社會獨有的社會關系場境存在,正是物質存在的一種特殊方式。并且,馬克思將這一物質關系進一步指向在經濟的社會形式中出現的經濟關系。
在此,馬克思還基于歷時性的視角,進一步說明了這個作為市民社會IV 的經濟關系基礎的歷史性改變。他說,當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le mode de leur commerce)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馬克思還專門解釋說,“我在這里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那樣”。這里的交往顯然已經不是赫斯的類本質交往,也不是狹義的經濟學語境中的交換,而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共同活動關系,之后,馬克思將用生產關系這一更加科學的概念取代它。關于這個作為市民社會IV 的經濟關系的結構性基礎的歷史轉變,馬克思非常具體地分析到,比如,“各種特權、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régime réglementaire du moyen age),曾是唯一適應于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系(relations sociales)”。?這也是一種歷史性的社會關系,只是封建宗法關系的場境存在直接依存于血親關系和土地上的農耕生產力,這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是整個封建政治國家等上層建筑的基礎。而當資產階級在新型的工業生產進程之上構序和塑形起來的商品-市場經濟活動,開始在封建社會的內部發展起來之后,“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如果想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得不變革基礎性的經濟關系和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于是,這就有了英國1640 和168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即“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相互沖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在那里,
一切舊的經濟形式(formes économiques)、一切和這些形式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曾經是舊的市民社會(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當時在英國都被破壞了。可見,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transitoires et historiques)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 (mode de production),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
這里出現作為舊有的société civile 正是市民社會IV,即決定了其他社會關系的經濟關系,也是作為政治國家基礎的經濟關系(結構)。中譯文竟然漏譯了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 中 的société civile,只是譯為“舊社會”,這樣整段表述的構境意思就完全不同了。這里的這個市民社會IV,即人們在一定時期中獲得的“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的,這是對歷史認識論中那個歷史性時間維度的另一種表達。并且,這個暫時和歷史的社會結構的基礎將隨著生產力的新發展,由生產方式的變革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由此,我們可以再一次看到,馬克思所說的一個社會結構中的基礎結構,是以經濟的社會形式中的生產、消費和交換活動的經濟關系構成,這當然不是貫穿全部歷史的“社會基本矛盾”,只是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中出現和發生作用的規律。
第二,市民社會IV 與觀念意識形態的本質。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錯誤時,指出他雖然看到了人們生產呢子、麻布、絲綢,卻不能正確在非物像的視域中理解人們只能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場境中進行生產,也無法理解經濟關系(市民社會IV)在一個社會結構中的基礎性作用,并且,他更不能在關系意識論中透視到,一切觀念形態的意識形態都不過是一定經濟關系的歷史性抽象和反映。馬克思說,
蒲魯東先生不了解,人們還按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呢子和麻布的社會關系。蒲魯東先生更不了解,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系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范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系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所以,范疇也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性的和暫時的產物。?
蒲魯東的錯誤,在于他將自己手中的觀念范疇當作了永恒不變的東西,而無法意識到觀念的本質只是一定歷史時間下特定社會關系的抽象表現。馬克思的這一觀點,與《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意識的本質是“我對我環境的關系”是一致的,只是,他在這種歷史唯物主義關系意識論原則的基礎上更具體地指認,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觀念和范疇都必然與特定時間中的經濟關系賦型相關聯。所以,歷史時間性的社會關系場境,會以一種人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歷史先驗構架,直接決定了人與社會的全部精神構境方式和歷史質性。因而,這些觀念和范疇,作為康德式的先天綜合判斷,將會與特定的經濟關系賦型構架一樣,都是歷史的和暫時的,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認識論的觀點。馬克思認為,
蒲魯東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leurs facultés productives)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rapports);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范疇(les catégories économiques)只是這些現實關系(ces rapports réels)的抽象(des abstractions),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真的是關系場境存在優先的,他時時刻刻告誡我們必須從一定歷史時間中的社會現實關系入手觀察社會定在,必須考察人們在特定生產力水平之上構序和塑形起來的相互關系,人們的意識和觀念只是這種特定社會負熵關系場境存在的歷史性的主觀映現。因為在《貧困的哲學》一書中,蒲魯東主要是在討論經濟學,所以,他將自己手中的經濟范疇都看成了非歷史的先驗觀念,他無法理解,人們在現實社會中的生活關系場境本質是由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生產力構序的歷史質性的改變也必然改變這種關系性存在的歷史質性,進一步,一切經濟范疇都只是特定社會經濟關系賦型的產物,蒲魯東“不是把經濟范疇看作是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作歷來存在的、永恒的觀念”。?其實,這一觀點與上述經濟關系決定政治國家的表述一起,就會塑形起基礎決定政治國家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完整理論。
其次,關于資產階級社會本質的歷史性關系定性。第一,在歷史認識論的維度中,資產階級社會必然是一種歷史性的、暫時的經濟關系下的現代私有制。針對蒲魯東抽象地討論只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才歷史性出現的機器、分工等問題,馬克思告訴他,在不同于資產階級社會的封建社會中,“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發展起來的”。?并且,農耕自然經濟關系場境中,并沒有機器、分工和競爭作為特定生產力歷史構序和經濟關系賦型的產物,這些工業生產工具、新的勞作方式和市場交換中才出現的復雜經濟關系場境,會是在特定工業的生產力水平之上才會歷史性發生的事情。具體些說,機器系統只是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基礎的工業生產構序的歷史性產物。針對蒲魯東將機器當作抽象經濟范疇的錯誤,馬克思說,“機器不是經濟范疇,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經濟范疇一樣。現代運用機器一事是我們的現代經濟制度的關系(relations de notre régime économique actuel)之一,但是利用機器的方式和機器本身完全是兩回事”。?如同前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過程中的“拉犁的牛”一樣,機器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工業生產的工具,而不是經濟關系,在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經濟關系之下使用機器,使之成為資產階級盤剝勞動者的武器,這種特定的關系性奴役場境并非機器本身的過錯。同樣,在封建社會中,根本不可能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分工,因為只是資產階級的經濟關系逐漸發展起來以后,才出現了在14-15 世紀早期資產階級殖民主義制造的世界市場中出現的奴役性國際分工,“在英國開始于17 世紀中葉而結束于18 世紀末葉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分工”,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分工。可以看出,馬克思此時對分工的理解已經開始發生重要的改變。
第二,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是一種間接的奴隸制和殖民主義奴役關系下的直接奴隸制。這是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新的認識。因為蒲魯東抽象地討論奴隸制與自由,而馬克思則告訴他,奴隸制本身也是一種歷史性的社會關系。在不久后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更深入地討論了這一問題。作為一種經濟范疇,奴隸這一概念不過是對歷史性的“奴隸制(l'esclavage)”社會關系賦型的主觀映現。馬克思還告訴蒲魯東,“奴隸制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在各個民族中存在。現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國把奴隸制如何掩飾起來”。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中,歷史上出現的直接的奴隸制卻在殖民主義奴役關系中畸變為一種新型的直接奴隸制。馬克思深刻地說,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是一種通過對殖民地人民的直接奴役關系建構起來的間接奴隸制 (l'esclavage indirect)。那么,什么是殖民地建立新型的直接奴隸制(L'esclavage direct)呢? 馬克思在這里說,
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等一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樞紐(pivot de notre industrialisme actuel)。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colonies)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commerce du monde),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機器 工業(grande industrie machinelle)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著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范疇。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混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
這是一個奇怪的歷史時空錯位關系。直接以可見的強暴式的掠奪方式建立起來的奴隸制,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中世紀之前處于不發達的經濟發展階段時出現的社會歷史形式,然而馬克思卻發現,這種直接的奴隸制卻成為今天資產階級“現代工業的樞紐”,沒有美洲的直接奴隸制的殘暴掠奪和壓榨,就沒有棉花;沒有大量的棉花,就沒有歐洲現代工業中的紡織業。在今天歐洲大陸已經絕跡的直接奴隸制,資產階級卻在另一個現實空間——“在新大陸則公開地推行它”。這種公開的殖民主義奴役,也成了資產階級社會(文明社會)所需要的世界貿易和大機器工業無法缺少的條件。這也意味著資產階級標榜的“文明”,其實是另一個落后土地上通過殖民主義直接奴隸關系支撐起來的間接奴隸制。其實,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社會本質是“間接奴隸制”的認定,還有一個更深的構境層面,即在他后來完成的資產階級通過形式上平等交換,而實質上無償占有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實現的。
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奴役本質
不久之后,馬克思用法文寫作并公開出版了全面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 一書的論著——《哲學的貧困》。在這本書的第二章中,馬克思展開了我們剛剛討論過的他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的基本觀點。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批判的重點不再是批評蒲魯東那種明顯的黑格爾式的觀念決定論,而在于分析他的經濟學的方法論中隱含的深層唯心主義,這其實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先導性,即當蒲魯東面對經濟學研究時,他一方面滿懷激憤地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可另一方面卻又將資產階級社會生產方式中歷史地出現的社會關系之反映的經濟范疇永恒化。實際上,這也是全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非歷史的意識形態本質。
首先,是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論說了李嘉圖與黑格爾在面對資產階級社會態度上的關系:“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了帽子,那末,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個英國人就是李嘉圖,一位銀行巨子,杰出的經濟學家;這個德國人就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一位專任哲學教授。”。很顯然,與《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不同,此時馬克思在經濟學理論構式上不再主要根據還有一絲主體向度殘余的斯密,而基本上轉到了客體向度中李嘉圖的立場上來了。這當然是馬克思在第二次經濟學研究中獲得的新進展。我們發現,馬克思已經在直接肯定李嘉圖是“當代的歷史學家”了。這個不同于經濟學稱謂的“歷史學家”,并非真的是說李嘉圖是一個歷史學研究者,而在歷史唯物主義客觀向度上,指認李嘉圖的經濟學話語無意識達及的客觀性維度。所以馬克思會認為,李嘉圖“已經科學地闡明作為現代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société bourgeoise)的理論”。馬克思在此文本中八次使用了不同于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會)的société bourgeoise 一語。實際上,這正是德文中已經轉喻為資產階級社會的那個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根據前面已經討論過的內容,我們知道李嘉圖“把人變成了帽子”,是指他的經濟學客觀上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畸變為物(帽子)的過程。后面,馬克思將會用人與人的關系場境顛倒地畸變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的事物化批判理論,接著李嘉圖往下說。然而馬克思又說,李嘉圖的觀點的確是“把人變成了帽子”,但這不是因為李嘉圖觀點的“刻薄”造成的,而是由于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客觀事實本身就是刻薄的。在這里,馬克思直接反對法國人本主義文學家對李嘉圖政治經濟學的攻擊。馬克思的這種肯定的態度,與《巴黎筆記》和《1844年手稿》中對李嘉圖的簡單否定(“犬儒主義”)是完全不一樣的。進一步,馬克思指認在黑格爾那里,他又“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過去我們在解讀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時,大多認為這是在批評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其實不然。依我的解讀,馬克思說黑格爾將李嘉圖的“帽子”變成了觀念,其實是發現黑格爾看到了李嘉圖客觀呈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系場境中發生的事物化顛倒,但他又用體現絕對觀念的國家與法批判性地超越它。這也就是說,馬克思意識到黑格爾在市民社會III 的批判構境中,將事物化了的原子個人在市場無序交換的經濟必然性王國中的物性自發構序狀態重新揚棄為自由王國中絕對觀念。這是馬克思更深一層的批判性構境。
其次,是對作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質的生產關系的科學透視。這是原先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話語中那個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際交往關系,向生產領域關系場境賦型的邏輯下沉。馬克思在談及蒲魯東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不知道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內生產,他不明白,這種生產方式的本質是人們總會在一定的社會關系賦型場境中的共同活動,這些社會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也會發生歷史性改變。
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 (rapports sociaux déterminés)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nouvelles forces productives)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mode de production),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la société avec le capitaliste industriel)。
這當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層級非物像認知中的雙重觀點,如同改變外部對象世界的實踐活動、生產勞動活動當下發生與消失一樣,作為社會定在本質的人們的社會關系賦型場境,也是當下發生并迅速消失于人們的共同活動之中,但是,如同一定的物質生產過程中通過勞動活動塑形出特定的對象性產品(麻布、亞麻)一樣,人們同時也不斷地將這種怎樣生產和生活的關系賦型場境歷史性地再生產出來。在許多年之后,列菲伏爾在《空間生產》(1974) 中將生產關系場境的生產變成了社會空間的歷史本質。馬克思在歷史認識論的維度上指認,當生產力獲得新的進展時,人們也會改變自己怎樣生產的構序方式和相互作用的社會關系賦型。手推磨時代的自然經濟生產力,必然賦型出帝王將相高高在上的封建宗法性的社會關系場境存在,而蒸汽機開創的工業生產時代,一定會產生出資產階級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場境存在。馬克思批評蒲魯東,指出他根本不能理解這種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場境關系存在本質,比如,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看到的“貨幣不是物,而是一種社會關系 (La monnaie,ce n'est pas une chose,c'est un rapport social)”。這也是那個交往異化構式的沒影點。在《穆勒筆記》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眼中的物性貨幣,被透視為人的交往類本質關系的異化。在此,貨幣是一種現實的社會關系。可見的對象物背后,捕捉到不可直觀的社會關系場境,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非物像的科學透視感。我們在生活中遭遇金錢,經驗常識會簡單地將其視作財富,而馬克思則讓我們深一步發現,這種物性實在的本質,其實是一種被遮蔽起來的社會關系之偽境。在這里,馬克思還沒有進一步說明,這種社會關系是怎樣歷史性地顛倒為“物”的,即經濟關系的事物化顛倒,以及物化錯認的復雜機制,這一點他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才逐步破境的。
也正是在這里,馬克思深刻地發現,這種社會關系的實質是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rapports de production),“這種關系正如個人交換一樣,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資產階級社會經濟活動中出現的貨幣,并不是直觀中可見的對象物,它是一種隱匿起來的社會關系,這是過去馬克思已經意識到的問題,但是,從《穆勒筆記》開始,這種從交往關系的異化中透視出來的交換,主要還是停留于流通領域中的,所以,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在討論市民社會IV時,大多使用了一定生產力水平之上的主體性的交往關系,這一觀點一直持續到不久前的《致安年柯夫的信》。而這里,馬克思直接指認出,貨幣除去是一種流通領域中發生作用的交換關系,同時,它也是資產階級社會中居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正是這個生產關系代表了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筑模質性方面。顯然,這離那個可以帶來新的金錢的金錢——資本關系更近了一步。可以發現,在過去馬克思使用人對人主體際交往關系的地方,他開始使用下沉到人對自然構序的生產關系的概念。馬克思的科學的生產關系概念正是在此時形成的,這應該也是歷史唯物主義場境關系存在論中最重要的進展。其實,廣義的生產關系應該再科學地區分為兩個構序層:一是那個“怎樣生產”的勞作活動構序和塑形的根本性關系,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功能水平之上的勞動分工與協作等狹義的生產關系; 二是這種勞作中的生產關系再賦型整個人與人交往的社會關系(如經濟的社會賦型中的經濟關系場境)的本質,由此再規制全部上層建筑的場境關系。這里,馬克思還提出,非物像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研究“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以及“這些關系(rapports)本身是怎樣產生的”。這也就奠定了走向對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生產關系本質進行科學的經濟學研究的正確方向。這應該是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說明自己的經濟學探索主旨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研究的邏輯緣起。
其三,是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本質在于將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永恒化。有了生產關系概念這一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進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也不同程度地越發深刻起來了。在馬克思看來,對于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有資產階級
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 (division du travail)、信用(crédit)、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rapports de la production bourgeoise)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恒的范疇。……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rapports)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mouvement historique)。
這個時候,馬克思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任何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都必然與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中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賦型相適應,因此都是歷史的暫時的生產關系的產生、運動和發展的結果,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分工”、“信用”和“貨幣”都是特有的歷史時間中賦型的生產關系,它們只是近代工業生產發展和資產階級商品-市場經濟的歷史產物。實際上,這里“分工”是出現在工場手工業中的勞動分工,它屬于狹義的技術生產關系,而“信用”和“貨幣”則是在狹義生產關系之上生成的經濟關系。馬克思在同期寫下的《道德化的批評與批評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斯密和李嘉圖的學生都會知道,現代私有制是整個 “資產階級生產關系 (bürgerliches Produktionsverh?ltnis)的總和”,這些生產關系都是階級關系,即“一定‘歷史運動’的產物”。這說明,在馬克思眼里,資產階級社會并不是一個物性對象堆砌的客觀實在總體,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場境關系存在,它是一種復雜“生產關系的總和”支撐起來的“現代私有制”,這本身就是一定社會“歷史運動”的產物。
馬克思分析說,“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productivité matérielle)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les principes,les idées,les catégories)。”這一觀點,正是前述廣義歷史唯物主義中關系意識論的進一步展開說明。這也是本文反復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意識論的用意,因為不能進入關系意識論的構境,是根本不可能深入理解馬克思的相關表述背后的非物像具體觀念賦型的。這意味著,任何一個社會中出現的思想觀念,只能是特定歷史時間中社會關系場境的主觀映現。“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relations)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produits historiques et transitoires)。”社會關系場境存在的特殊時間質性,規定了相應觀念和范疇的歷史性本質,這也是歷史認識論的核心構序點。對此,馬克思結合歐洲的歷史現實舉例說:“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與權威原理相適應的是11 世紀,與個人主義原理相適應的是18世紀”。可是,
為什么該原理出現在11 世紀或者18 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在每個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產力(forces productrices)、生產方式(mode de production)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后,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rapports d'homme à homme)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l'histoire réelle),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作劇作者又當作劇中人物(les auteurs et les acteurs de leur propre drame)嗎? 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恒的原理。
這是《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比較重要的一段表述。第一,一定的原理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些原理只不過是一定時期中的人們怎樣生存的關系場境的映現,具體說,這就是一定歷史時間中人們的“怎樣生產” 的勞動塑形方式和能力,以及這種生產構序方式所生成的人與人之間怎樣發生場境關聯的活動和相互作用構式,決定了這些關系場境主觀映現內容的關系賦型本質。相對于個人生活和認知活動而言,這就是社會歷史先驗構架之上“先天綜合”觀念架構的隱秘作用關系。第二,更重要的是,馬克思所指認的人們即是創造這一歷史的劇作者,又是其中的“劇中人物”,在存在論上,它直接體現了一種根本性改變,即工業生產構序通過給予自然物質存在以全新的用在性方式,人成為世界的主人;可當資產階級創造出商品-市場經濟王國時,卻又使社會關系賦型場境變形為經濟力量支配人的他性舞臺,人離開了自然存在的腳本創作了自己的歷史,卻又成為這一劇本中被無形驅使的木偶角色。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存在論中的奇怪悖論。而在認識論維度上,根本性的認知對象異質性轉換為: 我們是在看我們自己表演的作品,但我們卻認不出自己所創造的世界。第三,馬克思強調說,這種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物的存在論和非二元認知構架中的特定關系場境,不會出現在11 世紀歐洲的農耕時代中,因為人不是自然經濟的劇作者,人只能歷史性地成為18 世紀工業文明的劇作者和劇中人物。所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只能是研究一定歷史條件下(14-18 世紀)人們借以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以及這一經濟關系發展的“個人主義原理”的特殊規律性。這是社會關系場境存在論和歷史認識論理論賦型中的一次重要的進展。
然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將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視為人類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態,視為亙古不變的非歷史的東西。馬克思分析道:“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 一種是人為的(artificielles),一種是天然的(naturelles)。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la bourgeoisie sont des institutions)是天然的。”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學說史上,這是從重農主義開始強調的生產和經濟活動中的非人格化“自然性”構序意向。而從實質上看,
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rapports de la production bourgeoise)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lois de la nature)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lois éternelles)。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Ainsi il y a eu de l'histoire,mais il n'y en a plus)。
這里的“自然規律”當然是在黑格爾的“第二自然”反諷的構境中使用的,它具體是指處于資產階級盲目市場交換和競爭的經濟熵增中自發構序起來的生產和經濟活動,是排除了過去農耕勞動中的主體意志和經驗習慣后的非人格化客觀運動機制,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這種經濟熵增和自發構序運動法則被偽飾成最符合的人天性的“自然法”和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社會中支配性的生產關系就成了永恒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說得是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政治革命中,是承認了歷史的進步性,而一旦自己坐了天下,則將資產階級的歷史時間中的生產關系偽飾成天然的、永恒不變的自然規律,這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歷史性的一種本質遮蔽。
三、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發生學與經濟學研究
首先,關于資產階級社會和歷史分析。這應該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后,馬克思第二次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發生做這樣的歷史描述,也是第一次公開發表這樣的觀點。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社會不是天然的自然秩序,而是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上的特定生產構序和經濟關系賦型的產物。這恰恰針對了上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立場。第一方面,從統治階級主體來看,馬克思說,“我們應當把資產階級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是資產階級在封建主義和君主專制的統治下形成為階級;第二是形成階級之后,推翻封建主義和君主制度,把舊社會改造成資產階級社會”(société bourgeoise)。這是說,資產階級是在封建社會內部逐步生成的,然后才會有從政治上推翻封建專制,并將舊社會改造成資產階級新世界的可能。同時,馬克思也是從主體的構境中使用capitaliste (資本家)一詞,來表征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主體代表。在此書中,馬克思近20 次使用capitaliste 一詞,并且比較集中地使用capitaliste industriel(工業資本家),以表現與農業土地上的主體所有主——地主的不同質性。在后來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本質——資本統治關系形成了全新的科學認識之后,capitaliste 一詞才從主體視位中的資本家主體轉換為描述社會客觀本質的資本主義的形容詞。這是后話。
第二方面,從客觀社會結構發展進程來看,“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掌握起來。一切舊的經濟形式(formes économiques)、一切與之相適應的公民關系(relations civiles) 以及作為舊日市民社會(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 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這里,我再一次看到馬克思精確地用法文中不同于société bourgeoise 的société civile,來表征市民社會IV,即作為政治制度直接基礎的經濟形式。這里有三個隱性構境層:一是馬克思注意到資產階級社會是從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這為他之后科學地說明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復雜社會賦型中同時包含多重異質性生產方式的觀點,奠定了先期邏輯構序條件; 二是資產階級迫使一切舊有的社會定在開始形式上從屬于資本創造了一定的基礎性認識; 三是馬克思精細地區分了資產階級經濟關系之上“公民關系”的場境存在,并且指認這種關系是由舊有的封建社會關系場境的廢墟中得以塑形。
第三方面,從客觀工業生產發展的進程來看,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生產構序基礎也是歷史生成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客體向度中比較重要微觀推進,可在邏輯構序的具體分析中,它似乎開始接近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話語,因為它的話語實踐開始不再具有一般社會運動的普遍特征。如果說,封建社會的生產基礎是手推磨式的勞作構序和塑形,那么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基礎則是蒸汽機,即機器系統的工業生產技術構式。這是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已經說明過的觀點。不過這里分析更加具體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生產基礎是非自然的工業勞動。他說,與農耕勞作中的自然經濟不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絕大多數的產品不是自然界供給的,而是工業(l'industrie) 生產出來的”。這是一個物質生產構序中在社會負熵源上的質性差別,在過去自然經濟的畜牧業和種植業中,絕大部分生產產品都是自然物,人的勞動生產只是在選擇和優化生長條件上作用于外部自然對象,并不能根本改變無機物質和生物存在的自然有序性和負熵構式,而在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直接物質基礎的工業生產中,則是由勞動構序和創造出來的社會負熵中的非自然產品,因為工業生產中的勞動生產,已經開始直接構序和塑形物質存在方式。其實,這恰恰是經濟學話語中配第發現不同于“自然財富”的“社會財富”的基礎,當然也是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的客觀前提。這才真正歷史性地生成馬克思所指認的特定歷史現象: 人既是社會歷史的劇作者,又是這一歷史的劇中人的關系存在論場境。這是馬克思在歷史認識論中,第一次明確指認出認知對象的改變,即從外部自然的物性對象存在向人的活動構序產物的轉換,而工業勞動生產的特殊構序和負熵質也會改變認識活動構境的本質。馬克思說,“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 是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生活的直接生產力構序基礎,而“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這是資產階級社會中工業生產形成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生產關系的賦型。先是工場手工業生產構序中勞動分工的出現,這是勞作構序中的技術生產關系。馬克思說,“工廠手工業的特點不是將勞動分解為各個部門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從事很簡單的操作,而是將許多勞動者和許多種手藝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個資本的支配”。在《布魯塞爾筆記》中,馬克思摘錄了拜比吉《關于機器和工廠的經濟性質》(CH.Babbage,Traite sur L’E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Paris: Bachelier,Imprimeur -Libraire pour Les Sciences)一書里關于這種勞動分工的相關討論。這是發生在工場手工業中資本支配下的勞動分工,勞動分工會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這里,我們看到馬克思的態度與不久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處于勞動異化構式沒影點處的分工證偽是明顯不同的,這可能是馬克思第一次正面描述斯密等經濟學家已經指認的勞動分工,雖然這一分析并不十分具體。在后來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詳細討論了簡單協作和勞動分工問題。然后是機器化大生產構序的歷史在場,“機器是勞動工具的結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種操作的組合”,機器的本質是從勞動主體構序和塑形對象的活動和協動關系轉向客體性的工具系統工序賦型,機器生產促進了原先在工場手工業中出現勞動分工(協作)。“工具積聚發展了,分工也隨之發展,并且vice versa〔反過來也一樣〕。正因為這樣,機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明都使分工加劇,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劇也同樣引起機械方面的新發明。”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關系。我們不難體會到,這是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比較少有的對社會物質生產過程的客體向度描述。當然,這種描述也是在歷史唯物主義非物像透視的第一層級構境之中。因為,這是在觀察非直觀的物質生產構序在工業階段發生的具體對象性塑形和構式方式的變革,這里的機器系統和分工,都是客觀生產技能賦型的新方式。我推測,這些新的認識,大多來自于此時馬克思正在從事的第二次經濟學研究,特別是從烏爾、拜比吉等人那里對現代工廠和機器生產的研究成果中獲得的。我也注意到,在《布魯塞爾筆記》中,馬克思摘錄到拉博德關于協作問題的論述。這種客體向度的描述,在后來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經常出現在馬克思思考相對剩余價值發生的客觀條件中,當然,他也具體討論了機器化大生產中,科學技術作為資本的力量對工人的外部壓力。最后,由于機器和蒸汽等自然力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并且,“美洲的發現和美洲貴金屬的輸入”成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繞道好望角到達東印度的航道開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體系,以及海上貿易的發展”等,也必然促進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賦型的空間擴展和自身生產力的強勁發展。
其次,是關于資產階級社會的初步經濟學分析。這當然也是馬克思第二次經濟學研究的成果。與《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致安年柯夫》中的哲學分析不同,在這里,馬克思第一次公開討論了此時他眼中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構序的歷史性質和經濟關系賦型的特質。一是資產階級社會中交換成為統治關系。這是一個接近經濟學的判斷,但卻內嵌著特殊的政治批判。馬克思認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產品,整個工業存在都轉化商業(toute l'existence industrielle était passée dans le commerce),當時一切生產完全取決于交換(l'échange)”。這是說,工業生產所塑形的勞動產品,已經不再是為了滿足人的直接需要(效用),而是為了功利性的商品交換,工業生產構序為資產階級商品-市場經濟創造了客觀前提,而交換關系則使工業生產本身賦型為商品生產。為此,馬克思還進行了歷史認識論中的比較分析,他說,與封建社會中的交換不同,“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superflu),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產品不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對象;而現在,資產階級社會全部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交換,一切都可以在市場上買賣,這也意味著,交換關系統治了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當然,這種關系場境存在作為社會負熵質,卻是一種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特有熵化和自發物性關系構序的事物化偽境。因為現象學和批判認識論的缺席,馬克思在此并沒有去深究這種關系顛倒的根本原因。他告訴我們,今天在資產階級社會中,
人們一向認為不能出讓的一切東西,這時都成了交換和買賣的對象,都能出讓了。這個時期,甚至像德行、愛情、信仰、知識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買賣的對象,而在以前,這些東西是只傳授不交換,只贈送不出賣,只取得不收買的。這是一個普遍賄賂、普遍買賣的時期(temps de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de la vénalité universelle),或者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東西都變成市場價值(valeur vénale)并到市場上去尋找最符合它的真正價值的評價的時期。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普遍賄賂、普遍買賣”金錢世界,人們生活中的“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東西” 都必須在市場中找到具有交換性的“市場價值”,甚至過去不能交換的愛情和良心都成了買賣的對象,通俗地說,人的一切存在都必須先拿去變賣才能存在。這里,我們似乎又看見赫斯的影子,有所不同的是,馬克思此處對交換的分析已經是從經濟學的話語來塑形的。在馬克思將來的經濟學研究中,他將歷史性地說明,商業資本向生產資本的歷史性轉變,在交換關系背后,是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瘋狂追逐。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不是交換關系成為統治,而是資本的抽象關系成為統治。并且,同樣是在批判金錢關系,與《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義勞動異化構式不同,馬克思這里并沒有現象學式的批判認識論構境,而是基于經濟學話語中的“市場價值”居統治地位的事實指認,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才被徹底改變。當然,“市場價值”還不是一個準確的經濟學術語。
二是以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價值的規律成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定歷史規律。在批判蒲魯東的唯心主義錯誤中,馬克思對比了蒲魯東與李嘉圖的觀點,“在李嘉圖看來,勞動時間確定價值這是交換價值的規律,而蒲魯東卻認為這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綜合”。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節點,因為這可能馬克思第一次公開肯定勞動價值論。這也應該是馬克思在第二次經濟學研究中取得的最重要的進展。我們一定要注意,勞動時間和價值關系都不是可以直觀的物性實在,所以,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入口,仍然是歷史唯物主義非物像的關系場境存在論。在此時的馬克思看來,“李嘉圖的價值論 (théorie des valeurs) 是對現代經濟生活的科學解釋(interprétation scientifique); 而蒲魯東先生的價值論卻是對李嘉圖理論的烏托邦式的解釋”。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李嘉圖承認“勞動時間確定價值這是交換價值的規律”,恰恰是從現實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中歸納出他的理論公式的,這個公式正是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生活的本質抽象。與《巴黎筆記》和《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與勞動價值論擦肩而過的情況不同,此時他已經意識到,李嘉圖(斯密) 的勞動價值論將是自己進一步揭露資產階級經濟剝削的努力方向,這對他科學地說明資產階級社會統治的本質將是關鍵性的一步。從認識論的維度看,這也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構式基礎,從斯密轉向了李嘉圖。有趣的是,在馬克思思想構境的深層,原先在《巴黎筆記》中肯定斯密經濟學內嵌勞動主體性本質,否定李嘉圖經濟學基于客觀物性系統(“犬儒主義”)的態度有了一種奧妙的改變:李嘉圖經濟學中從現實經濟關系出發的勞動價值論,更有可能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走向對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剝削秘密的揭露。
三是資產階級社會經濟活動中客觀發生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是在這里,馬克思第一次指認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過程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當然也是馬克思第二次經濟學研究的成果,在他讀到的法國經濟學家西斯蒙第等人那里,已經談到了這種經濟危機現象。在這里,馬克思提出,“在以個人交換為基礎的工業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l'anarchie)是災難叢生的根源,同時又是進步的原因”。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活動的本質是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都處于自發性活動的總體無政府熵增狀態之中,這既是商品-市場經濟進步的內驅力,也會是產生自身復雜矛盾的根源,由此,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運動“由于不可避免的強制(fatalement contrainte),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de prospérité,de dépression,de crise,de stagnation)、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的更替”。這是馬克思在經濟學的話語中,第一次從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活動內部矛盾的歷時性發展狀況,科學地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走向消亡的努力。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公開高舉起科學社會主義旗幟的全新基礎。
注釋:
①居利希 (Ludwig Gustav von Gülich,1791-1847):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德國保護關稅派領袖。1810—1812年,他曾在哥廷根大學進修財政學(國民經濟學),1817年在柏林洪堡大學旁聽經濟學。1830年出版了《關于現代主要商業國家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于1842、1844 和1845年先后出版了這本書的第三至五卷。
②Karl Marx: Exzerpte aus Gustav von Gülich.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VI/6,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3.
③此書在1846年6月出版,馬克思于12月讀到此書。以下簡稱《貧困的哲學》。該書中譯文參見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1 卷,徐公肅、任起莘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 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1~32 頁。
⑥安年柯夫(Pavel Vasilievich Annenkov 1813-1887):當時是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駐巴黎的通訊員。他在巴黎看了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一書后,于1846年11月1日寫信給馬克思,談了自己對這本書的看法,并征求馬克思的意見,由于書商的拖延,馬克思到這年的12月底才看到蒲魯東這部著作,他用了兩天時間瀏覽了一遍,就用法文給安年柯夫寫了這封回信。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88 頁。Karl Marx,Marx an Pawel Wassiljewitsch Annenkow,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Ⅲ/2,.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79,S.70-80.
⑦參見拙文《馬克思“市民社會”話語實踐的歷史發生構境》,《東南學術》2021年第1 期。
?我已經完成《回到馬克思》第二卷的第二稿。此書不久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