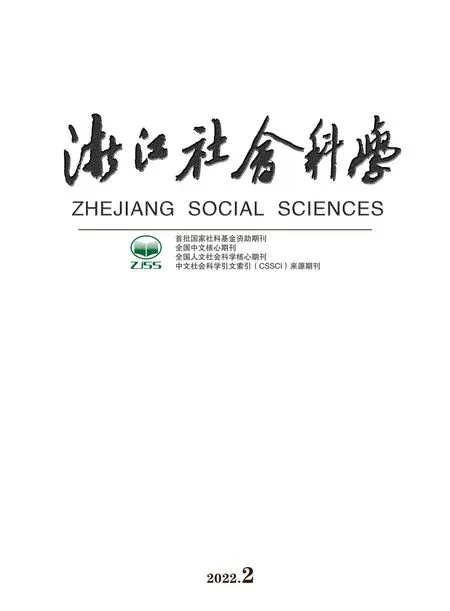理論轉向與邏輯躍升:馬克思社會批判圖景的歷史性建構*
□ 付文軍
內容提要 馬克思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社會批判家。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省察和現實體認,馬克思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的實質性批判。然而這種科學批判圖景并非一日之功,它有一個邏輯躍升的過程。從《萊茵報》時期到《巴黎手稿》,馬克思直面現實的物質利益難題而展開了對社會的人本主義批判;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哲學的貧困》,馬克思以分工和所有制為抓手展開了對社會的原則性分析;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馬克思聚焦于勞動和資本關系而展開了對社會的全面解剖。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不再是單一的道義譴責,而是深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病理學解剖”。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依然是21 世紀社會批判和革命的指導思想,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應賡續馬克思的批判傳統而直面現實問題并回應時代之問。
“資本主義”不僅是馬克思立言著說的時代背景,更是馬克思著力分析和批判的對象。在社會批判思想史上,馬克思展開了出類拔萃的工作。一是馬克思善用辯證法則全面地解析了資本主義的“內與外”,即馬克思不僅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現象的精準評析,還展開了對資本主義內在機理的科學剖解; 二是馬克思利用歷史分析范式科學地展現了資本主義的“古與今”,即馬克思在哲學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經濟批判的多重語境中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歷史脈絡的全景呈現。簡單地說,直面資本主義自身,唯物、辯證且歷史地展開對資本主義的考辨,繼而深刻地回應人類“歷史之謎”,這是馬克思終其一生的工作要旨。當然,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路與邏輯也并不是自其開始就是科學的,它有一個“邏輯躍升”的過程。從“萊茵報”時期的“戰斗檄文”到《資本論》,馬克思的一系列文本忠實地記錄著馬克思社會批判的理論轉向與邏輯生成。
一、從《萊茵報》時期到《巴黎手稿》:立足社會物質利益難題的人本主義批判
因入職大學而不得,馬克思旋即為《萊茵報》撰稿并深入地接觸社會現實。這便是馬克思從“書齋走向現實”的過程,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遭遇到了有關“物質利益”的難題。1859年馬克思在回顧這段經歷的時候特意指出:“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①。初出茅廬的馬克思在觸碰到諸如書報檢查制度、等級議會制度、私有財產權利和社會貧困等社會現實問題時,他開始局促起來——擁有高超論辯技巧和淵博法學知識在堅硬的社會物質利益問題面前卻顯得乏力。經過沉思,馬克思還是毅然決定“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②。正是在這“一進一退”間,馬克思開啟了對所在世界的理論省思和強力控訴: 要在對“舊世界”的無情批判中“發現新世界”③。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通過對專制權力、等級制度的法哲學思辨而展開了對自由和理性的暢想。面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府頒布的嚴苛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不僅斥責其為一種“拙劣的警察手段”④,還強力斥責了這種“不自由”的檢查制度所帶有的“怯懦的丑惡本質”⑤。它扼殺了自由,阻礙了人們對于真理的追求。在批判書報檢查令的過程中,馬克思以費爾巴哈式的語調闡發了對自由的美好想象:自由是人類全部精神存在的“類本質”,是“剛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⑥。在對萊茵省議會關于出版自由的討論中,馬克思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自由背后牽涉的復雜社會利益問題。貴族等級、騎士等級、市民等級和農民等級紛紛基于自身的立場發表了對出版自由的意見,每一等級都有著對自由的渴求。“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可見,各種自由向來就是存在的,不過有時表現為特殊的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的權利而已”⑦。在理想的狀況下,自由本是“理性的普遍陽光所賜予的自然禮物” 而普遍地歸屬于每一個個人⑧,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自由是一種普遍性存在。這種普遍性在現實生活中卻變成了特殊性,自由只是少數人擁有的特權,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馬克思的思路中,對自由和理性的暢想與反對專制主義是交叉進行的,即在反對專制主義的過程中豐富對自由和理性的理解,在對自由和理性的理論述說中集中火力批判專制主義。
到了《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通過集中批判黑格爾法哲學而展開了對社會的唯物主義批判。黑格爾用思辨的方法和抽象的邏輯闡釋了他的法哲學理念,家庭和市民社會均被視作“國家的概念領域”,家庭和市民社會之于國家的關系也被當作了“觀念的內在想像活動”⑨。顯然,黑格爾對于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考察是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調的。馬克思敏銳地察覺到了黑格爾的問題,“家庭和市民社會都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活動著的;而在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⑩。在唯物地改造黑格爾觀點的基礎上,馬克思著力批判了對國家和人們生活的抽象理解方式并確立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正確思路。正因此,馬克思才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確認了批判理路的轉向——批判的領域從“天國”降至“塵世”,批判的內容從宗教批判、神學批判轉向了法的批判、政治批判。直面德國現實,馬克思發出了“向德國制度開火”和對德國展開“搏斗式的批判”的口號?。這種批判不再是維護統治根基的烏托邦式革命,而是摧毀統治大廈支柱的社會革命。雖然此時馬克思批判的對象是工業不發達的德國,但馬克思在對德國理論和現實的雙重批判中確認了接下來工作的重點:一是“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 是需要著重加以梳理的課題?;二是徹底摧毀德國奴役制必須積極致力于無產階級和哲學的“聯姻”工作。簡單地說,馬克思對德國社會的批判旨在謀求以哲學為“頭腦”、以無產階級為“心臟”的“德國人的解放”?。雖然此時的馬克思顯然還停留在哲學和政治領域展開對社會的批判,但馬克思卻通過批判性研究而得出了科學考察社會的基本原則,即從物質生產生活出發來理解各種社會關系。
按照“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原則?,馬克思開始在巴黎閱讀整理經濟學著作并做了深刻反思。《巴黎手稿》就是這一時期閱讀經濟學著作和反思社會現實的見證,它不僅記錄了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閱讀與整理,還再現了馬克思對社會現實狀況的思考與總結。直面資本、地租和勞動分離的“經濟現實”,馬克思直言這種分離是“有害”的和“致命”的分離。正是因為這種“分離”,使得資本家迅速攀附至社會權力之巔并牢牢把控了社會的主動權。由此便產生了兩種截然相異的生存圖景: 資本家可以養尊處優,工人則被視作能夠勞動的低等動物和僅僅有著最基本肉體生存所需的牲畜。在資本積累和資本家的競爭過程中,工人持續貧困的狀況是始終不會有絲毫改變的。“當資本家贏利時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當資本家虧損時工人就一定跟著吃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鐵律”?。國民經濟學已經將問題亮了出來,“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降低為最賤的商品; 工人的貧困同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成反比”?。更為明確地,“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有感于上述國民經濟的“事實”,馬克思竭力審思了這類現象的實質所在——異化。在私有制度之下,勞動及其產品是作為“異己的存在物”而現身的,它與勞動者之間不斷裂變而與之對立。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全面闡述了勞動異化的四種情形。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詳細分析了異化勞動的肇因——私有財產。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馬克思展開了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性分析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認知。在對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理論剖析中,馬克思還確認了異化的揚棄之路。馬克思將未來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視為是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它是“通過人”而實現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是人向合乎自我本性的一種“復歸之路”。就此而論,《巴黎手稿》的理論路線至少有兩條: 一是立足于實驗和工業的狀況而通過經驗的觀察和對國民經濟學理論的批判性研究洞悉異化勞動的現實和私有財產的運動,在異化和私有的狀況中展開對資本主義的強力批判; 二是在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的理想本質和處處受限的堅硬現實的“兩歧”中而找到了擺脫困境的方法,為解答人類歷史之謎提供了“鑰匙”。這一時期的馬克思雖然已經開始涉足經濟領域并借此展開了社會批判,但受制于人本主義的研究范式而使得這種批判并不徹底和科學。這種批判雖然開始觸及到私有財產及其制度,但關注的焦點多停留在交換、分配領域。這種批判雖然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但對于社會的批判深受抽象思辨分析范式的影響而不夠徹底。當然,馬克思此時的分析思路和批判范式都不盡科學,但聚焦于經濟領域而關注經濟事實、解釋經濟現象和分析經濟矛盾而展開對社會的實質性批判和歷史性理解是今后社會批判工作的策略和方向。
二、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哲學的貧困》:以分工和所有制為抓手的唯物史觀批判
1845年的馬克思開始了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徹底清算,并形成了堅持客體與主體相統一、直觀性和抽象性相配合的研究思路。立足于“人類社會”,馬克思發出了“改變世界”的呼號?。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開啟了對以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為代表的德國哲學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德國哲學的問題以及答案都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這些哲學家由于未能處理好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問題而陷入了困境。以思辨的方式來觸及現實,以“詞句”來反對“詞句”,這就將批判的矛頭定格在了思維領域而不是現實領地,這樣的批判也就只是同現實影子進行的斗爭而無力對現實世界展開理據充分的駁斥。正基于此,馬克思斷然與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鑣,以“現實的個人”及其活動(包括他們的物質生產生活條件)為前提而展開了對社會歷史的考察。根據“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的原理?,馬克思聚焦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而科學地展示了不同分工的發展階段和不同所有制的具體形式,繼而開啟了他的社會批判工作議程。
分工是生產力發展最為顯著的標志,“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分工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和“迄今為止歷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不僅使生產力得以成倍增長,還造就了一種原本不存在的“集體力”。當然,作為一個復雜社會事件的分工還會對人類生產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著眼于這種“相互關系”,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分工的社會歷史效應。分工在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同時,也會誘發種種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分裂”或“分離”問題。一方面,與一定生產方式的分工相適應的是職業、行業和活動勢力范圍的分殊。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分工直接導致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城市和鄉村、工商業和農業之間的分離和對立,這就給每一個人的活動劃定了一個強加于他的“特殊的活動范圍”。如此也就有了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商人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的身份差異,個人的身份標簽限制著他自身的活動范圍、對應著他在分工中的地位。由于分工所造就的這種“固化”,人們逐漸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聯合性物質力量而推動社會歷史的進程。因為這種分工并不是出于人們的自愿選擇而是“自然”的產物,它實質上就是一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通過對國民經濟學家著作的閱讀,馬克思就已經洞察到了分工的雙重社會效應——“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精美完善,同時卻使工人陷于貧困直到變為機器”。另一方面,分工還會導致單個人或單個家庭的“特殊利益”和所有互相交往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分裂與矛盾。在這種矛盾中,“共同利益”會“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而體現和維護其基本欲求。“在每一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系、語言聯系、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系的現實基礎上”,就產生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階級。任何力爭取得統治地位的階級就必須要奪取政權和掌握國家機器,“把自己的利益又說成是普遍的利益”以便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而“合乎理性”的形式。從個人視域來看,每個單個個體所要追求的只是“自己的特殊的、對他們來說是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 而已,“共同利益”則被視作是“‘異己的’和‘不依賴’于他們的,即仍舊是一種特殊的獨特的‘普遍’利益”。由是觀之,分工造就了私人“特殊利益”和大眾“共同利益”之間的分裂甚至對立,繼而導致了階級統治的產生。在唯物史觀創立的過程中,分工是馬克思考察社會歷史問題的一條重要“引線”,它直接關乎生產力的發展和交往關系的更新,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對于馬克思來說,分工在本質上是一種復雜的“社會關系”,而這種“關系”的核心就是“所有制”。在私有社會中,分工和交換就是“私有財產的形式”。更為明確地說,“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歷史已向我們展示了分工的不同階段與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之間的契合、對應關系。由于分工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先后歷經分工“很不發達”的“部落[Stamm]所有制”、分工“比較發達”的“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以分工造就的“共同體”為基礎的“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 和由機器大工業所鑄就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不同的“勞動組織的形式”,它們所透露出的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較為全面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真面貌,即勞動者“受勞動產品的支配”、積累起來的勞動(即資本)以物的形式(即貨幣)來實行統治、個人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換而匯聚并發生聯系。從所有制及其背后隱藏著的勞動力支配權入手,馬克思展開了對大工業時代的批判性考察。大工業使得競爭、需求都“普遍化”了,消滅了民族的特殊性并開創了“世界歷史”,但也造成了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和異化的社會狀況。在資本主義批判史上,《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的工作要旨并不在于集中火力批判社會,這一時期的核心工作在于通過揭示簡單的社會事實——“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而制定“生活決定意識”的科學方法論。也正因此,《德意志意識形態》 這一關鍵性文本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也僅僅停留在原則層面。
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問世為馬克思提供了批判的靶子。馬克思著成《哲學的貧困》而著力批判了以蒲魯東為代表的改良主義的觀點,并科學駁斥了改良派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對于分工、信用、貨幣、機器和資本這些“經濟事實”,國民經濟學家們聚焦于財富的生產和占有并將所觸碰到的經濟范疇都描繪成“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范疇”,繼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合理化的論證。因此,國民經濟學家熱衷于經濟運行的解釋,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經濟關系生成的歷史運動與過程。蒲魯東則將這些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視為抽象的思想,他力圖借用抽象來詮釋“抽象形態的運動,純粹形式上的運動,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蒲魯東按照黑格爾《邏輯學》的套路而將一切經濟范疇都歸為“邏輯范疇”,將一切經濟運動、生產行為和過程都歸為“方法”,最終揭示了抽象形態的運動或純粹理性的運動過程。蒲魯東同國民經濟學家一樣,始終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視為“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和永久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這種思維方式明顯是帶有形而上學色彩的,這種非歷史的觀點、態度和對考察對象的經驗歸納式地抽象分析,是迎合資產階級統治需要的,代表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直面諸多經濟事實,在對經濟范疇的唯物史觀批判中再次確認了“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因此,“手推磨”和“蒸汽磨”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形態。在破除形而上學思維的基礎上,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分工、機器、競爭、壟斷、所有權、地租以及工人同盟的罷工行動等社會經濟范疇和現象。只有將經濟范疇視為現實物質生產生活的抽象,才能準確把握經濟范疇的本質意涵,也才能通過經濟范疇而窺見其背后的社會制度。換而言之,馬克思在對經濟范疇的歷史省思和現實批判中洞察到了它們的歷史性本質,它們是與經濟基礎有著密切關聯的暫時性存在。對于資本主義大工業來說,“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是其形成的歷史條件。隨著資本統治的展開,被壓迫階級必然要呼吁解放并投身于革命,革命解放就必然意味著新社會、新制度的建立,而“要使被壓迫階級能夠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不再能夠繼續并存”。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嫻熟地運用了唯物史觀的分析范式強力駁斥了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并確認了社會經濟范疇的物質性和歷史性。
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唯物、辯證且歷史地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則性剖析。他以分工和所有制為抓手而粗線條地勾勒出了社會批判的總體理論圖景,以現實個人及其活動為出發點而為他的社會批判作了方法論的奠基性工作,以唯物史觀為武器破除了資產階級“永恒論”的神話。
三、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聚焦于勞動和資本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開啟系統批判資本主義的經典文本。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現實社會存在為對象,堅持客觀性的基本原則,精準地考察了資本主義的產生、運行和發展變化趨勢,繼而揭示了這一社會的內在矛盾及其存在限度,為人們改變現狀、引領未來提供了“真正客觀有效的指導原則”。作為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只“開啟”了對資本主義的科學批判而未詳盡地展開,科學批判資本主義的工作在《資本論》中才得以“完成”。由于剩余價值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經濟規律的“發現”,馬克思積極回應了資本主義的“時代之問”和解答了人類“歷史之謎”。
《共產黨宣言》只“開啟”了資本主義的科學批判之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科學呈現了資產階級及其社會的歷史性生成過程與規律。得益于生產的發展,從中世紀產生的城關市民中發展出了最早的資產階級; 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殖民地的開拓等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力地推動了“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的進程。隨著經濟權力的獲得,資產階級迅速奪取了政治統治的勝利,使得整個現代的國家政權作為“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而發揮作用。“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歷史效應進行了辯證批判。資產階級以其革命性的生產方式而將世間的一切都打造成了資本的專屬,依托于不斷的技術革新和社會革命而迅速瓦解了舊時代一切僵化、固定和落后的觀念與關系,普遍性的聯系、世界性的交往、吞噬性的資本和廣闊性的市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一切民族都卷入資本文明的洪流之中。原本分散的人口、財產和生產資料都被聚攏在資本的勢力范圍之內,一切都服務服從于資本增殖。正因此,資產階級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歷史中創造的生產力要遠遠大于“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隨著資本主義機制的不斷運行,原本可以施展魔法的“魔法師”卻失去了魔力,現代的生產力開始“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這一“理論武器”闡述了造成這一局面的因由:“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這也是消滅私有制、改變財產私人性質的根本理由。究其實,《共產黨宣言》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來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這種批判是一種原則性的歷史批判。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實質性批判工作是在《資本論》中完成的。身處倫敦的馬克思以英國作為典型案例,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復雜關系并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律。《資本論》昭示了馬克思立足于日常經濟活動而深刻“展現資本邏輯支配下的日常行為與觀念建構的內在關系”以“實現對社會存在本身的批判分析”。具體而論,馬克思抓住了“勞動和資本”這一“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而科學破解了資本主義的諸多謎疑。也就是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勞動”的闡析和對“資本”的解構而確認了“在現代社會中工人并沒有得到他的勞動產品的全部價值作為報酬”這一事實,繼而為無產階級積極推動揚棄資本主義的運動提供了學理支撐。
一方面,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的闡析而確認了雇傭工人的生存際遇。在對商品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確認了勞動的二重性——作為使用價值創造者的“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和作為價值形成過程的“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過程。前者是具體勞動,它塑造了可見的物質世界; 后者是抽象勞動,它形成了不可見的社會關系。在對資本的歷史追蹤中,馬克思發現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與“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 在勞動力市場上相遇并發生聯系的時候,資本時代才得以誕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的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種特殊的勞動既具有一般勞動過程的普遍特點,又具有特殊勞動的價值增殖特色。這種雇傭勞動實際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在勞動過程中,工人的勞動隸屬于資本家并受資本家監督;在勞動結束時,勞動產品并不為勞動者所得而是資本家的“所有物”。通過對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比較,馬克思發現了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因此,資本家通過對勞動力的支配而無限延長雇傭工人的工作時長,繼而獲得更多量的增殖額。雇傭工人只要一被納入到資本體系中,就被當作一個零部件而被安置在機器上,配合、服侍機器生產。長此以往,“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奪去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鍛造出一種“兵營式的紀律”和普遍遵守的“工廠法”而迫使雇傭工人必須在技術上服從于資本生產的要求。這些紀律和法律法規逐漸演變為堅固的“工廠制度”,規訓著雇傭工人并使工人徹底地從屬于資本。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要說明的是: 工人的勞動本質上是“為資本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要將“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幸福是一個謬論,成為雇傭工人(勞動)并不是幸福的事情,反而是一種痛苦和不幸。無論社會經濟狀況如何,一無所有的勞動力的占有者“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正是在對“勞動”的闡析中,馬克思確認了資本主義勞動的狹隘性。“勞動過程只表現為價值增殖過程的一種手段”,勞動并不是勞動主體本質力量的確證,反而是其受苦受難的源頭。這就為打破、推翻這種舊體制找到了階級基礎——雇傭工人是革命的主體力量。
另一方面,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的解構而呈現了資本邏輯的布展之道。通過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查悉了“資本主義客觀現實活動的內在聯系、運行軌跡、發展趨勢”。這種聯系與趨勢,實際就是資本邏輯。資本增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終極目標,資本的增殖邏輯“座架”著整個社會并宰控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命運。G—W—G’(G+ΔG)這一在流通領域表現出的“資本總公式”直截了當地表達了資本旨在以“價值增殖”為“決定目的”或“動機”。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就是“以創造利潤為導向的過程”,永不停歇地謀利是這種生產的本性。“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的形式怎樣,生產過程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周而復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正是這種永不中斷的生產和再生產模式,資本才能源源不斷地再生出更多的利潤。可見,資本“只能是生產關系”,而且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一旦確立起來,就有了自主性和自身的生命,并能利用其他社會關系來增殖自身”。在對資本增殖邏輯的考察中,馬克思科學地給出了剩余價值率的各種計算公式。這些公式的給出,一方面使得勞動力受剝削、受壓迫的程度有了可計量的科學工具和準確表現,另一方面則彰顯了資本的生產關系本質的真實蘊含,即這種生產關系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或“無酬勞動時間的化身”。這也是資本之所以能夠自行增殖的秘密所在。通過對資本及其運轉邏輯的考察,馬克思向世人展示了這一生產方式的不義之處,為廣大雇傭工人在更深層次上認識到自身受剝削受壓迫的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學理依據和現實支撐。同時,馬克思還攜其“批判的”和“革命的” 辯證法破析了資本主義的出路問題,即在對資本的肯定性理解中包含著對其必然滅亡趨勢的理解。資本以其高效率、大體量和快周轉的方式將人類文明推到了一個新高度,然而這種生產方式又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創傷。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同步、資本生產和經濟危機的迸發、社會權力與私人權力的對抗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工人被釘在資本之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而這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資本,資本主義生產的“惟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也是“資本自身”。馬克思循此思路找到了積極揚棄資本剝削制度的方法——“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這其實就是利用資本自我否定的邏輯來完成“改變世界”的偉大抱負。
小 結
資本主義批判是作為革命家和科學家的馬克思的終生目標。從哲學、宗教批判到政治、法的批判,再到經濟批判,馬克思完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在揭穿“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之后,繼續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馬克思對于社會現實的批判不單單是道義譴責和規范性批判,還是對現實問題的實質性批判。他敢于直面問題本身,善用辯證分析之法,深諳唯物史觀之道,科學地闡釋了諸多現實難題,并以此展開了對舊世界的批判和對新世界的展望。時至今日,我們依然需要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需要沿著馬克思的道路前進。
以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為指導,續寫21 世紀資本主義批判的新篇章。資本主義以其強大的調節能力而繼續盤踞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敘事和社會主義敘事是21 世紀的主導性敘事話語。21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們的重要任務就是完成馬克思的“未竟之業”,繼續推進資本主義批判并積極致力于共產主義的建構。要順利完成這一工作,首先就要在當代繼續展開對勞動和資本的科學性解剖和實質性批判。在當代社會中,資本邏輯從對生產資源的暴力宰制轉向了對經濟活動、金融資源的“隱性掌控”,勞動者的抗議之聲和反抗意識都淹沒在了資本洪流之中。直面當代資本主義的各種調節舉措,我們必須明白的是:這些措施都始終是要服務于資本增殖的,雇傭工人受剝削和受壓迫的狀況絕不會有絲毫更改。廣大雇傭工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當代馬克主義工作者需要積極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沿著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之路而妥善應對當前的新情況,積極回應當代的新問題。在通達“自由王國”的路途中充分駕馭資本、解放勞動,為從根本上“消滅資本”和建構自由人的聯合體而不斷貢獻智慧。
注釋:
①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412、412 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 頁。
⑨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