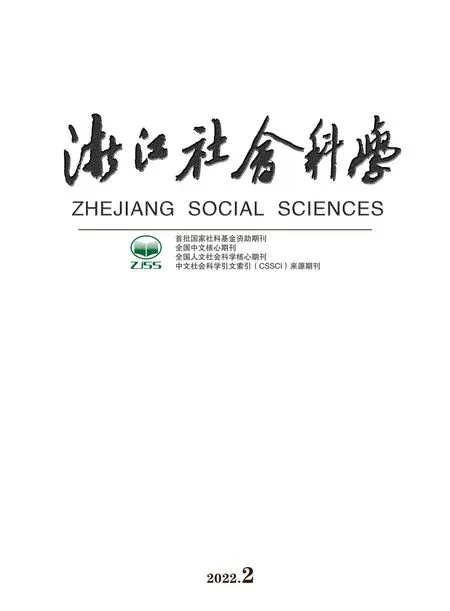唐詩之路視域中的賀知章
□ 肖瑞峰
在唐詩璀璨奪目的藝術長廊里,浙江蕭山籍詩人賀知章當然不是最具光環的詩國巨擘,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都不可能成為研究的熱點。但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他曾與李白那樣的登峰造極者交往甚密,且有提攜、揄揚、獎掖之恩。據現有史料可以認定,在李白揚名立萬的過程中,他發揮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如果沒有他“解金龜換酒”的豪舉,并賜予其“謫仙人”的美譽,初入京城、藉藉無名的李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名聲大噪,迅速得領詩壇風騷。同樣,在唐詩之路的視域中,賀知章也不是最為引人注目的人物,就現存作品而言,他不可能處于核心位置,但有理由認為,他是最早涉筆唐詩之路的詩人之一,盡管他描寫唐詩之路的作品不多,而且用筆甚簡,卻為后人“導夫先路”,帶動了后代吟詠浙東唐詩之路的名篇佳作的涌現。在浙江詩路文化研究方興未艾的今天,他理應得到我們更多的關注。
作為越州永興(今杭州蕭山)人,賀知章出生與成長于錢塘江詩路與浙東唐詩之路的交匯處,是勾連這兩條詩路的關鍵性人物之一。他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而集中體現為詩書雙絕。《舊唐書·賀知章傳》說他“醉后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他的書法作品傳世的有鐫刻于紹興城東南宛委山南坡飛來石上的《龍瑞宮記》和流傳到日本的《孝經》草書等。詩歌作品留存至今的則僅有19 首。由《舊唐書》本傳“醉后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的描述看,他的創作量應該是相當可觀的,而創作時的狀態也與他激賞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有某種神似之處,所以,我們不難推斷出,這19 首作品只是其全部創作中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都已經亡佚不存了,正如韓愈在《調張籍》中斷言李白、杜甫的傳世作品“遺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那樣。在現存的19首作品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毫無疑問是《詠柳》和《回鄉偶書》: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詠柳》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回鄉偶書二首》其一
這兩首膾炙人口的作品看似與我們今天所熱議的“唐詩之路”了無干系,實際上它們所抒寫的對故鄉的依戀、對故鄉兒童的愛憐、對故鄉風物的喜愛,正是對唐詩之路的側面烘托或曰多元寫照。即以《詠柳》而言,時值二月,已是柳條泛青,柳葉綻綠,一片春意盎然。它所展現的絕對不是北國都城的氣象,而是作者的故鄉,亦即浙東唐詩之路上的景觀。這說明,故鄉的春天以及浙東唐詩之路上的春景永遠駐扎在他的心靈深處。史載,唐玄宗天寶三年(744年),賀知章以86 歲高齡稱病請旨還鄉,歸隱會稽故里。這意味著他以浙東唐詩之路為人生起點,也以浙東唐詩之路為人生歸宿。換一種表述,也可以說,他最終完成了以浙東唐詩之路為圓心的人生閉環。
誠然,在賀知章的19 首存世作品中,除了《詠柳》和《回鄉偶書》外,多為祭祀樂章和應制詩。但也有一些作品直接為唐詩之路傳神寫照,如《回鄉偶書二首》其二: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
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這是一首不幸為享有盛名的姊妹篇所掩蓋的懷鄉佳作。詩中蘊蓄著萬千心事的意象就是浙東唐詩之路上的核心景觀——鏡湖。離鄉日久,而朝廷中人事紛爭不斷,令詩人為之心寒。于是格外懷念故鄉的山水風物,贊賞它們的不改故態、不易舊轍。“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這其中寄寓了多少感慨,既是對鏡湖的形象化描寫,也是對朝廷中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亂象的一種喻示。其內涵甚至比它的姊妹篇還要深刻。
鏡湖在賀知章心目中是故鄉的代表性風物,是他的鄉愁的藝術載體。《回鄉偶書二首》的經典意義就在于,分別從鄉音和鄉愁兩個層面、兩種視角凸現了作者的故鄉情結,揭示了他在故鄉與他鄉、入世與出世之間的困惑、迷惘與糾結。而故鄉與他鄉、入世與出世,正是今天的唐詩之路研究所要著力探究的命題。
賀知章以鏡湖為意象的作品還有《答朝士》和《采蓮曲》:
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莼菜亂如絲。
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吳兒。
——《答朝士》
稽山罷霧郁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
莫言春度芳菲盡,別有中流采芰荷。
——《采蓮曲》
詩人對鏡湖景色的生動而又貼切的描寫,傳導出他對山水林泉之美的由衷喜愛。在他的作品中,有一首《偶游主人園》是常遭忽略的。詩云: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
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徑入不相識的主人家小坐,蓋因愛其林泉之美也。詩人對林泉之美的愛慕是達到了癡迷的程度的,或者說已經浸潤到骨髓里,這才不管不顧地擅入園中。這一行為可以說是反常而合道,即不合常理,卻合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君子之道。由此加以推導,他對唐詩之路上的風光景物的描寫肯定不止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這些。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采蓮曲》一詩中是將“稽山”與“鏡水”相提并論的,而稽山鏡水幾乎已成為浙東唐詩之路核心區域或曰精華路段的代稱。中唐詩人涉筆于浙東唐詩之路時大多仿賀知章筆調,而賀知章較早描摹的“稽山鏡水”這一意象也為他們所遞相沿襲。劉禹錫《浙東元相公書嘆梅雨郁蒸之候因寄七言》:
稽山自與岐山別,何事連年鸑鷟飛。
百辟商量舊相入,九天祗候老臣歸。
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掃翠微。
今日看書最惆悵,為聞梅雨損朝衣。
詩的頸聯描寫越州景色,而就令人神往的稽山鏡水著筆。“平湖”,指鏡湖。元稹《以州宅夸于樂天》一詩也就“稽山鏡水”加以生發與鋪展:
州城迥繞拂云堆,鏡水稽山滿眼來。
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
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
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
賀知章另有一首題為《曉發》的五言律詩,因篇幅較《回鄉偶書》《采蓮曲》等七言絕句增廣,所以對山水景物的描寫要更為細膩:
江皋聞曙鐘,輕枻理還舼。
海潮夜約約,川露晨溶溶。
始見沙上鳥,猶埋云外峰。
故鄉杳無際,明發懷朋從。
由“故鄉杳無際”可知,這首詩創作于異鄉。但編織于詩中的 “江皋”“曙鐘”“輕枻”“海潮”“川露”“沙上鳥”“云外峰”等意象,都屬于他的故鄉,屬于浙東唐詩之路,是他從對故鄉、對浙東唐詩之路的深刻記憶中提煉而出、熔鑄而成的。賀知章性格豪放,交游廣闊,晚年尤放蕩不羈,自號“四明狂客”。惟其如此,以他為圓點形成了多個文化氣氛濃郁的朋友圈。長安為官期間,他常與李白、李適之、李琎、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飲酒賦詩,時謂“醉八仙”。又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司馬承禎時相過從,人稱“仙宗十友”。今天,我們檢視描寫錢塘江詩路和浙東唐詩之路的作品,不難發現,其中有許多上乘之作都出自賀知章這兩個朋友圈的筆下,尤其是“仙宗十友”中的孟浩然與“醉八仙”中的李白,更以其出神入化的詩筆,成為唐詩之路的直接締造者,極大地豐富了浙江詩路文化。而他們對浙江山水的喜愛與吟詠,固然因為浙江山水本身具有足夠的吸引力與感召力,卻也不能排除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賀知章的影響。
賀知章與李白的交誼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他倆都是以豪飲著稱的酒仙,杜甫在《飲中八仙歌》 中為賀知章傳神寫照說:“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而對李白的描繪則是:“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兩人有許多共同點,但最突出的一點應該是“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對酒憶賀監二首》是李白天寶六年(747年)游會稽時為悼念已仙逝的賀知章而作。詩前的小序追懷往事,不勝感慨:“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歿后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這種撫今追昔的哀悼之情在詩中一泄無遺:
其一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
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為松下塵。
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
敕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
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
念此杳如夢,凄然傷我情。
詩中處處留有往事的痕跡以及對這些痕跡的深情撫摸。此外,引人矚目的就是詩中還貼有不少浙江山水的標簽,如“四明”“山陰”“鏡湖”等等。可以肯定,天寶元年至三年,賀知章與李白在長安聚飲時,話題不是單一的,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情感世界的各個角落。至于自然界的風光景物、天象節候,諸如花卉草木、鳥獸蟲魚、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風霜雨雪等等,也會為這兩位博學廣聞的豪客所縱論。由此而產生的一個合理推測是,深愛故鄉的賀知章會非常自然地多次向李白言及浙江山水之美,從而讓李白對浙江山水產生了濃烈的向往。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是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因為它所吟詠的天姥山在浙江境內,所以尤為浙江讀者所喜吟樂誦。但絕大多數讀者都沒有注意到該詩開篇處的一個細節:“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云霞明滅或可睹。”李白在這里明確說他是因為聽了某位“越人”對天姥山的介紹,往游天姥的強烈愿望才油然而生。這位“越人”是誰? 從未見學者深究,似乎無關宏旨。其實,這位“越人”作為李白與浙江山水之間的觸媒,還是有必要加以考索的。竊以為這個“越人”,即便不能確指為賀知章,賀知章也應該在備考者之列。
這或許是一個“大膽的假設”,還需要進一步“小心的求證”,一如胡適之所倡導的那樣。但這并不是石破天驚之論,至少在時間點與空間位置上是契合的:李白被以“賜金放還”的名義逐出長安與賀知章辭官歸隱,這兩起轟動京城的事件一同發生在天寶三年(744年),而前一事件在時間上要稍后。賀知章辭行時,李白賦寫了《送賀賓客歸越》一詩:“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詩中提到秀麗的鏡湖風光足以激發賀知章的“逸興”。而《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則寫于天寶四年,僅后于此詩一年左右。根據這一時間節點,我們無妨合理想象:賀知章辭別李白之際,再次隆重推介天姥山等浙江勝景,邀約李白前往游覽,李白暫時不克“親游”,便采用“夢游”的方式,借助非現實的夢中境界,一方面寄托蔑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表達他對浙江山水的無限神往,作為對賀知章的推介的一種穿越時空的呼應。
從唐詩之路的視角來考察賀知章,我們還可以發現另一具有非凡意義的文學事件,而這一文學事件對浙東唐詩之路的形成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賀知章天寶三年辭官歸隱會稽時,唐玄宗不僅僅“詔賜鏡湖剡川一曲”,讓他結廬于浙東唐詩之路的核心區域,朝夕徜徉于秀麗的稽山鏡水之間,也不僅僅在京城東門設立帳幕,率文武百官為他餞行,讓他倍感榮寵,而且在觥籌交錯之際親自染翰,即席賦寫了《送賀秘監歸會稽序并詩》:
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歲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
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僚悵別深。
序與詩本身皆平平無足道,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圣上賦詩送行以及詩題中特意標示“會稽”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時應制奉和者甚眾,且無一例外,都以《送賀監歸會稽詩應制》為題,場面頗為壯觀。這些作品曾被編為詩集一卷行世,名為《賀監歸鄉詩集》。最早收錄在北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孔延之編纂的《會稽掇英總集》中,計37 首。南宋鄭樵的《通志》卷七十、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焦竑的《國史經籍志》卷五也載錄了這一集名。作者除唐玄宗外,另有宋鼎、嚴向、齊浣、王鐸、韓宗、韋述、席豫、崔璘、嚴都、魏盈、韓倩、李巖、李璆、李適之等人,其中甚至包括史稱“口蜜腹劍”的宰相李林甫。盡管這些應制之作不乏敷衍成篇、感情浮泛、結構雷同、語言粗糙者,但也有不少篇章真心折服于賀知章敝屣功名利祿、歸隱故鄉山水的高風亮節,而出以誠摯、流暢的筆墨。即便奸相李林甫所作,也隱然有歆羨與欽敬之意:“掛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真侶,辭恩訪列仙。睿文含日月,宸翰動云煙。鶴駕吳鄉遠,遙遙南斗邊。”而與賀知章同預“醉八仙” 之列的李適之更在詩中依循唐明皇定下的基調,徑直以“高尚”一詞稱許他:“圣代全高尚,玄風闡道微。”
當然,我們所要評鑒的不是這37 首具體作品,而是這次君臣唱和的文學史意義。竊以為其意義就在于:作為一次群體創作活動,它是對浙東唐詩之路的最早的共同關注和集體吟詠。“稽山”“鏡水”等浙東唐詩之路的標志性符號,是唱和中出現的高頻詞,如“稽嶺白云生”(席豫)、“綵帆收鑒水”(李彥和)、“稽山鶴駕迎”(崔璘)、“輕舟鏡湖上”(梁涉)等等。更有盧象的《送賀秘監歸會稽歌》將諸多符號糅為一體:“山隂舊宅作仙壇,湖上閑田種芝草。鏡湖之水含杳防,會稽仙洞多精靈。須乗赤鯉游滄海,當以群鵝寫道經。”在這里,浙東唐詩之路上的諸種影像已得到相對完整的呈現。歸結到既定的話題上,如果沒有賀知章的歸隱會稽之舉,就沒有這次大規模的以“會稽”為關鍵詞的君臣唱和活動,稽山鏡水就不會被唐玄宗及他的詩臣如此眷顧,得到如此頻繁而又清晰的顯影,而浙東唐詩之路也就少了一批發軔之作,會遲滯其形成的節奏。
這組將賀知章與浙東唐詩之路綰合起來的唱和詩,一直未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有趣的是,因為它在當時所產生的轟動效應,有好事者竟然偽造了托名于李白的同題詩作:“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寧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對此,已故著名唐詩專家陶敏先生已辨其妄,茲不贅言。我想說的是,藉李白以造假,恰恰說明,這組作品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綜上所述,在浙東唐詩之路形成與傳播的過程中,賀知章功不可沒。可以說,他是一個地位與作用被長期低估的詩人。在浙江詩路文化研究漸入佳境之際,我們應當給他以更為精準的歷史與現實定位。換言之,將賀知章置于唐詩之路視閾中加以審視,一方面我們可以對賀知章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獲得更準確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浙東唐詩之路的歷史成因及演進軌跡取得更深入的認知。遺憾的是,我們過去從未將賀知章與浙東唐詩之路扭結在一起,在詩路文化的理論框架下探討二者的雙邊關系。這說明,我們在研究浙東唐詩之路時,視野還不夠宏闊,視角還不夠多元,方法也不夠豐富、靈活。對浙東唐詩之路的研究是這樣,對與它相并列的另三條浙江詩路(大運河詩路、錢塘江詩路、甌江山水詩路)的研究又何嘗不是這樣呢?